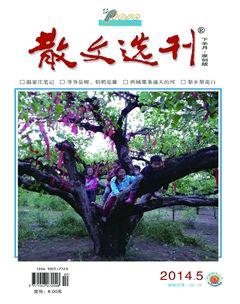讀書情思
傅全章
每當我走進書店或圖書館,看見書架上那層層的各類書本,我都會心潮起伏,感慨萬千,想起自己當年“餓書”的年代——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國家困難,壓縮辦學規模,我初中被“提前”畢了業,回到家鄉當了“回鄉知青”。那時我才十五歲,還戴著紅領巾!那時,我和社員一起岀工勞動,一樣吃不飽飯,我還特別“餓書”?!在校時,因為我的語文成績好,假期可以比別人多借課外書。如今離開了學校,哪里還能有書看?我生性最怕求人,也厚著臉皮去找還在學校的同學幫我借書。我記得別人幫我借過《三國演義》和蘇聯的《形形色色的案件》。不好意思老去找人家,就和生產隊另外兩三個小青年去找有藏書的人借,結果碰了一鼻子灰,被人家拒絕。我得知本隊趙大伯家樓上有書,就討好他的兒子,征得他兒子的同意,和他兒子一道,搭梯子上樓,在蛛網和灰塵中偷偷把裝書的箱子打開。我記得取岀的書是《圣經》。《圣經》也讀,雖然基本讀不懂,“聊以充饑”吧!有時父親讓我到住家附近鄉場鎮去賣米糠,我總會把賣的錢中悄悄拿岀一部分買上一本薄薄的書,如歷史小叢書《陳玉成》、《李自成》之類。在回家的路上,把兩個籮筐疊在一起,用扁擔穿上籮繩,扛在肩上。右手壓住扁擔,左手拿書,邊走邊看。一般都是到家時大體上也就讀完了。有時走在路上,發現路邊有字的紙,總要拾起來讀,這些紙是不是別人揩屁股的也不得而知。
我父親雖是農民,但他是個讀了一些書的人。在我讀小學二、三年級時,父親就寫了四句話給我:“讀書不用心,將來不成人;等你長大了,看你又何成?”幾十年過去了,至今仍記得這幾句。
我不會因為家里沒有高檔家具而自慚,我卻因我有數以千計的書冊供我閱讀和利用而感到精神充實。
因為自己有“餓書”的經歷,所以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期,我在《散文選刊》上登載出售自己的《龍泉山放歌》一書的啟事時,在啟事文末寫了一句:“經濟困難者,作者愿贈書。”收到全國二十六個省、市近二百人來函索書,我也一一按址寄去。他們中有大、中學生、工人、農民、干部、解放軍。這說明很多人是想讀書的!
著名政論家、歷史學家、作家鄧拓先生曾寫過《有書趕快讀》的文章,讓我們不要把書束之高閣,要抓緊時間讀。我國著名女作家冰心老人也諄諄告誡青少年:“讀書好,好讀書,讀好書。”古代大書法家顏真卿也有“黑發不知勤學早,白首方悔讀書遲”之言,沒有書讀的時代過去了,有書不讀的現象卻到處都有。
為了讓自己有報效國家、能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讀書吧!
責任編輯:黃艷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