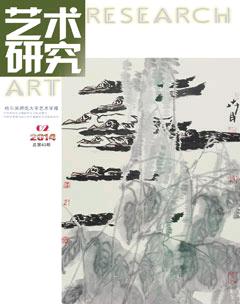中國民族聲樂文化價值的多維度解讀
楊立軍
摘 要:中國民族聲樂是傳統文化一顆璀璨的明珠,發展至今已有千年的歷史。其作為一種音樂文化,有很高的藝術價值。本文從文化傳承、文化滲透、文化導向三方面對其進行多維度的解讀。有助于從文化層面對民族聲樂有一個深入的了解。
關鍵詞:民族聲樂 演唱風格 文化價值 聲樂美學
文化是支撐社會體系運行和發展的核心動力之一,它包括語言、信仰、道德、法律、歷史、風俗、知識、藝術等等多個內涵,更包括構建內涵所具備的能力,以及構建過程中所形成的習慣和經驗。近年來,作為一種文化的表現方式,民族聲樂的文化價值被學界廣泛討論,而關于“文化價值”的概念與范疇,也因為學科、角度的不同而存在多種認知和解讀。筆者認為,無論如何解構“文化價值”,它都應從“人”的視野出發,在具象的文化體系中,立體化地研究、認識“價值”作為人文現象的意義、功能與意向。因此,本文在探索中國民族聲樂的文化價值時,著意于站在其多維度構建的視角,以中華民族文化體系為支撐,以“人”觀“樂”,旨在縱橫之間探尋民族聲樂在文化范疇的幾點核心價值。
一、縱向——文化傳承價值
中國民族聲樂的發源與形成,建立在繼承傳統文化與民族特色的基礎上,其發展至今仍是中國傳統聲樂藝術文化的歷史見證與延續。
從民族聲樂發展的角度來說,在幅員遼闊、民族眾多、地域特點鮮明的中華民族大地上,它凝結了《詩經》與《楚辭》的精髓,既有“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詩經·國風·周南·桃夭》)的美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詩經·國風·衛風·碩人》)的風華;又有“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楚辭·離騷》)的悲憫,“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楚辭·漁父》)的情懷。它表現了禮樂的等級制度,為王宮、大夫與士兵呈現不同的編制、調式、旋律與唱腔。它既在漢唐大曲中承載著中國古代宮廷抒情歌舞的藝術成就與魅力,又迅速在宋元市民音樂中尋找到戲劇音樂與說唱音樂的精妙,更于明清四大聲腔崛起時,雕琢昆山腔的水磨細致、百轉千回,賦予京劇板式的變化與皮黃腔的突出成就。進入近現代以來,學堂樂歌、藝術歌曲等外來旋律與唱法的傳入,群眾歌曲的廣泛流傳,各地民歌與地方戲的蓬勃發展,以《白毛女》為標志的中國新歌劇的迅速崛起,專業藝術院校中民族聲樂專業的建設,現代媒體對民族聲樂作品的傳播,使得幾乎每個華人心中,都有一首摯愛的民族聲樂作品,久唱不衰,回味綿長。
從民族聲樂審美的角度來說,《禮記·樂記·師乙篇》(漢·劉德)要求歌者的聲腔應上時昂揚,下時沉著,轉折時利落,停止時平穩,一字一腔循規蹈矩,即“上如抗,下如墜,靜止如槁木,居中矩,句中鉤”。①《夢溪筆談》(宋·沈括)中的“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強調了聲腔貫通融會之美。②《唱論》(元·燕南芝庵)在提出演唱者“聲要圓熟,腔要徹滿”的同時,不忘強調“凡人聲音不等,各有所長”。③《曲律》(明·魏良輔)歸納出“曲有三絕,字清為一絕;腔純為一絕;板正為一絕”的新的審美觀念。④《樂府傳聲·頓挫》(清·徐大椿)與《顧誤錄·度曲十病》(清·王德輝、徐元澄)則論述了演唱中剛柔處理之法,即“唱曲之妙,全在頓挫”(《樂府傳聲》),“曲剛勁處要有棱角;柔軟處要能圓湛。細細體會,方能成絕唱”(《顧誤錄》)。⑤清末民初以來,民族聲樂的審美標準仍繼承古代,即音色自然,字正腔圓,講究韻味,追求意境。
中國民族聲樂的發展橫貫古今,它的每一次探求、發展、融合與轉變,都進一步構成并豐富了所謂中國民族聲樂的概念,及形式與內容之上的文化內涵與價值。
二、橫向——文化滲透價值
任何一種藝術形式可純粹,卻不可單一,民族聲樂亦是如此。發展至今,它不僅在縱向上兼具傳承與淬煉的重任,更在這一過程中橫向借鑒、吸收、融合了多種音樂元素與唱法,彰顯了民族聲樂在不同文化藝術領域橫向滲透的能力與屬性。
一是與原生態民歌尤其是少數民族民歌的融合。這類民歌來自深山大川、廣袤平原、魚米之鄉,在長期歷史積淀中磨合,并形成了個性化極強的演唱模式,甚至其中有些已經發展成一套完整的聲樂藝術體系。它們是我國各族、各地區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過程中,結合當地風土人情、地域特色凝練而成的,帶有“原始文化”烙印的民歌,包含著濃郁的民間音樂氣息。它們為古今音樂創作者與表演者提供源源不斷的靈感,它的唱腔、咬字、旋律乃至服飾,都是一個民族、一個地域、一種文化的符號。中國民族聲樂始終堅持對原生態民歌藝術元素的吸納,譬如,《白毛女》中喜兒的音樂主題,如《北風吹》等,旋律素材來自于河北民歌;郭頌的《新貨郎》詼諧地表現了東北人民的性格特點;“湖南民歌之父”白誠仁的《洞庭魚米香》、《挑擔茶葉上北京》、《小背簍》等,蘊含了湘文化的真摯樸實;才旦卓瑪的《唱支山歌給黨聽》、譚晶的《在那東山頂上》,充分展現了藏族民歌的高亢唱腔;曲比阿烏的《遠方的客人請你留下來》吹來了涼山彝族的風;王洛賓改編的《在那遙遠的地方》、《掀起你的蓋頭來》等等一系列新疆民歌,充滿了浪漫纏綿的異域風情;德德瑪演唱的《美麗的草原我的家》、《草原夜色美》等,帶著一股草原的遼闊與芬芳撲面而來。
二是對傳統戲曲與說唱音樂的借鑒。我國傳統戲曲音樂與說唱音樂在產生之初,其旋律乃至唱腔素材,常取材于當地民歌、小戲,根據不同時代觀眾欣賞趣味的變化和追求,民間藝人們不斷探索聲樂與器樂在戲曲與說唱中的板腔變化、伴奏藝術等,逐漸形成了樣式豐富、韻味各異的傳統戲曲與說唱藝術。從廣義的中國民族聲樂概念來說,戲曲和說唱音樂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屬于特定的藝術種類;從狹義的中國現代民族聲樂概念來說,對這種傳統的聲樂演唱方式和形式的學習與借鑒,既是所謂“學院派”出身的民族聲樂演員的必修課,又為創作者、演唱者們拓寬藝術眼界、擴展涉獵范圍、豐富藝術表現、增強文化修養提供了保障。如,民族歌劇《小二黑結婚》中最著名的唱段《清粼粼的水來藍瑩瑩的天》,便廣泛吸收了山西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及評劇的旋律和唱腔;江蘇民歌《紫竹調》是滬劇中的常用的曲調;東北民歌《月牙五更》帶有濃郁的二人轉特征等。
三是對美聲唱法與通俗唱法的吸納。一方面,新中國建立之初的50、60年代,隨著西方聲樂技巧與經驗的引進,以及聲樂民族化的學術討論,評論界曾就唱法問題的“土洋之爭”有過幾番激烈的辯論。“土”即以陜甘一帶為代表的解放區所流行的民族民間傳統唱法,以及由此衍生、發展的以《白毛女》等新歌劇演唱方法為代表的唱法;“洋”即以西式音樂藝術院校為代表的意大利美聲唱法。這場觀念上的討論也促進了中國民族聲樂唱法對其它唱法的吸收和融合,為實現建立自己的民族聲樂學派奠定了一部分基礎。我國老一輩的藝術家,如吳雁澤、馬玉濤、耿蓮鳳等,都是最初探索民族唱法與美聲唱法相結合的開拓者;而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彭麗媛、宋祖英、張也等歌唱家,則在繼承民族聲樂傳統,吸收美聲唱法經驗的基礎上,大膽創新,逐漸形成了當代民族聲樂演唱的體系、風格和審美標準。另一方面,隨時“改革開放”的到來,港臺校園歌曲、流行歌曲迅速得到年輕人的喜愛,民族聲樂演唱也將流行唱法的某些風格、技巧融入自身體系之中,這種唱法不僅受到國內普通觀眾的歡迎,更得到世界舞臺的認可,如朱哲琴、薩頂頂、龔琳娜等歌者正是通過將兩種唱法與藝術表現形式相結合的方式,得到了西方音樂評論界與國際音樂獎項的肯定。
中國民族聲樂藝術的橫向滲透,是站在傳統聲樂藝術的頸背之上,以博大的胸懷,兼收并蓄更有利于推動民族聲樂發展,更有利于推廣民族聲樂文化的藝術精華。
三、交叉——文化導向價值
近年來,每當談及中國民族聲樂的藝術特征、審美原則與教學標準,都繞不開“科學性、民族性、藝術性、時代性”這幾個關鍵詞,金鐵霖、劉輝等當代民族聲樂教育家,都提出過類似的觀點。筆者認為,對這“四性”的解讀,可以分為兩組,而且,它們作為目前最被業界所肯定的一種藝術準則,也代表了民族聲樂在文化建設與發展上的一種積極的導向作用。
首先,中國民族聲樂的科學性與藝術性,應是對這一藝術形式理性與感性平衡的追求。民族聲樂的科學性,又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通過合理的訓練方法和有效的教學手段,建立一個以理性認知為主的客觀視角,以便由此進一步理清民族聲樂的現狀、問題及今后的發展道路;二是以民族聲樂的實踐探索與理論建設為核心,探索聲樂藝術在技巧、風格與審美等方面客觀存在的共性特征或普遍規律,從而完善民族聲樂表演與教學體系,使這一藝術形式本身得到本質上的升華。而民族聲樂的藝術性,則是相對主觀的概念,是對其藝術表現力的一種概括。譬如,吸收了古今中外聲樂藝術之所長的中國當代民族聲樂,相較于傳統民族聲樂,具備更甜美、自然的音色,更寬廣、厚實的音域,更能滿足當前社會主流藝術思潮的需要,更能獲得觀眾的喜愛,這正是它所表現出的藝術表現力,也就是藝術性之所在。
其次,中國民族聲樂的民族性與時代性,則可視為其發展的立足點和趨勢。民族聲樂的民族性,已被從業者一再強調,它應是一個開放的概念,是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精神與意識,再追求他民族的人文情懷與藝術價值,從而不失“本我”的“神韻”,又能優化“自我”的形態。秉承著這一原則,民族聲樂可大膽借鑒與改革,而不會模糊甚至改變其作為民族文化藝術先鋒的屬性。民族聲樂的時代性,既揭示了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又解釋了民族聲樂在各個歷史時期均受到大眾喜愛與關注的本質原因。任何藝術形式的時代性,都彰顯出它與社會發展的同步性與適應性,民族聲樂正是在縱向的歷史發展軌跡與橫向的聲樂藝術融合、借鑒中,不斷調整自身的步伐,僅僅跟隨時代的發展,滿足時代的需求,這是一種蓬勃頑強的藝術生命力,更是一種敢于探索的寶貴品質。
受到經濟與科技的影響,世界大同的趨勢愈發明顯,越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民族藝術所表現出的個性就愈加珍貴。中國民族聲樂是中華民族藝術的精品,是東方音樂文化的瑰寶,它的傳承、發展與提高,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我文化”不同于“他文化”的意識形態。我們站在全人類聲樂藝術的高塔之上,望向中國民族聲樂那縱橫綿延的文化支脈,心中無限慨嘆之余,更志于為它的明天貢獻力量。
注釋:
①戴德,戴圣.禮記[M],江西美術出版社,2013.
②沈括.夢溪筆談[M].吉林出版社集團責任有限公司,2010.
③燕南芝庵.唱論.
④魏良輔.曲律.
⑤徐大椿,吳同賓,李光譯.樂府傳聲[M].中國戲劇出版社,1982.
參考文獻:
[1]徐大椿,吳同賓,李光譯.樂府傳聲[M].中國戲劇出版社,1982.
[2]沈括.夢溪筆談[M].吉林出版社集團責任有限公司,2010.
[3]戴德,戴圣.禮記[M].江西美術出版社,2013.
[4]劉輝.再論中國民族聲樂的文化定位問題[J].中國音樂,2006(1).
作者單位:沈陽音樂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