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向前走”,犬儒方能“向后退”
李斐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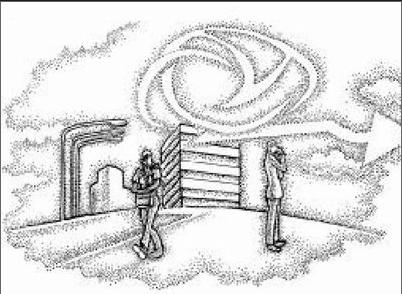
西安出了一件糊涂案——一個女大學生遇了賊,小伙子小孟挺身而出,幫她解圍,結果,賊打傷小孟后跑了,女生幫小孟墊了藥費后,也走了。
明明女生自己也是受害者之一,她干嘛躲起來呢?小孟托人打電話給那個女生,跟她商量要報案,電話那頭的女生甩給他一連串理由:“我現在給你作證能咋?你是能把西安全部的小偷都逮住還是咋?你能保證小偷不來給我找事?我已經夠可以了吧?”
最后,女生鏗鏘地用一句話把自己跟這件事撇干凈:“又不是我讓你抓的小偷,對不對?”
小孟說自己“心里很委屈”,但這筆賬讓人算得更糊涂——女生被盜,她不愿意站出來報案;別人因此受傷,她也不愿意站出來作證。她的行為基準就是“向后退”:遠離問題中心,退得越遠越好,哪怕這樣辜負了別人的付出,哪怕這樣傷害了自己的利益。
有人給這個女生的行為作診斷,叫做“犬儒主義病”,它的癥狀是“堅信牽扯進任何事情肯定都是麻煩”,而這病的病根則來自“對正義公平缺失的根深蒂固的恐懼,從而更加保身和利己”。
只要隨手翻翻新聞,就不難發現,這種病的患者還真不少。比如前不久,一個老大爺倒在大街上,路過的行人圍成一個圈,一個個大眼瞪小眼地看著老人痛苦地躺在地上,卻沒有人敢向前走一步。
圍成圈的人未見得不愿意扶起老人,可他們心里更優先的行為準則警告他們:只要向前一步伸出手,接過來的就可能是所有未解決的社會難題。誰也不愿意為了一時的好心,背負起社會積怨留下的病根。于是,世界上出現了一個叫“壞環境”的假想敵,人們最好的對策就是“躲”。
然而,我們越是向后退,離彼此越遠,當退到角落時,我們會變成一個個孤島。
1964年,美國《紐約時報》報道過一則“向后退”達到極致的案例。文章說,一個女人在住宅區被殺,“38個人站在窗口,卻默不作聲”。38個看客“向后退”,聽著女人的尖叫,最終眼睜睜看著她一個人死在深夜的紐約。
在那篇轟動一時的報道里,美國旁觀者留下了幾乎一樣的理由:“我可不想惹麻煩。”
為了這個令人震驚的理由,人們在后來50多年里都在反復討論這件事:為什么人會變成這樣?
答案究竟是什么?有人拿出法律做支撐,“不作為”被定義為犯罪;有人用美名和金錢做獎賞,鼓勵人們“見義勇為”。人們都在期待一種外部推動力,能夠在背后推我們一把,領著我們前進,最終建成好的環境。
但事實上,真正能讓人向前走的力量,永遠都只來自于自己。人們所抱怨的“壞環境”,無非是給自己找的借口。我們就是“環境”,環境好與壞,從來都只跟我們自己的選擇有關:當我們都選擇“向后退”,世界自然會變得疏遠而冷漠;當我們都選擇“向前走”,問題或許就會迎刃而解。
比如說,在那則《紐約時報》的報道里,旁觀者的冷漠后來被證明只是記者的肆意杜撰。看到女人遇害的時候,附近有居民大吼著喝止兇犯,還有人當場就拿起電話報警。
所以,不管環境是好是壞,能夠作出決定的只有自己。而我們的決定,反過來又會成為“好環境”亦或“壞環境”。
這就像是在那場跟小偷的對決中,小孟本也可以“向后退”,避開這場跟自己毫無關系的麻煩,可他決定趕走作惡的壞人——讓正義“向前走”,讓犬儒“向后退”。
(劉名遠薦自《時代郵刊》2014年第2期 圖:廖新生)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