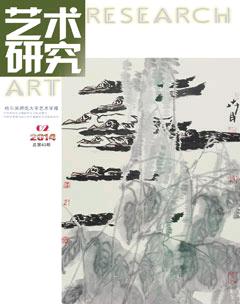試論現實主義理論在中國古代畫論中的運用
彭貴軍+丁月華
摘 要:中國的古代繪畫有一個從先秦到晚清一脈相承的中國式現實主義繪畫優良傳統。在這個傳統中,作為創作實踐的伴隨者則是中國古代畫論中豐富的現實主義理論。本文試圖簡略考察一下現實主義理論在中國古代畫論中的運用。
關鍵詞:現實主義 古代畫論 傳統繪畫 創作啟示
自從1855年法國畫家庫爾貝在巴黎舉行了個人畫展以后,人們開始在美術評論中頻繁使用“現實主義”一詞。庫爾貝在畫展前言中寫道:“求知是為了實踐,這就是我的思想。像我所見到的那樣如實地描繪出我生活的那個時代的風俗、思想和面貌,總之,創作活的藝術,這就是我的初衷。”應該說這是對繪畫中的現實主義原則非常恰當的描述,他幫我們了解現實主義的繪畫實踐,也幫我們把握中外的現實主義繪畫理論。
如果以庫爾貝的概括為線索來考察中國的古代繪畫,就會發現接近這個原則的作品是很多的,它們共同構成了先秦到晚清一脈相承的中國式現實主義繪畫優良傳統。在這個傳統中,作為創作實踐的伴隨者則是中國古代畫論中豐富的現實主義理論。本文試圖簡略考察一下現實主義理論在中國古代畫論中的運用。
一
面向客觀現實,真實反映現實對象的存在,是現實主義的根本要求。中國古代畫論中與此相關的理論是很多的。
首先,在表現對象上,中國古代畫論中有一條基本的現實主義理論原則貫穿始終,那就是要求藝術家面向客觀現實,把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的具體事物作為繪畫的表現對象,作為藝術的源泉。這與浪漫主義把主觀的情感作為主要表現對象的原則相反,它要求畫家到自然和人類社會中去找尋表現的對象,反對那種完全以意為之的創作方式。這一要求把畫家和客觀世界緊密地聯系到一起了,樹立了現實主義創作的基本前提。
唐代著名畫家張璪把自己的創作經驗概括成八個字,即“外事造化,中得心源”。這里所謂的“造化”即指客觀世界的物;“師造化”就是對外物進行認真地觀察研究,把外物作為反映的對象、師法的目標。“中得心源”是指藝術家在對外物深刻觀察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的藝術構思。這里,“中得心源”是建立在“外師造化”的基礎之上的,而不是主觀主義的憑空臆造。
“外師造化”的理論一經提出,就被后世具有現實主義精神的藝術家和理論家所接受。他們相互承襲,使這一理論不斷發展,貫穿于整個中國古代繪畫藝術理論之中。
唐代大詩人白居易說:“學無常師,以真為師。”唐代畫馬名家韓干曾對皇帝說:“陛下內廄之馬,皆臣之師也。”元代趙孟頫說:“到處云山是吾師。”清代花僧石濤說作畫要“搜盡奇峰打草稿”。所有這些都是主張繪畫要以自認事物為本,對自然事物進行“摹繪”。這與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模仿說”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其基本精神無疑是現實主義的。
其次,古代畫論中的現實主義,要求繪畫在反映對象時,按其客觀的本來面目加以表現。關于這一點早在先秦就已見端倪,最早當推戰國時期韓非子的畫論。在《韓非子·外儲說》中載有這樣一段對話:“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曰:‘犬馬最難。‘孰最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者,于罄于前,故易之也。”這里提出的觀點為后人長舉不衰,即所謂“犬馬難狀而鬼魅易寫”。這里除了提出藝術要從客觀對象出發的觀點以外,還提出了另外一個理論,即對藝術提出了一個現實主義的衡量標準。也就是說,要求藝術家在反映對象時要接近對象的本來面貌。
當然,一些畫家所畫的鬼魅也是很著名的,甚至不乏畫家專畫鬼魅。在這里應該指出的是,和西方以圣經故事為題材的繪畫一樣,那些所謂所謂的鬼魅圖像,實際上是一種人物畫。畫家創作的鬼魅圖像并非無影無蹤的鬼魅,而是有血有肉的現實人物的異化形象。所以這些繪畫的本質精神與韓非的觀點本不矛盾。
按照客觀事物的本來面貌反映事物,是中國古代畫論中現實主義的基本要求之一,是韓非以后許多藝術家的共同主張。漢代的王延壽提出“隨色象類,曲得其情”。南北朝的宗炳提出“以形寫形,以色貌色”。唐代的裴孝源提出“隨物成形,萬類無失”。白居易提出“畫工無常,以似為工”。如此等等,都是一個主張。尤其著名是南齊的謝赫,他提出了為后世畫家奉為圭臬的“繪畫六法”,其中第三法“應物象形”,第四法“隨類賦彩”。這里的“應物”、“隨類”與前面所舉各家之主張完全一致,都要求畫家忠實于客觀對象,要求繪畫貼近對象的本來面目,要求所繪對象始終不離現實之本。
第三,提出了真實性的主張。“外師造化”和“應物象形”,用今天的畫來說,就是要以客觀現實為反映對象,要接近事物的本來面目。這兩方面的主張基本奠定了中國古代畫論中現實主義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之上,歷代藝術家、理論家又進一步提出了“求真”的要求,也就是說,他們已經看到了現實主義藝術的根本所在。
宋代的韓琦說:“觀畫之術,唯逼真而已,得其真之全者絕也,得多者上也,非真即下也。”這里的“逼真”可以與“外師造化”、“應物象形”互為表里,明確主張真實。在山水畫的發展史上起了繼往開來巨大作用的五代著名畫家荊浩對真實性的要求,可以作為這一主張真實性理論的代表。他在《筆法記》中說:“畫著,畫也,度物象而取其真”。一語道出了現實主義的精義所在。“度物象”是要求畫家對客觀物象進行一番認真的觀察,“取其真”則是要求作品所追求的實質。“度”、“取”的結合,才能達到徹徹底底的反映現實。正是在這種尋求客觀事物之真的指引下,歷代畫家不辭勞苦,創作了無數具有恒久藝術魅力的繪畫珍品。
二
現實主義原則要求藝術家在用形象反映客觀對象時,不要自然主義地對現實對象亦步亦趨,更不是機械地摹寫,而是主張在把現實對象轉移在紙上的過程中,應所有選擇,所有提煉,有所概括。要抓住對象的主要特點,用適當的筆墨淋漓盡致的加以表現,而對那些旁枝末節,或那些與本質無關的部分,則可略而不著。
中國古典畫論中在這方面有許多精辟的論述。漢代劉安在《淮南子》中曾批評畫家作畫時“謹毛而失貌”的缺點,指出了只注意事物非本質方面的描繪而失去了總體面貌、失去了本質精神的錯誤偏向。唐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說,為了反映事物的總體面貌,不需要面面俱到,毫發畢現去描繪對象的每一個細節。他說:“畫物特忌形貌彩章,歷歷俱足,甚謹甚細,而外露巧密。”在他看來,不但不需要甚謹甚細,而且與劉安一樣,認為過于細密反而會失去事物的全貌。他還說:“不患不了,而患于了。既知其了,亦何必了,此非不了也。”這些主張都是反對自然主義的細節堆砌,要求以典型的細節突出反映事物的總體面貌和本質特點。endprint
我國古代畫論中的現實主義理論要求畫家表現人物時要在個別人物身上展示出某一類人所共有的風貌,這里已散發出以個性表達共性的濃厚氣息,例如宋代畫家郭若虛在《圖畫見聞志》中論及人物畫時說:“釋門則有善巧方便之顏,道像必具修真度世之范,帝王當崇上圣天日之表,外夷應得慕華欽順之情,儒賢即見忠信禮義之風,武士固多勇悍英烈之貌,隱逸俄識肥遁高世之節,貴戚蓋尚紛華侈靡之容,帝釋須明威福嚴重之儀,鬼神乃作丑者馳之狀,士女宜富秀色婑烏果切媠奴坐切之態,田家自有醇甿樸野之真。”這樣的論述雖然流露出一些政治偏見,但就其在藝術上要求畫家在畫某一個人時能夠表現出人物某種特定的階層及相關共同特征,這還是頗有見地的,直到今天對我們也不無啟發意義。
另一方面,中國古代畫論中的現實主義理論不但要求反映事物的共性,而且特別注重反映事物的個性。在人物畫方面,許多畫家和理論家都以能反映人物的個性特點,特別是人物獨特的精神風貌為高。例如,畫諸葛孔明,就要把他獨特的胸中韜略表現出來,畫陶淵明,就要把他傲骨清風的特點刻畫出來,畫李白或白居易,不能只是畫成醉酒老翁,而是要表現出李白之風流、白居易之灑脫的氣質。
概括化、典型化的理論,是現實主義理論發展到高級階段才能提出來的理論。在中國古代畫論中已初步提出了這一理論,而且有的地方論述地比較得體,從中可以看到我國古代畫論中的現實主義理論依據達到了一定的水平。
三
現實主義作品往往使人在欣賞時產生身臨其境的感覺。我國古代畫論要求人物刻畫時能達到使人“對之如面”的程度,對景寫生時要求能達到“舉頭忽看不似畫,低首靜聽疑有聲”的地步。這種真實生動的藝術效果,離開了細節上的精心描繪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細節的真實應是現實主義的基本構成要素。
首先,中國古代畫論中的現實主義的細節要求,主張以客觀對象為標準,要與對象本來的細節相吻合,是生活中實際存在的或是應該存在的,不應是隨意虛構的。
如人物畫在人物形體的細節描繪方面,要求以實際生活中的人為標準。歷代諸多理論家都對人物的形體比例、色彩等有過十分詳細的論述,有的甚至規定了嚴格的尺寸,不可任意為之。清代人對這方面的論述較多。如蔣驥論畫人物的眼睛時說:“至眼亦有大小,不可任意為之。當以鼻之大小比數。大抵寫照在兩目,但須得其人之自然,不可少有假借勉強。”所謂“得其人之自然”,是指不可在細節方面失真。沈宗騫也提出繪畫要“如印如鏡”的主張。這些要求和主張都是站在現實主義立場上提出來的。
第二,古代畫論中的現實主義要求細節的真實要有利于形象內在本質的表現,尤其是對于表現對象本質關系重大的關鍵性細節,更須十分重視。畫家們在創作實踐中認識到,關鍵性細節有點染全局的重要作用,正所謂“畫龍點睛”,那關鍵的一“點”是決不可任意為之的。
唐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載有這樣一段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他說:“畫人數年不點睛,人問其故,答曰:‘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媸,本無關乎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睹中”。主張“以形寫神”的顧愷之認為全身其他地方都無關妙處,而只有眼睛這一個地方才是傳神寫照的關鍵之處,所有他煞費苦心,竟達數年“不點睛”的程度。
同樣,精通畫理與畫法的蘇軾進一步發揮了這個觀點。他在《傳神記》中寫道:“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形寫影,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顴頰。吾嘗于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為吾也。目與顴頰似,余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蘇軾認為眼睛和顴頰是畫人物的關鍵所在,只要這兩個地方畫好了,便“余無不似”。同時,他進一步認為關鍵性細節會因人而異,有所不同:“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畫家必須仔細觀察,甚至需要躲在暗處“陰察之”,才能找到對象的關鍵所在。抓住了這個關鍵性的細節,就抓住了對象的靈魂。
第三,古代畫論中對人物畫的環境、服飾、器具,以及時間、地點等都要求有準確無誤的細節真實。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造成整個畫面真實感的必要條件之一。歷代藝術家的諸多作品,只在某個這樣的細節上稍有疏忽,就大大影響了整個形象的真實感。尤其是歷史題材的繪畫,對人物的服飾及周邊環境的要求更是嚴格,稍有不周之處,便可能產生笑話。
對此,古代畫論中有許多的論述。宋代郭若虛在《圖畫見聞志》中有一段專門論述人物畫衣冠器具的文字,很具代表性。在文中,他開宗明義地說:“自古衣冠之制,薦有變更,指事繪形,必分時代。”接著他詳盡地考證了什么時代的人物應該穿什么樣的服裝,如“三代以前,人皆跣足。三代以后,始服木屐。”又如“漢魏以前,始戴幅巾”等。同時更進一步考證了哪些階層的人物應該有什么樣的服飾特點,如“秦始皇時,以紫緋綠袍為三等品服,庶人以白”等等。
四
中國古代畫論中的現實主義理論還十分注重形與神的統一。形神理論是古代畫論中現實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貫穿于古代畫論的始終。
早在漢代,劉安就已經注意到形神問題,他在《淮南子》中批評畫家“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悅,觀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此處所說的“君形者”指的是主宰人物身形的神情氣韻,他要求繪畫能夠“以神君形”。
在古代畫論中比較自覺地提倡形神理論的晉代著名畫家顧愷之,在他的繪畫理論中,“形神兼備”是人物畫的最高標準。在談到摹寫法則時,顧愷之提出了“以形寫神”的命題,把神似問題明確提出。“以形寫神”的命題指出“形似”與“神似”兩者之間的正確關系。他在對人物畫的品評過程中總是本著這個標準的。他把有形無神,或神似不夠的畫,一言以蔽之曰:“雖美而不盡善也。”這里所謂的“不盡善”,即沒有達到他所要求的形神兼備的最高標準。
南齊的謝赫進一步把形神理論加以系統化。至此,形神理論已經確立,并趨成熟。他把“氣韻生動”放在了繪畫六法之首。他評丁光道說:“非不精謹,乏于生氣。”評夏詹說:“氣韻不足,精密有余。”換言之,這些畫家的創作是神似不足,形式有余。可見神似是繪畫的精義所在。endprint
唐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寫道:“今之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在期間矣……至于鬼神人物,有生動之可狀,須神韻而后全。”自此以后,“神似”雖未居于“獨尊”的地位,至少也是站在“最尊”的位置上。與謝赫一樣,張彥遠雖然強調神似,也并不忽略形似方面。不同于后來有人只求神似,所謂“離形得似”的脫離現實主義原則的主張。他一方面主張“以氣韻求其畫”,另一方面也沒有忘記“形似在期間”,并且說:“夫物象比在于形似”,不過“形似須全其骨氣”罷了。可見,他反對的只是“空陳形似”、“空善賦彩”的偏向,要求“形神逼肖”。
到了宋代,陳郁把人物畫的神似理論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提出了“寫心”的口號。他認為:“寫形不難,寫心惟難。”如果只能寫形不能寫心,那很多外形相似的人就不能彼此區分開來。他說:“蓋寫其形,必傳其神,傳其神,必寫其心;否則君子小人,貌同心異,貴賤忠惡,奚自而別?形雖似何益?故曰寫心惟難。”這里把“寫心”作為傳神的手段,同時也視為區別人物的根本點,是頗有道理的。
清代的沈宗騫也說:“天下之人,形同者有之,貌類者有之,至于神,則有不能相同者矣。作者若但求之形似,則方圓肥瘦,即數十人之中,且有相似者矣,烏得謂之傳神。”他甚至認為:“故形或小失,猶之可也。若神有少乖,則竟非其人矣。”但是他并不忽視形似,所以又說:“為神之故,則又不離乎形。”
自唐、宋以來,隨著山水畫、花鳥畫的進一步發展,畫論中亦可見諸多論述山水畫、花鳥畫的形神理論。如宋代鄧椿提出“人之有神”和“物之有神”的主張。他要求畫家能夠表現人和物的“神”。宋代趙希鵠認為能夠畫出“花果迎風帶露,飛禽走獸精神逼真”方為妙手。明代高濂要求畫山川要有“煙巒之潤”,畫樹木要有“搖動之風”,畫花鳥要有“若飛若鳴若香若濕之態”等等。
強調神似,要求以形寫神,是現實主義理論的真實性要求。因為對象本身自有形神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都須加以表現。所以神似并不是脫離對象,而是更真實的反映對象。如宋代梁楷所繪《太白行吟圖》,我們看到作者用“減筆”畫法,在形態方面極力精簡線條,但在留下線條處卻無不飽含神韻,詩人在運思措句中的一瞬間的神態,畢現無遺。一個風流、豪爽、恣情、傲世的李白,躍然紙上。這即是得神似之妙的現實主義佳作。
通過以上簡要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具有濃郁民族風格的中國古代畫論中的現實主義理論是相當豐富、十分完整的,在諸多方面達到了比較到的水平。這一珍貴的理論在中國繪畫史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直到今天仍能給予我們許多有益的啟發。
參考文獻:
[1]俞劍華.中國古代畫論類編[M].人民美術出版社,2007.
[2]王伯敏.中國繪畫通史[M].三聯書店出版社,2008.
[3]唐志契.繪事微言[M].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
[4]鄭逸梅.藝海一勺[M].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
[5]沈宗騫.芥舟學畫編[M].山東畫報出版社,2013.
[6]劉安,馬慶洲注評.淮南子[M].鳳凰出版社,2009.
作者單位:成都蓉城美術館
重慶師范大學美術學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