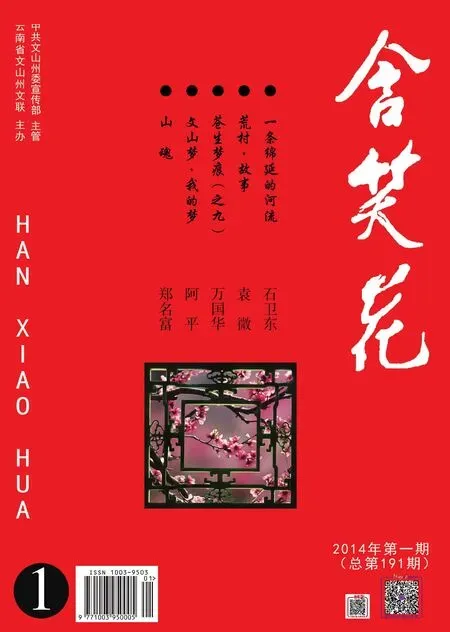蒼生夢(mèng)痕(之九)
◆萬國華
蒼生夢(mèng)痕(之九)
◆萬國華

十四、迷離情懷
64
好像沒怎么在意,地球已繞著太陽轉(zhuǎn)了一個(gè)圈。
懾于陳庚將軍統(tǒng)一指揮的解放大軍二野四兵團(tuán)和四野的一部分,繼續(xù)解放福建、廣東和廣西,不日將向云南進(jìn)發(fā)的絕對(duì)性趨勢(shì),駐于云平鎮(zhèn)而臭名昭著的國民黨578團(tuán),就倉惶如漏網(wǎng)之魚而奉命撤離,前往百多公里以外的錫都個(gè)舊去駐防。云平鎮(zhèn)從此又恢復(fù)了幾年以來難得的和諧與寧靜。繼而,中共黨組織和人民政府就由地下轉(zhuǎn)為地上,并在廣大民眾的熱烈擁護(hù)下,公開辦公,服務(wù)人民。時(shí)值1949年歲末。
這個(gè)時(shí)候,因?yàn)閷?duì)于共產(chǎn)黨之宗旨內(nèi)涵理解不深,麻耀昌就坐不住了;他之所以心存芥蒂,況且心神不寧,乃因面臨云平鎮(zhèn)即將掀起的迎接解放大軍入滇、繼而打土豪、分田地、定階級(jí)成分的空前熱潮。值此界定新、舊社會(huì)兩重天的重大歷史時(shí)刻,他就深深感覺到,自己這么一個(gè)尷尬的、近四年前就被國民黨反動(dòng)勢(shì)力嫌棄,一腳踢出老遠(yuǎn)的人物,卻又因?yàn)殚L期衣食無憂,不是廣大勞苦民眾當(dāng)中之一員,故而成為一個(gè)無論國(民黨)、共(產(chǎn)黨),左右均不看好的人物,進(jìn)而也深感自己及其家人都已臨近最危險(xiǎn)之邊沿;這一步走不好,后果不堪設(shè)想。
老麻對(duì)于自己及其家人命運(yùn)的擔(dān)心,不無道理。其一、雖然說,他早在1946年元宵節(jié)之后,因私自放走具有重大通共嫌疑的趙大寶,所以被免去當(dāng)了近20年云平鎮(zhèn)長之職務(wù),之后又被貶為一介庶民,此事從面子上說,似乎他是為共產(chǎn)黨間接地做下一件小事,但說到底吶,那是他在為其女婿著想,況且如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誰也沒見其女婿趙大寶的影子,是死是活,其真實(shí)身份是國(民黨)還是共(產(chǎn)黨),誰能說得清呢?其二、雖說近一年以前,他在白泥田村邂逅中共地下武裝的重要領(lǐng)導(dǎo)人,以家中祖?zhèn)髅胤饺呦追郏瑸槠渲蝹⒗^而使得痊愈;再又以重金,秘密支援革命武裝購買糧食,對(duì)革命隊(duì)伍起到一定的幫助作用,但他也認(rèn)為,是在當(dāng)時(shí)那種情況下,人家對(duì)他曉以大義,他不得已,才被動(dòng)性為之;說到底吶,自己畢竟從民國十五(1926)年起,干過近二十年國民黨云平鎮(zhèn)的鎮(zhèn)長、且長期兼任保安團(tuán)長呀;雖然說,自己除了當(dāng)年委派團(tuán)丁痛打過老疤楊做成一頓,此外從來做事都比較含蓄,表面上沒仗勢(shì)欺人,直接或間接地也沒與誰有過血債,但自己卻在近二十年如一日的歷程當(dāng)中,無數(shù)次地利用手中握有大鎮(zhèn)長兼保安團(tuán)長之權(quán)力,大撈老百姓血汗錢,既使家財(cái)日積月累,越來越多,又為保官而經(jīng)常性地投其所好,賄賂上峰,甚至于賠上了自己當(dāng)年一朵鮮花似的老婆桑花;此外,還長年累月地,在家中養(yǎng)著最多時(shí)節(jié)達(dá)到二十多人的長工……于是他就想,像他這樣的人,若不成為共產(chǎn)黨革命的對(duì)象,那就只有不足百分之五的幾率了。
所以,他就當(dāng)機(jī)立斷,做出了兩個(gè)最為明智的決定——
第一、多給鄒老三、劉小芹兩個(gè)長工一個(gè)月工錢。叫他倆當(dāng)天就回鄉(xiāng)下老家去,永遠(yuǎn)不要再來了,免得以后跟著他麻氏一家人倒大霉的同時(shí),也免去他在解放后還私養(yǎng)長工的一條罪狀;這鄒老三和劉小芹雖說也是深得麻家好處的長工,但在當(dāng)時(shí)泰山壓頂似的大是大非面前,也生怕再在麻宅呆下去,就會(huì)連累自己,于是求之不得,急急地答應(yīng)下來,然后盡快離開麻宅而去。
第二、就在兩個(gè)長工離去的當(dāng)天夜里,他于夜間麻白鳳與小玉睡著之際,點(diǎn)燃一盞防風(fēng)式小馬燈且?guī)鲜蛛娡玻苄⌒牡仡I(lǐng)著桑花向后園子而去,然后他將桑花帶入一間不起眼的、平時(shí)只是用于堆放糧食與雜物的儲(chǔ)存間,掩了門,將西北角腌著各種咸菜的五六個(gè)壇子挪到一邊,再清掃地面,然后用一把小鍬,逐一撬開墻角一隅的七八塊磚頭,就露出了一塊四方形且很厚實(shí)的木板,再把木板撬開,就現(xiàn)出一個(gè)黑黢黢的、兩平尺左右的洞。老麻輕聲對(duì)桑花說,這是你還沒進(jìn)入我麻家門檻的十多年以前,我爺爺就指令著我父親,找了幾個(gè)邊遠(yuǎn)的窮民來修建的;他對(duì)那些做工的人說,修這個(gè)地下儲(chǔ)存室,只是為了窖酒之用。可是,后來他在臨死之前,曾單獨(dú)關(guān)照我,說我如今做上官了,這做官也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這個(gè)秘室,絕不能輕易讓人知道;爺爺說了,我們可以在人生最為關(guān)鍵之時(shí),在其中暫時(shí)性藏人、或者藏些值錢的物件。說到此處,老麻就對(duì)桑花說,如今已然改朝換代,這七、八十年以來,祖上所留下、以及我掙得的錢財(cái),除了再建與繼續(xù)完善咱麻氏大宅院,其余大多用在購置田產(chǎn)和家具上了;現(xiàn)如今,這下面也就只剩十根金條、兩、三斤大煙和二十八錠滿清時(shí)期的白銀了;此外,還放了一些雜七雜八的古玩字畫;哦,那幾斤大煙,是我爹生前作為制作三七消炎秘方的配料一次性買下的;你知道,我們家的人一個(gè)都不抽大煙的,只是你當(dāng)年為了趕時(shí)髦抽過一陣子。我想,為了保存好祖上積下的精神和物質(zhì)財(cái)物,除了已經(jīng)放入“下面”、今后用以保命和做大事的“黃、白、黑”和那些雜七雜八的物件以外,還要將大部分?jǐn)[在天頤院、少部分?jǐn)[在紫光院博古架上的古董、以及老父親鉆研了一輩子的三七養(yǎng)身著作等,一并藏入這地窖當(dāng)中,等以后世道對(duì)我們家沒有危險(xiǎn)之時(shí),再酌情考慮,嘗試著拿出來;但一定要用在人生最為關(guān)鍵的時(shí)刻。還有,為了不至于引起鳳兒等人懷疑,除了不動(dòng)紫光院的擺設(shè),天頤院那兩大架子上的古董也只選一半看上去比較漂亮的放入這下面就行了,其實(shí)我爺爺認(rèn)為最重要的那些物件,他先前大都放入其中了。從今以后,這件秘事只有我倆人知道。如果哪一天,我真被人家姓共的處決了,那么天長日久的,你和鳳兒、還有小玉過日子肯定不容易,那時(shí)你也看看世情如何,如果方便的話,也可酌情從中取點(diǎn)“黃貨”、“白貨”或者“黑貨”出來,換點(diǎn)過日子的油鹽柴米。
老麻把話兒說到這里,桑花就被感動(dòng)得脖子發(fā)粗,差一點(diǎn)兒就要哭將出來。老麻見狀,立即制止了她,然后二人輕手輕腳地,來來回回,使用一個(gè)長工們平時(shí)裝雜物和背蔬菜的背簍,來回幾次地折騰與搬動(dòng),好會(huì)兒時(shí)間,才將剛才所提到的那些、以及還沒提到的一些貴重物件,一次又一次地挪到這間房子里,藏進(jìn)了這個(gè)鮮為人知的地窖當(dāng)中。老麻這一舉動(dòng),還真讓桑花開了天眼似的,對(duì)他更是刮目相看。
讓麻氏成員心驚肉跳的事情說來就來。老麻才打發(fā)走兩個(gè)長工,進(jìn)而藏下重要家財(cái)?shù)牡谌欤捅还伯a(chǎn)黨新政權(quán)的民兵控制了,人家告訴他一家:從現(xiàn)在起,只準(zhǔn)老老實(shí)實(shí),不準(zhǔn)亂說亂動(dòng);至于如何處理他一家子,一切聽候通知。
幾個(gè)民兵進(jìn)入麻宅,又對(duì)老麻及其家人講下這一通話時(shí),他一家子(包括桑花、小玉、麻白鳳以及將滿四周歲的趙春山)都在;為此,平時(shí)認(rèn)為頗有身價(jià)的麻白鳳其人,也深感好日子過到頭了似的,竟然像只害著瘟病的母雞,身子骨也抖瑟起來。那幾個(gè)民兵對(duì)之宣告了人民政府的命令而離去以后,老麻感覺問題委實(shí)嚴(yán)重了,就又對(duì)桑花和小玉說,看這樣子,你們母女倆還得分開過日子;因?yàn)檎f到底,玉兒與咱并沒有太特殊的關(guān)系,誰也說不準(zhǔn)人家會(huì)給咱家定一個(gè)什么樣的罪,弄不好也會(huì)連累玉兒跟著我們一起遭罪的;現(xiàn)如今吶,她的家鄉(xiāng)也解放了,就讓她回老家去吧;今后,若她想你了,那也只是三十多里的路程,要來走一走、看一看,也是容易的事情。說到底,咱總不能連累了玉兒哇,她剛剛從小女孩進(jìn)入花季呀。
……哦,仔細(xì)想想,也是這么個(gè)理。所以,盡管玉兒一千個(gè)不樂意回歸老家,但她還是就在當(dāng)天,被老麻和桑花雇來的一輛小馬車,將其請(qǐng)回鄉(xiāng)下那個(gè)叫做阿摩密的小村子去了。玉兒走的時(shí)候,她抱著桑花左一聲干媽、右一聲干娘地叫著,哭的忒傷心,猶如生離死別。
之后,面對(duì)當(dāng)前這樣的、做夢(mèng)也沒想到的世道變遷,歷來跋扈驕矜的麻白鳳其人,竟然也惶惑癥式的問老麻:爹呀,那么你說,我該咋整呀?現(xiàn)如今趙大寶那天殺的,他又不知死哪里去了哇?
唔……這個(gè)嘛……,老麻想了想說:你有三條路可走:一是繼續(xù)呆在我們麻氏大院,與我們一起熬日子;二是回小十字街你老公公家,但是估計(jì)你回去那邊日子也不會(huì)比這邊安逸;三是趁此時(shí)機(jī)與我麻家劃清界線,去投靠你的親生父親——他是誰,如今我可以告訴你了。可是麻白鳳和桑花都異口同聲地說:哇——不不不不不不呀!
此前,桑花對(duì)于老麻,還在心里頭十二分地感佩,認(rèn)為他不愧為曾在官場摸爬滾打近二十年的絕世高手,對(duì)于世事既能洞明,情急之中處理問題,更是練達(dá)通透。首先,他打發(fā)走了鄒老三和劉小芹;接著,又神鬼莫測(cè)似的,把那些“事兒”搬入天知地知的地下儲(chǔ)存室;再接著,就又名正言順地送走玉兒姑娘;他老麻處理起這些事情來,不但方寸不亂,而且從容不迫,可以說,惟古今成大事者,方有如此先見之明以及老辣果敢的手段。可是,當(dāng)她抬頭再看老麻時(shí),卻見到了老麻面龐陰霾縈回的情狀,一時(shí)間不但少了幾分“大英雄”氣慨,而且兩眼渾濁,其情感意象,居然委婉蒼幽,就深知這個(gè)小男人的心理情愫,乃因一輩子沒有生育能力,就把生命的大部分賭注,壓在了與他沒有血緣關(guān)系的麻白鳳身上了。可是,桑花也深深知道,眼前的親生女麻白鳳,歷來自私自利,從沒在心里頭萌生過要對(duì)誰感恩的情愫,她過去不會(huì),現(xiàn)在和將來也許都不會(huì)吧?想到這里,桑花心里就像被蛇咬了一口似的,一剎時(shí)疼痛起來。天哪,這是誰做的孽哦?
說到這里,古往今來,都被蕓蕓眾生稱道與使用、進(jìn)而將其精髓發(fā)揮到極至的所謂“隱忍”、“得饒人處且繞人”、“退一步海闊天空”、“包容與大肚”之類的中國儒學(xué)文化,就頗有意蘊(yùn)悠遠(yuǎn)的哲學(xué)意味了。如果說,當(dāng)初因?yàn)樽非髠€(gè)性解放而拋開女兒和丈夫、進(jìn)而離家出走近二十年又返回家園的桑花其人,在硬著頭皮回歸故里之際,沒能得到老麻以德報(bào)怨的資助,一者,她不可能在老麻被那馬牟氣得暈死過去的關(guān)鍵時(shí)刻,毅然回到老麻身邊;二者,就在斯時(shí)斯地,看著老麻將再次陷入空前之政治漩渦的關(guān)鍵時(shí)刻,平時(shí)看似十分軟弱的一個(gè)風(fēng)塵婦人,也不會(huì)講出一番似乎只有在武俠小說中,喝過雞血酒的俠士才能講出的——那種俠骨柔腸的話來——她當(dāng)時(shí)就對(duì)老麻這樣安撫道:你都近六十歲的人了,這輩子除了一件事情(性生活)不如意,其他方方面面,也算滿足了吧?如果老天爺真要讓你過不了這個(gè)坎吶,那么無論如何,就是上刀山下油鍋,還有我這個(gè)不像樣子的婦人陪著你哇,怕什么嘛,這輩子咱經(jīng)過與見過的還算少嗎?
呵呵,佛家一首詩文說的甚好:
凡事從容修省,
何須急躁猖狂?
有涵有養(yǎng)壽緣長,
穩(wěn)似一生福量。
一時(shí)間,老麻竟被桑花這幾句發(fā)自肺腑的言辭感動(dòng)起來,卻不知說什么好,只是點(diǎn)了點(diǎn)頭。可是,話又說回來了,老麻如果想把懸吊著的那顆心徹底放下來,也不能夠因?yàn)樯;ㄟ@么地說出幾句只能算中聽而不中用的話吧?因?yàn)槊鎸?duì)眼目前的陌生世道,有誰能夠左右猶如天要下雨、娘要改嫁之類的事情呢?于是,老麻就在心里感嘆:除非斗轉(zhuǎn)星移;或者,當(dāng)年被他通了情報(bào)而遠(yuǎn)走他鄉(xiāng)的女婿趙大寶,能夠在很近的時(shí)日里,很及時(shí)地當(dāng)著共產(chǎn)黨任命的一個(gè)大官回到云平鎮(zhèn)來。否則。怕是一切都枉然了。
說來既是奇跡,卻也是情理中的事。老麻似熱鍋上的螞蟻惶惑不已的日子,僅僅熬了三天半,他那一顆懸吊著的心就落將下來了;然而,也不是如他所臆斷的所謂“斗轉(zhuǎn)星移”,也不是趙大寶當(dāng)著一個(gè)由共產(chǎn)黨任命的大官來到了云平鎮(zhèn)。而是他做夢(mèng)也沒有想到,中共云平區(qū)委的朱國邦書記和政府的馬小波區(qū)長,就偕兩個(gè)民兵和一個(gè)中年老漢去到麻家;那位中年老漢,就是兩年前親自撐船,將他和桑花渡到白泥田村,進(jìn)而秘密會(huì)見趙小蘭等人的那一位共產(chǎn)黨的堡壘戶主。
是時(shí),三言兩語的,該老漢與老麻說了兩句客套話之后,就由朱書記當(dāng)面向老麻說明上級(jí)轉(zhuǎn)來的,即一年以前被他在白泥田村以三七消炎粉醫(yī)好的那位
大人物的信函:
……滇七縣云平鎮(zhèn)麻耀昌先生,雖然曾在舊社會(huì)當(dāng)過國民政府之云平鎮(zhèn)鎮(zhèn)長近20年時(shí)間,卻又因其在幾年前,由于私自放走具有進(jìn)步思想的女婿,而被當(dāng)局免職進(jìn)而再被貶為平民;之后,他在我黨同志的感召下,能夠分清形勢(shì),擺脫身上各種羈絆,比較主動(dòng)地在其人生最為關(guān)鍵之時(shí)刻,站到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立場上來;除了以祖?zhèn)髅厮帪槲尹h之革命事業(yè)有所幫助,還積極捐出巨資,讓我軍購買軍糧,這在一定程度上對(duì)我們黨領(lǐng)導(dǎo)的革命事業(yè)做出了積極貢獻(xiàn)。鑒于此況,也是為了完整、準(zhǔn)確地履行我黨“三大法寶”(黨的領(lǐng)導(dǎo)、武裝斗爭、統(tǒng)一戰(zhàn)線)之方略,特建議當(dāng)?shù)攸h的組織、人民政府和土改工作隊(duì),在給該麻先生定階級(jí)成分時(shí),充分考慮他這幾年以來為革命做出的有益之事,如在未發(fā)現(xiàn)其對(duì)我黨和人民政府有不軌行為的前提下,應(yīng)將其階級(jí)成分定為“開明鄉(xiāng)紳”為宜。
此外,迎接解放大軍入滇追殲國民黨反動(dòng)勢(shì)力之工作,已在各地轟轟烈烈地展開,你區(qū)定然不會(huì)例外;因此,我認(rèn)為該麻先生,在大半生中執(zhí)掌云平鎮(zhèn)大權(quán),對(duì)于多方面事情了如指掌,謀劃辦事定能收到事半功倍之特效。故而建議你們,將其納入當(dāng)?shù)赜姍C(jī)構(gòu)之成員,使其才干得以彰顯,從而服務(wù)于我黨新生的革命政權(quán)和廣大人民群眾……
這里,要特別說明的是:這位朱書記雖然揣著這封信函去了老麻家,卻考慮到身份與尊嚴(yán),以及其他更深層次的政治因素,他并沒有當(dāng)面對(duì)老麻宣讀這張攸關(guān)老麻下半生政治命運(yùn)的信函,而是以口頭形式,向老麻做了基本意思與首長信函一致的傳達(dá);但在最后,卻把首長的提議,修改成他們區(qū)委和區(qū)政府的決定,特別強(qiáng)調(diào)“因此,區(qū)委、區(qū)政府已經(jīng)做出決定”之言辭,讓他即刻參與云平區(qū)人民政府關(guān)于迎接大軍路經(jīng)云平鎮(zhèn)的有關(guān)籌備工作。而這張完整地揣在該領(lǐng)導(dǎo)口袋里的紙片子,是在時(shí)間的腳步向前邁出35年后,即1985年某月某日,編修該縣地方志的大筆桿們,才在地區(qū)檔案館的卷宗里發(fā)現(xiàn)的。
于是,在那時(shí)那刻,老麻聽到了當(dāng)年那位大領(lǐng)導(dǎo)對(duì)于他之身份的確定,以及區(qū)委、區(qū)政府通知他即刻參與云平區(qū)迎接大軍籌備委員會(huì)辦公的消息時(shí),他竟然驚呆了,先是大腦中一片空白,繼而又感覺天空中飛翔著的鳥兒也停止扇動(dòng)翅膀似的;于是,就自個(gè)兒在心里嘀咕起來:這突如其來的好運(yùn)氣會(huì)是真的嗎?這是何等地出人意料,以及何等地對(duì)于咱老麻及其家人的特大肯定呀……可是吶,他后來曾幾次這樣對(duì)家人說:即便是當(dāng)年的蔣中正總統(tǒng),還有一去不復(fù)返的慈禧老佛爺,他們都沒有直接給過麻氏宗親什么好處;倒是人家共產(chǎn)黨哇,真正開明得讓咱五體投地吶。可是,咱老麻卻以小人之心,度人家君子之腹了。羞愧呀!
那天那時(shí),桑花也因一時(shí)之激動(dòng),竟然當(dāng)著那幾個(gè)“公家人”的面,嗚嗚咽咽,潸然淚下。
半個(gè)月后,入滇追殲國民黨反動(dòng)勢(shì)力的解放大軍之一部分,他們?yōu)榱藸帟r(shí)間、搶速度、抓戰(zhàn)機(jī),故而以每天180至200里的急行軍速度,由東而來,向西奔去;見此雄師驍勇而來,且有翻江倒海之精神,正做著迎軍工作的老麻,他雖然見多識(shí)廣,也沒見過這等恢弘壯美的氣勢(shì),便一時(shí)間感動(dòng)不已,高聲贊嘆:大風(fēng)起兮云飛揚(yáng)哇,且看這——雄師入滇,威武浩氣,崢嶸無比;只可惜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是也!
這樣的日子持續(xù)了十幾天。有天夜里,為了迎軍累得不行的老麻突然翻了個(gè)身,頗有興致地對(duì)桑花說:我好像看見大寶了。趙大寶,我和你的女婿呀!
65
迎軍工作結(jié)束不久,趙小蘭與張?zhí)鞆?qiáng)的簡樸婚禮,就在滇七縣城舉行,這是一個(gè)革命化的婚禮,一切從簡,只是開了一個(gè)幾十人參加的茶話會(huì),領(lǐng)導(dǎo)和證婚人講幾句祝福的言辭,大家唱了幾首歌、笑鬧一陣子,婚禮即成。三天后,新婚燕爾的趙小蘭夫婦,就被委以新的使命,前往云平鎮(zhèn)履職。
幾十年過去了,趙小蘭都沒忘記,1950年仲春,那個(gè)不同以往的春天氣象、春天事態(tài)、春天情懷。那景致,居然就像邊地民眾傳說中的陽光社會(huì),頗具魅力,也很詩意地姍姍來臨。于是,民眾不分族群,寨子不分大小,到處鑼鼓喧天,歌聲蕩漾,歡慶打土豪、劃階級(jí)、分田地、做主人的曠世盛事;為此,蒼穹之下,蕓蕓蒼生,盡都感受到這人世間最為撩人的氣象與熱烈景觀。
有一首民歌,這樣形容云平地區(qū)廣大民眾之心情:
太陽出來紅又圓,
各族娣妹笑開顏;
山笑水笑人歡笑,
人民當(dāng)家掌大權(quán)。
就在這樣的春情春意里,已經(jīng)一十九歲的趙小蘭記得十分清楚,當(dāng)她與新婚丈夫張?zhí)鞆?qiáng)一起,踏上云平古鎮(zhèn)的石拱橋、且能見著如詩似畫的一河碧水,流淌于橋下的路徑時(shí),不但看到了十分熱烈的景致,而且深切感受到鵝黃披著綠柳,鴨子水面生波,妍妍桃花簇紅英,朵朵杏臉開祥蕊;房前花,屋后樹,萌發(fā)綠蔭,洲上藻,水中蘆,都具幽情;更兼谷雨之后好晴天,禁煙才過,草長鶯飛,正當(dāng)三月韶華的迷人春色,心中委實(shí)親切萬分,興奮不已。故鄉(xiāng)情愫哇,千金難買。
趙小蘭夫婦這次來到云平區(qū),是因中共滇七縣委為充實(shí)云平區(qū)領(lǐng)導(dǎo)班子,而委任前往履職的。當(dāng)時(shí),張?zhí)鞆?qiáng)被委以云平區(qū)副區(qū)長一職,趙小蘭也被委以云平區(qū)共青團(tuán)委書記。此前,他夫妻二人已經(jīng)商定,到了云平鎮(zhèn),先不回小十字街老宅子看望父親和張劉氏,就即時(shí)進(jìn)入?yún)^(qū)委、區(qū)政府報(bào)到,繼而開展工作;絕不休息,也不拖塌,盡快進(jìn)入工作狀態(tài),把一腔熱血獻(xiàn)給嶄新的祖國和嶄新的時(shí)代。只待各方面理出頭緒了,才利用入夜后的時(shí)間,去看望小十字街趙氏宅子里的親人,同時(shí)也告慰他們:自己已經(jīng)走上人生的紅色正道了;今后,自己的一切,都屬于共產(chǎn)黨和普羅大眾。
可是,人世間的事情,往往都有兩面性質(zhì),絕不可能只往一個(gè)方面傾斜。有時(shí),甚至是這樣的情況:大白天把歡娛寫在臉上,應(yīng)對(duì)各種恭維;可是,暗夜中只身獨(dú)處時(shí),心里又在流淚和泣血。為此,趙小蘭在其歲月中,曾多次捫心慨嘆:人哇,各有各的難處;其實(shí)吶,哪個(gè)也不知道自己的肚子有多疼。
趙小蘭夫婦去到云平區(qū)委、政府的半月前,鑒于轟轟烈烈的迎軍工作也已結(jié)束,麻耀昌其人就理所當(dāng)然被客客氣氣請(qǐng)回家了。為此,他嘴上不說什么,但心里似乎嗅到了某種只可意會(huì)而不可言傳的政治氣息;哦,樹欲靜而風(fēng)不止哇……于是,趙小蘭一上任,就聽說了這么一件事情:就在她夫婦倆將到云平區(qū)委、政府報(bào)到的前幾天——那天清晨,她名副其實(shí)的老親爹麻耀昌先生,竟然在那種特殊且重大的政治背景下,分明知道區(qū)委、政府的主要領(lǐng)導(dǎo)不怎么待見他,他卻不顧老婆桑花和女兒麻白鳳的反對(duì),主動(dòng)進(jìn)入?yún)^(qū)委和政府的大門 (其實(shí)就是兩塊牌子一批人員),向朱國邦書記和馬小波區(qū)長說出這么一件事情——
老麻是這樣述說的:現(xiàn)如今,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廣大勞苦民眾,翻身做了主人,他這個(gè)被黨和政府看好的“開明鄉(xiāng)紳”也要緊跟形勢(shì),做出一點(diǎn)實(shí)事來,以表麻某對(duì)于黨和政府的謝枕之情。他說,他要做兩件實(shí)事:一者,如今他年紀(jì)大了,家中又沒有子嗣,所以擬將祖上留下的三十二畝水田和二十三畝旱地捐獻(xiàn)出來,讓人民政府酌情分給生活困難的貧雇農(nóng);二者,他親眼見到新生的人民政權(quán)辦公場所過于擁擠,經(jīng)過深思熟慮,決定主動(dòng)將祖上留下的、由兩個(gè)院子組成的大宅院劃出一半以上,即將宅院大門以內(nèi)所有平房和空地,包括較為寬敞與豪華的紫光院在內(nèi),無償奉送云平區(qū)委和人民政府,盼之作為辦公場所使用;他和家人吶,只住天頤院以及使用后園子就行了。他還說,為了體現(xiàn)黨政機(jī)關(guān)之尊嚴(yán),方便民眾辦事情,以及主動(dòng)避開他一家人不該知道的黨政機(jī)密,他除了要將天頤院的大門堵死,并建議在新堵上、又刷了石灰漿的墻壁上,工工整整地寫下“共產(chǎn)黨萬歲、毛主席萬歲”字樣;與此同時(shí),再從后園子那邊打開兩道新門,一是要進(jìn)入后園子,二是要重開天頤院的新門;再者,紫光院與天頤院之間那條通往后園子的小徑,也將一并徹底堵死。這樣一來,他麻氏一家人的耳目,就徹底地與人民政權(quán)不沾邊了,無論什么事情,既看不見,也聽不著;除了更方便群眾你來我往,云平區(qū)的領(lǐng)導(dǎo)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他一家人也能夠享受清靜的生活。為此,年紀(jì)尚輕、其實(shí)也沒有多少政治頭腦的區(qū)委朱書記和政府馬區(qū)長都十分高興,當(dāng)場贊揚(yáng)老麻這個(gè)開明鄉(xiāng)紳繼續(xù)為新生的人民政權(quán)做貢獻(xiàn),同時(shí)也問老麻: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來,區(qū)委、政府一定給予解決。可老麻卻爽快地說,沒什么要求,就是想討得一張區(qū)委或者區(qū)人民政府開具的、按有公章的字條,說明他這位開明紳士已于某年某月某日,無償捐獻(xiàn)祖上全部田產(chǎn)和一半豪宅房產(chǎn),而為云平民眾和新生的人民政權(quán)做出“略表綿薄之力”的字樣即可。
哈哈哈哈,朱書記和馬區(qū)長一聽就特別地高興,連連說道“這是應(yīng)當(dāng)?shù)模欢ǖ模覀円欢〞?huì)給你這么一個(gè)字據(jù)的”;并且,書記、區(qū)長說辦就辦,當(dāng)場就讓秘書寫了這么一張包容了以上所述內(nèi)容的收據(jù)給了老麻。之后,朱書記和馬區(qū)長這兩位云平鎮(zhèn)的父母官很輕松地說道:這辦公場所和人員住宿問題,今天總算迎刃而解了;否則,還真讓咱倆頭疼呢。
這件事情,就像快刀斬亂麻那般,真是快、快、快。當(dāng)天,老麻一家人就在云平區(qū)委、政府七、八個(gè)工作人員配合下,只是草草收拾了紫光院和那一爿平房中一些必需的物件與家什,就履行其諾言,除卻一大幢“紫光院”豪宅外,其它搬不了和沒必要的家具與物件,也都一并留給了新生的人民政權(quán)。繼而,就在第二天,除了堵墻、堵路、以及老麻一家要重新打開兩道新門以外,在僅僅一天的時(shí)間里,云平區(qū)委、政府的幾個(gè)辦公室和部分工作人員,就入駐了麻氏宗親的紫光院以及大門內(nèi)的那爿平房。為了這一重大的捐獻(xiàn)房產(chǎn)事件,老麻除了得到他所需要的那一張“紙”,也獲得云平區(qū)委和政府一張捐產(chǎn)獎(jiǎng)狀。于是,從即日起,云平區(qū)委和政府的牌子分開掛,原國民黨的老鎮(zhèn)公所是區(qū)委,原麻氏宅院將被隔斷的一半“紫光院”及附屬平房是區(qū)人民政府,且決定原紫光院樓上作為辦公人員之宿舍,樓下均為辦公室。
后來,云平人都在私下里說,官場老手麻耀昌的頭腦好生管用哇。因?yàn)榫驮趦蓚€(gè)月后掀起的第二波擴(kuò)大鎮(zhèn)壓反革命之運(yùn)動(dòng)中,毗鄰地區(qū)與他相比,其家產(chǎn)少了許多的幾家地主,都受到理所當(dāng)然、或輕或重的制裁;惟有他,除了頭上那個(gè)“開明鄉(xiāng)紳”的環(huán)冠,還有身上揣著云平區(qū)人民政權(quán)開具的那一張“紙”和授予的那一張獎(jiǎng)狀,就是憑著這種看似抽象、卻絲毫不可小視的“玩藝兒”,老麻及其家人,方才得以有驚無險(xiǎn)地過著既有小酒喝、也有大肉吃的小日子。嗚呼,這是哪一種博大精深的文化積淀所演繹、所熏陶的“退一步海闊天空”、或者所謂的“移花接木”、“舍財(cái)免災(zāi)”抑或“九陰真經(jīng)”、“化功大法”之結(jié)果呀?
趙小蘭夫婦報(bào)到后,其住宿就安排在新的區(qū)政府,即以往麻氏大宅院之“紫光院”樓上,一間十幾平米的房間;在忙碌了整整三天時(shí)間,確實(shí)料理了不少必須的公事與入住的私事,才覺得該回家了,該回家看看了;七百多天前,因?yàn)樗呢?fù)氣離家,說不定老父親盼她歸里而望眼欲穿了呢。于是,就在入夜以后,趙小蘭帶上此前買給父親的一條褲子和一包煙絲、給張劉氏的一塊頭巾以及給阿彪的一顆五角星和一包糖,心情十分悅愉地偕丈夫張?zhí)鞆?qiáng),走進(jìn)了離開兩年多的小十字街老宅。
雖然身披夜幕,但憑直覺,趙小蘭分明感受到了:門前那一對(duì)自幼不知撫摸過多少次的石獅子,此時(shí)少了一些往昔的生動(dòng)氣息;門口那一片按說應(yīng)當(dāng)搖曳多姿的三角梅花,似乎也顯得出奇地靜默與抽象,對(duì)于久違了的房子主人之回歸,似乎并沒興趣投之歡娛與多姿的搖曳。
哦喲,這是咋回事哇?趙小蘭進(jìn)到堂屋就問:這堂屋咋空蕩蕩的,咱家的八仙桌和那兩條長形春凳呢?
哦,顯然蒼老了不少的趙家昌溫婉而答:被人民政府的人借去做辦公用具了。說是以后還要?dú)w還咱家的。
這個(gè)……趙小蘭沒說出來,只是在心里嘀咕:怪不得我看區(qū)委會(huì)議室的桌子板凳好像在哪見過似的。他們是“借”咱家的物件去做辦公用?
……
該說的該問的該交流的,譬如家中各人的健康、趙大寶本人以及他老丈人麻耀昌和麻白鳳的近況、將滿四周歲的小侄子趙春山長的如何,阿彪在校讀書學(xué)習(xí)可好等等的話題交流過后,趙家昌就說出讓趙小蘭沒有心理準(zhǔn)備的一個(gè)政治性話題:這次搞土改,定階級(jí)成分,咱家被定為“富農(nóng)”了。
“爹呀,咱這個(gè)家被定成富農(nóng)了?可是……”
趙家昌又緩緩而說:還是大寶的老丈人麻鎮(zhèn)長(他仍如此稱呼)的命好,被定了個(gè)“開明鄉(xiāng)紳”,聽說上面有大人物肯定了他對(duì)革命做過的好事情。
趙小蘭豈能不知呢——當(dāng)時(shí),黨和政府對(duì)于廣大農(nóng)村的執(zhí)政大原則是:緊緊依靠雇農(nóng)、貧農(nóng)和下中農(nóng),團(tuán)結(jié)中農(nóng)和富裕中農(nóng),營造成95%的革命陣營,孤立、打擊5%的地主和富農(nóng)。于是,出于真實(shí)情感的流露以及對(duì)于世事的把握,她就連連發(fā)出為什么為什么為什么?這是為什么呀的詰問之詞?她認(rèn)為:要說對(duì)革命有貢獻(xiàn),那么老父親趙家昌對(duì)革命的貢獻(xiàn)不是云平人也能見得著的嗎?老父親把一兒一女送出家園并投身革命,自己卻成了革命的對(duì)立面,這也太滑稽了吧?按趙小蘭的意愿,怎么著她的父親也可像麻耀昌那樣,劃個(gè)開明鄉(xiāng)紳的成分才合情理哇。可是,她做夢(mèng)也沒有想到:她這個(gè)一心投身革命的年輕戰(zhàn)士之父親及其家庭,會(huì)被定為革命陣營的對(duì)立面:富農(nóng)。可悲哇!
為此,一輩子淳樸得就像泥土一樣的趙家昌憂郁著說:小蘭哇,人家搞土改工作的領(lǐng)導(dǎo)說了,咱家有這么大一個(gè)宅子,雖然是我和師傅幾十年來靠打拼積蓄的成就,但畢竟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實(shí)物,這十幾年來我們家每到春秋兩季忙得不可開交時(shí),也還請(qǐng)上兩三個(gè)短工幫襯著做事,這些都是定成分劃階級(jí)的依據(jù)。我們家被定成富農(nóng),是恰如其分的,一點(diǎn)也不過分;但人家也說了,一是我這輩子人品不錯(cuò),從來沒有欺貧媚富的劣跡:這二吶,人家也知道你哥哥趙大寶當(dāng)年參加抗日遠(yuǎn)征軍去緬甸與日本人干過仗,后來還因?yàn)樗粷M意國民黨政府那一套,才被迫離家出走至今音訊杳無的,加之如今你又成為真正的革命人了,所以這事情呢,就是鑼做鑼的敲、鼓做鼓的打,一碼歸一碼,就是我的富農(nóng)成分不能不定,說了這是上面的上面的上面——編制出來的框框套套,我們?cè)破芥?zhèn)1140家人,要“套”出5%的革命對(duì)象,就是要套出11家地主、47家富農(nóng);所以套來套去的總是不夠數(shù),我和另一家就在最后被套進(jìn)去了。但是有兩點(diǎn),一是絲毫不影響你們后一代參加革命工作的光榮;二是只要我一直真誠擁護(hù)黨和政府的主張,老老實(shí)實(shí)做人做事,不要與那些貨真價(jià)實(shí)的壞分子攪在一起,也就不會(huì)有誰來找咱家的麻煩。哦,這時(shí)趙家昌頓了頓,看了張?zhí)鞆?qiáng)一眼,才又接著說:還有,如今女婿也是咱區(qū)的副區(qū)長了,看見大寶和你們都趕上了大好的時(shí)光,走上了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大路上,不要說人家只是給我定了個(gè)富農(nóng)成分而沒難為我,就是真地對(duì)我有些不公正、不體面的處理,我也心甘情愿認(rèn)了。真的,阿蘭哇,只要你和阿寶倆兄妹過得好,老爹我什么都能認(rèn)下的。哦,趙家昌又說:麻鎮(zhèn)長前幾天告訴我了,他說:好像是見著你哥哥阿寶了;那時(shí),他們正飛快著緊急行軍,往西邊方向趕,后來聽說是要忙著去打國民黨軍的飛機(jī)場。遺憾的是,就連麻鎮(zhèn)長也沒能與他講上一句話。
可是,可是……爹哇,趙小蘭沒接這個(gè)茬,仍糾結(jié)剛才的話題:咱云平鎮(zhèn)大大小小哪個(gè)鄉(xiāng)親不知道,你吶,不但是個(gè)石匠,是個(gè)靠手藝養(yǎng)家糊口的石匠,而且是一個(gè)憨厚得就是變成狗,也絕不會(huì)咬人的大好人呀!
哦……這人世間的事情哇,即便佛家,怕也難得參透的吧?于是乎,堂屋中的趙家昌和張劉氏、趙小蘭和張?zhí)鞆?qiáng),心中無不風(fēng)風(fēng)雨雨,欲說還休。只有那個(gè)年紀(jì)尚不滿十歲的小弟阿彪,仍在興致盎然地把玩著小蘭姐姐給他的那顆五角星。
可是,知父莫若女。這時(shí)刻,趙小蘭分明感覺得到,她那慈祥的父親,為了安慰她和張?zhí)鞆?qiáng)能在今后的歷程中不要為他的既定命運(yùn)而分心,就在那張苦經(jīng)風(fēng)雨的老臉上,呈現(xiàn)出一種溫、良、恭、儉、讓兼而有之的微笑。
更加打動(dòng)趙小蘭內(nèi)心的,是趙小蘭的繼母,那個(gè)自幼對(duì)于趙大寶和趙小蘭兄妹來說,因?yàn)闆]有血緣關(guān)系,只有在極為避不開時(shí)才會(huì)對(duì)之稱呼“阿媽”的張劉氏其人,說了幾句石打石(實(shí)打?qū)?的心里話。她說蘭子哇,你是知道的,我這人很笨,平時(shí)就不會(huì)說話;可是現(xiàn)在我要告訴你,讓你記住:早在日本人投降那年的春天,我的家人和房子,都被那些天殺的日本人開飛機(jī)過來炸沒了,是你這個(gè)無比善良的阿爹,他收留了阿彪我們娘倆,還給了我一個(gè)名副其實(shí)做他婆娘的名分;我好感動(dòng)哇。所以我已經(jīng)發(fā)過重誓,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無論何時(shí)何地,我們現(xiàn)在這個(gè)家庭,如果遇到九災(zāi)八難,也無論是遇到麻風(fēng)病還是溫疫流行,或者天塌地陷,我都是你爹的人,永遠(yuǎn)陪在他的身邊,為他做飯,為他洗衣,為他做一個(gè)女人必須要去做的一切事情。現(xiàn)如今,我們這個(gè)家的情況,你也知道了;你是革命人,你的哥哥——多年沒回過家的阿寶也一定是革命的人,看著你兄妹倆都出人頭第、將來還會(huì)大有出息,我和你阿爹無比高興哇,所以我們倆老商量過了:為了你和阿寶今后的前途著想,從今以后,你們要少回家,或者別回這個(gè)家;只要你們過的好,就是下地獄,我們都會(huì)笑著走進(jìn)去的。哦,乖(mei音)哇,你們就放心吧。
為此,許多年過去了,云平鎮(zhèn)還有人這樣贊嘆道:咱云平鎮(zhèn)“兩大‘昌’”的婆娘,對(duì)待自己的男人真不賴。
于是,趙小蘭的淚水奪眶而出,大有萬箭穿心之感。終于,她禁忍不住了,只好一咬牙,帶著滿臉的淚水,離開了這個(gè)自幼給予她無比溫馨的堂屋。
幾個(gè)月后,組織上考慮到趙小蘭必須輕裝上陣的實(shí)際問題,將其夫婦調(diào)至遠(yuǎn)離云平140余公里的阿達(dá)縣工作。從此以后,趙小蘭在其生命歲月中,她一般每年才回云平鎮(zhèn)一次,每次回去僅僅住上兩天三天即離開。她在1967年最后一次離開老宅時(shí),飽噙淚水看著躺在棺材里老父趙家昌的遺體說:爹哇,你這輩子算是白養(yǎng)我了啊……
66
趙小蘭夫婦抵云平區(qū)委、政府報(bào)到之日,麻耀昌已經(jīng)帶著眼目下很少的一家子人,搬入經(jīng)過封堵老門并打開新門的“天頤院”生活了三天。
因?yàn)楹髨@子的圍墻雖然被挖開,卻由于時(shí)間關(guān)系,除了從“紫光院”移過來的部分家什物件還胡亂擺在地上,最要緊的是,無論新打開后園子的圍墻缺口,還是“天頤院”南墻已經(jīng)破開的豁口,都必須分別安上門,否則家不像“家”了,特別這“天頤院”的大門,要安得與老宅“身份”相稱,就得需要內(nèi)行人手才行,不是老麻這等賦閑之人可以為之;所以,還得找能工巧匠前來做活才行。找誰呢?還是找親家趙家昌嗎?可他是石匠呀?
在此當(dāng)口,即趙小蘭夫婦到云平鎮(zhèn)上任第七天之入夜掌燈時(shí)分,歷來只知享受,卻不太顧及聲名與面子的麻白鳳其人,終于因?yàn)檫@些天參與桑花一道收拾屋子很煩累,就對(duì)老麻提出,說她想搬回趙家去住;她還說,反正自己不錯(cuò)也錯(cuò)了,那個(gè)578團(tuán)也早走的無影無蹤,她與牛德安那雜種的破事吶,就像做了一場大夢(mèng)似的,模糊了,不存在了。她又說,無論好歹,她也是趙家在光天化日之下,用轎子抬進(jìn)家門的兒媳婦,而且也為趙家生下了兒子趙春山;現(xiàn)如今,再過幾個(gè)月,都要給兒子舉辦四周歲生日宴會(huì)了,這客當(dāng)然得他老趙家置辦;所以吶,她得搬回老趙家去住。接著,她就糾纏老麻,讓老麻去找趙家昌說一說情,讓她搬回去。
此時(shí)的老麻,心里正為諸多亟待處理的事情堵著胸口,還真想嘮叨一番發(fā)瀉一下呢。于是,老麻就竹筒倒豆子似的,把這兩天以來遇到、并與親家趙家昌交流過的真實(shí)情況抖了出來。老麻直說道:你若搬回去住,你公爹和他婦人當(dāng)然沒說的,也能為你帶一下孩子,可是你不會(huì)不知道吧?那個(gè)趙小蘭和她丈夫回到云平鎮(zhèn)來了,她男人當(dāng)了云平區(qū)的副區(qū)長,她當(dāng)了一個(gè)什么什么的小頭目;她吶,過去對(duì)你的事情就忒不待見,也可以說,正是因?yàn)橐姴坏媚愕男袨椋乓粴庵拢鲩T干革命的。現(xiàn)如今的趙小蘭哇,可以說,她就像一只站在房頂上打鳴的大公雞嗡(甕)叫得很,能容你回她趙氏門宗去嗎?其實(shí),為了這事,你公爹也已經(jīng)在昨天晚上進(jìn)入紫光院,哦——就是區(qū)政府找過她,讓她同意你回趙家去過日子。她卻說了,你一時(shí)半會(huì)的不能夠進(jìn)趙家門檻。一者,一提到你,她就覺得你當(dāng)年與別人的行為委實(shí)對(duì)不起她哥哥趙大寶,她不想再因?yàn)槟氵M(jìn)入趙家,繼續(xù)成為再讓云平民眾說出趙家長哇、短哇的是是非非;二者,趙家現(xiàn)在不同以往了,階級(jí)成分上是“富農(nóng)”——她這話倒也有幾分道理的——如今她父親趙家昌被擺到了革命陣營的對(duì)立面,你在這時(shí)候進(jìn)入趙家,別的甭說,她的親侄子哦,就是你生的這個(gè)趙春山將要辦的四周歲宴席,怕也沒幾戶人家敢于去賀喜的了——老實(shí)說,我那親家老趙也說了,他根本不敢為大孫子的生日辦客了;而今,別說你現(xiàn)在去趙家不會(huì)讓云平人待見,還極有可能招到大家的議論;所以一切的一切,要等趙大寶回來才能裁決。此外吶,這時(shí)他看了看桑花其人,才悠悠而說:我也曾與你阿媽講過的,上月在做迎軍工作時(shí),我好像看見奔跑在隊(duì)伍中的一個(gè)年輕人特像趙大寶——哦,人家是爭時(shí)間搶速度往近百公里外的方向趕,沒一個(gè)人會(huì)停下來脫離隊(duì)伍,說是要爭分奪秒,去晚了怕國民黨軍隊(duì)乘飛機(jī)逃跑。所以吶,趙大寶還活著,這是肯定的;趙大寶是革命軍人,也是肯定的了。所以,你就忍一忍吧,我想最多半年,他無論如何是要回來一趟的。那時(shí)候,你回得了、或是回不了趙氏那個(gè)家,還能不能繼續(xù)是趙家的兒媳婦,這一切,就聽他趙大寶一句話了。
眼見不知天高地厚的麻白鳳還想講點(diǎn)什么。老麻就發(fā)了狠話斥責(zé)道:才幾天時(shí)間,你不是嫌做點(diǎn)家務(wù)活太累,就是嫌吃的不可口、住的不舒坦。哼哼,不信走著瞧,你難過的日子可能還在后頭吶;否則,我能一咬牙,把祖宗留下的田地和一半宅子捐獻(xiàn)出去嗎?
第二天,壬午時(shí)分。老麻因?yàn)樽蛞菇逃?xùn)麻白鳳一事還在心里頭有些不爽快,加之只能煩勞親家趙家昌去請(qǐng)兩個(gè)工匠來安裝大門的事情,總是不見其人影,就只喝了一碗桑花做的稀飯,竟自拿了一本刻于清嘉慶年間、他爺爺麻有志生前留下的《三國演義》卷一,再又端了個(gè)木板凳出門,坐到已經(jīng)破了墻口亟待安裝大門的園子邊沿,想一邊等老趙率著工匠來臨,一邊再一次翻看和頓悟作品開篇那一段“滾滾長江東逝水……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的詩文,就有久違了的老疤楊做成其人,正風(fēng)風(fēng)火火似的,向老麻這邊趕來——
究其原委,乃因老疤楊前往趙家宅子尋找趙家昌,而張劉氏又告之:老趙已經(jīng)出門往老麻這邊幫助安裝大門來了;所以,一時(shí)之間,老疤楊心里頭就產(chǎn)生一種怪怪的情緒,他要對(duì)老麻搞一搞幸災(zāi)樂禍的惡作劇——這老疤楊因?yàn)楫?dāng)年親自駕車,將侄兒趙大寶送走回到云平鎮(zhèn)以后,半年當(dāng)中,天有不測(cè)風(fēng)云,他因?yàn)榧抑邢嗬^老人死的死、老婆病的病等諸方面不順暢之事,曾經(jīng)讓趙家昌帶話給老麻,說明看在趙大寶左邊是侄兒、右邊是女婿、因而手心手背都是肉的份上,想請(qǐng)老麻借二十塊光洋急用,按說他所借的那一點(diǎn)錢,在老麻眼里壓根兒算不了什么;可是,雖說老麻當(dāng)年求子心切,一心盼著桑花的肚子能夠大起來,然而現(xiàn)如今吶,他一想到老疤楊就是麻白鳳之親生父親這一點(diǎn),心里頭就有一種更比醋意更甚、以及更比吃下蒼蠅還難受的意識(shí)涌上心頭,于是根本不管他老疤楊與趙家昌、與趙大寶、也與他老麻牽扯著幾分哭也哭不得、笑也笑不了、因而最好別牽扯上的親緣關(guān)系時(shí),就一口拒絕說:不可能;之后,老疤楊只好一咬牙,即便在半年之內(nèi),相繼把家中最值錢的兩頭牛、一匹馬、三口豬出賣,也沒能擋住江河日下似的貧困態(tài)勢(shì),并且繼老人死去之后,又賠上那久病婆娘的一條性命,因而在土改工作隊(duì)進(jìn)村以后,他就被定為最能依靠的對(duì)象——貧農(nóng),繼而又被指定為云平區(qū)貧農(nóng)協(xié)會(huì)第五小組的組長。如果土改工作隊(duì)提前四年進(jìn)入鎮(zhèn)子里來,他老疤楊的階級(jí)成分嘛,確切地說,一定會(huì)被定為“富裕中農(nóng)”,這就是一個(gè)人的“運(yùn)氣”問題了;人的命運(yùn)哇,就是如此這般地不可確定。現(xiàn)如今,按說在他老疤楊做成的頭上,也沒什么光環(huán)值得炫耀,可是當(dāng)他聽到、看到今日之老麻,已然像落水的鳳凰那般,遠(yuǎn)不如大公雞光鮮顯眼了,于是就心生硬要沖到老麻面前,說兩句刺激老麻神經(jīng)的話語,以報(bào)當(dāng)年老麻沒借錢給他、從而讓他小日子每況愈下的一箭之仇——這是因?yàn)楝F(xiàn)如今的他,居然也成了光榮的、可以理直氣壯逛大街之貧農(nóng)協(xié)會(huì)的第五小組之組長了!
于是,老疤楊就急匆匆地繞了幾個(gè)小胡同,去到老麻家過去的后園子,身子一站到老麻跟前,幾口大氣還沒喘勻,他就張口報(bào)復(fù)開了;他是這樣奚落老麻的:哈哈哈,幾十年來高高在上,而且穿錦衣、吃玉食均不在話下的麻大鎮(zhèn)長哇,你怎么也會(huì)落到不得已把大門讓給別人走,自家打開后園子又將小胡同當(dāng)前門出入這般田地哇,還像窮酸書生那樣,坐在這小木板凳上,幾乎是當(dāng)著街面看書度日子了呀?繼而,他見老麻抬頭看了看他卻沒有回話,又覺得不太過癮,就又說道:以后吶,說不定你得瞧我的臉色行事了吧?你什么雞巴“開明鄉(xiāng)紳”?就算你把家產(chǎn)、田地全部捐了、再搭上這把老骨頭,對(duì)你認(rèn)可不認(rèn)可吶,還得咱們貧下中農(nóng)說了算,也就是我老疤楊這些人說了算哦!
哎喲,你想怎么著哇?這時(shí)候,頭腦一時(shí)發(fā)漲的老疤楊,他壓根兒沒想到(其實(shí)理當(dāng)想到),心中也憋著火氣的麻白鳳其人,竟然從天頤院正待安門的堂屋間沖了出來,站在離他十步之遙的位置,把雙手交叉抱著,眼里放出不屑一顧的冷光,開口就反擊老疤楊道:你也別忘了,他的女婿趙大寶,可也是干著革命的人吶;現(xiàn)如今,他女婿還在正規(guī)軍里能耐著、光鮮著、威武著,莫非你不知道嗎?隨著這一話音,老疤楊又看見另一個(gè)女人也從天頤院匆匆來到麻白鳳跟前,此人自然就是麻白鳳之生母桑花了;當(dāng)時(shí),桑花懷里還抱著麻白鳳近四歲的兒子趙春山(其實(shí)也是老疤楊真正的外孫),緊接著,老疤楊還看見了桑花那一雙雖然很平靜、卻已準(zhǔn)備著應(yīng)對(duì)一切的目光已經(jīng)聚到了他之身上。
一時(shí)間,老疤楊頓覺雙腿打顫,就趕緊換了一副面孔,他笑著說:不好意思。是開玩笑、開玩笑的。都是親戚,自己人吶。哦,我是來看看我三姐夫他是不是來這里了。繼而,就像家中起火要趕過去潑水似的,急急地離去了。
后來,老疤楊私下里曾這樣感慨過:媽的,在她娘倆面前,我他媽的,就是個(gè)絕對(duì)的慫人。
67
入夏以后,讓趙家人、特別是讓趙家昌幾乎盼穿雙眼的趙家驕子趙大寶,他在淮海戰(zhàn)役晚期集體投誠并被編入解放軍某部,以解放軍正排級(jí)文化教員身份,直接參加舉世聞名的渡江戰(zhàn)役、廣東戰(zhàn)役、粵桂邊圍殲戰(zhàn)役之后,又在大軍將向云南進(jìn)發(fā)之前,其文化教員級(jí)別被提升為副連職級(jí),進(jìn)而隨軍直接參加滇南戰(zhàn)役,前后在解放軍隊(duì)伍中歷經(jīng)戰(zhàn)火一年多,終于在離開故土四年之際,又回到了他魂?duì)繅?mèng)縈的云平鎮(zhèn),回到了小十字街他家老宅里。時(shí)年,他正好25周歲,卻經(jīng)歷他一生當(dāng)中脫胎換骨似的崢嶸歲月。
趙大寶回到家,屁股還沒落到板凳上,就說出咋的不見麻白鳳身影,咋的不見他沒能謀面的孩子,孩子是男是女,長的如何這些令人難以回答的話題。
之初,看到兒子歸來,趙家昌那高興的樣兒,絕不比兒子第一次結(jié)婚,將翠香姑娘娶進(jìn)家門那般遜色,他正想著,是否急急地去告之內(nèi)弟老疤楊做成這一消息,再讓阿彪快快地進(jìn)入?yún)^(qū)政府,去當(dāng)面告之趙小蘭和張?zhí)鞆?qiáng)這一大喜事,再讓她夫妻二人回家,會(huì)同老疤楊一起,與哥哥趙大寶見見面,吃一次樂呵呵的家人團(tuán)圓飯。可是,當(dāng)他使走了阿彪去請(qǐng)趙小蘭偕夫回家,卻沒等到他再出門去請(qǐng)老疤楊之際,他就因?yàn)橼w大寶詢問麻白鳳母子的話題,而隱約地感到心口疼痛;盡管他強(qiáng)壓心頭痛苦之情緒,支支吾吾以“她母子在娘家住著,一切還好”的囫圇話語遮隱過去,繼而阿彪也把趙小蘭夫婦找回家了,老疤楊也被勤快的阿彪請(qǐng)到堂屋來一塊兒吃飯,但那頓團(tuán)圓飯,也理所當(dāng)然沒能吃出高潮,就草草收?qǐng)觥?/p>
簡言之,因?yàn)閮蓚€(gè)話題:一是麻白鳳當(dāng)年的風(fēng)流故事,二是新產(chǎn)生的“家庭成分”問題。于是又有了兩個(gè)結(jié)果:一者,為了兒子和子孫后代的前途,趙家昌想讓兒女們與他這個(gè)階級(jí)成分偏高的父親劃清界線;二者,至于如何處理無法遮隱下去的麻白鳳問題,一切由趙大寶自裁。可是,為了這第二個(gè)話題,老疤楊很鄭重地告之趙大寶:阿寶哇,你兒子趙春山還小,他需要一個(gè)既有父親、也有母親的家庭,能不離婚,就盡量別離吧;其實(shí)人世間的事情,臉面也算不了什么,只要咬一咬牙,時(shí)間長了,一切都會(huì)過去的!其實(shí)說白了吧,我是堅(jiān)決反對(duì)你與麻白鳳離婚的。
可是……趙大寶的心里,一時(shí)間就像刀子戳傷似的疼痛不已,委實(shí)難以把持心態(tài)。這這這,這是咋回事哇?
長話短說。1950年初以來,趙大寶隨部隊(duì)從廣西出發(fā),繼而,進(jìn)入滇東南開始,一路奔襲,一路戰(zhàn)斗,直至隨軍解放春城昆明。接著,又參加了一段時(shí)間的剿匪工作,就被宣布轉(zhuǎn)業(yè),被安排在與滇七縣毗鄰的阿米縣教育部門工作。他這次回到云平鎮(zhèn)老家,本只想看看父親和家人,親一親后來才知性別與名字的兒子趙春山;然后,與麻白鳳名義上的父親麻耀昌(他此前不知桑花歸里)商議一下,如果可能,想將麻白鳳和兒子接至他工作的阿米縣城過日子的。可是,他做夢(mèng)也沒有想到的是,他兒子的母親麻白鳳,會(huì)在他逃離家鄉(xiāng)、意欲亡命天涯的日子里,與一個(gè)國民黨軍的小排長私通,從而鬧得云平鎮(zhèn)幾乎家喻戶曉;國軍的一個(gè)小小排長,竟然睡在了共軍副連職文化教員之老婆的肚子上;這這這這,對(duì)于他這么一個(gè)既要臉面、更顧政治前途的年輕革命者來說,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忿事,更兼回到家里,就聽說一輩子像黃牛一樣篤實(shí)厚道的老父親,如今也被劃到革命陣營之對(duì)立面,這自然是兩件極不光彩的事情。然而話又說回來了,作為一個(gè)年輕的革命人來說,雖說家庭出生由不得自己選擇,但革命的道路是可以選擇的;況且老父親的人品,在云平鎮(zhèn)有口皆碑,說得自信些,父親就是戴著“富農(nóng)”帽子生活下去,全鎮(zhèn)人絕沒有要與他過不去的事情發(fā)生。可是,這麻白鳳就不同了。雖然,他在決斷此事之際,大腦中也不止一次地閃現(xiàn)出貴陽城里的妓女,以及當(dāng)年在國民黨舊軍隊(duì)中馬副團(tuán)長老婆馬纓花與他有染的往事。但那些往事,絲毫平衡不了眼目前的現(xiàn)實(shí):一是云平鎮(zhèn)民眾盡都知道了,他這個(gè)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下的副連職革命青年之妻,居然與對(duì)立面的國民黨軍之小排長有肌膚之染、肉體之歡,這不是那些國民黨人變相地給了他一個(gè)脆響的巴掌嗎?二是古往今來,由儒學(xué)衍生出來的,那種在云平鎮(zhèn)民眾中區(qū)分好女人與壞女人之重要標(biāo)準(zhǔn)的共識(shí),正所謂根深蒂固,他那不足十斤重的頭顱,戴得動(dòng)那么大、那么重的綠帽子嗎?三是在那種政治大背景下,如何舍取關(guān)乎自己、也關(guān)乎子孫后代前途命運(yùn)的大事情呢?敢馬虎、敢含混、敢草率、敢做大豬頭大日膿包嗎?除非,他為了包容這個(gè)家庭所有成員,本著“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耶穌精神,從而放去自己讓人眼紅、進(jìn)而打心里羨慕得要死的革命干部之身份和物質(zhì)待遇,回到云平老家來,過一種任人評(píng)說與遭人白眼的、只能了卻一生的窩囊生活——可是怎么可能吶?
所以,無論麻白鳳如何地死乞白賴以及麻耀昌、老疤楊也出面說情,但趙大寶與麻白鳳共同演繹的,這一場從開始就顯出滑稽意象的婚姻,終于在重大且嚴(yán)肅的政治背景下,由云平區(qū)副區(qū)長張?zhí)鞆?qiáng)、團(tuán)委書記趙小蘭等領(lǐng)導(dǎo)親自出面,督促民政干部認(rèn)真審理,不幾天就可強(qiáng)行判決。
為了這一出在幾年前就傳遍鄉(xiāng)里的鬧劇,如今就要有一個(gè)預(yù)料之中卻也姍姍來遲的收?qǐng)觯^大多數(shù)民眾認(rèn)為:趙氏門宗的兒男趙大寶確也不失為頂天立地的男子漢,敢做敢為敢擔(dān)當(dāng)。惟獨(dú)老疤楊做成特別的不高興,并且還以長輩身份對(duì)趙大寶說了幾句難聽話:你小子當(dāng)真有出息了,哼哼,天亮才見白頭霜;你今后日子長著吶,不信走著瞧吧,不信天上的太陽就只照你一人身上。
因此,看著大惑不解的兒子再次陷入老疤忿罵的痛苦當(dāng)中,趙家昌只好在沒第二人在場時(shí),把一個(gè)驚天隱秘告之兒子趙大寶:寶兒哇,這疤臉老舅吶,他原本就是麻白鳳的親生父親呀!
啊!這這這這這這……趙大寶竟然好半天沒有回過神來。
阿寶你想一想,其實(shí)吶,你疤臉老舅他也就是想,想讓他的親骨肉麻白鳳跟著你光宗耀祖哇。這血緣一事,那是打斷骨頭也連著筋吶!
可是,讓趙大寶心靈大受折磨的事情,在第二天又出現(xiàn)了:趙大寶雖然一定要與麻白鳳離婚,卻又一定要親眼見一見和親一親他與麻白鳳共生的兒子趙春山,這是人之常情,況且兒子都有四歲了,他還沒見一面呢。可是,就因?yàn)檫@個(gè)理當(dāng)不成問題的心愿卻轉(zhuǎn)化成很大的問題,原因在于那一根筋似的麻白鳳,她因?yàn)橼w大寶一心要離婚,就鐵了心要報(bào)趙大寶的一箭之仇;她說,如果一定要離婚,此番絕不讓趙大寶見著兒子。為此,趙大寶既大為惱火,卻也無可奈何,因此與麻白鳳結(jié)怨更深;于是,趙小蘭對(duì)麻白鳳的驕橫跋扈更加堅(jiān)定了此前支持哥哥離婚的決定,并給丈夫張?zhí)鞆?qiáng)施壓,讓其親自出面,定要把麻白鳳剔出趙家人的行列,并且,還要讓趙大寶見到和得到自己從未某面的親兒子。
是的。此離婚案終究要塵埃落定的。三天,僅僅三天時(shí)間,此事就獲搞定;趙大寶與麻白鳳,從茲解除婚姻關(guān)系,大路朝天,各走半邊。這是云平區(qū)人民政府自宣告成立以來,強(qiáng)制性宣判的第一樁離婚案子。具體的判案情況是:該二人共同的兒子趙春山,判由男方撫養(yǎng),今后一切費(fèi)用亦由男方全力支付;趙家在小十字街的宅子,女方擁有四分之一享受權(quán);至于如何處理此房產(chǎn),全由女方?jīng)Q定,既可以長久地住下去,也可以請(qǐng)公證人對(duì)其享有的那一份房產(chǎn)估出一個(gè)公正價(jià),再由男方一次或作幾次付于女方。等等。
嗚呼!對(duì)于麻白鳳而言,這就是農(nóng)村人打比方說的“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了。她本想以兒子做賭注挽救婚姻,卻又被反作用的力道震懾得骨軟筋麻——她再能耐,能斗得過由小姑子趙小蘭夫婦出面催辦的人民法庭嗎?因此,她傷心得泣不成聲。然而,麻耀昌卻對(duì)之安慰道:算了。大雁南飛,河水東流;這一切的一切,都是既無情也無奈的憾事了。倒是你當(dāng)好好地想一想,從今以后,將要如何的過日子吧!
唉!桑花嘆道:這都是命,是命哇!
這時(shí),也只有在這時(shí),麻白鳳才打心眼里認(rèn)可她的親生母親桑花,并發(fā)自肺腑,大聲地喊了一聲:阿媽呀……就癱軟在桑花身上了。
從此以后,因?yàn)楦鞣矫娴脑颍榘坐P終于在心靈深處對(duì)自己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正視現(xiàn)實(shí),要咬緊牙關(guān),一步一步改變自己與生俱來與民眾格格不入的壞毛病。然而,在她心里,也孕育著一種恨,一種對(duì)于趙大寶的、刻骨銘心的恨。這種恨,惟有她死,才會(huì)在心中隱退。
趙大寶處理完與麻白鳳的離婚事宜,他十天的探親假眼看就滿,卻有一大難題橫擋在其眼前,這就是:如何處理兒子趙春山一事;如今,人民政府的民政助理員已將兒子判于他之名下,他已經(jīng)與對(duì)他十分陌生的兒子親近了兩天;可兒子才四歲,將其帶往新的工作崗位比較麻煩,兒子對(duì)他似乎也沒有感情,老父和繼母張劉氏倒是提出可以交由他們扶養(yǎng)幾年,只等到了適合讀書的年紀(jì),再做是否將其帶走的打算。可是,趙大寶卻覺得,一是父親與繼母年紀(jì)偏大,卻還要繼續(xù)為了生存而付出繁重的勞作,若再把孩子長期性交給他們太不應(yīng)當(dāng);二是又怕他離去以后,孩子因想念親娘而吵鬧著要回到麻白鳳身邊,按理說,兒子回麻白鳳身邊小住一久也是情理中的事情,可是就怕出現(xiàn)一去就難得返回趙家的麻煩事發(fā)生;三是父親如今的階級(jí)成分,已經(jīng)成為大多數(shù)貧下中農(nóng)不敢親近的政治理由,他嘴上不說,但其心靈深處未免有苦難言,如果再讓他們分出一份心來照管孩子,這無疑又有給其沉重之身心增加無形的壓力,況且長此以往的,孩子幼小的心靈深處,難免產(chǎn)生陰影。于心何忍哇?
當(dāng)然,他也想到,讓父親出面去找麻耀昌再轉(zhuǎn)麻白鳳商議,讓兒子趙春山繼續(xù)留在她之身邊,等過幾年孩子要上學(xué)再來帶走。可是,麻白鳳因?yàn)殡x婚一事沒能穩(wěn)住陣腳并且輸?shù)靡粩⊥康兀褪钩龅筱@潑婦慣用的殺手锏:她說繼續(xù)帶好孩子沒問題,但趙大寶須與她恢復(fù)夫妻關(guān)系,否則她絕不再撫養(yǎng)與呵護(hù)趙大寶的骨血;其實(shí)她心靈深處也曾想過,這只是下定決心搏回趙大寶的權(quán)宜之計(jì),若趙大寶真的不復(fù)婚而只身離開云平鎮(zhèn)而去,那么天長日久的,她也會(huì)照顧好親生兒子趙春山的。可是,這種想法她不樂意披露出來,更絕不能讓趙大寶知道;因?yàn)樗J(rèn)定這么一個(gè)死理:趙大寶若讓她疼痛下半生的日子,她發(fā)誓也要讓趙大寶疼痛下半生的歲月。況且,她還讓趙家昌帶著假話去報(bào)復(fù)趙大寶,說她時(shí)間不長就要嫁人的,身邊帶個(gè)孩子不方便。她此時(shí)做出了這么一個(gè)公開性的決定,實(shí)為三流婦人之所為,可以說,其言辭壓根兒沒在大腦中過濾,其生命歷程中孰是誰非的天平,又再一次向趙大寶那邊傾斜了一些,進(jìn)而也給今后的趙春山知其原委之后,心中留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
于是,就為了麻白鳳這一連串說出來經(jīng)不起歲月驗(yàn)證的話語,讓趙氏一家子以及不少的云平人絕對(duì)地當(dāng)真了,人家從此就覺得她心性特別刁鉆,更不待見她了。于是乎,她就落得個(gè)“假亦真時(shí)真亦假”的悲慘結(jié)局。這是后話。
面對(duì)當(dāng)時(shí)那種狀況,必須按時(shí)回歸阿米縣教育部門的趙大寶,他還是邁出了艱難的步子,一步一步離開云平鎮(zhèn)。他走之前,經(jīng)過再三權(quán)衡,還是答應(yīng)了親妹妹趙小蘭的主動(dòng)提議:走一步看一步,先把兒子趙春山交托趙小蘭夫婦或者趙家昌夫婦撫養(yǎng)。他認(rèn)為只有這樣,他才比較放心,心境平衡。此外,在他臨別前少不了要舉行的那次重要家宴上,少了老疤楊做成其人。在后來的幾十年歲月中,趙大寶與老疤楊的關(guān)系,無論怎樣的時(shí)移世事,但二人心中的芥蒂,始終沒有完全消除。為此,在2010年某月某天,被高薪聘到作者故鄉(xiāng)某學(xué)院,擔(dān)任英語教師的美國一年輕男子,聽了此作品中的這一片斷后,竟然十分納悶地提問:你們中國人,怎么如此看重血緣關(guān)系哇?筆者答曰:你去問上帝吧!
68
之后,上級(jí)考慮到趙小蘭夫婦在當(dāng)?shù)夭惶軌蚍攀止ぷ鞯膶?shí)情,就做出了將其調(diào)往他處的決定;兩個(gè)月后,當(dāng)趙小蘭夫婦接到將調(diào)至距離云平140余公里的阿達(dá)縣金平區(qū)政府工作之際,卻遇上趙家昌得了傷寒半個(gè)多月臥床不起的不堪實(shí)情,眼看老父親重病在身,家里生活舉步維艱,加之生怕趙春山也染上疾病,今后對(duì)哥哥趙大寶不好交待,所以趙小蘭在臨走之前,專門找了麻白鳳談心,大意是目前趙氏門宗情況特殊,希望麻白鳳通情達(dá)理,把親兒子趙春山接過去照管一段時(shí)間,以后的事情,相信時(shí)間不長,就會(huì)有一個(gè)大家都能接受之結(jié)果的;反正說來說去吶,也都是為了孩子能夠平安、健康地成長。趙小蘭又問麻白鳳:你看行嗎?
按說,這是個(gè)于情于理都不在話下的事情,可是自幼習(xí)慣了心高氣傲的麻白鳳其人,雖然心里也覺得趙小蘭的意愿說得過去,但一想到上次與趙大寶的較量上輸?shù)奶珣K,多少也與趙小蘭夫婦從中斡旋的作用分不開;現(xiàn)在趙家出現(xiàn)意外之事了,才想到要將孩子托付給她這個(gè)親娘呀?于是她就大口馬牙地罵道:趙大寶那雜種不是有能耐嗎,你們把孩子交給他帶呀;再說了,要不是當(dāng)初我爹把他連夜送走,他趙大寶的尸骨怕是早就被野狗拖走了——沒良心的東西;今天,你們兄妹倆是有能耐了,可你們父親的成分還沒我爹光彩吶——如今,我親爹好歹也是個(gè)開明鄉(xiāng)紳,是你們共產(chǎn)黨團(tuán)結(jié)的對(duì)象呢!所以嘛,這事你就別找我;或者,得你哥親自回來一趟,親口求我,我才樂意接收小春山,否則你趙家就看著辦得了。
其實(shí),麻白鳳雖然說出這一番話,心里也留了一點(diǎn)的余地;她想,一是趙小蘭聽了她這番大泄私憤的話,能夠向她道一個(gè)近似于放屁暖狗心的歉,或者過了半把天時(shí)間再去求她,她才比較有面子地將兒子接受下來。可是,這趙小蘭其人,一是年輕好勝且有著比較亮麗的身份,二是沒當(dāng)過母親不太懂得麻白鳳的心理情愫;所以她聽了麻白鳳這番夾槍帶棒的話,沒當(dāng)場指責(zé)昔日的嫂子太刁鉆就算不錯(cuò)了,怎么可能如了麻白鳳之愿、再來個(gè)進(jìn)一步的乞求她這位昔日的風(fēng)流嫂子呢?所以,她一咬牙,就做出了暫時(shí)性把親侄子帶走的決定。
不過,趙小蘭在臨走之前,還是聽了其夫張?zhí)鞆?qiáng)的建議,專門讓區(qū)政府里辦離婚的那位同志向麻耀昌轉(zhuǎn)話,并讓其轉(zhuǎn)告麻白鳳,說是眼目前的事情,一時(shí)半會(huì)兒的解決不了,她只好人走到哪,就把親侄兒帶到哪;但請(qǐng)麻白鳳放心,無論到了哪一天,麻白鳳都是趙春山的親娘,等孩子長大了,會(huì)讓他明白一切事理,以及讓他來找親娘的。那人向老麻轉(zhuǎn)這話時(shí),趙春山已被他的姑姑帶走大半天了。
之后有人說了,麻白鳳聽到親兒子趙春山被趙小蘭帶著遠(yuǎn)走他鄉(xiāng)的消息時(shí),她就“天吶”一聲,大大地哭了一場,繼而病倒臥床。
在麻白鳳氣憤病倒的日子里,由于桑花給予她無微不至的關(guān)懷與護(hù)理,所以該母女之間的關(guān)系,進(jìn)一步融合了。每當(dāng)見到麻白鳳對(duì)桑花喊出那一聲“媽”,老麻都深感桑花內(nèi)心涌起了無限感慨的巨浪,卻也欲言又止;終于在那一天,桑花親自照顧麻白鳳吃下一碗臥有雞蛋的面條,又卷起衣袖,準(zhǔn)備為麻白鳳洗衣服時(shí),麻白鳳終于被感動(dòng)得下了床,一是口里不但叫了一聲“媽”,而且請(qǐng)求桑花原諒她過去無知與任性行為。她說;從今以后,她要脫胎換骨,重新做人,一切事情,絕不由著性子來。于是,大半生歷經(jīng)世態(tài)炎涼,嘗盡人生苦果的桑花其人,就一時(shí)間感動(dòng)得熱淚滾流,她終于禁不住內(nèi)心之激動(dòng),一下子去到麻白鳳跟前,將麻白鳳攬進(jìn)懷里的同時(shí),喊出那一句不知憋了多少日子的話語:我的心頭肉哇!繼而,母女倆就淋漓盡致地哭將起來。她一邊哭又一邊說:別太傷心了,哭太多會(huì)傷身子骨的;再說了,這趙春山無論與誰生活在一起,他都永遠(yuǎn)是你的親生兒子,人家趙小蘭都說了,這也是為孩子的前途著想,希望他長大了能夠有出息;從今以后,咱娘倆就好好地陪著你爹(即老麻)吧,無論日子如何地艱難,只要我們都不再分開,也就知足了。
這個(gè)時(shí)候,親眼見此感人情景的老麻其人,就感同身受,連連點(diǎn)頭;他說鳳兒哇,你母親這話說的忒好吶。我是個(gè)快走完生命歷程的人了,幾十年來,可以說在財(cái)富上要風(fēng)得風(fēng),要雨得雨;然而仔細(xì)一想,還真的再一次得出“錢財(cái)乃身外之物”的結(jié)論。人生在世,假若沒有親情,即便每天睡在金山上,心里也是空蒙著、懵惑著呀。你吶,不要太在乎過去的日子,你只要不回首往事,不留戀過去,只把眼睛往前面看,你就會(huì)覺得:其實(shí),我們還是大有希望的。
老麻這話,在一段時(shí)間內(nèi),竟然成了桑花娘倆的內(nèi)驅(qū)力。
當(dāng)時(shí),老麻見桑花母女都對(duì)他講出高瞻遠(yuǎn)矚的言詞而感佩不已,就又如此安撫道:那么——從今以后,咱就換一種方式,把日子過下去吧。這人世間的事情吶,其實(shí)說白了,就是三十年河?xùn)|,三十年河西;該認(rèn)命時(shí),咱還得認(rèn)命。不過吶,不信你們等著瞧,最多半年,趙小蘭就會(huì)把咱們的小春山送回云平鎮(zhèn),交給她老爹培養(yǎng),那時(shí),我們要見這孩子還會(huì)難嗎?。
哦喲,為什么?麻白鳳和桑花都詫異地詢問。
為什么?天機(jī)能說破嗎?走著看就知道了。
(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