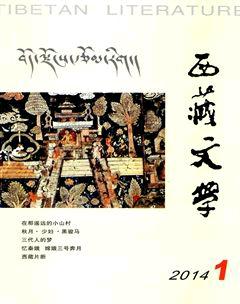三代人的夢(短篇小說)
德本加
1
大家都這樣說,如果沒和拉先離婚,她也不會招惹這么多是非,這叫咎由自取!如果不是一個沒腦子的家伙,誰還會娶她,她就是一輩子守寡也是活該!我來到這個崗位的時間不是很長,所以不是很理解這些話的意思。因此,我想這件事問才吉大姐她一定會給我一個很清楚的回答,但是才吉大姐現在在哪里呢。
才修是我唯一的酒友,所以我記得那天我倆好像是去喝酒的。一進那家逼仄的小飯館,才修盡可能地湊過來在我耳邊絮叨了幾句,用嘴巴往一邊指了指。左側的桌子旁一個古銅色皮膚的小伙子在吃飯,他的旁邊還有一個女孩。她不知是在假裝害羞還是怎么回事,吃了幾口之后面帶微笑地盯著小伙子的臉,還在低聲說著什么。小伙子一副毫不在乎的樣子,只是專心地吃飯,對女孩不加理睬。才修看著那情形,露出一絲微笑,使勁搖著頭。
我確實沒明白是怎么回事。當我聽說那個有著古銅色皮膚的小伙子是拉先時,我不由再次仔細地看他。他大概二十五歲的樣子,吃飯時不停地顫動著的那兩撇胡子我始終也忘不掉。他倆不是早就離婚了嗎?聽人說那次是她的錯。那今天他不會是又跟她在一起了吧?啊嘖嘖,她到底是誰呢?
2
1919年秋天下了一場大雪。有些人說從他們記事起就沒有下過這樣的大雪。
吃了晚飯,男人披著白氈衣到羊圈邊上睡覺去了。女人給自己鋪被褥時想起昨晚因為太擠把自己的腦袋都擠到枕頭邊上了就把枕頭給加長了。她又點了一盞酥油燈,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才覺得一天的活計到此結束了。但是她又往火塘撒了一把柏樹枝,向三寶祈禱一番后才鉆進被窩里希望能有一個好夢。說不清是不是到了午夜時分,夢里一個披著白氈衣的男人進來睡在了她的旁邊。他沒說一句話就鉆進了她的懷里。她的每一根感知的神經都在向她證明著那個人就是自己的丈夫。一種愉快的感覺傳遍了她的全身,她連眼睛都不愿意睜開了。
“昨晚那個人是誰?”第二天,男人有點不高興地問。
“誰?”
“那個穿著氈衣的。”
“誰不知道你的氈衣,肩膀上還有一塊補丁。”她以為他是在跟自己開玩笑。
“……”
男人出去放羊了,女人則開始懷疑起來。這時,她的心里不可抑止地生出了想扶養一個孩子的念頭。之前他倆沒有孩子。
雪的反光像月色一般把夜晚的景致給照亮了。矗立在后面的神山貢布拉格像平常一樣雄偉壯觀。午夜了,在雪的反光中他又悄悄地來了。雪很厚,“吱吱”的腳步聲不是很清楚。他還是披著白氈衣。他把白氈衣蓋在身上后就輕輕鉆進了她的懷里。是他!她覺得渾身舒服,不想說一句話。他倆沒有說話。她的手碰到了鍋。她隨手抓住氈衣的領子蓋在他的身上。夜晚寂靜依舊,雪地依然白晃晃一片。她睡著了,睡得很香很沉。睡夢中他倆在云里霧里歡愉,就像在天界一般。沒有了一絲人的習氣,沉浸在天界的幸福中。突然,一聲驚雷之后,他就無影無蹤了。這是個夢。那聲驚雷把她從睡夢中驚醒之后,她還在找他,但是他已無影無蹤了。
早晨,她燒好早茶,提著半勺子奶茶走出屋子朝著貢布拉格神山撒去時她驚訝地張大了嘴巴。貢布拉格神山的正前方印著一張黑黑的大手印。大手印的每一根指痕似乎在撫著山的兩側。啊嘖嘖,她想起了昨晚的夢。開始她的心里一陣恐慌,接著漸漸變成了一種敬仰。那天下午,幾個牧童首先發現了那個奇特的大手印,接著這個游牧村落就變得沸沸揚揚了。人們在挖空心思地議論紛紛。
“肯定是地震了,你看山崖都滑坡了。”小孩們說。
“不是,像是桑煙繚繞的樣子。”老人們說。
“怎么可能呢!保護神展開了雙手,要趕緊煨桑祈禱。”活佛和頭人們說。
就是讓無數個人支著耳朵聽上七七四十九天,她也沒向任何人說過有關那天晚上的任何事。那年夏天,她生了一個孩子,取名為格貢拉雅。
3
“她叫華措,二十二歲。”才修又談起了她。我也開始在他的話語間猜想她神秘的面容。
“她很漂亮。”
“漂亮?”
“是啊!”才修硬是喝完了一瓶啤酒,使勁搖著頭說,“確實很漂亮!我敢肯定你從沒見過那么漂亮的女人。但是她生不逢時啊!漂亮的女人們都有自己的使命,她們的無與倫比的美麗也是因為人類的某種需要而存在的。但是從古至今那些青春活潑的少女,尤其是那些美麗的女孩,她們的情感往往被權力和金錢所掌控,到最后她們自己也意識到沒有完成賦予自己的那個使命,便有了‘悲劇這個詞存在的意義了。你認為呢?”
“好像你也很牽掛她啊。”
“我不知道。不管怎樣,她和拉先離婚是個錯誤。問題在于他們之間出現了第三者。”
“誰是第三者?”我盯著他的臉看。
“我也不知道。從大伙兒的嘴里傳著各種各樣的話,但是這些話也未必可靠。以后總會水落石出的。”
“喝酒!”
拉先去某個大學進修了。據說他走時臉上的表情很正常。同事們把他的行李綁在車上,還像平常一樣開著各種玩笑。最后,他自己也抑止不住離別的傷感,和同事們一一握著手。等他上車時,他們才看見他的臉整個地紅了,眼里閃著一絲晶瑩的光。
拉先走了。他沒有任何留戀地在朋友們的關懷和祝福聲中走了。他走后的一個月里,這個小鎮里許多“新聞”像風一樣飄蕩著。這些“新聞”大概也是從這個小鎮邊緣的中學——拉先和華措當初結婚時的那間小小的屋子里傳出來的。從一個人的嘴里傳到另一個人的嘴里,傳著傳著人們就瞪大了眼睛,豎起了耳朵,到最后驚詫不已,甚至在突然間哈哈大笑了。但是我并不相信這些,雖然所有的人都是在根據自己的需要生活著,但生活畢竟還是很公平的。
“他倆之間相差二十五歲。”
“是因為金錢。”
“是啊,活佛也回去和自己的老婆辦離婚手續了。”
4
阿媽像往常一樣靠著鍋臺后面炕上疊起來的破皮襖坐著。她手里沒有念珠,嘴里也沒有發出念誦嘛呢的聲音,只是一個人想著什么。平常每當太陽升起或者太陽落山時,她都會往鍋臺邊上的那個扁平的鐵勺里撒上一把桑料,然后蠕動著嘴唇念起經來。
天快黑時,拉杰把羊群聚攏到帳篷前面就進來了。朦朧的火光下只有自己的影子在晃動著。拉杰站在屋中央像是在發呆又像是在想著什么。一會兒傳來了一聲嘆息,那聲音像是從很遙遠的地方傳來。
“阿媽—”拉杰突然跑向鍋臺的后面,“阿媽,你怎么了,你怎么了……阿媽……”
一會兒之后傳來了一聲很微軟的聲音:“我沒有煨桑,今晚你要煨桑。”
拉杰第一次拿起鍋臺邊上那個鐵勺,盛上火往上面撒了一把桑料。繚繞的桑煙一下子從帳篷的天窗飄向了天空。
“好孩子,你知道自己的父親是什么樣的嗎?”她顫抖著聲音嘆了一口氣說。
“阿媽,你怎么了?”
“……沒有,我沒事。今晚我給你講你阿爸的事情,你要聽好啊!”
在朦朧的火光下一個故事的講述開始了。
“……你父親名叫格貢拉尤,他是神山貢布拉尤的幻化之子。他在安多一帶幾乎家喻戶曉。你是格貢拉尤的兒子。你本該生來就和別人不一樣。你現在十六歲了,但是你整天和孩子們打架,把衣服弄的破破爛爛之后才回家,這怎么行啊!從今往后不許你再打架!虎父無犬子!你的阿爸死了已經十六年了!
“你阿爸活著時用活的山羊來祭祀,每年要祭祀好幾次。那是他必須要做的。因此,無論遇到什么事,貢布拉格都會親自來護佑他,解決所有的麻煩,這是真的。
“有一次你阿爸和我倆去農區買面,二十頭牦牛馱了四十個馱子,往回走了兩天的路程時有六頭牦牛爬在地上吐出舌頭不動了。那時天也快黑了,我倆就下了馬。你阿爸支起三塊石頭生火,我趕緊去提水燒茶,把路上的干糧都拿出來了。但是你阿爸不喝一口茶,他洗了手往火堆上撒了一把桑料,站了起來。啊嘖嘖,說不清是怎么回事,就像是發生了幻覺,不知從哪里冒出了一個騎著白馬穿著白衣的人,把那幾個牦牛抱起來立在地上之后就無影無蹤了。
“后來我倆就沒有任何麻煩地回到了家里。”
拉杰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著阿媽的嘴里看。他在羨慕自己傳說中的父親。他不相信自己是他的兒子。
5
活佛和華措結婚那天,我叫上才修去喝喜酒了。婚禮現場的布置跟內地差不多,掛滿了各種顏色的彩條,屋里屋外的墻上貼著大紅的“雙喜”。十多桌酒席排成了三行,每桌酒席邊上圍著七八個人。還有幾個坐小轎車過來的大人物。活佛也跟平常大不一樣,穿了一套筆挺的黑西服,還打著領帶,看上去似乎小了十多歲的樣子。他很恭敬地在招待那些大人物。
“他發福的體型和身高很不協調,像個矮子一樣。”才修在我的耳邊說了這些話,冷笑了一聲。
“閉嘴!咱倆不是來喝喜酒的嗎?”
“你看,除了幾個廚師,他們單位的年輕人一個也沒來。”
一會兒之后,才修又聳了聳肩膀看著我繼續說:“你知道活佛和拉先是什么關系嗎?”
“不知道。但是當拉先知道這些時,他倆一定會彼此怨恨的。換上你也不例外。”
“你錯了,拉先早就知道這事。”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大伙兒都這樣說。”
“我不相信。”
“拉先走時還去拜見了活佛。”
“為什么?”
“他帶了兩包茶和一條哈達去祈請活佛保佑呢。聽說那時他的眼圈也是紅的。”
“請活佛保佑什么?”
“聽說是為了進修的事。他請活佛……哦,她來了,你看看,她今天穿的多華麗啊。”
我也趕緊順著他的目光看。活佛和一個姑娘從后面的小門進來了。她是華措嗎?我不由地給了自己一個問號。她穿著一件新的水獺鑲邊的氆氌袍子,頭上戴著的禮帽上插著的兩朵紫黃色花使她增色不少,平靜的臉上掛著一絲迷人的微笑,那微笑里似乎暗藏著一種能把人的魂兒一下子勾過去的力量。她和活佛一起為客人們敬著酒,這時給我的一種新的感覺就是他倆應該是一對父女。
回到宿舍時才修有點醉了。他又說起了她:“她怎么樣?我說的沒有一點夸張吧?”
“那迷人的微笑使她增色不少。”
他一邊抽煙一邊使勁搖著頭:“有時候我也這樣想,那些美麗的女孩之所以美麗,就是因為有迷人的微笑的裝飾,如果世上缺少迷人的微笑,哪還有這么多美麗的女孩啊!”
“我也這樣認為。”因為他的醉我也附和道。
一會兒之后,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似地看著我說:“如果這個地球不是圓的,她也不可能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之中。這就是所謂的命運啊。”
“是啊,人的命運是很難說清楚的。”
6
1936年,一千多名馬匪到貢布神山一帶收苛捐雜稅,部落的百姓們慌慌張張地將牛羊丟棄在山溝里四處逃生去了。
天快黑時,格貢拉雅像平常一樣煨桑,滾滾的桑煙遮天蔽日。他備上馬鞍,背著那把老式的叉子槍,單槍匹馬地就上路了。來到一個山口,他下馬準備稍事休息時,一只喜鵲落在他前面的土塊上“嘎嘎嘎”地叫了三聲就飛走了。他趕緊騎上馬往下走時,啊嘖嘖,前方的山腳下一伙匪兵趕著馱著馱子的馬和騾子黑壓壓地沿著一條山道正向他的方向走來。他一邊祈禱貢布山神,一邊對著匪軍把叉子槍支在地上大聲地喝了一聲。那伙匪兵一時像是洪水被大壩攔住一樣躊躇不前。那個絡腮胡子的匪兵頭子藏在一塊大石頭后面嘶啞著嗓門喊道:“我們是馬司令派來守衛邊防的,你這個自不量力的家伙膽敢阻撓我們嗎?”
阿媽對拉杰講他的父親的時候這樣講過:“確實是貢布神山護佑了他。馬匪的子彈像雨點一樣落在他身上時,他的身上只是留下了一些灰色的印痕。這樣說你肯定不相信。但是他一個人堵住匪軍,七七四十九天沒讓一個匪兵沖出山口。最后,他的子彈全部打光了。”
從沒有子彈的那天下午起,他覺得匪兵一天比一天多起來了。那時,他為了讓匪軍上當,從他們的眼皮底下往咕如大森林的方向跑。匪軍也緊緊地追在了他的后面。
茂密的森林中人和馬很難穿行,他爬到山頂時東方的天邊已露出了魚肚白,才知道新的一天又開始了。他穿了沒多久的那身羔皮袍子被子彈打得千瘡百孔,零亂不堪。一解開腰帶滿懷的子彈就叮叮當當地撒落一地,他也不由地搖了搖頭。
他在那里藏了八天八夜也沒見匪軍有一點動靜心里就放松起來,最后竟沉沉地睡著了。不知過了多久,有一陣子他在睡夢中聽見了馬的嘶鳴聲。他一下子醒過來起身看時,看見自己的馬正豎起耳朵圍著他轉。他知道有敵人就往前走了幾步,沒想到前面竟是一個無底深淵。隨著一聲呼哨聲,五百余名匪兵從他的身后圍了上來。匪兵們看見他手里沒有武器,就壯著膽子到了他的跟前。
“哈哈哈,你有本事就飛上天吧!嘿嘿嘿,給我活捉這個家伙!”那個蓄著絡腮胡子的匪兵頭子捋了捋胡須發出刺耳的聲音大笑著。格貢拉雅像是一只毫無畏懼的老虎昂首站在峭壁上,使那些匪兵們不敢繼續靠近,像草人一樣顫抖著。那個匪兵頭子一時也呆在那里不動。
“哈哈哈,聽好了,我格貢拉雅傲立天地間無人匹敵,你們不要癡心妄想抓到我!看哪!”他一邊呼喚著貢布山神的名字,一邊像大鵬展翅一樣從峭壁上跳向了深淵。匪兵們站在原地驚訝得不知該如何是好,有些哆嗦著連手里的槍也掉在了地上。
匪兵們毫無辦法,最后只好打聽著去了他的部落。格貢拉雅到家里拿了兩褡褳子彈和一把鑲著銀子的槍又去打匪兵了。他和匪兵周旋著打了六年,上至阿沁雪山腳下,下至神山拉日宗嘎,到處都有匪兵的尸首。六年間他只回了三次家。
1947年,匪軍把他們全家和部落里五十個年輕人趕上了絞刑架,并到處放話如果格貢拉雅十五天之內不歸降就要殺了他們。
村邊的格貢神殿旁排列著五千余名荷槍實彈的匪兵。那個蓄著山羊胡子的匪兵頭子在絞刑架下帶著滿意的表情走來走去,偶爾看看腕上的手表。一碗茶的功夫,突然間一聲槍響,遠處卷起一陣黑旋風,隨之格貢拉雅騎著一匹馬沖來了。他沒帶任何武器。
“哈哈哈,我相信你會來。確實是條漢子。馬司令很賞識你啊!如果你能受降于馬司令,起碼也會給你一個師長的位子,這點我可以向你保證。你們藏族不是有句諺語叫‘一條好漢再猛也不算好漢嗎?啊?哈哈哈。”匪軍頭子使了一個眼色,格貢拉雅的家里人和五十個年輕人被松開綁趕到了一邊。匪軍頭子再次看著格貢拉雅微微地笑。
“哼哼,你沒聽說過我們藏族還有句諺語叫‘與其像狐貍一樣夾著尾巴逃跑,不如像猛虎一般帶著微笑死去嗎?”格貢拉雅從懷里掏出一把手槍對準了自己的腦袋。他的親人和年輕人都哭了起來。匪兵們驚恐萬狀地倒退著。整個村落的人大聲地呼喚著他的名字。
“啪—啪—啪—”
三聲槍響接連傳遍了廣闊草原,峽谷之間,山嶺之巔,云層之上,化成了人世間最最遼遠的一曲悲歌。連續十五天貢布神山的山體被一層灰蒙蒙的霧籠罩著,若隱若現……
7
商店門口幾個牧民盤腿而坐,一邊曬太陽一邊聊天。他們的話題是關于阿尼才吉的死。
“她是活佛妃子的繼母。”
“不是親生母親嗎?”
“不是。聽說她是撿來的,到現在也不知道親生父母是誰。那個老太婆真是個心地善良的人啊!”
那天我在街上再次看見了她。她抱著一個約莫兩歲的孩子和幾個老太婆一起往百貨商店的方向走著,跟以前相比變化真的很大。原先苗條的身材幾乎已經變形了,碩大的屁股像是牧民家里的皮囊;原先掛在臉上的迷人的微笑全然不見了,眼神中充滿了狡黠的光。這時,我的心里不由地生起一絲失望的感覺。
旁邊的幾個小伙子看著她輕蔑地說:“驕傲得什么似的,像頭母豬!”
“她抱著的小孩是前一個老婆生的,她還說是她的兒子!”
“活佛不是在賓館里也有一個相好嗎?聽說前天他倆吵起來了,那個外地來的生病的姑娘也站在了活佛一邊。其實那姑娘也沒什么病!”
我想再仔細看看時,她已經進了百貨商店,旁邊那幾個小伙子也不見了蹤影,真是兩頭都沒撈著啊。我只好兩手叉在胸前看著自己的腳尖回到屬于自己的小屋了。
沒過一星期活佛和華措離婚了。這幾天對我來說是“收獲”較多的幾天。一些人還像以前的我一樣操著半生不熟的漢語說著“不可能”。但是此刻的我卻有著不一樣的想法,用十分肯定的語氣對他們說:“世上的很多事就是在不可能中發生的,就跟我們心中的一些想法往往是靠著機緣巧合來實現沒有任何區別。”我四處打聽這件事的原委,想找個機會消除人們的好奇心。
引起這件事有兩個很重要的原因,如下:
A.活佛自從在外面有了一個相好之后,偶爾晚上也不回家,第二天臉色像蔫了的蘿卜一樣鉆進家里倒在沙發上一邊休息一邊說:“昨晚上面來了幾個很重要的客人就……”
B.她給曲藏活佛寫了那封信之后自己懶得上街就讓那個“病姑娘”去送。下午活佛回家坐在沙發上時,那個“病姑娘”笑瞇瞇地把信交給了他。
這事再往細里講就是這樣:
星期六晚上,學校團委舉辦了一場舞會。大概到了十二點,華措回家打開門時很吃驚。今晚他沒有出去,一個人靠在沙發上喝酒,差不多快喝了一斤了。
“回來了?”
他看見華措進屋,就一直用發紅的眼睛盯著她看,有點失落的樣子。她不在意地把旁邊的小凳子放在了一起。
“在我身邊你就那么痛苦嗎?”他含混不清地說了一句,不敢看她似地低下頭,用右手扶著額頭,“我看見你的信了。”
“什么?”
“寄給曲藏的那個。”
她很驚訝,一時不知如何是好,站起身走來走去,憤憤地說:“那你去賓館晚上也不回家是怎么回事?我一個人在家里受不了!你知道在外面在說什么嗎?我還要裝作沒有聽見那些閑話的樣子!沒想到你還偷看我的信!”
她哭了起來。
“這些就不要再提了,總之這事算是完了。如果你真不想呆在我身邊,或者在我身邊你受著那么大的委屈,咱倆可以離婚。”他硬是往嘴里灌了一口酒。
“這……這算是什么理由?”
“不是,我也不會讓你吃虧的。這個家里你想要什么……不是,這個家里一半的東西歸你。如果還有什么困難,我都會全力幫你的。”
聽說在離婚證上簽字時,她的臉上像以前一樣掛著迷人的微笑。
8
“打倒牛鬼蛇神!”
“千萬不要上階級敵人的當!”
“要將無產階級專政進行到底!”
晚上,村子中央的一個破院子里高喊革命口號的聲音像熊熊燃燒的火焰一般呼呼作響著。火堆邊上拉杰穿著一件油膩的皮袍,手里拿著一本紅皮的毛主席語錄,滾瓜爛熟地背了一則毛主席語錄,高喊“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其他人也跟著他喊,那叫喊聲布滿了村落的上空。
一會兒,從火堆里躥出了一片一片的火苗,人們一下子安靜下來了。
“披著豹皮的驢子,作惡多端的臃忠你聽好了,你為什么把這些‘牛鬼蛇神的器物給藏起來了?快說!你想欺騙誰?還吹噓自己懂害人的巫術嚇唬過哪些人?這些是不是你的罪過?快說!”拉杰用食指指著一個大胡子的老頭不停地問著。那個老頭彎著腰、低著頭,像是在認錯似地顫抖著,不敢看拉杰的臉,會場上的人們也不敢說話。
第二天晚上,幾個戴著紅袖章的人把雍忠老人的手從后面反綁起來,臉差點就挨到地上了。拉杰的鼻尖上閃過一絲奸笑說:“嘿嘿,你這個人民的敵人!現在你念咒啊!來咒死我啊!你的本事哪去了?”
老頭子依然不敢說什么。那些戴著紅袖章的猛地推了一把,他就像一棵根子腐爛了的老樹一樣倒在了地上,右手的袖口觸到火堆上散發出一陣焦味。
第三天晚上,拉杰像往常一樣穿著那件油膩的皮袍,拿著毛主席語錄,背了一小段,喊了幾聲“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今晚他似乎更加激情高漲,昂首挺胸地說:“月底要把每個村子的各類反動分子召集到公社學習班召開一次批斗大會!反革命分子臃忠也是這次批斗的對象!他在五八年披著僧侶的破袈裟和解放軍作對,現在又使用‘牛鬼蛇神的伎倆蒙騙人民群眾,這樣的罪魁禍首我們永遠也不能饒恕他!”
臃忠老人站不穩腳跟。
半夜時分,拉杰回到家時老婆生了一個女兒,他很高興。天剛亮,幾個紅衛兵慌慌張張地跑到了他家里。
“他死了!”
“在哪里?”
“在會場里吊死了,還在一塊白石頭下面壓著這張紙條。”說著把半張破破爛爛的磚茶的包裝紙遞給了他。那上面歪歪扭扭地寫著一些字和很多圖案,字面的意思大概如下:“你這樣一個不怕因果報應的家伙成為格貢拉雅的兒子實在很可悲!我咒你的后代掉進一條逆流的河里從此斷子絕孫!如果不這樣,就證明我確實無能!”后面還寫著個梵文。
9
我在屋里正在看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長篇小說《百年孤獨》。我被小說奇妙的藝術張力和豐富的想象力深深吸引,忘記了時間的存在。突然,“咣當”一聲門被打開了,才修急匆匆地沖進屋里說:“快快,有人跳河自殺了,快去看!”
“是誰?”
“誰知道呢,快走吧,大伙兒都走了!”
河流的拐彎處聚集了很多人。人們擁擠著把脖子伸向河邊發出各種疑問:“從哪里跳進去的?”“是哪里的人?”“是誰?”等等。這里的河面大約有二十多米寬,河水在這里緩緩地往左轉了個彎就逆轉方向從對面的斷崖邊上向前流去了。有一兩個人脫了外衣趟到河里左顧右盼地摸索著什么,但也不敢往河中心走,搖著頭回來了。周圍的人們只是干著急,沒什么法子。才修毫不猶豫地脫掉衣服準備跳進河里時,幾個老頭從后面抓住他罵道:“你想送死嗎?不知道這里的水有多急多深嗎?”才修似乎也感到害怕了,不知如何是好。
“聽說是個女的。”
“應該是華措,和活佛吵架后她往這個河邊跑了。”
“不是早就離了嗎?”
“是啊,但是分家時活佛沒給她那個沙發就吵起來了。”
“就為那個?”
“就為那么點東西?”
我不相信。我什么也不想說,也不想聽周圍的人們說著的那些話。這些年我耳聞目睹了很多像夢一樣的事情,我實在是感到厭倦了。
華措死了。人們都跑去看她的尸體時,只有我一個人低垂著頭留下來,毫無知覺。我緩緩抬頭放眼望去時,天地間空蕩蕩一片。這道狹長的河谷寂靜一片,這條寂靜的河流也緩緩地逆流著。這時,我的視野里模糊地浮現出了以前的一個故事,這個故事也漸漸融入到了蕩漾的河面上,讓我油然而生出一種困頓的感覺。最后剩下的竟是巍然屹立在前方的貢布拉格神山,不遠處湍急的逆流河,還有毫無知覺地站立著的我的影子了。
10
我和才修圍著一張桌子面對面地坐著時,中間肯定是少不了一瓶酒的。我倆之間的共同話題早就不存在了,因而這會兒也沒什么可聊的。但各自又想找點話題出來。
“拉先也一樣,幾乎一事無成。”
微微有點醉意的才修想起什么似地說了這句話。今天我的心情也不怎么好,拿起酒杯喝了一口。他側眼看了看我又說:“實在是很可笑,前天我去州上時看見他了。他和他老婆從大街上迎面向我走來了,他還裝作沒看見!”
“他的老婆是誰?”
“我倆在飯館里不是看到了嗎?就是她!確實是個傻女人。拉先在大學呆了兩年,再呆一年就畢業了,但是她沒讓他去。”
“為什么?”
“誰知道呢!說是不這樣就要離婚。拉先不忍心丟下剛滿一歲的女兒就答應了她。但是現在他倆很幸福。”
我不想再問什么了,靜靜地沉思。平常這樣的時候我什么也不想聽,那怕聽見外面有人說話也會很煩。我喜歡安靜。他像是知道了我的心思似地冷笑了一聲準備繼續喝酒時,酒瓶早已空了。
我倆出門時,夕陽的余暉照在周圍的大樓上,像是刷了一層紅土,鮮艷無比。剛剛結束播音的路口電線桿上的廣播喇叭里傳來了十一屆亞運會的會歌。歌聲淹沒了這個閉塞小鎮上的所有聲音。
“我們亞洲
山是高昂的頭
我們亞洲
河像熱血流
……”
(譯自《崗尖梅朵》)
責任編輯:邵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