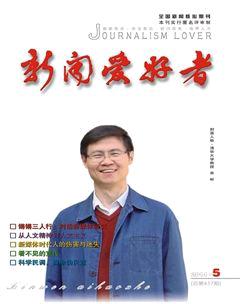庫利的傳播學研究及其思想價值
柯澤
【摘要】作為美國第一代最為重要的社會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庫利在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的博士論文不但研究了鐵路系統作為交通運輸手段對于美國社會產生的影響,同時也考察了鐵路在傳播信息、凝結美國精神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他的鏡中自我理論、首屬群體理論不但從社會學角度探討了人的社會化過程等問題,而且也探討了傳播在社會組織、社會過程、社會秩序以及共同體建設等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庫利的傳播學研究是對19世紀美國社會轉型的回應,他的傳播學思想包含著對民主的期盼。
【關鍵詞】《交通運輸理論》;鏡中自我;首屬群體;“大人生”;大共同體
一、庫利涉足傳播問題研究的職業和學術背景
漢諾·哈特在《傳播學批判研究》中對19世紀后期以來美國傳播學研究發生的背景作了比較恰當的評述,他說:“民主理論為美國的傳播理論和研究的歷史指引前進方向,技術對傳播性質的沖擊也指引著傳播理論和研究的歷史走向。美國的哲學思考和社會實踐專注社會進步的觀念,同時又對語言、符號和交流表現出濃厚的人文主義興趣和語文興趣;傳播學研究的歷史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的。”[1]
庫利是美國學院體制內最早對傳播問題進行認真研究的學者,學術界公認美國傳播學研究的思想源頭在芝加哥學派,庫利無疑是最早和最重要的源頭之一。
嚴格地說,庫利并非屬于芝加哥學派的成員,但是他的思想與芝加哥社會學派一脈相承,而且在許多方面,庫利的理論創造在先,影響更大。此外,芝加哥社會學派的重要人物杜威、米德等都出自密歇根大學,庫利在密歇根大學輔修社會學時還選過杜威的課,他們都是當時密歇根大學一個俱樂部(Samovar Club)的成員,這些因素使得人們把庫利也歸入芝加哥社會學學派中的人物。
施拉姆是較早開始研究庫利對于傳播學研究的貢獻的,他認為庫利的《社會組織》不僅僅是社會學著作,同時也是傳播學著作。施拉姆引用該書關于傳播的一些論述斷言:“先于傳播學四位先驅的一位學者是查爾斯·庫利,他在《社會組織》一書中寫下了許多關于傳播的論述,告訴我們他所研究的新領域與傳播之間的關系。”[2]
彼特·西蒙森在《重建傳播學歷史》一書中比較深入地研究了庫利對于傳播學研究的貢獻。他認為庫利是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第一個十年間美國傳播學研究的先驅人物,他說:“那個來自密歇根大學城的人是英語世界中第一個從現代大學職業專家的角度明確提出傳播概念的人。”[3]92
庫利涉足傳播問題研究與他自己的成長經歷和思想經歷密切相關。事實上,庫利自己也明確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在1897年的日記中寫道:“我的思想和寫作非常自然地與我的生活聯系在一起。”“我自童年就開始的日記是我思考的持續記錄,我業已完成的社會學研究和其他研究不過是在完善和印證我的日記。”[3]108簡言之,庫利早年在州際商業委員會和統計局的工作經歷最終使他將關注的目光投向傳播領域。
查爾斯·庫利家族來自新英格蘭,他的祖父托馬斯·庫利在1640年以前就來到馬薩諸塞州的斯普林菲爾德定居,后來前往紐約阿提卡的一個農莊。托馬斯·庫利生有15個孩子,因為貧寒,孩子們需要自己掙學費完成教育,其中第八個孩子托馬斯·麥金太爾·庫利后來成為庫利的父親。托馬斯·麥金太爾·庫利通過多年的奮斗在1859年的時候成為密歇根大學法學院的教師和首任系主任,1864年當選為州最高法院法官,任職長達20年。1887年他被美國時任總統格羅弗·克利夫蘭任命為州際商業委員會的首屆主席,直至1891年。1893年他當選為美國律師協會第16任主席,庫利在父親當選為州最高法院法官那年,即1864年出生。
庫利的青少年時期備受病痛折磨,所幸他出生在一個條件非常優越的家庭,這使他得以在長期疾病的折磨中完成學業。1880年他入讀密歇根大學,他選讀的課程包括四門語言、一些歷史課程以及一些機械工程等。他16歲入學,但是因為健康狀況不好,他在大學待了7年才畢業。大學期間為了治療和療養,他先后游歷了美國以及歐洲很多地方,于1887年畢業于機械工程專業。畢業后,庫利又回到密歇根大學繼續學了一年的工程學。在此期間,他開始閱讀斯賓塞的作品,并繼續攻讀政治經濟學專業研究生。他父親建議他多接觸社會,積累經驗。當時他父親已經被任命為州際商業委員會主席,居住在華盛頓特區,1889年3月,他父親給他寫了一封信。
親愛的庫利:
我的意見非常明確,并且已經決定。為了你自己好,你應該立即來到我這里待上6到12個月,你將在我這里學到很多東西,比你留在阿安伯(Ar bor)當一個教師所能夠學到的東西多6倍還不止。如果你來了以后覺得實際情況并非如此,你可以立即離開。如果你決定不來我這里,你將犯下大錯誤。
永遠愛你!
托馬斯·麥金太爾·庫利[3]99
作為州際商業委員會主席的托馬斯·麥金太爾·庫利對于技術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有十分敏銳的目光,他甚至認為當時聯邦政府的產生就是源于電報以及鐵路技術發明之后所形成的相互依賴。[4]15庫利顯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他父親觀點的影響。
1889年庫利來到華盛頓并在州際商業委員會和統計局工作,前后共兩年。在這兩年中,庫利利用自己在統計學方面的知識調查和研究了美國的交通運輸問題,這項調查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降低交通事故。他根據自己的調查寫了一篇論文《鐵路交通的社會影響》(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Street Railways),他借用斯賓塞的社會有機體概念,將城市交通系統看作社會的器官,承擔著自己的功能,但是他認為城市交通系統的功能絕不僅僅在于運輸貨物和人口,它還能提供更為廣泛的公共服務。1990年他在美國經濟學學會的一個會議上宣讀了這篇論文,哥倫比亞大學的兩位著名教授富蘭克林·吉丁斯和萊斯特·沃德也參加了這個在華盛頓召開的會議,他們對庫利極為欣賞,鼓勵他參與到社會學研究中。endprint
1892年庫利回到密歇根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博士,輔修統計學和社會學,他同時獲得兼職講師的教職。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他接觸到了德國學者阿爾伯特·沙佛爾的思想,沙佛爾是德國著名記者以及社會學家,他的著作《社會實體的結構和生活》在德國和美國擁有廣泛的讀者,他認為溝通社會實體各個部分的東西是傳播,傳播是連接社會的神經交流系統。在此期間庫利還選修了杜威主講的政治哲學課程,杜威認為語言是社會有機體的中樞系統,這一中樞系統之于社會正如神經系統之于生命體;新的傳播機制可以使社會中樞系統更有效地運行,如果知識能夠被報紙之類的“社會感覺器官”(social sensorium)以科學的方式組織并傳播,一個更加統一和智能化的社會將從中產生。這些觀點都深刻地影響了他對自己正在研究的鐵路交通系統的看法,并把傳播的觀點帶到自己對鐵路交通問題的研究中。1894年他以論文《交通運輸理論》(The Theory of Transporation)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①。1894年至1895年他在密歇根大學繼續保留兼職講師的教職,并于1899年成為助教,1904年成為副教授,1907年成為全職教授。
庫利1905年加入美國社會心理學學會,1918年當選為該會主席。但是身為美國社會心理學學會主席,他卻很少參加該會的活動。他一生過著恬靜而淡泊的學者生活,他一直小心地與政治保持著距離,即使是在他所在的密歇根大學,他也與那里的辦公室政治保持著必要的距離。1912年10月在圣路易斯舉辦的一次美國社會心理學學會上,當時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經濟學系主任、著名社會學家富蘭克林·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s)向庫利發出邀請,希望庫利到哥倫比亞大學出任教職,經過慎重考慮,庫利謝絕了這一邀請。那時的哥倫比亞大學是美國僅次于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學研究中心,而且當時報業大王普利策已經承諾捐助該校創辦新聞學院。如果庫利接受了這一邀請,他極有可能成為美國領先的傳播學經驗學派研究領袖。1928年后他的身體每況愈下,被診斷為癌癥,1929年5月7日去世。
二、庫利的傳播學思想
庫利一生都在密歇根大學學習并且從事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教學和研究,他的主要著作包括《人性與社會秩序》(1902年)、《社會組織》(1909年)和《社會過程》(1918年)。
事實上,庫利對傳播學研究的貢獻最早見于他的博士論文《交通運輸理論》,該論文的材料和觀點主要來源于1889年至1892年庫利在州際商業委員會和統計局工作時他對美國鐵路交通系統所做的調查和思考。1887年美國鐵路里程已經由1850年的9000英里發展到16萬英里,鐵路安全以及服務公共利益成為當時美國鐵路發展必須優先考慮的問題,庫利收集有關美國鐵路發展的數據,編制鐵路安全準則,他從斯賓塞的社會學觀點出發探討鐵路對城市發展的影響。庫利也說自己所做的研究與傳播問題非常密切,他說:“我的博士論文《交通運輸理論》試圖從社會有機體概念出發全面解釋鐵路的功能,但是,為了研究這一領域,我不得不考慮精神機制方面的內容,我必須把所有的語言、所有發射和記錄的手段都考慮進去,它們的功能其實類似于交通運輸,甚至它們與社會過程的關系更密切。我通過歷史和現實研究這兩類機制,直到我能夠生動逼真地認清它們的本質和社會意義。我從社會有機體這一角度來探討這一切,因此,傳播其實是我的首要訴求,這篇論文印證了我一直孜孜以求的社會有機體的觀點。”[3]103
庫利是從多維角度來考慮交通運輸問題的,他不僅僅關注交通運輸問題的物理層面,更關注這一問題的社會關系層面,包括交通運輸所提供的功能,通過交通運輸所形成的體制和機制以及文化。庫利認為,鐵路、電報、電話等交通通信技術的發明急劇縮短了物品和思想傳播所需的時間和空間,物品和觀念的傳播日益構成現代社會特殊的組成部分。在庫利的論文中暗含著這樣的思想,即傳播環境的變化必然會引起人的存在方式的變化;庫利注意到人類從言詞表達、姿態表達、交通運輸發展到印刷以及新興媒體發展所引起的人類進步這一事實,由此開辟了傳播學研究的新領域。實際上,庫利在《交通運輸理論》中已經開始把傳播視作歷史發展的中心。1894年庫利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彼特·西蒙森認為美國傳播學研究就誕生于這一年。
1894年以后庫利的研究日益從傳播的物質方面轉移到傳播的人類觀念領域,他的三部主要著作都寫于1894年之后。庫利明確說:“所謂社會不過是一些人的事件影響到另外一些人的事件,這些事件就是傳播,因此,傳播的歷史也就是歷史的基石。”[3]110庫利敏銳地意識到當時美國社會正在發生的巨變以及在這一巨變到來之時傳播可能起到的作用,他提出了所謂“大人生”(The Great Life)這一概念。在庫利看來,傳播媒介構成了整個社會器官的形式,它是思想的真正外表和可見形式;書寫使得歷史成為可能,印刷意味著民主,因為印刷為普通人帶來了知識;傳播速度的加快、傳播范圍的擴展,使人類有可能在更高層面上形成新的社會組織。[5]在1909年出版的《社會組織》中,庫利給傳播下了一個很寬泛的定義,他說:“所謂傳播就是人的關系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機制,就是一切心靈符號,加上在空間里傳達這些符號以及在時間里保存這些符號的手段。傳播手段包括面部表情、態度和姿態、聲調、語詞、文字、印刷術、鐵路、電報、電話以及其他一切最新的征服空間和時間的成就。”[6]
如前所述,人們普遍認為庫利的學術貢獻主要在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方面,但是庫利貢獻于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的地方其實也是他貢獻于傳播學的地方。庫利的三部主要著作《人性與社會秩序》、《社會組織》和《社會過程》表面上看都是在研究社會,但是在更深刻的意義上這三部著作都是在研究人和人際傳播。正如于海所言:“庫利深信,只有理解個人,即人性,才能有望把握社會,即社會秩序。”[7]但是,庫利眼中的人已經不再是麥獨孤筆下本能的人,也不是歐洲傳統社會中那種原子化的人。庫利說:“獨立的個人是在經驗中不存在的抽象物,同樣,脫離個人的社會也是如此;它既可能從個人方面考慮,也可以從社會即普遍的方面考慮;而且事實上,它永遠包含著個人和普遍兩方面。”庫利又說:“我們說社會是個有機體,這意味著它是一個通過互動而存在和發展的各種過程的復合體。整個社會是一個統一體,它的一個組成部分所發生的變化都要影響到所有其他的部分。它是一個龐大的互動組織。”[8]互動是傳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屬于人際傳播;庫利的邏輯是,社會的人由互動而產生,社會由互動的人組成,因此互動不但是人形成的重要機制,同時也是社會形成的重要機制。庫利不僅僅是在研究人和互動,他其實也是在研究傳播。endprint
庫利的社會互動思想顯然受到達爾文和斯賓塞思想的影響,在達爾文和斯賓塞看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從來不是孤立的,達爾文認為自然界充滿了物種之間的競爭,斯賓塞將人類社會看作社會有機體,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物種之間、人與人之間相互連接,彼此競爭,推動自然界和人類歷史的進化和發展,競爭是二者理論的核心,不同的是庫利把互動看作是個人以及社會形成和發展的核心機制。
鏡中自我和首屬群體是庫利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它們實際上是對個人以及社會形成機制的一種微觀研究,研究的邏輯出發點仍然是人際互動,即人際傳播。由于這一微觀領域的發現,庫利背棄了以麥獨孤為代表的歐洲心理學的研究方向,以麥獨孤為代表的歐洲心理學僅僅研究本能的個人,而否認社會心理的存在。庫利創造了一個以人的交往和互動為基礎的全新的社會學以及社會心理學,這是一個充滿了巨大想象的研究空間,但是它并非憑空而生。
庫利在首屬群體和鏡中自我中發現了民主,滿足了他對民主社會以及民主價值的信仰。庫利把社會現實歸結為人們彼此之間的想象,他堅信“人們彼此之間的想象是可靠的社會現實”。他通過研究首屬群體得出這樣的結論:以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和交流為基礎的溝通和交往是社會的發源地,生發于首屬群體的價值觀念和人際模式最終會擴展到社會,同時也形成社會。庫利堅信人類能夠進步乃是因為人類具有同情心,個人之間的互動必然會造就共同體、國家和世界,必然會造就民主社會。
更加重要的是,庫利在20世紀前后傾力研究互動理論也是對現實的回應,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對美國未來社會發展的隱憂,我們要正確評價庫利對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以及傳播學的思想貢獻,就必須回到當時美國的現實中。
庫利所處的時代正是美國社會從傳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時代,伴隨著大都會的形成,交通網絡日益發達,人員的流動日益頻繁,人們的交往方式、謀生方式以及生存方式急劇變化,這樣的轉型對于美國社會意味著什么?對此,詹姆斯·凱瑞以非常形象的語調評述道:“19世紀90年代似乎是這樣一個關口,人們突然脫離過去,脫離了他們魂魄所系的生活老路,他們急于創造,卻不知方向所在,也不知道前路如何。”[9]詹姆斯·凱瑞認為庫利正是在這一關鍵時刻創立了自己的社會學理論以及傳播學思想。庫利的社會學和傳播學研究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當一個建立在家庭、鄰里、村落、小型社區基礎上的傳統社會及其組織正在被一個建立在市場規則基礎上的大型都市化和工業化社會所取代的時候,社會將以怎樣的方式組織,社會秩序將以怎樣的方式構成,庫利試圖從技術的進步、交通通信方式的改變以及傳播的發展中去尋求問題的答案。
三、庫利傳播思想中的民主期盼
庫利對民主抱有堅定的信念,對美國社會借助于傳播實現真正的民主抱有堅定的信心,他對傳播問題的研究始終沒有脫離如何實現民主的基本視角。柯林斯評價說,庫利的社會學思想包含著相互關聯的四個維度,他的方法是有機體式的,他的觀點是進化論式的,他對前景的展望是道德式的和進步式的,他的理想是民主的。[10]這樣的評價同樣適合庫利的傳播思想。
實現民主的先決條件之一是公眾在精神上的聯合以及自覺參與到公共政治生活之中。美國思想傳統的根基是個人主義,這種個人主義主要源于洛克等歐洲啟蒙思想家的自然權利學說。由于追求絕對的個人自由和權利,加之美國歷史上社會組織管理的松散性特點,美國社會原子化的特征十分明顯,美國人被認為特別不適合結成公共社區以及精神共同體。作為社會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的庫利敏銳地洞見到美國社會的原子化傾向對美國未來民主發展的威脅,他創立鏡中自我和首屬群體理論是要表明一個事實:自我的形成離不開他人,離不開與社會的互動;社會生活是一個活生生的有機體,個人與社會的協調發展是實現社會和諧發展以及實現社會民主的必由之路。庫利說:“自我與社會是共生的,有關自我與社會相互分離,自我與社會相互獨立的概念是一種幻覺。”[11]他的首屬群體和次級群體理論是鏡中自我理論在具體社會關系之中的放大版和升級版,庫利正是通過這一后來的理論版本在具體的家庭環境、社區關系中研究了人與人之間如何互相影響,自我人格如何在具體的社會關系中相互生成。庫利正是通過自己對日常生活的細致觀察和分析發現了一個不可知的世界,創立了真正美國本土化的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理論,并發現了一個前人未曾注意到的傳播問題領域,同時也讓人們從中看到了民主的希望。
庫利一再聲稱,人們之間的想象是可靠的社會現實,此舉遭到了許多研究者的誤解甚至批評。庫利的學說被許多人說成是超驗論,彼德斯干脆說庫利是一位唯心主義者,他不無譏笑地說庫利的學說是一種企圖使思想完全脫離肉體的學說,“庫利拒絕斯賓塞和赫胥黎的唯物主義,他把社會化為一個布滿哈哈鏡的大廳,或者把社會化為一個沒有肉體流動的符號場所”[12]。然而,這一切指責并非公正,庫利所言人們之間的想象并非脫離現實的想象,這些想象乃是他人和社會加諸每個個體身上的事實,這一事實在庫利那里被表述為“鏡中自我”,在米德那里被表述為“主我”和“賓我”,在弗洛伊德那里被表述為“自我”“本我”和“超我”,所有這些理論的邏輯起點都是把人置于具體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環境之中,去研究人格的形成以及人的社會化過程,去研究這些人格特征是否能夠滿足民主社會的需要。庫利與19世紀后期美國社會成長起來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他在哲學上信奉的是實用主義,他拒絕承認絕對真理和絕對理性,拒絕承認各種先驗的人性假設,他認為人性只能存在于具體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環境之中,偏離這一基本邏輯社會的理論才是超驗論和唯心主義理論。
庫利所處的時代是一個美國社會大轉型的時代,這些轉型包括: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由民主草創期向民主完善期的轉變;由車載馬馱的原始運輸通信時代向以火車、機械、電報、電子技術支持的現代運輸通信時代的轉變。在這樣一個時代,美國社會面臨的緊迫問題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的密切合作,社會行為的協調規范,美國人精神生活的重組和重建,精神共同體的培育更成為一項緊迫任務。對于這一大背景的性質以及與美國傳播研究起源之間的關系,詹姆斯·凱瑞的觀點極富啟發意義。凱瑞認為美國是一個缺乏共享精神文化遺產的國家,尤其是在西部邊疆地區情況更是如此;新的社會秩序不可能通過繼承或在不經意間獲得,它們只能通過眾人的努力,苦心經營,創造一種共同文化,并付諸社會體制而建立起來。這樣的共享情感、共享文化和共享社區可以通過討論、辯論、協商、傳播來組織和實現,至少在19世紀的美國傳播是社區創建和維系的活躍力量。凱瑞認為,在這樣一個時代沒有個人的位置,自由并不是一種解除個人羈絆,從而讓人獨處的消極東西;一句話,自由首先要求獲得公民以及公民生活之類的體制化的東西,它同時還要求獲得更精致的文化創造物,如行為模式、演講風格、演說模式、社會控制方式以及投票選舉等。杜威也很好地闡明了這一觀點,他說:“社會不僅僅由于傳遞、傳播而存在;從根本上來說,社會存在于傳遞和傳播之中。”[13]endprint
庫利的傳播研究以及他對傳播與民主關系問題的思考發生在這樣一個更大的背景之中。庫利對傳播問題的探討沒有止于鏡中自我、首屬群體這些最基本的社會關系領域,他還將這種探討延伸到“大人生”(The Great Life)、“大社會”(The Great Society)、“大共同體”(The Great Community)這類主題之中。在庫利看來,“大人生”是指包括道德、倫理、信仰、文化、價值等在內的精神存在,它對于作為生活方式的民主必不可少。就像他看待社會和個人一樣,他也將“大人生”視為一個過程,它貫穿于人的出生、成長、死亡整個過程之中;音樂、詩歌、書籍、閱讀、思考、寫作等都是“大人生”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它們滲透到“大人生”中。庫利是一個進步主義者,但是他認為進步是不確定的,進步只是一個過程,進步的獲得要靠每一個人的努力,對于“大人生”的追求正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對于“大人生”的追求旨在實現社會認同,最終,“共同體、國家以及人的聯合體統統融入到這一大人生之中”[14]。庫利認為傳播在“大人生”以及“大共同體”的創建過程中無所不包、無所不在,正是借助于傳播人們才可能結成社會關系和精神共同體。
庫利的“大人生”其實是19世紀美國進步主義知識分子廣泛信奉的“大共同體”概念的另一種表述。“大共同體”(The Great Community)概念最早源自19世紀英國社會學家沃拉斯,他用這一概念指稱那些在規模和復雜性等方面遠超過傳統社會的都市化社會。對于歷史進化過程中所出現的更大、更復雜社會現象的關注貫穿于歐洲知識分子的思考傳統之中。例如斯賓塞有關尚武社會與工業社會的比較,滕尼斯關于共同體與社會的思考,凱爾迪姆關于機械化社會與有機體社會的思考,西默爾關于小鎮與大都市的比較。在這些比較中,前者往往代表著其社會穩定性建立在成員和思想相似基礎上的小單位,如家庭、鄉村、部落等等。后者則代表著其成員和思想相似較少的大型單位,如城市、大都市等。在這些大型單位中,工業化力量已經開始出現。[4]17-18
19世紀美國進步主義知識分子在一定程度上繼承和借鑒了這一思想傳播,他們也用“大社會”“大共同體”之類的概念來觀察和研究一個正在轉型期間的美國社會。匡特(Quandt)在《從小鎮到共同體》一書中列舉了九位這樣具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他們是鼓吹進步主義改革的記者和演說家威廉·愛倫·懷特(William Allen White),都市改革家和作家弗雷德·豪(Fredric Howe),赫爾會所(Hull House)的創辦者簡·亞當斯(Jane Addams),政治理論家以及波士頓市政改革家瑪麗·帕克·福雷特(Mary Parker Follett),哲學家杜威(John Dewe),哲學家羅伊斯(Josiah Royce),美國現代社會之父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羅伯特·帕克(Robert Park),庫利也名列其中。這些進步知識分子不僅僅是美國社會大轉型的觀察者和研究者,他們本身也經歷和見證了這一大轉型。他們的共同點在于:他們都出身于美國的小城鎮,最終來到大城市謀求職業發展;他們寄希望于一個大共同體的出現,這個大共同體實際上就是傳統社會崩潰之后美國人共同生活的一個新的精神家園;他們都在思考美國未來的民主如何更好地生存于這個新的共同體的精神家園之中;通過對共同體的思考,這些進步主義知識分子不約而同地發現了傳播。他們相信美國未來民主生存的重要條件之一是一個新共同體的出現,傳播技術的發展是促成新共同體出現的重要手段。杜威認為新的傳播技術帶來了社會革命,“那些地方社區毫無例外地發現他們的事務已經被那些遙遠的、隱形的組織所決定,后者的影響范圍如此廣大,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一個新的人類關系時代已經到來”。他聲稱:“由蒸汽機和電氣化創造的‘大社會可能是一個社會,但是它不是共同體;那個建立在新的人際關系和人類行為模式基礎上的共同體是現代生活中的一個突出事實。”[15]
對于技術與共同體之間的關系、共同體與傳播之間的關系,匡特的總結非常精辟,他認為杜威和庫利那個時代的進步主義知識分子都相信連接社會的共享價值源于態度和思想的自由表達、自由交換;傳播的力量能夠將人們的精神協作轉換成為建立在身份認同和價值共享基礎上的共同體;傳播技術的發展可以造就這樣的共同體。[4]23從這一點來看,杜威和庫利等人先于英尼斯以及麥克盧漢,開啟了傳播技術主義的思想源頭。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階段性成果,批準號:13FXW001)
注 釋:
①根據Glenn Jacobs的說法,庫利在1890年美國經濟學學會舉辦的學術會議上認識了吉丁斯和沃德,此后與他們保持了幾年通信,1894年庫利就吉丁斯為他草擬的博士論題進行了答辯并獲得博士學位。見Glenn Jacobs:Charles Horton Cooley:Imagining Social Reality,University of Massacbusetts Press,Amherst and Boston,2006,p.8-10。但是這一說法似乎不成立,因為庫利顯然是在密歇根大學獲得的經濟學博士學位,但是1894年吉丁斯和沃德都就職于哥倫比亞大學。
參考文獻:
[1]漢諾·哈特.傳播學批判研究:美國的傳播、歷史和理論[M].何道寬,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27。
[2]Wilbur Schramm: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A Personal Memoir,Edited By Steven H.Chaffe and Everett M.Rogers,Thousand Oaks/London/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Inc,1997.
[3]Peter Simonson:Refiguring Mass Communication:A Histor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Urbana,Chicago,and Springfield,201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