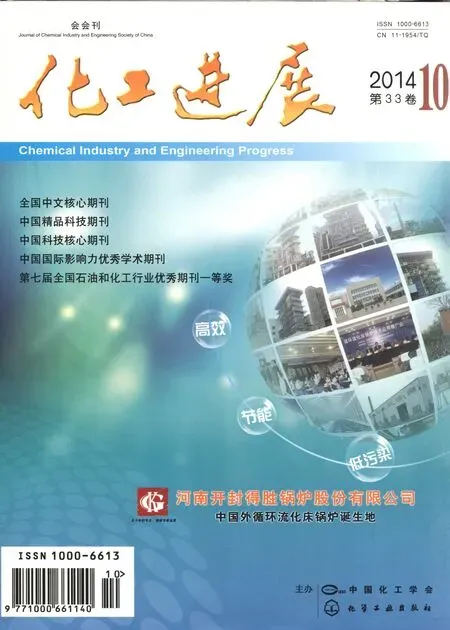吸附法脫除柴油中噻吩類含硫化合物的研究進展
王廣建,仙保震,劉影,付信濤,張路平
(青島科技大學化工學院,山東 青島 266042)
吸附法脫除柴油中噻吩類含硫化合物的研究進展
王廣建,仙保震,劉影,付信濤,張路平
(青島科技大學化工學院,山東 青島 266042)
綜述了吸附法脫除柴油中噻吩類含硫化合物的常用吸附劑、吸附脫硫的機理及吸附脫硫過程動力學研究的最新進展。闡述了近來研究較多的吸附劑主要有分子篩、活性炭和金屬有機骨架(MOFs)材料。目前傳統的加氫脫硫(HDS)技術雖然可以滿足當前柴油中硫含量的國家標準,但是其需要高溫高壓、成本高且對二苯并噻吩類硫化物脫硫率低,而吸附脫硫技術由于成本低、操作條件溫和、易脫除加氫脫硫難以脫除的硫化物、對油品品質影響小等優點成為當前柴油脫硫的研究熱點。吸附脫硫主要包括反應型吸附脫硫和非反應型吸附脫硫,反應吸附脫硫關鍵是有舊鍵的斷裂與新鍵的生成,而非反應吸附脫硫則是通過分散力使硫化物上的硫原子與吸附劑之間相互作用,從而達到吸附脫硫的作用。本文對吸附脫硫機理和吸附脫硫過程的動力學加以討論,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論基礎,并提出了脫硫吸附劑今后的研究方向。
分子篩;活性炭;脫硫;吸附劑;動力學
隨著國際燃油標準的提高,生產超低硫含量的柴油已成為當今發展的必然趨勢。柴油中的硫化物燃燒生成的SOx是汽車尾氣主要污染物之一。SOx既是形成酸雨的原因,也對NOx和顆粒物的產生有促進作用,還會造成催化劑的中毒使其催化活性降低[1]。此外,柴油中硫化物燃燒會導致空氣中顆粒污染物含量的增加,從而導致城市環境的嚴重污染[2]。因此,為了獲得低硫含量的柴油,研究者對柴油深度、超深度脫硫技術進行了大量的研究,開發新的脫硫技術已成為清潔柴油燃料生產的關鍵技術。
燃油質量提升的主要指標是硫含量的下降。對于柴油的硫含量,歐盟在2009年就開始使用硫含量低于10μg/g的燃油,美國和日本等其他發達國家也制定了相對嚴格的低硫標準[3]。為了與國際接軌,中國煉油廠必須降低原油中的硫含量以提煉出符合國家硫含量標準的柴油。根據國家最新燃油硫含量標準,中國汽柴油質量有望在2016年達到歐Ⅴ標準[4]。
柴油中的硫化物包括有機硫和無機硫。無機硫(元素硫、硫化物等)的含量較低,相對容易脫除;有機硫主要包括硫醇、硫醚、噻吩、苯并噻吩(BT)、二苯并噻吩(DBT)及其烷基衍生物,其中噻吩類含硫化合物占柴油總硫的80%以上,苯并噻吩和二苯并噻吩又占噻吩類的70%以上,因此柴油脫硫的關鍵在于如何有效地脫除噻吩類含硫化合物,尤其是對4,6-二甲基苯并噻吩(4,6-DMDBT)的脫除[5-6]。
加氫脫硫(HDS)技術是目前最為成熟的清潔油品生產技術,但存在一次性投資大、運行成本高和耗氫量大等缺點。此外,為了達到更低含硫標準的要求,必將需要高壓、高溫以及活性更高的催化劑,這必然導致油品成本大幅上升。此外,傳統的加氫脫硫技術對DBT及其衍生物脫除效果差,且十六烷值損失大。鑒于加氫脫硫方法存在的不足,人們又開發了許多非加氫脫硫技術,包括萃取脫硫、氧化脫硫、吸附脫硫、生物脫硫技術等。與傳統的加氫脫硫相比,吸附脫硫是近年來研究較多的脫硫方法,它具有操作條件溫和、十六烷值損失較小、成本低等優點,具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及應用潛力,因而成為當前柴油脫硫的研究熱點。此外,吸附劑尤其是活性炭的來源廣泛、價格低廉、比表面積大、吸附性能優異,因此,采用吸附法脫硫實現柴油深度脫硫甚至超深度脫硫是一項很有前景的技術。
1 吸附脫硫的機理
吸附脫硫主要是通過吸附劑上負載的金屬原子或表面氫原子與硫化物的硫原子或π軌道孤對電子成鍵,或者是吸附劑通過特定尺寸的孔道選擇性的吸附小于孔徑的硫化物,從而實現柴油中硫化物的脫除。常見的吸附劑包括負載過渡金屬的活性炭、分子篩及活性氧化鋁、MOFs材料等[7]。
根據硫化物與吸附劑的作用方式與機理,可將吸附脫硫分為反應型吸附脫硫和非反應型吸附脫硫兩類。反應型吸附脫硫通過吸附劑與有機硫之間的化學反應,把有機硫中的硫轉化為硫化物,固定在吸附劑上,從而達到脫硫目的。這種吸附劑的再生一般通過甲苯等溶劑洗滌[8]或需要通過氧化或還原反應來實現,將硫化物轉變為H2S、S或SOx。非反應型吸附脫硫則將含硫化合物吸附在吸附劑的表面或內部,吸附劑可通過脫附劑清洗或吹掃進行再生。本文從這兩方面綜述了吸附脫硫的研究進展。
1.1 反應型吸附脫硫
反應型吸附脫硫是吸附劑的活性組分(一般是過渡金屬或其氧化物)與含硫化合物中的硫原子發生反應,在強烈的吸附作用下,C—S鍵斷裂生成了金屬硫化物,烴類返回最終產物,其核心就是有化學鍵的斷裂或生成[9]。
菲利普斯石油公司(Conoco Phillips)成功研制出柴油吸附脫硫S-Zorb diesel技術[5,10],反應機理如圖1。
吸附劑吸附含硫化合物后,首先補充少量的H2,飽和噻吩上的不飽和化學鍵,降低噻吩上C—S鍵的鍵能,然后依靠吸附劑上活性位與硫原子之間強烈的相互作用,把硫原子從含硫化合物中分離并吸附到吸附劑上,形成一種新的結合物種,并釋放出剩余的烴類,從而脫除燃油中的硫。而廢吸附劑的再生則可以在再生器中燃燒,然后用H2還原即可[11]。
1.1.1 M—S鍵直接吸附
直接M—S吸附脫硫是指吸附劑上負載的金屬元素直接與噻吩類化合物上的硫原子成鍵,這種直接的成鍵方式相對于π配合吸附方式具有更高的選擇性。

圖1 S-Zorb柴油吸附脫硫機理
一般認為鎳基吸附劑對硫化物的吸附是通過直接吸附脫除的,在鎳基吸附劑上,鎳原子與硫化物上的硫原子直接作用在選擇性吸附脫硫中起著重要作用,且鎳基催化劑的吸附性能通常隨著溫度的升高而增加[2]。Seredych等[12]的研究結果也證明了S—Ni作用生成了鎳的硫化物,主要是NiS。但鎳基吸附劑對苯并噻吩的烷基衍生物,尤其對4,6-二甲基苯并噻吩(4,6-DMDBT)的脫除效果并不好,這可能是由于烷基的空間位阻作用,阻止了硫化物上的硫原子與表面鎳原子的接觸。S-Ni可能的作用機理如圖2所示[9]。

圖2 還原態Ni與噻吩反應吸附脫硫的可能機理
Kim等[2]以Ni/SiO2-Al2O3為吸附劑考察了對DBT和4,6-DMDBT的選擇性,結果發現該吸附劑對DBT的選擇性大于對4,6-DMDBT的選擇性,這也證明了在鎳基吸附劑上烷基的空間位阻影響了對4,6-DMDBT的選擇性。另外,在Ni/SiO2-Al2O3上,Kim等經計算發現70%已吸附的4,6-DMDBT分子被DBT分子取代,表明4,6-DMDBT分子在Ni/SiO2-Al2O3上的吸附是可逆的,4,6-DMDBT上的4-和6-位上甲基的空間位阻作用使得DBT具有相對較高的吸附勢。
Tian等[13]進行了Ce-Y吸附劑吸附噻吩的研究,并通過FTIR表征證明了M—S的吸附模式,研究結果也表明M—S吸附對于芳烴等競爭因素存在的條件下具有良好的選擇吸附脫硫性能。Li等[14]也通過實驗證明噻吩與Ce-Y吸附劑是M—S成鍵方式。
以上兩個小組的研究說明了M—S吸附進行吸附脫硫時,易受到噻吩類含硫化合物的空間位阻的影響,而且,噻吩類含硫化合物的支鏈越多,利用M—S作用越難脫除。但是,由于M—S作用是金屬元素與噻吩類含硫化合物中的硫原子直接成鍵,因而不宜受到其他非含硫化合物的影響,可以達到較高的脫硫效果。
噻吩類含硫化合物在鎳基吸附劑上可能存在兩種吸附構型:end-on adsorption、the side-on adsorption。在end-on adsorption垂直吸附構型中,噻吩類含硫化合物上的硫原子通過η1-S或S-μ3幾何構型直接與表面鎳原子作用,靠近硫原子的烷基取代基就抑制了活性位對硫化物的吸附。在side-on adsorption平面吸附構型中,整個硫化物分子以平面形式吸附于吸附劑的表面,這是由于芳烴環上的π電子起了主要作用。已知的噻吩-金屬配合物的幾何構型如圖3所示。
1.1.2 酸堿吸附
酸堿吸附主要是依賴改性后的活性炭、活性氧化鋁等載體表面大量的含氧酸性基團,與堿性的噻吩類含硫化合物作用來實現柴油中硫化物的脫除。
現已研究表明活性炭表面含有大量不同的酸性基團,包括羧基(COOH—)、內酯基、羥基(OH—)、酚羥基、羰基等,這些基團的存在有利于對噻吩類含硫化合物的脫除,尤其是對含有烷基的噻吩類含硫化合物,烷基對芳烴環來說是電子給予體,導致了芳烴環電子密度的增加,堿性增強,所以對噻吩類含硫化合物的吸附量也隨之增加。Kim等[2]研究了酸性氧化鋁對噻吩類含硫化合物的吸附,發現烷基是否存在對吸附量影響很小,實驗數據也證明了這一點,它對苯并噻吩和4,6-二甲基苯并噻吩的吸附量差別不大,其飽和吸附容量分別為0.040 mmol/g和0.038mmol/g, 因此認為酸性氧化鋁對硫化物的吸附主要是靠分子靜電勢和酸堿作用來實現的。
莫同鵬等[15]研究了不同的酸中心對噻吩類含硫化合物的選擇性脫除,柴油中的噻吩類含硫化合物屬于Lewis堿,其含有孤對電子,因而易于在Lewis酸中心吸附。研究發現,含硫化合物側鏈越多越容易脫除,這是因為甲基、乙基等側鏈的存在增加了噻吩類含硫化合物的電子云密度,其堿性也隨之增強,所以含有烷基側鏈的噻吩類含硫化合物的堿性比噻吩的堿性更強,因而更容易被含有L酸的吸附劑脫除[16]。

圖3 已知的噻吩-金屬配合物的幾何構型
余謨鑫等[17]研究了活性炭表面負載不同的金屬離子對二苯并噻吩吸附性能,并應用軟硬酸堿理論解釋了其吸附能力差異的原因。研究表明在活性炭表面負載Ag+、Ni2+、Cu2+、Zn2+可以提高對二苯并噻吩的吸附,這是由于在活性炭表面產生了新的活性位;而負載Fe3+反而降低了對二苯并噻吩的吸附,這說明不同金屬離子對活性炭的改性能力是不同的,改性后的活性炭對二苯并噻吩的吸附容量順序:Ag(Ⅰ) /AC>Zn(Ⅱ) /AC>Cu(Ⅱ) /AC >Ni(Ⅱ) /AC >AC >Fe(Ⅲ) /AC。軟硬酸堿理論的基本原理是:在軟硬酸堿理論中,酸、堿被分別歸為“硬”、“軟”兩種。“硬”是指那些具有較高電荷密度、較小半徑的粒子(離子、原子、分子),即電荷密度與粒子半徑的比值較大。“軟”是指那些具有較低電荷密度和較大半徑的粒子。“硬”粒子的極化性較低,但極性較大;“軟”粒子的極化性較高,但極性較小。此理論的中心主旨是,在所有其他因素相同時,“軟”的酸與“軟”的堿反應較快速,形成較強鍵結;而“硬”的酸與“硬”的堿反應較快速,形成較強鍵結。由軟硬酸堿理論可知,二苯并噻吩屬于軟堿,利用軟硬酸堿理論的“軟親軟,硬親硬,軟硬搭配不穩定”的原則可知,負載軟酸金屬離子能提高對二苯并噻吩的吸附能力。Ag+屬于軟酸,通過負載Ag+,增加了活性炭表面的軟酸,從而增強了對二苯并噻吩的吸附能力; Ni2+、Cu2+、Zn2+屬于交界酸,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對二苯并噻吩的吸附;而Fe3+屬于硬酸,局部硬酸的增加降低了吸附劑對二苯并噻吩的吸附。
以上各小組的研究都證明,活性炭表面酸量的增加有利于硫化物的脫除,而通過對活性炭的表面改性能增加其酸性基團的含量。余謨鑫小組的研究表明,當活性炭表面負載的金屬離子屬于軟酸時,對于噻吩類含硫化合物的脫除效果較好,因此,提高活性炭表面的含氧官能團含量有助于噻吩類含硫化合物的脫除。
1.1.3 耦合吸附
耦合吸附是指在吸附劑上同時負載M—S作用和π配合作用的金屬。若在一種吸附劑上可以同時具有π配合作用與M—S成鍵各自的優點,則可以達到更好的吸附脫除噻吩類含硫化合物的目的。
Wang等[18]通過離子交換的方法制備了Ni-Y、 Ce-Y、Ni/Ce-Y三種吸附劑,并將其用于模型油中二苯并噻吩的脫除實驗。實驗結果表明,負載有兩種金屬離子的分子篩Ni/Ce-Y具有最高的脫硫容量,其脫硫容量比Ni-Y和Ce-Y分別高出31%和16%,因此,作者認為這可能是由于Ce與Ni通過M—S作用和π配合作用協同作用的結果。
1.2 非反應型吸附脫硫
非反應型吸附沒有發生化學鍵的斷裂,即為物理吸附,含硫化合物被吸附在吸附劑的表面或是內部,而且吸附劑的再生過程比較簡單。當前研究較多的是分子篩、活性炭、MOFs材料等。由于4-和6-位上的DBT衍生物很難用傳統的HDS或鎳基吸附劑脫除,而活性炭對烷基DBT(尤其對4,6-DMDBT)具有較高的吸附選擇性和吸附能力,研究發現活性炭材料對噻吩類含硫化合物的吸附選擇性都按以下順序遞增:BT < DBT < 4-MDBT <4,6-DMDBT,活性炭對含有烷基的噻吩類含硫化合物的選擇性更大。這說明活性炭材料對于柴油深度脫硫有著廣泛的應用前景[8]。
物理吸附主要靠色散力的作用,包括微孔吸附作用。微孔在對硫化物的吸附脫除中起主要作用,一般來說,吸附量隨著微孔體積的增加而增加,而中孔控制著吸附過程的動力學。王新征等[19]認為不同孔徑的孔具有不同的吸附機理:大孔主要是吸附質要進入到活性炭內部的通道,外部大孔必須保持通道暢通,吸附質才能進入被吸附劑的內部孔道有效吸附;中孔既起著吸附質通道的作用,又對吸附速度有一定的支配作用,所以中孔對大分子噻吩類含硫化合物的吸附有重要作用;活性炭中孔道大部分為微孔,它的孔容對噻吩類含硫化合物的吸附容量起支配作用。噻吩類含硫化合物的分子直徑約為0.65nm,而微孔的平均孔徑大小在2nm左右[20]。就孔徑而言,如果吸附劑的孔徑比吸附質分子的直徑稍大,吸附質會被吸附劑強烈的吸附;如果吸附劑的孔徑小于吸附質分子的直徑,吸附質則不能進入孔道;如果吸附劑的孔徑比吸附質分子的直徑大的多,則吸附作用力很弱以至于吸附質分子能夠自由出入孔道。π鍵配合吸附是非反應吸附脫硫中研究較多的吸附脫硫方式。
π鍵配位作用就是噻吩類含硫化合物中的硫原子的孤對電子進入載體表面活性離子的空軌道,形成的鍵力比范德華力要大,比化學鍵要小,通過升高溫度或降低壓力可以使π配位鍵斷裂[9]。π配合吸附機理為噻吩類含硫化合物的大π共軛體系能與金屬陽離子空的s軌道形成通常的σ鍵,同時金屬陽離子中d軌道的電子能流動至噻吩類含硫化合物反鍵軌道,形成π配位絡合物。π配合吸附脫硫條件溫和,許多過渡金屬元素都具有π配合吸附脫硫的能力,是一種適用范圍廣、相對成熟的脫硫技術。
研究最為成熟的是金屬離子改性的分子篩,如Cu(I)-Y、Ag(I)-Y等。Yang教授課題組對π鍵配位進行了深入廣泛的研究。Yang等[21]研究了以正庚烷為溶劑對噻吩的脫除,結果發現Cu(I)-Y的吸附效果最好,而Cu(II)-Y吸附效果則不如Cu(I)-Y好,這是因為Cu2+沒有涉及π配位吸附。Kim等[22]研究了在活性炭上浸漬CuCl和PdCl2,以此來考察對催化裂化中C4類硫化物的脫除,結果發現PdCl2/AC>CuCl/AC > AC,這可能是由于PdCl2與硫原子形成較強的π鍵配合的作用。
Rodrigues等[23]利用金屬鹵化物固相浸漬法制備了PdCl2/SBA-15吸附劑,并研究了此吸附劑在固定床反應器中對苯并噻吩/異辛烷模型油與真實汽油脫硫性能的研究。研究發現,PdCl2/SBA-15吸附劑比SBA-15、純PdCl2具有更高的吸附容量,此結果與數學模擬和吸附數據的結果相一致。此外,使用后的PdCl2/SBA-15吸附劑利用異辛烷進行再生,再生后的吸附劑可以將汽油中1000mg/L的S降至50mg/L,此結果表明在重復使用3次后,吸附劑的硫吸附容量改變依然可以忽略。
Khan Nazmul Abedin等[24]利用亞硫酸鈉作為還原劑,在常溫常壓下將CuCl2還原為Cu+,并將其負載到活性炭上,研究了Cu+在吸附脫除燃油中苯并噻吩(BT)的作用,并與未作處理的活性炭對比發現Cu+/AC具有更快的吸附動力學。文中也指出,負載Cu+后,活性炭的比表面積和孔容均有所減小,但是BT吸附量卻提高,表明了Cu+與BT形成了π-絡合物。
上述研究小組通過對活性炭、分子篩負載金屬制備的吸附劑,對含硫化合物的吸附性能均比未處理的載體有了較大的提高。對活性炭、分子篩等載體的金屬負載與改性也是達到燃油深度甚至是超深度脫硫的一種途徑。
Xiong等[25]以負載鈰的活性炭為吸附劑,考察了吸附脫除燃油中噻吩類含硫化合物的性能。研究發現:活性炭負載0.15mmol鈰時,噻吩的平衡吸附容量從7.02mg-S/g-AC增加到14.2mg-S/g-AC。并且,在研究噻吩與苯在石油醚溶劑中的競爭吸附時,發現當苯含量從0增加到40%時,負載鈰的活性炭吸附劑的吸附量降低了70%,而未負載鈰的活性炭的吸附量下降了95%。這些研究表明,負載鈰的改性活性炭可以有效地提高噻吩類含硫化合物的脫除,也說明了負載鈰的改性活性炭對噻吩類含硫化合物的選擇性是特殊的化學作用而不是分散力。
Blanco-Brieva等[26]研究了金屬有機骨架化合物(MOFs)用于液體燃料吸附脫除有機硫化合物的吸附性能。研究發現,MOFs吸附劑比Y形分子篩對二苯并噻吩(DBT)具有更高的吸附脫除率,并且,不同類型的MOFs吸附劑對DBT的吸附能力也不同。
Shi等[27]通過浸漬法制備了含Mo的MOF吸附劑,并研究了其在異辛烷、環烷烴和苯存在的條件下吸附脫除BT的性能。結果表明,吸附劑中Mo的負載量達到20%(質量分數),比表面積超過了1800m2/g,并且在芳香族化合物存在的條件下對BT也具有良好的吸附能力。
Liu等[28]利用稀土金屬(Ln=Sm,Eu,Tb,Y)與1,3,5-均苯三甲酸分別作為金屬離子中心和配體制備了金屬有機骨架(Ln-MOFs)吸附劑,并將其用于噻吩/正辛烷模型油的吸附脫硫研究。結果表明,Ln-MOFs吸附劑表現出了良好的吸附脫硫性能。其中,Y(BTC)(H2O)·(DMF)具有最好的吸附脫硫性能:脫硫率達到了80.7%,吸附容量為30.7mgS/g(Y-MOFs)。并且,Ln-MOFs具有良好的可重復使用性能。
上述作者的研究均表明了MOFs對含硫化合物具有優良的吸附性能和良好的選擇性,且吸附容量大、重復使用性較好。由于MOFs材料具有多變的結構、較高的比表面積和有序的空間結構特點,在燃油深度甚至是超深度脫硫方面將具有巨大的應用前景。
2 吸附脫硫過程的動力學
研究吸附過程的動力學有助于開發新型高效的吸附劑,但吸附過程機理比較復雜,當前對吸附機理解釋僅停留在吸附方式上,具體的吸附過程的動力學仍需進一步深入研究。
Subhan等[29]通過超聲輔助浸漬法將Ni負載到介孔材料AlKIT-6上,制備的吸附劑用于商業柴油和模型油的吸附脫硫實驗研究。研究發現,實驗數據可以利用擬二級吸附模型和Langmuir等溫線對噻吩(T)、苯并噻吩(BT)和二苯并噻吩(DBT)得到很好的擬合結果。實驗結果和數據擬合模型證明,AlKIT-6吸附劑對T、BT、DBT的吸附速率主要受顆粒內擴散和空間位阻共同作用。
鞏睿等[30]通過研究MOF-5對苯并噻吩(BT)的吸附動力學曲線與吸附平衡曲線發現,初始模型油中的BT含量提高,增加了MOF-5表面液膜內外BT的濃度差,從而增大了BT移向MOF-5表面的動力。結果表明,模型油中BT初始濃度越高越有利于提高MOF-5對BT的吸附容量。該小組并利用準一級與準二級動力學吸附模型對實驗數據進行了擬合,發現MOF-5吸附BT的過程與準二級動力學模型更接近,并且顆粒內部擴散并不是吸附過程中唯一的速率限制步驟,而是液膜擴散與顆粒內擴散總體作用的結果。
趙明飛等[31]利用準一級、準二級吸附模型和班厄姆公式對吸附實驗數據進行了擬合。擬合結果表明,班厄姆公式可以更好地模擬吸附過程,并根據擬合數據計算出表觀活化能為12.25kJ/mol。擬合結果證明了吸附劑對硫化物的吸附脫除是以化學吸附過程為主,且溫度越高,吸附速率越快。
Xu等[32]利用浸漬法制備了Ni-Ce/Al2O3-SiO2吸附劑,用于Jet-A燃料的吸附脫硫研究,并利用擬一級、擬二級吸附模型和顆粒內擴散模型對吸附數據進行了擬合。結果發現,擬二級吸附模型可以很好地模擬吸附動力學過程,而且證明了吸附過程并不僅僅是速率控制,而是開始時受化學吸附和顆粒內擴散控制,然后是介孔擴散和微孔擴散共同控制。
上述研究均證明了吸附劑對有機硫化合物的吸附動力學過程不是某一方面單獨控制,而是速率控制與顆粒擴散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可以為開發制備新型吸附劑和改性吸附劑提供科學的理論基礎。
3 結 語
當前,HDS技術是最成熟的脫硫方法。但是,HDS技術在深度脫硫方面依然要考慮到以下問題:第一,HDS在脫除DBT的烷基硫化物,尤其是4,6-DMDB時受到限制,由于4-位和6-位上甲基的空間位阻阻止了硫原子與催化劑上活性位的接觸,從而使得HDS過程中對4,6-DMDBT的選擇性很低[4],要達到深度甚至超深度脫硫需要更加苛刻的反應條件;第二,該反應需在高溫、高壓及H2氣氛下進行,能量及氫氣消耗很高。
針對國內柴油脫硫現狀,要實現低成本深度甚至超深度脫硫,需要進一步在以下方面進行深入研究:首先,新型吸附劑的開發,該吸附劑應廉價易得,并且具有很大的比表面積和孔容以及合適的孔徑;其次,對現有吸附劑進行改性,尋找活性更高的金屬對吸附劑進行改性增強吸附劑與噻吩類含硫化合物間的作用力,提高吸附劑對噻吩類含硫化合物的選擇性;最后,將吸附脫硫與氧化脫硫聯用等可能會取得更好的脫硫效果。
[1] Ma X,Sun L,Song C. A new approach to deep desulfurization of gasoline diesel fuel and jet fuel by selective adsorption for ultra-clean fuels and for fuel cell applications[J].Catalysis Today,2002,77:107-116.
[2]Kim J H,Ma X ,Zhou A,et a1. Ultra-deep desulfurization and denitrogenation of diesel fuel by selective adsorption over three different adsorbents:A study on adsorptive selectivity and mechanism[J].Catalysis Today,2006,111:74-83.
[3]路文娟,楊延釗. 過氧化氫用于油品氧化脫硫的研究進展[J]. 化工進展,2009,28(4):605-609.
[4]王廣建,張健康,楊志堅,等. 活性炭負載銀吸附劑的制備與脫除苯并噻吩的研究[J]. 功能材料,2013,44(7):949-953.
[5]Song C. An overview of new approaches to deep desulfurization for ultra-clean gasoline diesel fuel and jet fuel[J].Catalysis Today,2003,86:211-263.
[6]余謨鑫,李忠,夏啟斌,等. 吸附法柴油脫硫技術進展[J]. 廣東化工,2005(12):42-45.
[7]李云華,張香文,王蒞,等. 燃油深度脫硫研究進展[J]. 化學工業與工程,2008,25(6):559-564.
[8]Zhou A,Ma X,Song C. Liquid-phase adsorption of multi-ring thiophenic sulfur compounds on carbon materials with different surface properties[J].The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B,2006,110:4699-4707.
[9]劉卉,高金森,趙亮. 吸附脫除噻吩類含硫化合物機理的研究進展[J]. 石油化工,2010,39(9):1059-1065.
[10]Song Chunshan,Ma Xiaoliang. New design approaches to ultra-clean diesel fuels by deep desulfurization and deep dearomatization[J].Applied Catalysis B:Environmental,2003,41:207-238.
[11]馮麗娟,高晶晶,王振永,等. 柴油吸附脫硫技術研究進展[J]. 精細石油化工進展,2006,7(6):46-50.
[12]Seredych Mykola,Bandosz Teresa J. Selective adsorption of dibenzothiophene on activated carbons with Ag,Co and Ni species deposited on their surfaces[J].Energy & Fuels,2009,23:3737-3744.
[13]Tian F P,Wu W C,Jiang Z X,et al. Adsorption of sulfur containing compounds from FCC gasoline on cerium-exchanged Yzolite[J].Chinese J. Catal,2005,26(9):734-736.
[14]Li F F,Song L J,Du L H,et al. A frequency response study of thiophene adsorption in zeolite catalysts[J].Applied Surface Science,2007,253(21):8802-8809.
[15]莫同鵬,賀振富,田輝平,等. 固體酸催化劑的酸性對噻吩類含硫化合物轉化的影響[J]. 化工進展,2009,28(1):78-81.
[16]吳亞娟. 烷基的電子效應[J]. 紡織基礎科學學報,1994,7(3):257-261.
[17]余謨鑫,李忠,夏啟斌,等. 表面負載不同金屬離子的活性炭吸附二苯并噻吩[J]. 功能材料,2006,37(11):1816-1818.
[18]Wang J,Xu F,Xie W J,et al. The enhanced adsorption of dibenzothiophene onto cerium/nickel exchanged zeoliteY[J].J. Hazard Mater.,2009,163(2-3):538-543.
[19]王新征,李夢青,居蔭軒,等. 制備方法對活性炭孔結構的影響[J].炭素技術,2002(6):25-30.
[20]陳蘭菊,趙地順,郭紹輝. 改性氧化鋁負載氧化物催化氧化噻吩的脫硫研究[J]. 化學學報,2007,65(16):1718-1722.
[21]Hernandez-Maldonado Arturo J,Yang R T. Desulfurization of liquid fuels by adsorptionviaπ complexation with Cu(I)-Y and Ag-Y zeolites[J].Ind. Eng. Chem. Res.,2003,42:123-129.
[22]Kim Kyu-Sung,Park Sun Hee,Park Ki Tae,et al. Removal of sulfur compounds in FCC raw C4using activated carbon impregnated with CuCl and PdCl2[J].Korean J. Chem. Eng.,2010,27(2):624-631.
[23]Anne Kerolaine O,Ramos Josy Eliziane T,Cavalcante Jr,et al. Pd-loaded mesoporous silica as a robust adsorbent in adsorption/desorption desulfurization cycles[J].Fuel,2014,126 :96-103.
[24]Khan Nazmul Abedin,Hasan Zubair,Min Kil Sik,et al. Facile introduction of Cu+on activated carbon at ambient conditions and adsorption of benzothiophene over Cu+/activated carbon[J].Fuel Processing Technology,2013,116 :265-270.
[25]Xiong Lin,Chen Fengxiang,Yan Xuemin,et al. The adsorption of dibenzothiophene using activated carbon loaded with cerium[J].Porous Mater.,2012,19:713-719
[26]Blanco-Brieva G,Campos-Martin J M,Al-Zahrani S M,et al. Effectiveness of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for removal of refractory organo-sulfur compound present in liquid fuels[J].Fuel, 2011,90 :190-197.
[27]Shi Fan,Hammoud Maha,Thompson Levi T. Selective adsorption of dibenzothiophene by functionalized metal organic framework sorbents[J].Applied Catalysis B:Environmental,2011,103 :261-265.
[28]Liu Xiang,Wang Jingyan,Li Qingyuan,et al. Synthesis of rare earth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Ln-MOFs) and their properties of adsorption desulfurization[J].Journal of Rare Earths,2014,32(2):189-194.
[29]Subhan Fazle,Yan Zifeng,Peng Peng,et al. The enhanced adsorption of sulfur compounds onto mesoporous Ni-AlKIT-6 sorbent,equilibrium and kinetic analysis[J].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2014,270:82-91.
[30]鞏睿,周麗梅,馬娜,等. 金屬有機骨架材料MOF-5 吸附苯并噻吩性能[J]. 燃料化學學報,2013,41(5):607-612.
[31]趙明飛,沈健. TiO2-SBA-15吸附脫硫性能及吸附動力學研究[J].天然氣化工,2013,38(4):19-23.
[32]Xu Xinhai,Zhang Shuyang,Li Peiwen et al. Equilibrium and kinetics of Jet-A fuel desulfurization by selective adsorption at room temperatures[J].Fuel,2013,111 :172-179.
Advances on adsorptive desulfurization of diesel for thiophenic sulfur compounds
WANG Guangjian,XIAN Baozhen,LIU Ying,FU Xintao,ZHANG Luping
(Colleg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Qingdao 266042,Shandong,China)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of commonly used adsorbents,mechanisms of adsorptive desulfurization and adsorption kinetics studies from diesel fuel. Molecular sieve,activated carbon and metal organic frameworks (MOFs) materials have been widely studied. Although HDS can be used to produce low-sulfur diesel that meets the sulfur regulations,this process operates at high temperature and high hydrogen pressure,high cost and low removal rate of dibenzothiophene. The adsorption desulfurization technology has become a research hotpot of diesel desulfurization because of its low cost,moderate operating conditions. easy removal of tough sulfide,and little impact on oil quality. Adsorption desulfurization consists of reactive adsorption desulfurization and non-reactive adsorption desulfurization. The key factor in the adsorption desulfurization reaction is breaking the old bond while generating the new bond. Non-reactive adsorption desulfurization applies dispersion force between the sulfur atoms and sulfur sorbent interactions,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adsorption desulfurization.
molecular sieves;activated carbon;desulfurization;adsorbents;kinetics
TE 624
A
1000-6613(2014)10-2764-07
10.3969/j.issn.1000-6613.2014.10.041
2014-03-14;修改稿日期:2014-04-21。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21276130)
及聯系人:王廣建(1963—),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催化新材料、環境凈化催化工程及反應器等領域的研究。E-mail guangjianwa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