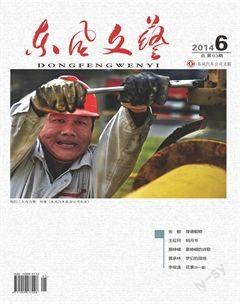嘟嘟
鄧炎清
嘟嘟是一條雜毛狗,通身淺黃色,間雜幾處輕描淡寫的水墨色。嘟嘟是我們從寵物市場買來的,聽人說出生不到五十天。寵物市場就在百二河邊那片水杉樹林里,是一個約定俗成的露水市場。平時大家有什么需要交換的,諸如貓、狗、鳥類,乃至熱帶魚類,樹木花卉類,都往這里帶,久而久之,這里就成了一個以寵物交易為主的露水市場。在這里,經過一輪象征性討價還價,連嘟嘟脖頸上那根繩索在內,我們總共花了七十元。說實在,嘟嘟也就只值這個價錢,雖說腿腳是有點矮短,臉型也是有點緊湊,一看就知道是經過了雜交改良的品種,但到底只是一條小草狗,血統又高貴不到哪里去吵,混跡于寵物市場就能把身價抬上去?嗤!
嘟嘟這個名字是鄧等給取的。鄧等是我們的女兒,已經九歲了,上到了小學三年級,正是發奮用力的階段。她哭著鬧著要養寵物,我們就用這樣一條狗來敷衍她。鄧等倒也開心,還沒把它抱上車,就給它取好了名字。“嘟嘟,嘟嘟,嘟嘟”,她沖它歡天喜地的叫著。嘟嘟呢,一上車就圓咕溜秋地趴著了,也不哼唧,也不動彈。你摸它皮毛,撓它癢癢,它就怯生生地往后躲,往身子里面縮,縮成一個圓圓的小肉團。過一會,再用眼角瞄瞄你瞟瞟他,一副受了委屈的小孩兒模樣。到后來才終于露出一點狗性來,在后排車墊上扎扎實實地拉了一泡尿。“狗東西”,我氣得大叫,老婆和女兒卻放聲笑起來。所謂事不關己也,在平時,這車內的衛生是不算她們分內活。
嘟嘟回到家里也是這樣。剛進門它就掙脫鄧等,立即鉆到了木質沙發底下去,任你怎么喊就是不出來。木質沙發底下那里有一只廢棄的舊拖鞋,它鉆進去之后就蹴在上面縮著了。從此以后,那里就是嘟嘟的狗窩了,是它翻箱倒柜做了壞事之后的避難所。那只廢棄的舊拖鞋呢,是它睡覺用的席夢思,是它用來鍛煉狗性的啃噬物,也是它長大之后春心蕩漾長夜難眠時的寄情物。后來,我們在陽臺用包裝紙盒給它做過一個狗窩,但各種引導之類的嘗試都失敗了,它就是不從,我們只好作罷。這是后話。現在,嘟嘟蹴在那只舊拖鞋上面,又一次很實在地撒了一泡尿。好大的一泡尿吔,從沙發底下曲里拐彎一直流出來,流到了客廳當中。我老婆當時差點沒氣得暈過去。這回輪到我開樂了。
那是二○○四年三月。太陽已經亮麗得有了溫度,天空也已開始藍得晃眼睛。桃花說紅就紅了,楊柳綠得婀娜多姿。屋外各色草木花卉紛紛擾擾,伸胳膊的伸胳膊,亮嗓門的亮嗓門。所謂“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大自然就是這樣,各有各的序列,各有各的軌跡。我的軌跡是上班下班,偶爾加一兩個班。從寵物市場回來,我就被電召去加班了。回到家已是晚上八點鐘。“老爸,嘟嘟吃火腿腸了。”“老爸,嘟嘟吃了三根火腿腸了。”“老爸,嘟嘟聽得懂它的名字了,不信你拿火腿腸叫它。”我這才又想起家里多了一個嘟嘟。“嘟嘟,”我拿一根火腿腸沖沙發底下喊,它果然慢慢湊過來了。我算是明白了,“嘟嘟”這個名詞對于它就是吃,或者干脆就是一根粉紅色火腿腸。
事情就是這樣。從此,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嘟嘟總是以為,普天之下,狗糧就是火腿腸,餓了就該吃火腿腸,而且,它那一副狗下水也只認火腿腸了。我們覺得這樣下去不行,長此以往,它可以吃窮一個家庭的。于是,嘗試給它加稀飯,把火腿腸切得細細的拌到稀飯里去,再用力攪勻。但是收效不大,嘟嘟可以輕而易舉地用它的舌頭一舔,再一卷,便把那些丁丁塊塊細小的紅顏色舔進嘴里,卷到肚里,就是不捎帶進去一點稀飯,頂多只是在嘴巴上胡須上沾染一點稀飯沫。
吃飽了,嘟嘟就開始玩自己。用粉紅色舌頭舔兩個小爪子玩。它趴在那里耐心耐煩地舔,左一口右一口地舔,上一口下一口地舔。在這一刻,它哪里還是一條狗,仿佛變成了一只貓。但如果你以為它真的像貓一樣地愛清潔,講衛生,那你就錯了,大錯特錯咧。它是無所事事,無事生非,在憋悶之中給自己找一點樂子罷了。嘟嘟舔得盡心了,疲憊了,就四仰八叉地稍事休息一會。感覺緩過勁來了,便又投入地玩自己。這一回是改用啃了。起先是抱住那只舊拖鞋啃,感覺味道不夠好,不夠特別,只是象征性地啃了一會便丟下了,它徑直跑到門口,在一堆鞋當中挑選了一只新的高跟鞋,叼住,拽到沙發底下去,這才盡情地啃了。它從前往后,從上往下,一路啃下來,那高跟鞋就全是牙印了,鞋袢也被它活生生地給拽掉了。蒼天呀大地呀,那鞋可是老婆剛買回來用于搭配那套新春裝的。老婆在衣服鞋帽的搭配上是刻意的,挑剔的,完美的,如果不能如她的心愿,她是絕不勉強遷就的,所以,每到換季,挑選與搭配衣服鞋帽就成為她個人乃至我們全家一個極其繁復的工程。嘟嘟居然不懂這個,膽敢啃噬老婆的高跟鞋,看來這回它的狗命不保了。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天空剛剛刮起風暴,眼看就要黑云壓城城欲摧了,卻忽而變得風和日麗了。聽得老婆的尖叫聲,嘟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躲進沙發底下,并且以嚇得魂飛魄散縮著一團的姿態,很快博得了老婆的惻隱之心,取得了她最終原諒它,并回報了它一個笑容,也就解除了丟命之警報。
好久以后,老婆還常常聊起這件事。她說,怪不怪吧,那一瞬間,我怎么就突然覺得那模樣是我們鄧等了。又說,我當時可不就真是這樣想法,把它當做鄧等了。她問,換了你,你會向一個乞求你原諒的小家伙掄一巴掌或踢一腳的嗎?又說,我想你是不會反對向一個小可憐突然笑一個的吧?
日子就這樣過去。嘟嘟慢慢融入了我們的生活,成為了我們家庭里的一員。下班時節,聽得門口腳步聲,或者掏鑰匙的聲音,嘟嘟就一準守候在那里了,只等門一開就迫不及待地撲向你,就像孩子撲向父母親一樣。它迎接到了你,就用舌頭舔你,舔舔你這里舔舔你那里,還把頭一個勁地依附于你的某個部位,使勁地蹭著。蹭夠了,就給你做游戲。
嘟嘟的游戲總是老三樣,一日咬尾巴,二日硌癢癢,第三就是追逐賽。所謂“咬尾巴”,是這樣的:它追著自己的尾巴咬著玩,轉著圈圈追著自己的尾巴咬著玩,眼看快要咬著了,身子一動,尾巴就又跑了,總快咬著了,總是咬不著,如此循環反復著,逗得你心花怒放,放聲大笑,情不自禁獎勵它一根火腿腸,或者一段鴨脖子。它就更加樂此不疲,直到氣喘吁吁實在是跑不動了。所謂“硌癢癢”就是:它四腳朝天地躺著,原地轉著圈圈,讓你來硌它下巴的癢癢,或者硌它肚皮的癢癢,它就咧著嘴笑著,享用著。見此情景,即使你心情不好,你也往往是樂于逗它一逗的。第三樣追逐賽一般是在室外,那里場地大,跑得開,跑起來了也夠盡心。嘟嘟開始是陪你散步,它一忽兒繞你前面,一忽兒繞你后面,轉著圈兒地繞,然后歡蹦亂跳地往前跑一氣,邊跑邊往回看,引導你追它,它又不真的拼命跑,看你沒有追上或者沒有追逐的意思,它會重新引導你來一遍,直到你真的開始追逐它。說實在的,我并不喜歡這種游戲,嘟嘟之所以屢次玩兒它,問題在于老婆與孩子,她們樂意。只要出門散步,她們總是帶上它,還唆使它玩兒這個,我有什么辦法。或許動物世界里也是有少數服從多數這個準則的,嘟嘟大概是知道并遵守的罷。
轉眼嘟嘟來我們家已經兩年了。據介紹,像它這個歲數,若是人類,應該是妙齡女郎的年紀,早已到了談情說愛,甚至談婚論嫁的時候。果然,問題說來就來。這時期,聽得門口腳步聲,或者掏鑰匙的聲音,嘟嘟也還是守候在那里,等門一開也還撲向你,但僅只是撲向你而已,它不再伸舌頭盡情地舔了,也不再真地依偎于你某個部位用勁地蹭了,它現在所做,就像鄧等此類小學生放學后必須要做一篇功課,就像我們這班公務員在單位往往道貌岸然例行公事,程序化了,模式化了。嘟嘟做完上述功課,就迫不及待地往外跑。一溜煙跑完五層樓,跑到了樓底下,又快步跑到對面樓房第二個門洞,守候在了那里。嘟嘟仰著脖頸望,拖著長音汪,它是在等對面三樓的那只咖色泰迪,它是在給泰迪發信號。嘟嘟的愛狂熱、奔放,就連示愛也是大膽的,熱烈的,不加掩飾與修飾的,就像劉曉慶,就像木子美,就像敢于愛到國外的芙蓉姐姐。但這又注定是一個不確定的追求與等待的過程。因為它要等到泰迪的主人回來放泰迪出來,它才有可能得到這份愛。那只泰迪倒也值得嘟嘟愛,一來,它與嘟嘟年齡相仿,看上去就像人類中有涵養、有地位、有氣質的帥小伙,所謂高富帥是也;二來,它對嘟嘟也算愛得明確與熱烈,每當嘟嘟在樓下呼喊,它也一準會在三樓答應,還火急火燎地撥弄著窗玻璃,沖著嘟嘟汪汪地叫。對此,樓下那個胖得跑油的女鄰居跟老婆開玩笑,說,拜托,你家嘟嘟是女的耶,矜持一點好不好,別動不動往人家那里跑?我心想,敢情又不是你,飽漢不知餓漢饑。又想,像嘟嘟這樣的雜交草狗,對泰迪是高攀,它為什么要顧這份矜持,裝這份含蓄?得到就是硬道理吵,傻B。
這期間,嘟嘟晚上常常是抱著那只廢舊拖鞋輾轉反側,或者發一氣呆,或者折騰一回。發呆時,它似乎有想不盡心思,連火腿腸也不肯多吃幾口,連游戲也不想多做幾回了;折騰時,它又似乎有使不完的精力,舔過咬過啃過之后還不罷休,再用腦袋撞,撞地板,撞墻壁,撞木質沙發Ⅱ也。有時,半夜起來上廁所,看到嘟嘟在撞墻,就會頓生憐憫,坐到沙發上跟它說一氣。我說,這時節哪有那么趁手,你就將就著用一回拖鞋?又說,要不給你支煙抽抽,緩釋緩釋一下情緒?最后回到床上,被它弄得居然也睡不著覺了。就想那紅樓夢里大觀園,在這夜深人靜的時候,但凡是水做的,薛寶釵是如此,林黛玉也是如此吧。
好容易等到五一黃金周,我們終于決定了送嘟嘟走。原因是,鄧等即將小學畢業,這期間,她不能有一絲一毫分心。正好我們計劃去武漢,看我們省吃儉用在東風陽光城購買的一套房子,于是決定把嘟嘟捎上,送得遠遠的。
也許是第一次走高速,速度快暈車的緣故,嘟嘟打自上車就不歡實,它蹴在變速桿后面,一路都是迷迷瞪瞪,恍恍惚惚的。到了武漢下了車,也還是似睡非睡,不吃,不喝,蔫蔫的,怏怏的,就像是剛大病了一場的樣子。
第二天往回趕,趁在蔡甸服務區加油的機會,終于把嘟嘟哄下了車。然后,點火,關車門,搖上窗玻璃。但此時,汽車行駛是緩慢的,是在慢慢地往前“埂”。我在看汽車后視鏡,在看嘟嘟。這時,嘟嘟像是睡醒了,它突然劃動四條矮而短小的腿,朝我們車輛拼命追過來,追過來。鄧等呢,早已經趴在后窗玻璃上淚眼汪汪了。她對它喊,你快呀,快跑呀。又對我們說,我再聽話,一放學就做作業還不行?到最后車轉過身來,惡狠狠地沖我們大吼,你們都是儈子手,你們這是要殺了它。再看看旁邊的老婆,她也已兩眼泛紅淚光閃閃了。心頭就像是被什么揪了一下地疼。哧一溜一,我踩下剎車,摘下前進擋,拉起手剎,推開了車門。不一會,車內又恢復到從前,高聲闊論,大呼小叫,像過節趕集,像過年聚會,氣氛熱烈,其樂融融也……
也是活該嘟嘟有一個美好未來,我們呢,也終于不必再當“劊子手”了。回到十堰第二天,嘟嘟就有了一個新歸宿——陪那個孝感老太太在小區值守自行車棚了。這可是一個歡天喜地、兩全其美的事情。
在我們回家路過自行車棚的時候,孝感老太太正在門前的幾張麻將桌間逡巡。聽得汽車聲,她轉身朝這邊望,又朝車里的嘟嘟笑。整個過程也就三五秒,這事擱在平時再正常不過,跟眨眨眼摸摸鼻子沒什么兩樣,稀松平常的。但這一次卻例外,老太太的一望一笑產生了化學反應,老婆的靈感一下給激靈出來了,于是叫停車,朝自行車棚走去。也就上一趟廁所工夫,老婆喜滋滋地回來了。她一進門就蹲下來,伸出兩只手,沖著嘟嘟動情地叫喚,來,乖乖,到媽媽這里來。又吩咐我們燒水給嘟嘟洗澡。她說,到別人家去,哪有不收拾干干凈凈、漂漂亮亮的。聽這口氣,仿佛是要嫁姑娘。真的Ⅱ也,她這一次可不真是把嘟嘟當作姑娘了。她幫它洗澡,用飄柔牌香波,搓一遍,又揉一遍。還給它梳理毛發,剪指甲。看那架勢,如果可以,她真敢給它描眼影、抹口紅……
嘟嘟在我們家吃的最后一頓晚餐,一定留在它的記憶里,它比火腿腸還高端、大氣、上檔次——吃烤鴨。嘟嘟呢,也還真給面子,就一個來回,一只烤鴨就被它風卷殘云消滅得只剩一個骨架了。臨了,卷了卷舌頭,開始做“咬尾巴”的追逐游戲了。
一周過去,我們有意無意間又吃了一回烤鴨。這回除了骨架還剩下不少內容。我們就全部打包帶上,在黃昏時節,散步到了自行車棚。在散步時,自然是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文地理,聊風土人情。聊著聊著就到了自行車棚。就看到一道黃色閃電沖出來,徑直朝我們撲將而來,是嘟嘟Ⅱ也。它是聽到我們說話聲音才沖出的吧?這情景就仿佛失散的孩子突然聽到了父母親。因此,它有這樣速度是不足為奇的,但是讓我至今都不甚明白的,這個身材與腿腳都相對矮小的家伙,那剎那是哪里來的能耐,居然一躍就到了我們胸前,與我們一般高了。事后,我們還隔三岔五地談論起這件事。老婆說,我算是明白了,動物,尤其是像嘟嘟這樣的狗類,它的忠誠可以瞬間放大它的能耐,哪里像我們人類!說到人類,就捎帶譏諷地拿眼朝我瞟。什么意思?你!
這以后,黃昏時節,嘟嘟也偶爾回訪我們。它爬上五樓,聽一會,發覺有聲音或者有亮光,就用爪子抓。進得門來,就舔我們手,就追逐尾巴做游戲,就四仰八叉轉圈圈。也用鼻子嗅,也啃,也偶爾得到火腿腸或者鴨脖子。就十幾二十分鐘,感覺夠了,就打道回府,從不耍賴在五樓多呆一會或者干脆過一夜,縱使鄧等暗中使了不少手段也留不住它。它得回去,它要跟孝感老太太一起做值守自行車棚的活計。
再后來,嘟嘟來得更少了,到最后,終于一次也沒來了。聽人說,孝感老太太回去了,她把嘟嘟也一并帶回去了。難怪。又不知過去幾天,孝感老太太的外甥女告訴鄧等說,嘟嘟做母親了,它一窩生了五個小寶寶。我們知道動物是不搞計劃生育的,就遙想嘟嘟這以后該是如何應對生活。
鄧等終于發奮努力,考上了中學。我們還是朝九晚五,上班下班,偶爾也加一個班。又一個春天到來,我們再也沒有聽到嘟嘟一丁一點消息。孝感老太太的姑娘買了新房,搬到別的小區去了。
這年暮春時節,我出差到柳州。我是第一次到柳州。發覺滿街是突突的摩托車,是狗肉招牌和狗肉店鋪。摩托車后面拖著的多是黑的、黃的、白的、花的狗。店鋪伙計在用火焰槍燒黑的、黃的、白的、花的狗毛。就眼神慌亂不夠用了。我在柳州街頭開始了尋找,左左右右里里外外地尋找,尋找嘟嘟和它的孩子們。因為我突然認定,摩托車后架上,或者左右店鋪里,一定總有一只是嘟嘟,也一定總有五只是嘟嘟的孩子們。找著找著心頭就像是被什么揪了撞了似的疼,來不及躲閃,也沒想躲閃,就汪汪汪地吐了,吐了柳州一大街。
還沒等到事情辦完,我當天夜晚就搭乘火車往回趕了。坐到火車上,才感覺疲憊極了,也虛弱極了。在睡眼蒙朧中,再回望漸行漸遠的柳州,惚兮恍兮,它模糊得沒有了形象,哪怕是輕描淡寫幾筆勾畫的輪廓也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