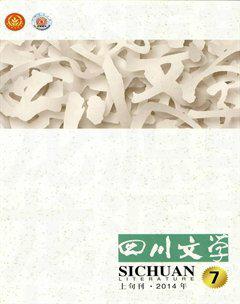意外(小小說二題)
◇李 云
一
汪市場教兒子汪小胖寫“民”字。兒子,他說,民工、人民、人民幣,都有民,這是個(gè)多么常用的字!你老爸我?guī)缀跆焯旄翊蚪坏溃@個(gè)字下面的兩提勾都向右,這一點(diǎn)都不難對不對?你們老師說你不會(huì)寫,怎么可能?你老爸我這么聰明能干,兒子也不會(huì)笨,是不是?汪小胖使勁點(diǎn)頭。
很快,汪市場發(fā)現(xiàn),汪小胖寫的這個(gè)字,下面的兩筆提勾老是向左。汪市場捉住他的手,一筆一劃地耐心地教,可能教了一百遍,可剛放手讓兒子自己寫一個(gè),汪小胖還是把提勾朝左邊勾去。是可忍孰不可忍,啪!一個(gè)耳光賞過去,汪市場咆哮著沖進(jìn)廚房,拖出正在做飯的老婆李翠花:“你去教!氣死老子了!”
汪市場在廚房抽悶煙,回想起開家長會(huì)的情景。
兒子汪小胖上小學(xué)一年級了。按戶籍就近入學(xué)汪小胖該讀鎮(zhèn)里的小學(xué),可汪市場仗著自己在縣城里修了幾個(gè)菜市場,認(rèn)識(shí)一些人物,就花了一筆重金把兒子送進(jìn)了縣里最好的實(shí)驗(yàn)外國語學(xué)校。他指望兒子好好讀書,將來考上好大學(xué),成為有文化的人,不要像他除了錢啥都沒有,明里暗里被人洗涮戲弄。他本來叫汪富貴,硬被別人改成汪市場。他聽著心里不爽,感覺有輕蔑的意思。可他不能跟人較真,人說是抬舉他呢。
老師按孩子的成績或存在的問題把家長分成了三堆。對三堆家長講不同的事不同的問題,說不同的話。最后把汪市場留下來了,說他兒子的問題比較特殊,所以他不屬于三推中任何一堆。為什么特殊呢,因?yàn)橥粜∨植粫?huì)寫民字,必須把這個(gè)任務(wù)布置給家長,叫他回家教。汪市場想這還不容易,就拍胸口保證教會(huì)。
現(xiàn)在他算是失敗了,痛苦地揪著頭發(fā),把希望寄托在老婆身上。
老婆又教了數(shù)十百遍,汪小胖還是要把民字下面的兩提勾向左勾。他手中的筆好像中了魔似的非要朝左,任爹媽怎么罵怎么打毫不改變。
汪市場聽見老婆大呼小叫喊拿板子來,他立即拖著一米長三寸寬的鋼板過去,汪小胖躲在墻角瑟瑟發(fā)抖,一見那鋼板,猛地把衣服撩起蒙住腦袋,像一只顧頭不顧尾的鴕鳥。汪市場掄起鋼板沒有打下去。只一屁股坐在地上,指著墻角,氣急敗壞:“你、你、你不是我的兒。”
他老婆白了他一眼,像牛一樣喘粗氣:“你什么意思?什么叫不是你的兒?”
汪市場打了一個(gè)激靈。他本來氣頭上一罵,被老婆如此一問,倒提醒了他什么。此后三天,汪市場不吃不喝躺在床上像死人一般。
第四天,汪市場跟老婆說,他要到外省去談個(gè)生意。
汪市場這一走就沒回來。李翠花意識(shí)到他不會(huì)再回來后才去查看,家里的現(xiàn)金、存折、卡和賬本都不在了。她本打算去報(bào)警的,可想了一想,自己手里還有這套住房和商鋪呢,再說還有個(gè)兒子呢,就由他去吧。
離家出走的汪市場在一個(gè)和以前完全沒了往來的地方開始了新的生活。他把以前認(rèn)識(shí)的一個(gè)女人接來了,住在一起,一心想再生個(gè)兒子。這一次他得保證兒子絕對是他的種,現(xiàn)在這個(gè)女人成天和他守在一起,在這個(gè)地方不認(rèn)識(shí)任何人。
他老婆李翠花也算是個(gè)精明過人的人了,跟隨他摸爬滾打多少年,一直做他的會(huì)計(jì)兼出納,過手的錢像河里的水嘩啦嘩啦地日夜流淌,從沒出過差錯(cuò)。而現(xiàn)在這個(gè)女人的頭腦似乎比李翠花的還好用,說話滴水不漏,做事八面玲瓏,汪市場想,跟這個(gè)女人一起生個(gè)孩子,無論是男是女都應(yīng)該不會(huì)有問題。
一年后,汪市場的手上就抱著一個(gè)嬰兒了,還是個(gè)男嬰,他簡直高興得快瘋狂了。他認(rèn)為上帝待他不薄,給了他無限希望。
他又開始拼命賺錢。為這個(gè)寶貝兒子建立教育基金。
一轉(zhuǎn)眼,這個(gè)小兒子又上小學(xué)了。汪市場很緊張,怕開家長會(huì)。每次他都讓孩子他媽跟學(xué)校老師聯(lián)系。每次他都問老師說什么沒有,那女人都說沒有說什么呀。孩子看上去健康、正常的,他便放下心來。
孩子讀二年級時(shí),有一天汪市場鬼使神差翻看了他的寫字本,突然大叫一聲“天啊,我的老天啊”,暈倒在地。原來小兒子也和汪小胖和一樣,寫的“民”字,下面兩提勾一律向左。
二
這天,張迪上車發(fā)現(xiàn)一號(hào)位有人坐了,是一個(gè)時(shí)髦女郎,穿著一件金黃色的緊身襯衣。他摸出自己身上的票,遞到那位女郎面前,很客氣地說:
“請你看看你的座位號(hào)。”
那女郎瞟了他一眼沒有反應(yīng)。
他站了一會(huì),對她說:“我暈車,所以兩天前我就預(yù)定了這個(gè)位子。”
張迪是一個(gè)科研人員,他們的科研基地在距市區(qū)120公里的一個(gè)山溝里。進(jìn)出溝里的路蜿蜒曲折凹凸不平,每個(gè)月他都有三四次往返。每次無論坐什么車他都暈暈乎乎很是難受。后來他發(fā)現(xiàn)乘坐長途公交車似乎要好受點(diǎn),于是他長期預(yù)定這條路線的長途車的一號(hào)位子。一號(hào)位在司機(jī)背后,靠窗。每次往返他都坐一號(hào)位。久而久之,他和司機(jī)、票務(wù)員混熟了,買不買票那個(gè)位子都會(huì)留給他,已成慣例了。
這時(shí)女郎淡淡地說一句:“我也暈車。”
“那你應(yīng)該早點(diǎn)買下這個(gè)位子的票呀。”張迪說。
“那我現(xiàn)在就買這個(gè)位置。”女郎掏出一張100元大票遞給售票員。售票員看一眼張迪,沒有動(dòng)彈。
張迪說:“這張票我已經(jīng)買了,錢給他沒用的!”。
乘客陸續(xù)上車,有票的依票號(hào)入座,沒票的現(xiàn)場買。人們對爭搶座位的事習(xí)以為常了,所以都只冷眼旁觀。
司機(jī)走過來調(diào)解,對女郎說:“美女,這個(gè)帥哥提前買了票,他坐自己的位子不是很應(yīng)該嗎?你說是不是?請你起來讓他。”
女郎說:“大哥,票是虛的,座位是實(shí)的。誰先來就先坐。”
“不講理是不是?你太不可理喻了!”張迪氣憤地伸手去拉女郎的胳膊。
女郎說:“別碰我啊,就算你有理,碰了我就沒理了。”
張迪想想也是,這下拿她沒轍了。
看來她就是耍無賴也鐵了心要搶這個(gè)座位。
司機(jī)看局面僵持了,轉(zhuǎn)而跟張迪商量,說下一班車相隔十分鐘,他可以打電話請售票員把下班車的一號(hào)位留出來,希望張迪同意。
只能如此了。張迪只好下車等了將近一刻鐘,坐上了另一班車。
上路不久,張迪他們就被告知:前一趟車出車禍了。
司機(jī)更加謹(jǐn)慎,小心翼翼地駕駛。售票員開始動(dòng)員乘客做好搶救傷員的準(zhǔn)備。
等他們趕到一個(gè)急彎處,就看見前一班車掉到了幾十米深的懸崖下,車已散架,乘客四處散落。他們是最先趕來救援的人。
大家緊急救人,張迪這一輛車上的所有人都開始行動(dòng)。哭喊聲、呼救聲響成一片,那場景真是太慘了,車內(nèi)車外都是傷者,有的只剩一口氣,有的氣都沒了。乘客的隨身物品遍地都是。
張迪搬掉一堆扭變形了的座椅,發(fā)現(xiàn)下面躺著一個(gè)年輕女郎,已經(jīng)昏迷過去,無聲無息,那件金黃色襯衣他是熟悉的,半小時(shí)前,他和她因?yàn)闋帗屪欢鵂幊场?/p>
張迪一把抱起了她,那女子已然面目全非,但她睜開了血肉模糊的雙眼。張迪立刻安慰道:“別怕,現(xiàn)在沒事了,沒事了。”
他一邊說著,一邊抱起她走向路邊,找一處平坦處輕輕放下,嘴里還不停安慰道:“馬上救護(hù)車就到了,你堅(jiān)持一下呵!”說完想站起身,再去救人。
他的衣袖被拉住了,是女子拉住了他。躺在地上的她,艱難而真誠地說:“對不起,剛才,我、我、搶了、你的座。”
張迪想說“沒關(guān)系”,可說不出口。他心緒復(fù)雜,你搶了我的座能沒關(guān)系嗎?這關(guān)系多大呀!本來應(yīng)該是我受傷的,硬生生被你搶去了,你哪是搶了我的座,你是搶了遭遇車禍的劫難呀。你替我去赴難的,應(yīng)該是我對你說“對不起!”
張迪哽咽著鼓勵(lì)她挺住,馬上就有救護(hù)車來了。
張迪就那樣半摟著她,為她流著淚,也為自己的僥幸流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