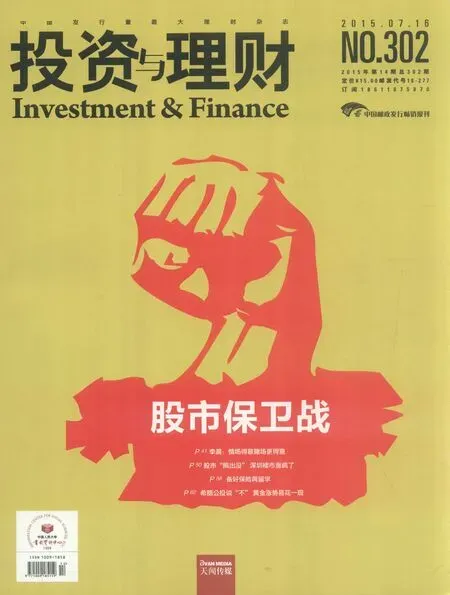歸家之路
殷萬喜



井士劍作品表達了現實與人的緊張關系,這種緊張關系是人的精神與社會物質的緊張關系的縮影。在現實與精神之間,井士劍沒有采取調和的態度,在他看來,這種調和的瞬間的詩意不足以彌合現代社會的裂變。也許是這個原因,井士劍沒有在象征主義的視覺圖像中止步,而是更進一步地走向視覺的寓言。在本雅明看來,寓言是我們在這個時代所擁有的特權,它意味著在這個世界上把握自身的體驗并將它成形,意味著把握廣闊的真實圖景,并持續不斷地猜解存在的意義之謎,最終在一個虛構的結構里重建人的自我形象,恢復異質的、被隔絕的事物之間的聯系。
井士劍的作品在寓言的意義上,呈現出完整的時代與內在體驗的真實圖景。他注重個體的內在經驗,陷于存在的困擾,他的作品帶有鮮明的經驗色彩,充滿了體驗的震蕩,并且在一種逃避與回擊的姿態中,表達了一種英雄主義的氣質。井士劍的作品更適宜當作一個“神話”來閱讀,這不僅是一個古典主義的神話,也是現代人的神話,現代大都市的神話。
在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現在生活的“自然”已經為“城市”所替代,在現代城市的生活中,除了游客,一般人在街市上的行走,往往具有很強的目的性,很少東張西望。蘇東坡文中的“茫然四顧”是一種文人的“張望”。井士劍所生活的錢江與西湖,已經成為城市中的“江湖”,他的《江湖》系列作品中的人物,具有一種看似悠閑的“張望”與“漫游”。“張望”決定了現代社會知識分子在城市生活中的思維方式,“漫游”決定了知識分子同風景的精神聯系,在這種“江湖”的“張望”與“漫游”中,井士劍展開了他與城市和其他人的關系。只有在城市中的漫游,他才能與他人發生聯系,只有在對城市的張望中,他才能認清自身。大城市并不在那些由它造就的人群身上得到表現,相反,城市的底蘊在那些游走于城市,并且迷失在自己的思緒的人身上得以揭示。
相比于蘇東坡對自然的依戀與歸屬感,我們時代的藝術家還算不上傳統意義上的“文人”。他們雖然也居有其屋,有些功成名就者甚至擁有大屋與豪屋,但他們對于其所處的城市,并沒有一種歸宿感與家園感。他們在城市中漂泊,沉湎于種種幻想或回憶,在這種幻想與回憶之中,他的自我意識得以孕育成形,并且在畫布上竭力呈現出云靄般的流動形狀,這成為畫家生命的意義與繪畫的理由。在井士劍的畫中,那些沉默無語的人雖然與朋友們共處一個空間,但他們時時在獨立蒼茫的暮色與悄然如水的夜色中沉思默想,讓思想與意識在飄浮的空氣中自由地游走,游走于光與影的交界之處,游走于晝與夜的交替之際,游走于靈魂與現實的交互轉換之中。當城市的居民酣睡于夢鄉時,他們卻無言地在湖上遙望著劃過天空的流星。
在這種略顯無奈的“江湖”游走之旅中,井士劍逐漸收起了自我體驗的同情,轉向對于他人的生存狀態的關注。“沒有氛圍的流星”是從尼采那里借來的意象,是一個孤獨的象征,它表明藝術家與詩人在大地上孤獨地注視著天空,他們曾經在城市中丟失了“詩意”的神圣光環,如今這種光環在晴朗的夜空中明滅閃耀。也許,海德格爾的預言更能表達我們這個時代的藝術的命運,他稱詩人(藝術家)是在世界的黑夜里更深入地潛入存在的命運的人,是一個更大的冒險者,他用自己的冒險探入存在的深淵,并用歌聲把它敞露在靈魂世界的言談之中。
使事物從一個世俗的實用中擺脫出來,恢復其原初的獨特性,并將這種新鮮直接帶入無言的凝想中,是井士劍在作品里處心積慮要達到的效果。在這個過程中,事物、現象和語言的片斷被一種活躍的思維聚集在一起,因而產生了一種揭示性的力量。井士劍作品中出現的石榴、流星、燈塔、山峰、游船和湖景,都是曾經輝煌的夢幻世界的余燼。而藝術家清醒時對夢幻的表達是自我意識的探尋。每個時代不僅夢想著下一個時代,而且還在夢想時推動了它的覺醒,它在自身內孕育了它的未來。
“懷舊”是井士劍作品中的重要主題,畫家在奢華的現實中看到即將逝去的無奈,也從對已逝年華的追憶中獲得新生。卡夫卡日記里有一段話可以作為現代人的銘文:“無論什么人,只要你活著的時候應付不了生活,就應該用一只手擋開點籠罩著你的命運的絕望……但同時,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記下你在廢墟中看到的一切,因為你和別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總之,你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已經死了,但你卻是真正的獲救者。”(卡夫卡《日記》,1921年10月19日)
如果你有機會到北京和上海的老餐館和酒吧,你會看到許多懷舊主題的設計與裝修,這其中明清家具與爵士音樂代表了不同的文化懷舊情緒。在我看來,普魯斯特的小說《追憶似水年華》和卡彭特的歌曲《Yesterday Once More》是現代社會中“懷舊”文學與“懷舊”音樂的象征。現代人被各種各樣的媒體信息所包圍,被大量繁殖的圖像所淹沒,他很難在自己的記憶中穿過信息與圖像的碎片,建立起對往事的完整回憶。他生活在大都市的海洋,為現實的物質需求而奔忙,內心深處卻渴望過去的時光,希望在現實的遭遇與藝術的創造中,召喚舊日的氣息,重溫過去的時光,這是在這個時代使經典與信心得以幸存的唯一希望。井士劍帶著這幅心中的圖景,去捕捉時代中富于生命的片斷,賦予他心中的樂觀主義以一種視覺的形式,去面對現代生活的混亂與絕望,走向靈魂的歸家之路。在技術對自然(也對人的歷史記憶)的侵犯中,人只有在“視覺形象”中,才能找到真實的內容,從而獲得一種補償性的自然,一種重建自我形象、在歷史的回望中把握歷史和自我。在我看來,一個藝術家,一個知識分子,能否把握住過去的事情,把握住一個活的自我形象,是他能否在這個時代有意義地生存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