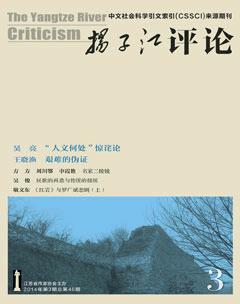從“歲月流金”到“鉛華洗盡”──對新時期以來文學期刊發展與嬗變的觀察與思考
潘凱雄
從“歲月流金”到“鉛華洗盡”──對新時期以來文學期刊發展與嬗變的觀察與思考
潘凱雄
如果給傳統的文學期刊下一個寬泛點的定義的話,那么它就是一種傳播文學信息的定期出版物。當然,傳播文學信息的媒介很多,除期刊外,還有報紙、圖書、廣播、電視以及現在的各種新媒體等。之所以要將文學期刊單獨拎出來予以討論,的確是因為她在新時期以來的文學發展中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成為觀察與思考這段時間我們文學創作、文藝思潮、文學運動、文學流變乃至整個文化生活嬗變的一扇重要窗口。
新時期以來先后公開發行的文學期刊大致在800種左右,發行總量達數億冊,如此龐大的數字共同匯成了這段時間中文學期刊的汪洋大海,而正是這龐大的數字無疑給我們的考察帶來了難以窮盡的困難。因此,即使作為這一時期文學期刊發展與嬗變全過程的親歷者與見證人,盡管我力圖描摹出其發展與嬗變的基本輪廓,但這種描摹無疑是個人化的,而隨之展開的評述則更是個人的一孔之見。
在我看來,新時期以來我們的文學期刊盡管品種繁多,規模不等,內容各異,但如果將其置于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發展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還是能夠發現其一些共同的發展軌跡:比如大致都經歷了從“計劃期刊”到“市場期刊”的身份轉型和從“風光無限”到“邊緣寂寞”的心理落差和尷尬處境。本文也將循著這樣的軌跡展開描摹與評說。
一、1978—1989:中國大陸文學期刊的流金歲月
1976年,伴隨著“四人幫”的被粉碎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結束,特別是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解放思想、撥亂反正成為這一時期我們社會生活的主旋律,長期以來桎梏著知識分子的文化專制主義的精神枷鎖正在逐步被砸碎,文學創作也開始迎來了自己百花齊放的春天,而裝點這個春天的一個重要標志便是眾多文學期刊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不僅種類多,而且發行量大。據《文藝報》統計:1957年,全國有文學藝術刊物83種,每月發行340萬冊(《文藝報》1957年第7期);而到了80年代中期,文學期刊的種類則飛漲到近600種,翻了七倍多,發行總數近25億冊,翻了近70余倍(《文藝報》1986年5月6日)。如《人民文學》月發行量曾達到150萬份,《收獲》120萬份,《當代》80萬份,就連青海省的《青海湖》、云南省的《個舊文藝》這些邊遠省市地區的文學期刊都可以發行到30萬份左右。80年代的文學期刊,無論是種類之多,還是發行量之大都高居中國期刊業之首,據統計,當時文藝期刊品種數約占全國期刊總數的八分之一,而印數則占全國期刊總印數的五分之一,足見讀者之眾,影響力之大。以文學批評期刊為例,按理說,因其專業性所限,其數量理應不會多,但即便是不多也有幾十種,差不多大多數省份都有一兩種專業的文學批評期刊,由此足見一斑。
這一時期的文學期刊從外在形態上看大致呈現出如下特點:第一,刊期上月刊與雙月刊雙峰并峙,前者謂之文學月刊,后者謂之大型文學月刊,顧名思義,既是大型,也就標志著篇幅大于月刊,因而容量也隨之大于月刊,這種大型文學月刊批量的出現可以說是這一時期文學期刊中一道嶄新的風景,是以往文學期刊中所不多見的。第二,主辦單位性質相對集中,即各級文聯和作家協會、部分中央部委及行業協會、部分文藝類專業出版社。如《人民文學》、《詩刊》、《中國作家》等隸屬中國作家協會;《收獲》、《上海文學》等隸屬上海市作家協會,《鐘山》隸屬江蘇省作家協會;各文藝專業出版社主辦的則如《當代》隸屬人民文學出版社,《小說界》隸屬上海文藝出版社,《小說月報》隸屬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部分中央部委及行業協會主辦者如《啄木鳥》之于公安部等等。第三,分布區域廣泛,形成了一個密集的文學期刊網絡,從中央到省、市、地區乃至縣一級都有自己的文學期刊,如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保有相當發行量的《佛山文藝》就出自廣東佛山這樣一個縣級市之手。第四,內容囊括文學領域的方方面面,既有統括小說、散文、詩歌、紀實、批評和譯作等不同門類的綜合性文學期刊,也有上述文體分門別類的專業文學期刊,既有刊發原創性作品的,也有選登、摘發類的選刊。
文學期刊外在形態的這些共同特點歸結起來其實也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品種眾多,個性不足;形態各異,結構雷同。如此這般無疑為它在下一時期走向邊緣和寂寞埋下了伏筆,這當然是后話,暫且按下不表。然而,無論這些文學期刊的外在形態如何缺乏個性,如何結構雷同,但由于它們共同置身于80年代的中國這樣一個特定的時空中,因而,它們對80年代的中國文學乃至整個國家的文化生活都發揮了不可或缺、不容小視的巨大作用。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考察80年代的中國文學發展乃至文化生活的面貌,離開了對這一時期文學期刊的考察無論如何都是一種巨大的缺失和明顯的片面。具體來說,文學期刊在這一時期的核心競爭力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80年代的文學期刊將文學提升到了推動時代發展的新高度,創造了一種時代特色極為鮮明甚至是開時代之先的文學,中國文學發展新的歷史時期由此而開辟。眾所周知,伴隨著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實事求是成為那一時期國人生活的主旋律,但思想的解放、亂的撥正和對“是”的追求終究都需要一個漸進和漫長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文學期刊常常通過自己的行為——無論是刊發作品還是組織活動——扮演了急先鋒的角色。比如《班主任》、《公開的情書》、《被愛情遺忘的角落》、《大墻上的紅玉蘭》、《陳奐生上城》、《古船》等一大批膾炙人口、足以令一時洛陽紙貴的文學作品都是首先通過文學期刊與讀者見面,其影響力與社會反響都遠遠超出了文學自身,當時一些在社會還屬十分敏感的社會政治問題,都是由文學期刊上刊出的這些文學作品提出了第一聲質疑,發出了第一聲吶喊,諸如“血統論”、“教育問題”、“知識青年問題”、“反右擴大化問題”、“知識分子問題”等等。我們固然不能說文學期刊刊出的相關文學作品對解決這些問題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但它們以其敏銳的政治觸角、生動的藝術形象在突破思想禁區、啟蒙民眾心智等方面所發揮的獨特作用則是毋庸置疑的。再比如,自上世紀50年代末“反右擴大化”開始到十年“文革”浩劫,對知識分子身心的迫害發展到登峰造極,一大批作家藝術家蒙受不白之冤,當他們在政治上尚未被平反昭雪之前,是這一時期的文學期刊悄然地將他們的名字連同其新作重新公開與讀者見面,用自己所能企及的行為率先為他們洗刷了歷史的冤屈,這樣一種事實上的平反其影響力絲毫不亞于一紙紅頭文件。凡此種種,無怪乎后來有學者評說:80年代的文學轟動是成功地引爆了政治、社會的興奮點,即使是在文學最有轟動效應的那些時候,公眾關注的也并非文學,而是裹在文學外衣里的那些非文學的東西。這種評說是否周全姑且不論,但至少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那個時期文學期刊的種種作為所產生的社會反響。后人常以春天來描述1978年以后的中國,那么說如雨后春筍般涌現的文學期刊是這個春天里一朵朵艷麗的報春花則一點也不為過。
其次,這一時期的文學期刊不時引領推動著這一時期的文學思潮,而文學思潮此起彼伏的涌動在一定程度上又推動著社會的進步和思想的解放。從“傷痕文學”到“為文藝正名”到“朦朧詩”到“反思文學”到“文學尋根”到“文藝學方法論”到“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到“重寫文學史”……這一時期由一場場文藝爭鳴構成的文藝思潮大都是由文學期刊所引發并展開,一連串文藝思潮的此起彼伏不僅推動了文學本體的回歸和走向多樣化,而且其影響所及則遠非一個文學界所能涵蓋。
第三,這一時期的文學期刊催生和促進了一些文體的發展,中篇小說在這一時期的異軍突起就得益于一批大型文學期刊的催生。比之于一般的文學月刊,這些大型文學雙月刊篇幅長,容量大,適于刊發中篇小說,從而促成了中篇小說的興起。在當時號稱大型文學雙月刊“四大名旦”的《當代》、《收獲》、《十月》和《花城》(另有說為《鐘山》或《中國作家》)上,每期都有相當分量的中篇小說見諸于版面,而一些在當時影響甚大、成就卓著的中篇小說諸如《人生》、《天云山傳奇》、《綠化樹》、《布禮》等也都是先刊之于大型文學雙月刊上。作為一種特定的文體,中篇小說以既針對現實作出敏捷反應,又能對一些問題作較為深入的開掘見長,它所承載的內容,短篇小說容納不了,但又未必需要長篇小說那樣厚重的積累。很難想象,如果沒有一批大型文學雙月刊的催生和促進,中篇小說能夠在這一時期得以如此迅猛的發展,如同在1949至1966年的十七年間,為人所稱道的不是長篇小說就是短篇小說而鮮有中篇小說。與中篇小說這一文體命運相似的則還有中長篇紀實文學,這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表現則尤為突出。
第四,這一時期的文學期刊對作家身份與地位的確立至關重要。如果說前面所說的一些文學期刊悄然地用自己的作為先于政治上為一些作家洗刷不白之冤的現象尚不具普遍性的話,那么,從創作與傳播層面看,80年代的作家和文學期刊之間那種水乳交融的關系則無疑具有廣泛的共性。一方面,80年代的作家不像現在的一些作家那樣或直接出書,或依賴于網絡,當他們開始文學創作的時候,總是要先在文學期刊上發表作品,然后再把散見于各種文學期刊上的作品集結成書,從這個意義上說,作家對文學期刊有一種依賴關系;另一方面,文學期刊同樣需要高度重視各個年齡段的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使期刊成為作家的集散地和培養作家的園地。幾乎可以這樣說,如果以簡單的作家代群劃分,出身于80年代以前的幾代作家中絕大部分都是通過文學期刊而開始自己的創作生涯并由此走向文壇的。
最后,這一時期的文學期刊對80年代中國文學生態的初步形成也發揮了自身的作用。在文化專制和文化集權的統領下,文學所呈現的形態只能是千篇一律,談文學生態既不現實也不可能,而當思想的牢籠一旦被沖破,文學的生態問題自然就被提到了臺面。立足于今天的視角,從大的層面我們大致可以將文學的生態描述成主流、新潮與消費三種狀態,而這樣一種三分天下的格局在80年代的文學期刊那里就已初露端倪。那個時期為數眾多的文學期刊在某種統一化的模式里擁擠了一陣子后便開始追求不同的個性,它們的不同選擇悄然孳生了文學的分流,比如《人民文學》、《當代》、《十月》等選擇了主流文學,《收獲》、《花城》、《鐘山》等偏向于“新潮”“先鋒”“實驗”,而《今古傳奇》等則選擇了消費,而這種分流恰恰是文學生態發生變化的一個重要標志。
不難看出,從1978到1989年的這一時期,文學期刊在當時的文學生活乃至社會生活中的位置舉足輕重,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這一時期的文學不僅是期刊中的文學,而且是期刊化了的文學,眾多的文學期刊孕育出了這一時期的文學,稱其為中國文學期刊的流金歲月一點也不過分。
二、1990—今:洗盡鉛華,回歸本位
當時光步入上世紀90年代,文學期刊在中國風光無限的流金歲月漸次逝去,其實,這樣一種轉變還可以追溯到80年代末,只不過人們在蜜月中沉溺的時間太長了而不愿正視現實而已。當文學期刊的鉛華真的褪盡時,那些期刊人一方面無限緬懷逝去的那段美好時光,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陷入惶惶然失措之中。
如果說80年代初中國社會生活中的關鍵詞是“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話,那么,到了90年代初,這個關鍵詞則為“市場”和“轉型”所替代,而正是這四個看起來不怎么起眼的漢字將曾經處于文學核心位置的文學期刊給沖擊得七零八落,直到淪為邊緣與寂寞的境地。
伴隨著90年代以來中國市場經濟的整體推進,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形成的數十年一以貫之的文學體制也產生了強烈的沖擊,文化市場的初步形成,文化傳播方式的不斷豐富,使得文學期刊的生存環境出現重大轉變。隨著政府行政撥款的逐步減少和文學期刊發行量的銳減,大多文學期刊的生存困境日漸突顯,于是關門的關門,“更張”的“更張”,為了化解市場危機而解決生存問題,眾多文學期刊紛紛以“市場”為中心,樹起了“轉型”和“改版”的大旗,上演了一出出“你方唱罷我登場,各領風騷三五年”的熱鬧。
面對“市場”與“轉型”,眾多文學期刊的表現明顯是無所適從,因而所采取的措施自然地烙上了應急性和功利性和印記。在這個過程中,那種明顯的帶有商業性的炒作或是直接與商業的聯姻的所謂“轉型”自不用多說,而更多的是那些以所謂“文學策劃”為名所進行的“轉型”其應急性與功利性則要隱蔽得多,以至于一些“策劃”、“命名”、“炒作”的科學性早已被置于九霄云外。歸結起來,看似熱熱鬧鬧的“策劃”與“命名”之手段其實也很單調:無非是其一,在一些核心概念前加上“新”或“后”一類大而無當的狀語,于是就有了“新寫實”、“新體驗”、“新狀態”、“后現代”、“后殖民”之類似是而非的“策劃”與“命名”;其二,簡單的代際與群落劃分,諸如“70后”、“80后”、“美女作家”等;其三,諸如“身體寫作”、“行走文學”一類意義含混曖昧的“命名”與“策劃”。看上去,這一個個“精心策劃”出來的辦刊手段熱鬧非凡,對某種文學現象也不無概括之意,但更多的還是為了“市場”的應急方案,與文學與市場的內在需求并無多少關系,這樣的“思潮”與80年代文學期刊對文學思潮的引領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撇開這些浮躁的應急“轉型”辦法不論,重新定位是這一時期文學期刊為了適應市場而“轉型”的常用辦法之一,而這種定位的調整使得原來總體上個性缺失、結構單一的文學期刊多少現出了一些差異性。歸納起來,90年代以后文學期刊的定位調整大致有五條路徑:一是由“純”向“雜”轉變,即在保留一定文學板塊的同時,走泛文學乃至文化路線,試圖使期刊具有針對性地直面鮮活的現實社會,走出單一的文學小圈子;二是打破區域界線,特別是地方性的文學期刊突破區域辦刊思路,以開放的視野與國家整體的文學態勢接軌;三是走個性特色鮮明的“專”與“特”之路,對目標讀者進行細分,從大眾傳播轉化成針對某一特定人群的傳播;四是變一刊為“一刊多版”,試圖拓展刊物的生存空間,在保留文學版的同時,開辟若干新的試驗園區;五是干脆棄文學而另覓文化、娛樂、綜合、新聞等其他門類。當然,對以上五條路徑的描述也只是相對而言,事實上,一些文學期刊對自身定位的調整不少也是在靈活地采用組合的辦法而非簡單地一條道兒走到黑。其間成功的經驗和不成功的教訓都有必要予以認真總結與反思。
論及成功的經驗,如下四條是值得記載的。即一,打破重復辦刊、千刊一面的慣例,追求特色的鮮明,追求人無我有人有我優的個性目標。80年代的文學期刊,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由小說、散文、詩歌、紀實和批評五大板塊組成,雖也有變化者,但無非是篇幅的多寡與重心的不同,而重新調整定位后的一些成功的文學期刊則顯然不同于這五大板塊結構法,一些特色欄目令人耳目一新,也由此吸引了讀者眼球,如《天涯》的“民間語文”、《作家》的“作家地理”、《佛山文藝》的“城市新移民”等;二,從盲目的大眾傳播走向相對準確的小眾傳播,根據讀者的年齡、性別、職業、文化程度、所屬地區等差異,對目標讀者重新定位并針對這些特定目標讀者的接受心理和審美趣味進行有的放矢的定向傳播,比如《萌芽》將目光聚焦于中學生群體,啟動“新概念作文大賽”,以此吸引了龐大的中學生群體對該刊及系列出版物的關注與追捧。三,充分做好風險評估和長期規劃,穩中求變,不輕易放棄刊物原有的影響力及連續性。如同樣隸屬于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的《小說家》變身于《小說月報·原創版》就是成功的一例,它不是輕易的放棄,而是充分利用了《小說月報》已經形成的品牌效應將兩刊予以重組,一個“原創”一個“轉發”倒也頗成系列與規模,改了一個刊名救活了一家期刊,這是穩中求變成功的典范。四,以辦刊的核心價值為統攝,追求風格的多樣化與互補性。如果一家文學期刊形象模糊,而且搖擺不定,就無法擁有穩固的讀者群體,反之,核心價值的基本統一,具體內容的差異互補就能形成良性互動,比如《佛山文藝》與其子刊《打工族》就是在同一核心價值的前提下盡量考慮同一類型讀者內在細微的差異,互相借力,互相提攜,因而產生了共贏的結果。
反過來,對另外一些定位調整不成功的文學期刊來說,大抵也是在如下四個方面步入了誤區。首先,誤以為“雅俗共賞”足以包打天下,結果卻往往是陷入雅俗不賞的尷尬,文學期刊的調整定位一定要有所放棄或拒絕,想什么都要的結果則常常是什么都抓不住。其次,盲目跟風,從一種個性缺失結構單一走向另一種個性缺失結構單一。當《萌芽》將目標讀者定位于中學生群體并獲得成功后,一時就有許多刊物紛紛辦起了自己的“中學生版”、“校園版”;當《散文》推出萃取刊發于海內外報刊散文精華的“海外版”時,又催生了一批“選刊”的出籠,如此毫無個性創意的跟風期刊其結果也就注定了它們的短命。再次,輕易放棄刊物長期的優勢與特色,盲目地一味迎合所謂消費者口味,在文學與市場間搖擺徘徊,導致兩邊都不討好,相反,《收獲》、《當代》等品牌期刊的謹慎態度倒是穩住了基本的市場份額,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只有穩定的核心價值才能抵御為善變為旨歸的時尚沖擊。最后,變臉過于頻繁無異于飲鴆止渴,一些文學期刊在“轉型”過程中頻繁玩起了“變臉”的花活兒,看似隨機應變,而這種隨意的背后實則暴露了辦刊人缺乏深入的市場調查和可行性論證,簡單地視改版為包治百病的良藥,以至于讀者連這本期刊的基本面貌都遺忘得一干二凈,這又怎么可能獲得生機呢?
綜觀上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期刊的種種嬗變,以市場為中心進行“轉型”確是這一時期文學期刊的主旋律,“轉型”的結果無論成功還是失敗,有一個基本事實我們卻不能不承認:即這一時期文學期刊單品的發行總冊數大大下降,文學期刊在80年代那種單期多則上百萬、少則幾十萬的“盛世”幾近絕跡,最多的單期不過三四十萬,能維持在月發行5萬份左右當屬幸事,而絕大部分文學期刊的單期發行數已下滑至萬份以下,有的甚至只剩千余冊。伴隨著發行量的下滑,其社會影響力必然日漸式微。無怪乎一些文學期刊的從業者在談到自己的生存狀態時不無悲涼地慨嘆:我們被邊緣化了。盡管筆者更愿意用“常態化”來描述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期刊的生存現狀與嬗變,但比之于80年代文學期刊在中國大陸的那段流金歲月,邊緣化三字的描述倒也大致不謬,且生動形象。
三、從“歲月流金”到“鉛華洗盡”的思考
中國的文學期刊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其生存境遇及社會影響力所遭遇的巨大反差難免會導致論者對其評價的莫衷一是:持“今不如昔”論者有之,他們無限眷念逝去的美好時光,痛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將曾經紅紅火火的文學期刊給撕扯得七零八落,認為文學期刊與市場化之間與生俱來的相互排斥,市場化就意味著文學期刊的最終消亡;持“扼腕相慶”論者有之,他們更尊重市場的現實,認為80年代文學期刊在這片土地上的風光不過是一種“虛熱”,曇花一現正常不過。
其實,如此巨大的反差都還只是局限在文學期刊傳統的出版業態范圍之內所作出的評價,倘放眼于本世紀以后愈來愈呈燎原之勢的數字化大潮,情形或許會變得更加復雜。對此,筆者更愿意本著尊重事實、尊重歷史、尊重未來的基本態度對尚未終結的文學期刊命運之變化作出以下基本判斷。
首先,無論如何都不能低估80年代文學期刊對中國的文學發展、文化發展乃至社會發展的巨大貢獻,不僅不應低估,而且還應給予充分的正面評價。現在時有論者以“文學性不高”為由來低估80年代文學期刊的貢獻,在他們看來,文學期刊在80年代的風光不過是種種“非文學”因素所導致。我承認這種說法具有部分的事實依據,但更以為此說完全脫離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對文學的理解也過于偏狹。沒錯,從純藝術的眼光看,80年代文學期刊上刊出的一些文學作品其藝術上確有粗糙生澀之處,其敘事遠不及今天的作品來得圓潤與嫻熟。但這些作品從思想觀念到文學觀念對當時中國社會文化生活的巨大沖擊以及所起到的先鋒開路作用無論如何都是一種客觀存在。
其次,如果跳出單一的文學圈,90年代以來文學期刊出現的嬗變其實也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中國社會與思想的巨大進步,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期刊所遭遇的“冷”恰是它本應有的一種常態。我始終認為,觀察事態變化的本質固然可以有多種視角,但其生存環境在多種視角中無論如何都是不可舍棄的。正因為如此,文學期刊從80年代的“熱”到90年代以的“冷”,如此“世態炎涼”莫不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而“熱”與“冷”的兩相比較則不難理解何謂“常態”,何為社會的進步了。比如,80年代的文學期刊之所以不時引起轟動效應的一個重要原因恰在于它率先提出并揭示了不少尖銳的社會問題,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些問題本來完全可以不由文學期刊和文學作品來提出來揭示,但當時社會種種條件的不具備、不允許,文學期刊自覺不自覺地承受了那種“生命之重”。而伴隨著社會的持續開放、思想的不斷解放,傳播方式多了,傳播渠道寬了,言路暢通了,文學期刊和文學作品難以引起轟動不就正常不過了嗎?這到底是社會的進步還是退步,而對文學期刊而言到底是邊緣還是常態?我想只要不是囿于文學一己的小圈子而難以自拔,是不難得出正確答案的。
最后,我想說的一點對曾經的文學期刊人而言或許更無奈、更殘酷。面對本世紀以降方興未艾的、不可逆轉的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生存數字化和閱讀分眾化的大潮,無論是傳統的紙介形態還是新興的數媒形態,在一定時間內,文學期刊的個性化與小眾化趨勢同樣不可逆轉,至于伴隨著傳播工具、傳播手段的不斷創新,期刊這種樣式本身究竟會發生什么變化乃至是否還會存在或許都會成為一個十分現實的問題。如果說自上世紀90年代之后文學期刊開始出現的“式微”還只是單一紙媒市場需求的變化,其走向當時還未必看得十分清晰的話,那么,現在的這種判斷無疑就要明晰得多,這同樣是不以個人喜好與否的意志為轉移。進行這樣的描述看起來很殘酷,但究其實只要想清一點也就釋然了,那就是文學期刊本身的結局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學不死、閱讀永存。對文學人讀書人而言,這就夠了。
(本文依據筆者在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的演講整理而成。)
※著名文學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