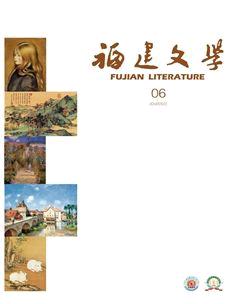寫作者言
游刃
●寫作與體重
與受胃病和饑餓困擾而消瘦的杜甫其詩之重相反,壯碩結實的李白的詩則以輕代表了文學的另一個巔峰。至少在明代之前,所有最優美的詩句都與輕有關(明季以降,文學的大部分注意力轉為敘述夢境之重)。有關人類是外星人的后代之說已無稽可考,但人類仰望星空時的情感則有如遙望故土家園一樣帶著天生的眷戀與鄉愁,每個人都有先天的變輕而飛翔的欲望。如何使自己輕到可以飛翔?減肥就是人類的潛意識,附著了我們與生俱來的一個夢想。如果說寫作就是對潛藏在我們體內夢境的一種轉移與敘述,那么,寫作同樣也是應對生活之重的反作用力,是一種象征意義上的減肥。在寫作中,體重是一個最大的難題,因此也是一個永恒的母題。保爾·瓦萊里說,我們“應該輕得像鳥,而不是像羽毛”。從這個意義上說,寫作者就是處于減肥焦慮中的鳥人。
●寫作與重復
布魯姆研究莎士比亞發現,莎士比亞是個剽竊天才。“他拿走一切可以拿走的東西。每當他在普盧塔克的書中找到合適的段落,就把它改成詩。” 歌德則對自己的寫作充滿悲觀,主要是基于這樣一種認識:如果我把應歸功于一切偉大前輩和同輩的東西除掉,剩下來的東西也不多了。艾略特甚至指出:“不成熟詩人模仿,成熟詩人抄襲。”米蘭·昆德拉在《帷幕》一書的開始就追問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一位當代作曲家,他創作出一部奏鳴曲,從形式到和弦到旋律都與貝多芬相同,那么又會怎么樣呢?藝術史與“純粹的”歷史相反,它是永遠現時的,是價值的歷史。這就意味著,在純粹歷史中的滑鐵盧如果被遺忘,歷史就會變得不可理解,而在文學史中,前人的寫作只是提供一種價值評判,其寫作作為事件已不具有意義。如果把寫作看作是一個純粹的事件,那么,它就會在文學史的時間縱軸上構成一種反價值行為。這個認識被博爾赫斯在他的小說《〈吉訶德〉的作者彼埃爾·梅納德》中推到了極端:這個叫梅納德的人“寫”了與塞萬提斯完全相同的《吉訶德》。小說分析了兩人完全相同的一段話,塞萬提斯生活于十七世紀,這段話“僅僅是玩弄辭藻,把歷史吹捧一番而已”。而梅納德與威廉·詹姆斯是同時代人,同樣這段話,則體現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實用主義歷史觀。貌似對前人的抄襲,作為一個寫作事件,實則是一次對歷史的勇敢反叛和對現實的深刻介入。
●寫作與白晝
任何一本書,都不可能有真正的開頭和結尾(如同我們設想一部時間史)。寫作只是參與宇宙無限過程的一個極短暫的片刻,用一小片陰影替換下那無邊的黑暗。這是一個帶有宗教情感性質的想象,因此帶有罪性。寫作就是為了去除掉日常枷鎖。我漸已習慣在白天寫作,即使如此,我仍不免陷入玄想、回憶、飄移無定和虛構,仍不免懷疑我的所見。一個人做白日夢或許就是一種佞妄,因他混淆了晝夜的功用,不在宇宙的秩序中。要是我輕易進入迷狂狀態,那我真是瀆神,幸虧沒有,但想入非非畢竟總歸有些虛妄。但丁說:“我——宇宙的破壞者,罪該萬死。”一想到還存在我們能參與其中的宇宙,它的無窮無盡與無邊無際,對這句話我便一點也不覺得夸張。
●寫作與雙手
性是寫作者腦海上空變幻多端的云朵。李漁在《閑情偶寄》里有一個奇怪的色情想象:共處一室的孤男寡女,他們的雙手如果不放在桌子上,就會出現在床笫上。基于如上假設,女人學習琴棋書畫,不過是為了讓她們的雙手沒得空閑。正是雙手的忙碌淡化和掩蓋了人的性需要。這是動用一整套文化系統對女性進行的規訓,是試圖對性進行壓抑和為性尋求物化對象的策略。有關性需要及其滿足的想象和敘述,已經成為現代文化強加給人的心理陰影:寫作者將使其手指成為力比多轉移的通道,以自己的雙手進行自我解魘和驅魔。難道寫作者的雙手作為感官,傳遞的是交媾的奧妙、色情欲望和性愛的美學?
●寫作與禁欲
托名為戰神山信徒的戴奧尼索斯在《天國階級》一書中提到那個經常以火為象征的“寫作的圣徒”。閱讀、傾聽、見聞、推測、沉思、書寫,竟然完全暗合了煉金術士對自己精神改造的整個過程(煉金術首先是精神修煉)。正如煉金術士要真誠,不可有逆道的投射一樣,為藝術而藝術的宗教也需要禁欲主義。有哪一種書寫能在暗中容納下宇宙論的復雜圖式?我們寫下的文字里也許有著波納文圖拉所說的被賦予了“星辰之德”呢。寫作是為了尋找開啟那座“玫瑰花園”的密鑰。也許有人將以文學史的諸多盛開的欲望之花來否定這些“寫作的圣徒”心中的神靈與魔術,然而,可悲的他們有所不知,即便在波德萊爾那里,欲望深處仍是一座偉大的“深遠幽奧的和諧”的象征的森林,而在蘭波那里,感官的放縱最終成為了天眼通之路。在榮格看來,一個沒有神心的人怎么可以進行精神修習和對自己的靈魂進行護衛?人們啊,那些昏暈、腐爛、頹靡、絢麗的誘人之果不過是幻象!你的書寫根本上也是用一種隱語描述著靈魂的轉變。禁欲是用功之人的命運。寫作即禁欲,過一種象征的僧侶生活。
●寫作與慢
生活在一世紀的昆提連(M.F.Quintilian,有些修辭學書上又譯作昆提利安)是古羅馬古典修辭理論集大成者,在那個極度重視口腦統一的雄辯時代,他看到了前人從未看到的使用筆桿子的好處,第一次將寫作提升到了與口頭表達相同的地位,他認為:雄辯的根基在于寫作。(劉亞猛《西方修辭學史》)盡管如此,他還是指明了手在寫作中的局限:手的動作慢,思想和寫作有兩種不同的速度,但是手的緩慢也有益處,在非口述情況下,寫作必須不與聲音而是與手、與肌肉相聯系,與手的緩慢性相連時,文稿的完成不至于過快。羅蘭·巴特在《符號學歷險》里,非常贊賞昆提連對寫作與身體的關系這個獨特的體驗。有一個論點頻頻被提及:寫作是慢的藝術。其實,關于慢的藝術,似乎應當基于這樣一個生理基礎,即手的動作的“慢”與思想及口頭表達的“快”的無奈對比,并對這種無奈的長期壓抑所形成的生理能量。羅蘭·巴特智慧過人,是他從寫作這個行為中,依賴身體感覺建立了一種與連續性無關的興趣。還是從手開始,他說:“寫作是手,因此是身體,它的沖動、抑制、節奏、思想、變動、糾葛、躲閃等等,簡言之,不是由于靈魂,而是由于被其欲望和無意識所點燃的主體。”(卡勒爾《羅蘭·巴爾特》)正是手的慢,寫作中帶動了身體的歡愉。
●寫作與咖啡屋
伏爾泰說過,作家就是一些與世隔絕的人。一本傳記是這樣描述傅立葉的:“從一開始作為一名與世隔絕的、無人問津的外省自學成才者,到他最后的歲月,成為咖啡館和巴黎王室閱覽室怪異的常客之一”,“他都要想方設法使自己同流行的觀念和主流思想脫離關系。”真正的作家如同這樣一些烏托邦發明者,他們是一些寄身于并不引人注目的小咖啡屋的孤客,他們把那里作為思想與語言的煉丹房,自由恬淡,冷眼旁觀,想入非非。他們目光渙散,卻不僅有著與烏托邦人相同的對社會與未來的想像力,更具有一種不為人知的能理解現實及其可能性的純粹而樸素的洞察力。《烏托邦之死》的作者拉塞爾·雅各比指出,十九世紀中葉開始,自從離開那些小咖啡屋走進官僚機構、大學討論課和會議室,這種洞察力已逐漸喪失,知識分子已由烏托邦走向鼠目寸光。
●寫作與床
福樓拜與普魯斯特都是屬于自閉性極強的作家,雖然他們各有各的原因,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他們自閉世界的中心都是一張床。這是處于身體外部的一張象征的床,一般的寫作者難以擁有的,即便一個躺在床上寫作的人,離這張極端的床也是遙若云泥。但是,如果把作品看作是一個白日夢,那么,每個寫作者的身體里都有一張床,一張與黑暗、欲望、靈魂,最終和死亡聯結在一起的床。與其說寫作是返回內心,不如說是回到那張床上安憩,放置好四肢以及各個器官,準備做一場夢。這樣看來,寫作如同床上戲,每一次的寫作都是一個對自己軀體進行自我擺布與調整、編織幻象的復雜過程,這一切無非是為了能感覺到那張床還在體內。
●寫作與對立面
威廉·布萊克在其《天堂與地獄的婚姻》里寫道:“如果不是通過‘對立面,任何事物都不能前進。吸引與反感、理性與激情、愛與恨,都是人類生活所必需。”卡爾維諾指出,巴爾扎克的《不為人知的杰作》傳達了一個思想:真理潛藏在無知與謬誤之中。十九世紀昏睡過去的想像力,到了卡夫卡那里終于被喚醒。米蘭·昆德拉認為,卡夫卡實現了夢與現實的交融,小說終于可以擺脫真實性的枷鎖。喬治·巴塔耶在諸多大師身上發現了文學中惡存在的意義,找到惡在文學中的最高價值。安德烈·布勒東則宣稱,所謂的超現實主義,無非就是將生活與死亡、真實與幻想、過去與未來、溝通與阻滯不作為對立面看待。寫作的真義之一,就是它能使我們發現并重新界定那個對立面。
寫作與字數
一堆沙子,減去一粒,仍是一堆沙子,再減去一粒,仍是一堆沙子,以此類推,導向一個結論:一粒沙子也是一堆沙子。與之相反,寫作則是一個逆堆悖論:一個字不能構成一篇文章,兩個字同樣不能構成一篇文章,三個字也同樣不能,以此類推,導出這樣一個結論:即使寫無限多的字也不能構成一篇文章。不能陳述本質,一切皆為幻象。可寫作真能陳述本質嗎?
●寫作與讀者
“我并非是為了少數精選的讀者而寫作的,這種人對我毫無意義。我也并非是為了那個諂媚的柏拉圖式的整體,它被稱為‘群眾。我并不相信這兩種抽象的東西,它們只被煽動家所喜歡。我寫作,是為了我自己和我的朋友們;我寫作,是為了讓光陰的流逝使我安心。”(博爾赫斯《沙之書·前言》)十幾年過去了,關于讀者,這段文字仍然能令我感到當年內心神話破滅時的震撼。是的,我寫作,我就要你做我的讀者,我的神:你清晰,你寬容,你領悟,你辨識。你總在介入卻并不現身,你細細讀過卻不留痕跡。我寫作,我永為你留著唯一的通道,我假想你的身影,你的眼眉和手指,你越來越迫近我的呼吸與心跳,然而,我永不知道你是否進入。我寫作,我更加自重也倍感孤獨,因你既在場又不在場。
●寫作與顏色
我們從未真正理解過也從未能描述過顏色。米沃什就曾質疑:南瓜黃熟了,然而實際上南瓜是橙色的,為什么要用橙子,用orange來形容?北方國家的人有幾個見過橙子?古銅色、天藍色、米黃色……如果不借助類比,離開具象的物體,我們怎么能表達出顏色與顏色之間的細微差別?可是,類比像是一條無限循環的鏈條,用一個喻體來形容另一個喻體,如此反復,最終,我們能追索到哪里才能停止下來?我們的局限就在于我們并沒足夠的能力分辨出一種紅色與另一種紅色的差別,貌似相同的顏色不過是處于近鄰關系的兩種不同顏色而已。紅并不是紅。我們所見的紅色并非就是原初的紅色。寫于十四世紀作者佚名的《泥金抄本之技術》提到三種主色:黑、白、紅,其余顏色則為人工色。三色合一,喻示了神的三位一體,喻示了無限的存在,其中紅可以理解為圣子,顯示神的奇妙。紅只是模仿了原初的紅,從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越過其中無限循環的顏色與比喻的鏈條,我們復制下那個關于“紅”的標記、表象甚至幻象。
責任編輯 林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