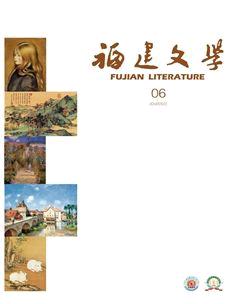被一只蘋果穿透的時光
鄭曉紅
1
長在梢頂上的蘋果最紅,這個道理我打小就知道。所以,我們倆抱住斜伸出去的大樹杈像翻雙杠一樣用腿鉤住,一個翻身,就輕松地騎在樹杈上了。下面的事更簡單了,我們倆蹬住樹杈,一級一級的,樹杈變成樹股,樹股變成樹枝,腳底下越來越顫悠了,我們就越接近頂梢了。最紅的蘋果掛在最高的梢子上面,擠眉弄眼的,像專門給人下套似的。
果然就是個套。我們倆晃晃悠悠地墜在高處的枝子上,竭力向最耀眼的蘋果伸出手時,樹底下就傳來一聲粗蠻的吆喝,蘋果樹的主人,一個粗胖松弛的老男人,揮動著手里的鐵锨,向我們倆做出兇狠的表情。她馬上哭了起來,她的眼淚讓我猝不及防,一直以來都是她罩著我,我百依百順地跟著她跑,可是,在緊急關頭我還沒來得及向她討教我們該怎么辦時,她先哭得一團漿糊了。老男人在下頭揮舞著鐵锨,他問我們是自己下來還是讓他像鏟樹瘤一樣鏟下來。我鎮定一下回答他,如果他不向老師告狀我們就自己下來,否則我們就住在蘋果樹上。他兇狠地答應了我的條件,于是,我們倆像尺蠖那樣一拱一伸地退下來。
我們倆還沒沾地他就一手一個捏住了我們的后脖子,像提線木偶一樣,我們倆蕩蕩悠悠跌跌絆絆的,被提到了果園隔壁的學校。學校里正在集合放學路隊,全校的孩子都推推搡搡地聚在那兒,她哭得更大聲了。我忙不迭地告訴校長,我們一個蘋果都沒有摘,一個蘋果都沒有吃,也沒有一個蘋果被撞得落下來。那你們沒放學跑到果園做什么?你們爬到人家樹上做什么?我轉頭看著她,她哭得渾身哆嗦,兩條清鼻涕像兩條吊在絲上的毛蟲,索落落吊下去,哧溜溜吸上來。我笑了一聲,忍住,沒忍好,又噴出來一聲,忍不住了,我捂著肚子笑得彎下腰去。
這下糟了,接下來連著一個禮拜的放學路隊集合,我都一個人站在前面示眾。她站在隊伍里面,和其他孩子說說笑笑的,偶爾也看著我,只是匆匆一掃。我垂著腦袋,頭發全都垂落到前面來,在頭發縫隙里,我模模糊糊地看著她,模模糊糊地想起梢頂上最紅的那只蘋果,最顯眼,最好看,最高,但只有一個。我甚至模模糊糊嘗到了那只蘋果的滋味,孤零零的滋味,她從前的千好萬好再也溫暖不了的凄涼滋味。
清早,她像一個禮拜以前那樣,來喊我一起上學。我慢吞吞地提著書包出來,她來拉我的手,我讓開了,把書包帶子一圈一圈繞在手上。她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踩著清早的露水。她梳得毛毛糙糙的兩條長辮子在背上甩過來甩過去。我們必須經過那個果園,必須看見最高的那棵蘋果樹高高地越過墻頭,最紅的蘋果還留在枝上。她飛快地側過頭去看,我們倆一起盯著那只差點摘下來的紅蘋果。粗胖松弛的老男人扛著鐵锨準備打開果園鐵門的鎖,他轉過身看著我們倆,臉上帶著捉摸不透的笑容。
蘋果都熟了,其它的蘋果都紅著半邊臉,只有梢頭的那一只,紅透了。下課的時候,我們都趴在漏花墻的十字里看著那些成熟的果實,他們都吸著鼻子,好香啊,但我聞不到,我猜她也聞不到,因為她跟我一樣,始終默默無語。我看見那些果子沉甸甸地吊著,憂郁、沉重、欲言又止,其中一只果子,掉到了地上。
那些人挎著籃子摘蘋果,有一個女人摘了一只咬了大大一口,發出大驚小怪的聲音。那些豐盈的蘋果樹很快消瘦下來,像一個棄婦,披著一身破破碎碎的綠裝。當所有的蘋果樹都瘦下來之后,果園安靜下來,它們的樣子,像是沉浸在往事的回味之中,暫時停止了生長。在這個果園里,時間不見了,風也不見了。但我發現,那棵最高的蘋果樹上,頂梢的那只紅透了的蘋果還在。原來,時間藏到那只蘋果里面去了。
時間給人使了障眼法,誰都看不見那只最耀眼的蘋果,除了我們倆。
她待我加倍的好。那件事之前,都是我幫她挎著書包,我把手主動地交到她手心里。可現在,全倒過來了。她背著我的書包,她一次次想重新拉住我的手。
我們倆經過果園的時候,會突然步履匆匆,做出急著趕時間的樣子。但那只蘋果,高高地長在枝頭,沒人摘它,沒人打落它,沒人去搖一搖那棵蘋果樹,它自己也不肯掉下來。它把所有的紅都凝聚了去,沉重得像注了水銀。
那個禮拜天,我去林場場部門口的商店里打醋。我看見她和一個小男生湊在果園大門的鐵欄桿上,她把手臂從欄桿里伸進去,指著那個高高的紅紅的蘋果,那個男生舉著一只繃緊的彈弓,他緊緊地閉著一只眼睛。我慢吞吞地拖著步子從他們倆身后經過。她轉過身看到我,滿臉通紅。她一把奪過男生手里的彈弓,尖著嗓子喊:誰讓你打的?誰叫你打的?她把彈弓扔在地上。我已經走出好遠了。
她又來喊我上學。她沒幫我背書包,也沒試著拉我的手。她兩手都插在口袋里,臉還像禮拜天一樣,通紅通紅的,她走幾步,看看我,走幾步,看看我。她就像那些成熟了的、欲言又止的蘋果。她終于攔在我面前,從口袋里掏出一只蘋果來,很紅很紅,紅得閃著光。她說:它掉下來了,它自己掉下來了。
我看著她的眼睛,她看著別處。
我撲上去搡了她一把,她退了幾步,停下來,慢慢張開手臂。
她張開手臂的樣子,到底是想跟我和解?還是,還是聽任我接下來的欺凌?
我沖過去,狠狠地又搡了她一把,她退了幾步,重重地坐到地上。蘋果從她手心里掉出來,骨碌碌滾了好遠。
它那么容易沾上塵土,停止下來的它,已經不再是一只最紅的蘋果了。
2
那天我坐在車上,有人說,看,全是蘋果樹。
我望向窗外。冬天的大原上仿佛不生長別的東西,只有大片大片的蘋果樹。它們枝條開張,伸向四方,但不伸向太陽。指向陽光的最中央的枝干,早早被剪斷了。果農堅定地截斷了所有蘋果樹對太陽的夢想,他們給向上生長的大枝墜上磚頭,修正它們內心的思想,叫它們放棄對高處的渴慕,全都以俯向土地的角度成長。
它們都很矮,果實伸手可及。
它們的大枝,都以平行于大地的角度伸展出去,每一棵樹,都像張開著手臂。
車窗外大片蘋果樹閃過去,都緊盯著我,都張開著手臂。像她一樣。可是,三十年都過去了,三十年。三十年是多漫長的距離,要是把它像樹一樣豎起來,那肯定是大原上最高的一棵樹,可是,再高,有我們倆爬過的蘋果樹那么高嗎?
在超市里,我令人生厭地在木格子里挑揀蘋果,我要最紅的、滿身紅透了的,散發太陽味兒的、掛在頂梢的那種,但是沒有。它們都粉撲撲的,像撲了粉的嬌滴滴的臉蛋。它們一樣大,一樣圓,一樣光滑無斑,一樣甜脆,一樣沒有蟲眼。它們是被套在紙袋里掛在枝上的蘋果,像地底下的鼴鼠一樣,怕曬太陽。
我挑最好看的蘋果拿給我的孩子,他懶洋洋地接過去,看也不看一眼,就一口咬下去。他將只咬了一口的蘋果放在茶杯頂上。那只蘋果張著嘴巴臥在那里,欲言又止。我又想起她,她緊緊握著衣袋里的那只蘋果,臉通紅通紅的,她邊走邊偷看我,腳下踢著小石頭。
夏天,我費了好大的勁才找到她。她的鄰家站在地頭吆喝:她三娘,她三娘,有人尋你哩!這是一個沒有圍墻的果園,樹枝上掛滿了黃色的粘蟲板,有些向上伸的大枝上,用繩子綁著磚頭掛在上面。那些大枝還不太服帖,向上的渴望與向下的重量暗中角力。蘋果都開始上色了,微露酡顏。
一個女人從蘋果樹林里鉆了出來,她解下頭上的包巾,撲打著身上的樹葉和灰塵。最后,把包巾團起來擦了擦汗濕的臉。
我向她走去,她抬起頭看著我,停了下來。
她說:你?我點點頭。
她說:你來了。我點點頭。
她說:回家里坐。我說,不了,就是順路看一看你。
那去地里吧!她伸手想拉我,又縮回去。她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她的頭發隨便在腦后纏了個髻,還是毛毛糙糙的。她的后脖子右邊有一顆挺大的痣,以前我從沒注意過。
蘋果樹行里鋪著地膜,像汪著水一樣閃閃發亮。我沒話找話,說,這像河一樣。她回過頭,啥?我指著地上。她笑笑說,為了反光,下面照不上太陽的果子也能紅。她停在一棵樹旁,把遮住一只蘋果的幾片葉子摘掉,她說,不讓它們擋太陽,要不,紅得不均勻。她又給我來回比劃,樹行子要南北走向,果子都能見上太陽。
那你家的蘋果個個都紅。
不是的,樹頂上的蘋果才是最紅的,轉圓圈的都能曬上。
我們都不說話了。正在上色的果子把聲音都吸了去,緊密,沉重,個個都想落下來。
她沖著果園深處喊:那誰,給他姨摘上些果子,摘梢梢頂上的。
一個男人鉆了出來,頭發上沾著幾片樹葉。他笑道,前年到城里賣果子,專門摘了一袋子好的去尋你,都尋到你住的小區了,她又不去了,怕你認不得她,還專門揀樹梢梢上的果子摘呢,說是紅,吃起來香。
她在男人背上打了一把,扭過身看眼前的樹。
我眼前模模糊糊的濕,我說,你怎么會以為我認不得你?
她轉過身,我搡了她一把。她笑起來,我又搡了她一把。
她張開雙臂,像蘋果樹一樣。我和這棵掛滿果實的蘋果樹結結實實擁抱在一起。
責任編輯 林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