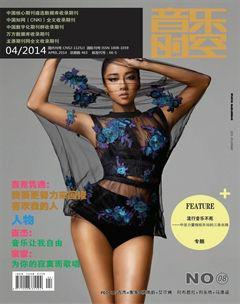流行音樂不死
沉默電話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期,臺灣魔巖唱片的三位歌手——陳綺貞、張震岳和楊乃文,代表了當時華語樂壇的新銳勢力。民謠、搖滾是他們的關鍵詞,而創作又是他們的共同性質。那一年,華語流行樂壇還沒有被聒噪的電子舞曲充斥,歐美的泛化風格也沒有成為唱片必備的部分,與此相對,豐沛的原創力、厚重的基礎感、純樸的本地化等內容,才是流行唱片的核心內容。在民謠、獨立搖滾唱片與流行音樂逐漸交融的趨勢下,這些歌手形成的既獨立特行,又不孤芳自賞的新風格,充滿了新鮮的音樂活力和強大的傳承能量。理所當然的,他們當時備受肯定,雖然與流行的天王天后性質不同,卻永遠不必擔心唱片銷量和樂迷口碑。即便音樂市場受到沖擊,他們的音樂形態也只是被洗練得更加純粹而已。所有作品隨著時間的改變,都是歌者內心坦誠的展現。他們不但讓我們相信獨立與流行間不存在的隔閡,又讓我們了解哪些是應該丟棄的糟粕,哪些是應該傳承的寶貴財富。十多年后的今日,即使他們各自都有了新的音樂理念,但依然是我們能坦然相信的音樂人。除了繼續擔任華語樂壇的中堅力量,他們也用自身所承受的時間之重,指給當下流行音樂三條出路——進化、回歸、堅持。
煉金師陳綺貞——從校園民謠清流到World Music
她的想象力,總是給你新的宇宙。
陳綺貞當年借民謠歌唱比賽出道,自資發行DEMO期間就飽受關注。雖被形容為“臺灣民謠的一股清流”,但實際上,她的音樂夢想是異常遠大的。第一張唱片由民謠結合古典音樂的方式,為自己的音樂品質打下了牢固的基礎。很多樂迷是從2000年的《還是會寂寞》這張專輯才發現陳綺貞,但那一張專輯對她來說,其實已經發生很大的改變了。如前所述,第一張《讓我想一想》雖在形態上走的是保守路線,但作品卻展示陳綺貞深厚的哲學內涵,這些做法與1998年正逐漸受到歐美流行音樂侵蝕的主流風格是有些相悖的。在音樂形態上似乎缺乏活力,但耐受性極強,即便在今天聽起來依然不會覺得過時。就是說,為了不做一盤沒有太多營養價值的快餐,陳綺貞的第一張唱片給聽者留下了遼闊的欣賞空間,足以抵御這漫長的時間風化。
而從《還是會寂寞》開始,陳綺貞對流行市場就有了新的觀念。當年她就與制作人王治平合作,嘗試將一些實驗性的電子風格放在唱片里。這種“電子”和所謂的歐美跳舞音樂是截然不同的,是以嘗試電子音樂技術為本的作品。去年聽到陳綺貞與鐘成虎等人合作的《52赫茲》,豈不知早在2000年,她就有《午餐的約會》這樣的電子作品正式發行過了。那簡直就像一個預示,告訴人們她的夢想是什么,她在穩定后將希求什么,儼然是一個未來的預告。但是,此后的十年,她始終沒有將這個夢想做成現實,而是繼續在民謠搖滾的領域中與主流風格劍戟相爭,試圖找到一個平衡的切點,去完成一個三部曲的偉大概念。終于,在“花的三部曲”(2005年《華麗的冒險》、2009年《太陽》、2013年《時間的歌》)主題末尾,陳綺貞在《52赫茲》的鋪墊后,正式將民族音樂、世界音樂等風格灌入電子軀干,放在正式唱片中。《時間的歌》讓我們看到她長達十六年的進化,是一個自我升華后修成的正果。
《時間的歌》同樣也是陳綺貞靈感成長的畫面展示,新作往往能找到過去的影子。比如《普魯斯特行動》編曲的喧鬧,暗藏玄機的秩序、獨到的和弦,以及隱藏在人聲背后的濃烈貝斯。歇斯底里的情緒猛推向前,一股被慫恿的振奮從內心升起;也有像《我親愛的偏執狂》里大段的掃弦,副歌持續不斷的夸張長音,多軌配器交纏的立體感,催促主動思考的神經。歌詞有《1234567》一般對自信缺乏、躊躇猶豫的點撥,雖缺乏完整的敘事要素,并將故事的兩端去掉,但交付自行想象的權力,讓人產生自然的共鳴。像神秘主義的吸引力,如題踏上阿蘭德波頓擁抱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的意識方舟——沒有中心人物,沒有故事情節,一旦由你賦予了開頭、結尾,就能輕易將那份感情占為己有。《普魯斯特行動》的平行象征,恰如我們聆聽陳綺貞的這些年歲,在激烈的和弦中,回憶每一個人被時間不停追趕的生活故事。
《時間的歌》文案宣稱:它不是一個“孤懸的、高潮式的結局”,對陳綺貞來說,它象征的是過去與未來的分界,或者說,是一個階段的完美結束。但它也不該是任何一個概念、任何一部整體、任何一副藍圖中的“一塊”,更不是所謂的“第三部分”。它的性質,應該像是在時間終點回溯整體的窗口,描述了最初的概念隨時間變化的全部過程,代表了波瀾起伏的整個樂章。將“變化”這一要點涵蓋在內,或許才是“時間的歌”想要表達的意思。此外,The Verse團隊遺留的電子音樂痕跡也深刻影響了這張唱片。李雨寰制作的《序曲:時間的歌》和《秋天蒙太奇》展示了極為扭曲、詭異的聽覺空間,與當年制作《小步舞曲》的輕盈姿色相比,充滿十足破壞性的快感,兩人十年的變化昭然若揭。陳建騏的Peace&Revolution則是一副The Verse意猶未盡的CaféDel Mar色彩,漸進式的編曲十分舒適,配器最豐滿的段落也有清晰的層次感。另外鐘成虎的《倒數》也非常值得一提,在民謠原味中加入Kalimba和笛子演奏,南非音樂家Warrick Sony和青年笛子演奏家胡帥的參與,讓這首旋律本來很流行的歌有了些不同尋常的質感。
無論賦予音樂多少哲學概念,多少文學觀點,說到底,音樂還是要回歸到與我們自身有多少關聯,每個人的感觸都不相同。所以,我們常常由大見小,甚至反其道而行,畢竟,對音樂的理解,始終源于每個人的生活經驗。相對的,時間也像是一種錯覺。就像我們無法擁有的事物,我們想歌頌它,又覺得無跡可尋。陳綺貞以自己獨到的哲學心理,賦予了音樂無限大的生命。即便作為獨立民謠的鼻祖人物,她也始終在探尋音樂中可以激發的新原子,并將其擊碎,以獲得新的宇宙,她就像音樂中的煉金師。雖然不是所有人都像她那樣充滿想象力,但她的進化史,總是能賦予他人新的啟示。
隱士張震岳——從痞子搖滾到新原住民音樂
即便卸甲歸田,也依然用心感染你。
不得不說,幾乎所有人都是從“如果說你要離開我/把我的相片還給我”這句歌詞認識張震岳的。1997年退伍回歸樂壇,張震岳拋棄前兩張專輯失敗的偶像風格,成為了不折不扣的民謠痞子。《我要錢》、《愛之初體驗》、《把妹》、《喝酒》,乃至中期的《放屁》、《狗男女》等尖銳、犀利的歌曲,讓人們永遠都忘不了他那副滿鬢糙漢的憤世面孔。那是作為張震岳永遠都不會消失的一種“狀態”——盡管他已表示再也不會演唱粗口歌曲,但人們卻永遠不會將其作為時間的殘物而丟棄。想必,就算要將它們與現在的張震岳徹底隔斷,也會在所不惜。當年的他,就是有這么大的影響力。endprint
但對于了解張震岳音樂更深一層的人來說,都知道在他的硬漢外表下,實際有一顆柔軟脆弱的心。為什么這樣說呢?確有證據——張震岳是臺灣鮮有的、專門為流行女歌手寫歌的創作人。包括藍心湄、李心潔、江美琪、蘇慧倫、莫文蔚、卓文萱等等,都特別向他邀過歌曲。他的作品似乎有一股立足女性視角的細膩力量,就算不是每首歌都量身填詞,旋律中也總是以易于消化、吸收的動人溫情感染聽者。所以,他除了自己演唱的歌曲,其他創作都賣到了女歌手的唱片里,這是臺灣男創作歌手中少有的例子。其實說張震岳瘋狂嗎?搖滾嗎?也是見仁見智——《這個下午很無聊》有招搖囂張的浪蕩,卻也在結尾唱著內秀的《秘密》引人深省;《秘密基地》再有《自由》的激烈狂放,還是用《勇氣》、《愛不要停擺》、《愛我別走》等擱下一半的深情座位;《有問題》中狗男女、放屁罵得再爽,還是有《在凌晨》唱著青春期般男孩糾結稚嫩的情愫。所以,張震岳必是深刻的、溫情的、治愈系的。他只是有很多面,但那都是人在成長中必經的“階段”。于是不出所料,在出道二十年之時,他回歸故土的殷切向往,以淳樸豁然的《我是海雅谷慕》,重塑了自我的心之彼岸。
《我是海雅谷慕》昭示故鄉、親情的深涵意義,展示他久釀的醇美、習于沉淀的心。時間磨去年少輕狂的棱角,長大成熟、歷經滄桑的男人,終于悟得自己名字的含義,落葉歸根,江流匯海。抽象的人文感情,一瞬間成為觸手可及的現實。從張震岳的口吻中聽不到虛假浮夸,只有純粹直白的感慨宣泄。因為是原住民的特殊身份,這份解甲歸田的故鄉情結也更顯真切。《我是海雅谷慕》的民謠濃度極高。在風格傳統的風險下,歌曲的旋律極佳,甚至突破一般的悅耳程度,連續下來,并沒有審美疲勞的滯贅。此外,像是呼應唱片主題和封面海天一色的風景,音樂的畫面感很強,將人迅速拉進自然質樸的情緒世界,很多歌曲都有環境音效的融入,以及沒有過多修飾、眾人參與的原始化和聲,似有Live般的錯覺,鄉土人文的質感加成不小。
張震岳所希求的,是一種建立在傳統原住民音樂上的發展式流行。例如從唱片中的《先這樣吧》可以聽到,音樂色彩明顯豐富了,與純民謠作品的形態有所不同,是具有都市感的主流作品。和《在凌晨》及《愛我別走》神似,用現代的外殼包裹原始野性的心,在鋼筋水泥中憧憬向往不得不失去的愛,又只能面對無可挽回的局面,在海角天邊無奈喟嘆。中板風格耐聽且易消化,傳唱性較高。《消失在你的世界里》很有《一開始就沒退路》的樣貌,編曲更加明快,情緒有振奮起跑的激勵感,副歌部分緊緊貼住人聲的合成器音效也是亮點。《唉唷喂呀》和《上班下班》魚貫而出,融合爵士的民謠搖滾風格,配合說唱橋段、編織精彩的吉他彈奏,一定程度上重現了張震岳痞子式的性感韻味。《唉唷喂呀》中表現出的幾分不正經,也讓人有了心滿意足的松懈:張震岳還是那個粗口不停、在演唱會當著幾萬人脫光屁股、率性、天真又粗糙的漢子,這一點沒有改變,著實令人安心愉悅啊。
唱片第三階段,再次回到溫暖深情且具有社會議題的篇章。其實這也是《我是海雅谷慕》所強調的主題:關于土地、海洋、環保、人文關懷等理念。《我家門前有大海》、《別哭小女孩》等作品,就像串聯成一部真實又富有藝術氣息的紀錄片,將故鄉在現實生活中所經歷的、變化的,都用音樂的方式呈現出來,講述給更廣闊的人群。不憤世、不埋怨,卻也帶著堅韌不肯妥協的力量,絕不是懦弱地忍受著。而為自己所愛的、珍惜的、擁有的,則不惜一切代價,以骨骼、血液、靈魂相連的羈絆去付出最大的力量。這份骨子里的誠摯,自是想裝也裝不出來。若不信,再聽聽《我是海雅谷慕》中結尾的《抱著你》,只第一句“如果明天/看不見太陽/整個世界/會變成怎樣/在最后這一刻/讓我輕輕抱你/抱著你/抱著你/抱著你”純凈深厚的聲音,眼淚就要沒預警地掉下來了。張震岳成了看破塵世的隱士,但依然用自己的靈魂,感染著我們同樣誠摯的內心。
戰士楊乃文——從玩味搖滾到發揚搖滾
改變不重要,重要的是忠于自己。
楊乃文應該說是這三位音樂人中變化最小的,她一直在堅持搖滾風格。但是,所謂“變化”本就是不可度量的,它與“深化”的概念只隔了一層紙。想起1997年,那個吸煙、冷艷的搖滾酷妹,一頭長發、桀驁不馴地唱著《星星堆滿天》,我們一眼就認定她必是華語女性搖滾的唯一可能。而在貫徹流行搖滾這條路上,她又是如此堅持和強韌,沒有一絲躊躇游移。女爵、Queen,楊乃文像是與這些關鍵詞共生,但是,相比女王的張揚和孤傲,似乎戰士堅韌、頑強的氣質才更適合作為她音樂人生的側寫。從昔日玩味搖滾的激情與癲狂,到今日貫徹搖滾深入心靈的力量,楊乃文的音樂所展示的,不是曲風和事業方向的簡單問題,而是音樂與人生的成長錘煉。
1999年的唱片Silence是臺灣百佳之一,也正是這張專輯,讓人看到華語女性搖滾新的可能性。楊乃文的搖滾音樂自然也有歇斯底里的嘶吼、壓抑與宣泄的展示,但蘊藏在那低沉聲音之中的,始終是股由內至外、不浮表象的純粹能量。當年在唱片封面明確地寫著:楊乃文,愈沉默愈有力量——這口號可謂細致剖析了楊乃文以及她獨特的音樂姿態。包括出道作品One在內,楊乃文一度展示給我們強硬的獨立意志,冷冽、深刻,但絕不孤傲清高。她無可模仿的關鍵,絕不僅僅在于充滿辨識度的嗓音。音樂生涯漫長,屬于個人的唱片數量不多,但她在華語樂壇的位置卻是不可取代的。與華語樂壇其他女歌手相比,楊乃文顯得純粹而又低商業性,并忠于搖滾。她所擁有的絕不是膚淺的王位,而是執著展示所愛音樂的舞臺。
當然,十多年來楊乃文也有過別的嘗試。雖不能說《應該》、《女爵》等唱片讓楊乃文偏離了搖滾本質,但《應該》側重的市場流行性以及《女爵》少許文藝氣息的侵染,讓曾經魔巖Monster Live巡演舞臺上那個長發、冷酷的楊乃文默然失去了某種特有的情緒。我們知曉Silence的搖滾特質是獨有的,而在這些專輯中,似乎都缺少了什么,缺少了屬于楊乃文的搖滾韻味。只是,在這些唱片中她尋找出路的旅程,可以看作她思考人生的縮影。終于,2013年的Zero讓她找到了。新作傳達出很多訊息,但在“原生態搖滾”這一點上,與任何一張過往專輯相比,都是最強烈、最顯著的。endprint
也有人說,Zero是楊乃文重新昭示自我的開始。但“回歸原始”的概念蘊含了另一番滋味,我們強調的是她“實質上從未改變”的重點。和首張唱片One數字呼應,直白的字面含義,其實是自己人生中的橫向比較,孤注一擲的鏡像。一面保有原始的搖滾樣貌,又在制作技術、人文氣質等方面不落時代。《鸚鵡》、《小丑的姿態》、《日落西沉》三首歌曲排在專輯首位,從簡單振奮的編曲方式中,讓人再次感受往昔的灑脫,是概念的最佳昭示。像《鸚鵡》即便沒有副歌突兀的高音和吶喊,卻在緊密的節奏里緊抓情緒,使人嗅到急待爆發的深沉:既不歌頌愛情的偏執,又沒有惡意的嘲諷,只表達宛若第三人的冷靜情感,以及以物喻人的想象色彩,這也是楊乃文此次最為突出的進步。后兩首更趨向當年的經典曲目Fear,雖沒有Monster、Silence般猛烈激昂,卻是在進化、權衡后的本質搖滾成色。這三首歌讓人在第一時間就感受到“歸零”的強烈暗示,沒有繁瑣編曲的噪雜,沒有嘩眾取寵的元素摻雜,只有聲音中的濃厚與強勁,展示如當年的那份恣情和純粹。
而楊乃文給人留下的深刻記憶,終究是她音樂中的冷酷不協。雖然《祝我幸福》意外地開辟了流行市場,也讓部分根本不可能聽楊乃文的人得以了解,但始終是Silence毫無矯情、不屑一顧的冷艷面容,令九十年代末積蓄的大量擁躉忠實至今。就像這張專輯中由馬念先作詞的《我從來不懂你的幽默》,雖沒有激烈的和弦編曲,但卻表現出久違的經典情緒,嘲諷、無視、于己無關,深沉、乖僻、不茍言笑。踩著貝斯閑逸的低音節拍,簡約復古的音階結構,沒有起起伏伏,孤傲的艷麗卻在平靜中爆發。《小心我撒野》也展示了楊乃文依然存在的可塑性。楊乃文將創作者的個人特質作為背景,以自己的嗓音進行重塑,在特別的畫布上涂鴉成更詭秘的色彩,將兩者所長進行最佳匯聚,讓歌詞直白的缺陷顯影不深。此外,《小心我撒野》也是高音展示最為盡興的一首。盡管每張唱片發行的間隔都比較長,但她每一次演繹,都步步為營充滿篤實和強勁的力道,也同時展示專業、謹慎的生活姿態。Zero理應影響新一代的歌迷,而對于老擁躉,也必是淚流滿面的經典場面再現。楊乃文讓我們看到,改變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忠于自己。
有一些聲音常說,聽十幾年前的華語歌曲,和現在幾乎沒有分別。間接表達的意思,或許是這么多年,我們沒有絲毫進步。但是——我們是不可能沒有進步的。不但我們的技術進步了,我們的音樂思想也同樣進步了。如果我們沒有進步,我們根本就不可能生存下去。盡管困難,但華語音樂一直都存在著,用自己的方式,以自己的步伐,在眾多優秀音樂人的努力下,展示出特別的面貌。只是我們需要新的出路,這沒有疑議。進化、回歸或堅持,有了這些可以信賴的音樂人,我們的音樂,將會繼續好好地活下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