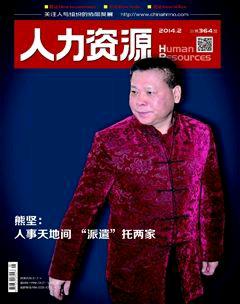2013年十大員工關系案件點評(下)
柴文聰
六、多家企業身陷裁員風波
【事件回放】
2013年1月,攜程網開始大面積裁減地面銷售人員,除保留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七大機場渠道外,其他二三線城市機場、火車站、汽車站等地面銷售人員將全部裁撤。
2013年3月,成立不到四年的匯豐人壽突然宣布關閉個人營銷渠道,近百名保險銷售人員被裁減。
2013年7月,郎酒銷售公司的部分員工突然接到裁員通知,其中大部分員工于2012年入職。隨后,公司方表示,裁員決定屬公司內部正常的人事調整,主要是因為目前員工隊伍過于龐大。
【入選理由】
2013年的世界經濟依舊不景氣,不少企業紛紛陷入裁員風波。
【事件點評】
在百度搜索中輸入“2013年裁員”可以發現,幾乎每隔幾天就會發生一起裁員事件,所以有人打趣稱:2013年流行“裁員風”。然而,相信大多數企業的管理人員對于這類“冷幽默”笑不出來。
細究這些裁員糾紛會發現,一部分用人單位通過合法途徑來執行裁員,而另一部分用人單位則往往出于各種考慮,選擇“旁門左道”的方式裁減員工。
通過合法途徑實施裁員,法律風險自然相對較低。只是,即使是“名門正派”式的裁員,仍然需要注意許多細節。譬如,在采用合法化、規范化管理的同時,也不能忽略人性化管理,當用人單位在遵循合理、合法裁員的同時,還須建立暢通的溝通渠道,在充分保護員工尊嚴的同時,給予其必要的心理疏導。
裁員造成的社會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可以考慮采取下列方法加以改善,比如:設立老員工俱樂部、建立員工關懷基金等。老員工俱樂部的設立是為了向員工表明:一旦用人單位的財務狀況有所好轉,被裁員工將具有優先雇傭權,這與《勞動合同法》中的立法精神一脈相承,同時也是通過“心靈契約”保持被裁員工與用人單位的感情。寄希望通過“旁門左道”來降低經濟補償金絕非易事,只要用人單位稍有疏忽,不但會官司纏身、形象掃地,最終還得支付經濟補償金。
最后,建議用人單位需要在裁員過程中堅守一條底線——裁人不裁心。裁員雖然可以使單位在短時期內降低人力成本,但卻可能導致員工士氣低落,甚至導致關鍵員工的非正常流失。一旦用人單位失去了“人心”,就將面臨人力成本(尤其是隱性人力成本)上升的困境了。
七、朵云軒員工競業限制案開審
【事件回放】
陳某原是朵云軒拍賣有限公司的油畫雕塑部主管。2011年,公司與陳某簽訂競業限制協議,約定陳
某在雙方勞動關系解除或終止后2年內,不得直接或間接從事同行業相似崗位的工作,同時公司每年支付陳某5萬元的競業限制補償金。若陳某違約,應按竟業補償金總額的5倍支付違約金。2011年1月和2012年1月,朵云軒兩次支付了各5萬元競業限制補償給陳某。2012年2月,陳某辭職,同年4月,朵云軒發現陳某在另一家拍賣公司任總經理。朵云軒認為陳某違反了競業限制條款遂訴至法院。法院一審判決陳某繼續履行競業限制條款,并支付朵云軒違約金。但陳某不服,提出上訴。
【入選理由】
競業限制,是保護商業秘密的一道“閘門”,但如何用好這道“閘門”,不少公司卻并不知曉。
【事件點評】
此案焦點在于競業限制補償金的支付時間與方式。《勞動合同法》對于競業限制補償金的支付時間和方式做了明確的要求,即競業限制補償金應在勞動者離職后,由用人單位按月發放。從立法的角度而言,“按月支付”對勞資雙方都能起到有效的監督作用。而在實操中許多用人單位會覺得按月支付競業限制補償金比較麻煩。更傾向于將競業限制補償金一次性支付給員工。筆者認為,這樣極易產生勞動爭議。究其根源,在于用人單位向在職勞動者支付競業限制補償金會被認為是勞動報酬的一部分。因此,用人單位有必要嚴格區分勞動報酬與競業限制補償金。
勞動報酬的數額,是根據勞動合同的約定和企業用工制度加以確定的。競業限制補償金,是勞動合同解除或終止后,用人單位在競業限制期內支付給員工的經濟補償。對于競業限制補償金的支付,用人單位不應附加其他條件。此外,雖然補償金的數額可以約定,但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四)》(以下簡稱“《司法解釋四》”)中的規定,競業限制補償金的標準為勞動者在勞動合同解除或終止前12個月平均工資的30%且不低于勞動合同履行地最低工資標準。一旦雙方約定了競業限制補償金,用人單位便不得隨意扣減。
一些用人單位對競業限制補償金的操作較為規范,但也會遇到一些問題。比如,當員工違反競業限制條款時,用人單位須對員工違約負舉證責任,然而實踐中不少用人單位卻發現舉證困難。對此,首先建議用人單位能在日常管理中對保密信息采取嚴格的分層機制,盡可能地避免重要的信息或機密被大多數人知道;其次,做好員工離職前的脫密轉崗工作,這樣便于公司更新重要或機密信息;再次,用人單位應做好勞動者離職后的溝通管理,一方面能樹立企業形象,為企業文化起到正面宣傳的作用,另一方面能使用人單位掌握離職員工的近況,及時預防勞動者違約的行為;最后,若離職員工最終還是發生了違約的情況,用人單位可以采取靈活的取證方法,譬如電話錄音、快遞確認等。
八、空乘“吐槽”飛機餐遭解雇
【事件回放】
2012年2月7日,維珍航空公司在其官方微博上宣布:公司于 2013年3月1日起,對上海起飛的航班啟用全新的“精致餐食”服務。當天,兩名維珍航空公司的空乘在未透露自己真實身份的情況下,對公司的上述微博轉發并評論:“飛機餐的東西少,又難吃,光改餐具有什么用?”
數天后,維珍航空將兩名空乘停飛。在經過兩次約談后,公司認為這兩名空乘發表的微博內容影響惡劣,對公司造成損害,遂以嚴重違反公司規章制度為由將二人解雇。不久,兩名空乘狀告上海外航服務公司人力資源分公司與英國維珍航空公司上海辦事處,要求恢復勞動關系,并分別支付工資與加班費14萬和
12萬余元。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做出一審判決:維珍航空解雇行為合法,駁回兩空乘的全部訴請。
【入選理由】
員工在社交網絡發貼“吐槽”卻成了“違紀”,想不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都很難。
【事件點評】
這是一起員工“因言獲罪”而引發的勞動糾紛。本案雖已告一段落,但爭論卻才剛剛開始。多數網友對該案的判決結果表示不滿,普遍認為,員工在微博平臺上“吐槽”純屬個人自由,法院的判決有失偏頗。然而,從法律角度分析,員工對公司隨意“吐槽”的確是存在法律風險的。
空乘作為航空公司的員工,需要對公司忠誠,至少不應做出有損公司的行為。本案中,空乘認為自己在非工作時間內,在未表露自己是航空公司員工的前提下進行微博評論與轉發,這對公司并不造成影響,因此,該行為純屬言論自由。然而,當事空乘可能并未考慮到自身行為所產生的負面影響,當事人對公司微博的消極評論及轉發很可能會被其他人所看到,這樣足以造成“滾雪球”效應,對航空公司的品牌和名譽造成不利影響的“威脅”——事實上,由于這兩位空乘的評論以及該事件的后續進展在微博平臺上持續地“發酵”,維珍航空公司也的確受到了一定的負面影響。此外,雖然這兩名空乘并未在評論中提及自己的身份,但這兩名空乘的微博賬戶中卻顯示其所在的公司為維珍航空,所以,這兩名空乘的評價較之于普通消費者而言具有更高的外界認可度,對航空公司產生的不利影響也要比一般的消費者要大。
那么,如何看待員工的“言論自由”與“違紀”?筆者認為,區別這二者的標志在于:第一,員工評論對象是否為公司;第二,公司是否對“員工公開提及與工作有關的事情”制定過相應的規章制度,譬如,制定《社交網絡管理制度》,若員工對企業制度簽字并予以確認后,員工發表與公司相關的言論就受到約束,一旦違反便屬于違紀。
為了避免這類事件的再次發生,建議用人單位做好以下兩點。第一,在公司內部宣教此事,讓員工知道隨意評論公司是可能存在法律風險的;第二,建立暢通的內部溝通渠道。古語有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內部溝通渠道如不暢通,則會嚴重影響員工關系管理。
九、沃爾瑪工會遭員工起訴
【事件回放】
2011年7月,沃爾瑪員工王某被公司以“不誠信”為由解除了勞動合同。王某對此不服,與公司對簿公堂。2012年,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終審判決,認定沃爾瑪違法解除勞動合同,應予賠償。
贏得官司之后,王某又把沃爾瑪深圳香蜜湖分店工會委員會告上法庭,案由為“名譽權糾紛”。在庭審過程中,王某認為工會沒有經過相關調查程序就直接同意沃爾瑪辭退了自己,并未起到為己代言的作用,實屬失責。
【入選理由】
本案系中國首例員工起訴工會的案件,具有標桿意義。
【事件點評】
本案是中國首例員工起訴工會的案件,有利于改變我國基層工會“不作為”、“不稱職”的現狀。
眾所周知,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是工會的一項基本職責,為此,工會需要就職工的切身利益與職工溝通并核實,此外,也需要就勞資雙方的矛盾居中調解,以減少雙方可能會出現的損失。
然而現實中,不少基層工會卻遭到用人單位的抵制,或是成為用人單位的附庸。主要表現為工會不敢
替職工維權,或者不糾正用人單位的錯誤。本案的現實意義在于,給那些消極工作的基層工會組織敲響警鐘,使其盡快回歸工人之家的本位。否則,一方面可能會受到外界的指摘;另一方面,員工也可提出罷免工會主要領導。
《司法解釋四》第十二條規定,成立工會的用人單位單方解除勞動合同時,除了具有合法的解除理由外,還必須事先將理由通知工會,否則視為違法解除勞動合同,屆時用人單位需向員工支付兩倍的經濟補償金。在此建議,已成立工會的用人單位在單方解除勞動合同時,應及時通知工會,并對近一年之內單方解除的勞動合同進行歸納梳理(勞動爭議申請仲裁的時效期間為一年),并將解除理由書面通知工會。
十、員工訴公司勞務派遣無效
【事件回放】
徐某是1號店的勞務派遣員工,入職之后從未休過年假,在法定節假日仍被要求加班,但卻沒有得到加班費。作為勞務派遣工,徐某每月只有4天休息,每天需上班8-10小時,卻無法享受同等工作量快遞員的收入和福利。2012年底,徐某將1號店和相關勞務派遣公司告上仲裁庭,要求確認1號店與自己的勞務派遣合同無效,雙方建立的是勞動關系。
2013年7月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認定:勞務派遣合同有效。徐某不服,向羅湖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2013年9月,徐某訴1號店(上海益實多電子商務有限公司)、亞洲人才(勞務派遣公司)和深圳人才(勞務派遣公司)的勞務合同無效案一審開庭,經過2小時的法庭激辯,當庭并未宣判。
【入選理由】
本案系《勞動合同法(修正案)》頒布后首例勞務派遣糾紛,勞務派遣中的“三性”問題再次引發關注。
【事件點評】
《勞動合同法修正案》于2013年7月1日正式實施,而《勞務派遣若干規定》草案又于2013年8月7日向社會征詢意見,有人說2013年是“勞務派遣年”,這起勞務派遣糾紛案件自然會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
本事件中,勞務派遣員工因認為自己最基本的勞動權益——休息權與勞動報酬權被用工單位——1號店侵害,所以,希望通過提出勞務派遣無效,以追認勞動關系的確立。那么勞務派遣的有效性如何確立呢?相比于原《勞動合同法》中“勞務派遣‘一般在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實施”的規定,修訂后的《勞動合同法》明確了“勞務派遣用工是補充形式,‘只能在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實施”。“一般”與“只能”這一詞之差,就將勞務派遣的有效性確定了下來。只有當工作崗位符合臨時性、輔助性或替代性這三者中任意一性時,該崗位才可采用勞務派遣形式。
當立足于勞務派遣的“三性”角度,不難想象類似的勞動爭議可能會越來越多。有許多企業在使用勞務派遣時,被派遣崗位均不符合“三性”要求。而《勞務派遣若干規定》(征詢意見稿)中提出,在企業違規被罰款后拒不改正的情況下,在非“三性”崗位或者超比例使用被派遣勞動者視為與用工單位建立勞動關系。雖然《勞務派遣若干規定》尚處于征詢意見階段,但卻具有一定的指導性意義。因此,對于用工企業而言,這一點是尤為需要注意的。
那么,用人單位應如何應對呢?首先,可對現有崗位進行梳理,篩選出不符合“三性”要求的崗位;其次,調整崗位用工模式,對于其中可“轉正”的崗位,予以轉正;對于不適合“轉正”的崗位,可采取其他的用工模式,如業務外包。用人單位在使用業務外包時,對承包方派遣的員工,應以“不管”為原則,以適當的“間接管理”為補充,切忌進行直接管理,否則,極易導致“真派遣,假外包”現象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