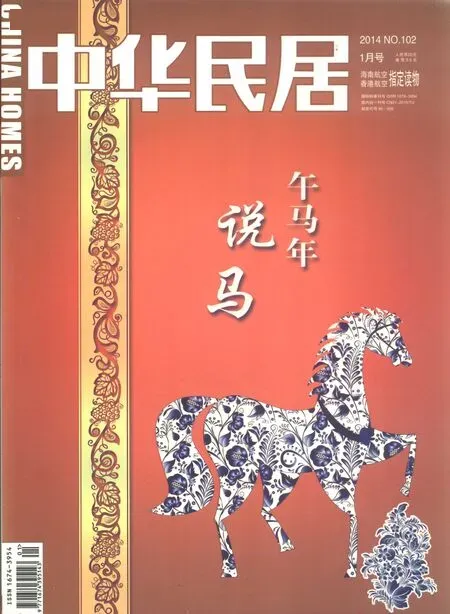馬與戰爭馬背上贏江山
撰文/拉 雅
馬與戰爭馬背上贏江山
撰文/拉 雅
它和人同受著戰爭的辛苦,同享著戰斗的光榮;它和它的主人一樣,具有無畏的精神,它眼看著危急,當前而慷慨以赴;它聽慣了兵器捕擊的聲音……
——法國作家布封
馬的從軍史
自古以來,動物從軍,時間最長、數量最多、貢獻最大的當然是馬。馬既有猛獸的爆發力,又有食草動物的持久耐力,容易馴良,不講究吃喝,又任勞任怨,那一雙耐磨的蹄子適合奔跑于各種地勢。種種得天獨厚的優勢,讓馬成為在冷兵器時代,甚至在熱兵器還沒有像現在這么發展成熟的時代里,對戰爭發揮了毋庸置疑的巨大作用。
軍馬先是挽車、后是供騎乘,是人類較早利用的牲畜,在全世界范圍內,馳騁疆場數千年,直到今天還沒有完全在軍隊中絕跡。馬參戰最初是用來挽車。從公元前2000年巴比倫人開始使用戰車起,到公元13世紀印度人最后使用戰車止,戰車曾馳騁沙場3000多年。中國是世界“戰車王國”。傳說在黃帝時期,中國就發明了車戰方法,打仗時大將站在車上。停戰休息時,便將車連接起來,圍成一圈,以保護中軍。只留下一隙,算是出入的門,叫做轅門。
商周時期,中原地區從游牧區引進良馬,以備軍用。大約到了西周時代,馬拉戰車已成為陸軍的主要兵種和主要突擊力量。車戰的規模小者數百乘,大者上千乘。最大的一次是宣王南征,出動戰車3000乘。到了春秋戰國時代,戰車發展到頂峰,戰車不僅成為陸軍的主要突擊力量,而且成為軍事力量的標志。后來,為了同北方、西北方游牧民族作戰,騎兵登上歷史舞臺,并逐漸取代戰車。
到了西漢,實際上漢武大帝之前的文景之治積累的不僅僅是金錢,更多是在積累反擊匈奴所需要的馬匹資源。漢武帝發動的幾場對匈奴的戰爭,都是靠騎兵取勝的。為了解決快速的騎乘用馬,漢武帝愛西域汗血馬,著貳師大將伐大宛,“取其善馬數十匹”。這種馬,是專供騎乘的“千里馬”,所以漢武帝要想方設法弄到手。這之后,歷代王朝莫不重視這個問題。唐時,是我國騎兵發展的鼎盛時期,《唐會要》說:“突厥馬技藝絕倫,筋骨合度,其能致遠、田獵之用無比,史記匈奴畜馬。”馬匹的質量和數量,是突厥國力的重要標志,所謂“突厥興亡,唯以羊馬為準”,即是此意。突厥貴族的財力,也是用馬來衡量的。這和東晉之后到唐的300年中靠兵鋒爭奪天下有很大關系。元朝起于大草原,其軍事用馬更是不在話下了,遠征到地中海一帶,所向披靡,靠的也是馬。到明清兩代,也都和蒙古進行了大規模的馬匹交易,保證了對戰馬的需求。

縱橫歐亞的蒙古騎兵
公元1200—1300年,中國北部的蒙古族,由成吉思汗創建并由他的繼承者保持了一支15—24萬人的騎兵部隊。這支部隊由三個騎兵縱隊組成,每個縱隊有1萬騎兵,大體相當現代一個騎兵師。每個騎兵縱隊包括10個騎兵團,每團1000人;每個騎兵團包括10個騎兵連,每連100人;每個騎兵連10個騎兵班,每班10人,所有騎兵一般都騎馬作戰。
為了確保和加強騎兵的機動性,每個騎兵都有一匹或幾匹備用馬。這些蒙古馬是經過極其嚴格的訓練的,不論嚴冬酷暑都生活在外面,具有極強的忍耐力,必要時可以連續行軍而不吃一點東西,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和最險惡的地形上通過。由于行軍時不需要為馬匹備帶飼料,士兵又自帶個人的裝備和食物,加之,大部分戰馬都是母馬,士兵都能喝馬奶生活,因此減輕了軍隊食品供應的負擔,不需要拖著龐大的后勤供應輜重車隊,也不必保留一個后方供應的基地。成吉思汗及其繼任者,憑借這支騎兵部隊,幾乎踏遍了整個亞洲和歐洲,所向無敵,建立了一個強盛的國家。
騎兵作戰過程當中,馬匹的快速與否,對戰爭的最終結果會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中國古代偉大的殲滅之戰數不勝數,如騎兵圍殲騎兵的漢匈漠北會戰,霍去病以5萬騎兵圍殲匈奴騎兵,斬7萬多人。最經典的騎兵戰役還要屬蒙軍征匈之戰。這一戰中,歐洲最好的匈軍,日耳曼軍、波蘭軍、薩克森軍等聯軍均敗在蒙古騎兵的錚錚鐵蹄之下,全軍覆滅,只有匈王貝拉考仗著千里良駒逃過了多瑙河。中國古騎兵向來是以驍勇善戰而著稱,這場戰爭中蒙古騎兵可算立了大功。
近代戰爭是空間戰爭,飛機大炮淘汰了大刀長矛,戰馬退役了。但就戰爭的整體言,部隊不能沒有馬,邊防哨所、山地巡邏、輜重馱運、交通聯絡,馬從軍現象依然還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