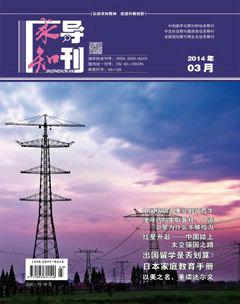甘于孤寂?堅守科學
陳圓圓
生逢抗戰,他在疾病纏身和顛沛流離的童年中成長;親歷“文革”,他在崎嶇不平的科研之路上壯志難酬;成績斐然,他是中國現代控制理論研究的先驅,中國科學院院士。
“人不笨,還努力,有機遇,敢堅持”——黃琳用這十二個字概括自己的一生。
童年:淘氣得一塌糊涂的舞蹈隊長
1935年11月30日,“一二·九”運動前九天,黃琳出生在江蘇揚州一個中學教師家庭。恰逢民族生死存亡攸關之際,黃琳的童年歷經離難。他出生不久就患上嚴重的肺炎,當時中國醫療條件十分匱乏,他母親差點放棄這個孩子,將他放在地上卷上草席準備送走。后來雖得救治,他的肺病卻未能根治。就這樣,幼年的黃琳一直籠罩在疾病“死緩”的陰影中。
不久,恐怖的日本大屠殺就蔓延到了揚州。1937年末,黃琳全家開始了長達近五年的逃難生活,輾轉于泰州農村一帶。“我們住在老百姓家,半夜槍聲一響就被大人從被窩里拉出來逃亡,這樣的日子不只是一兩天。”在此期間,父親斷斷續續地在每次避難所附近的中學或師范學校臨時教書,靠微薄薪水養家;母親則更多地陪著他們兄弟倆,給他們講岳飛、蘇武和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故事。在抗戰淪陷區,父母一度被迫更名改姓地生活,但堅決不與日偽合作。直到抗日戰爭結束,全家才重新在揚州安定下來。母親因堅持不在日本人手下做事,名字上了揚州的忠貞榜,隨后被任命為下鋪街小學校長;父親也由農村回到了揚州工作,后來成為新中國成立后揚州中學第一任校長。“我小時候父母都很忙,并未直接教給我什么。但我受他們一言一行的影響,有了頑固的愛國主義精神。”
由于黃琳的身體不好,父母對他的學習要求并不苛刻。黃琳笑說,自己小時候“淘氣得一塌糊涂,但幸好也不笨”。他剛上初中時就開始組裝簡單的電動機模型,大人考心算時會搶在哥哥前回答,還早早跟著哥哥去聽英文補習課。他最喜歡翻看教數學的父親的藏書,一本《幾何學辭典》看得津津有味。后來在揚州中學就讀,他“從來不用功,成績還可以”。同時,他還是長期活躍在校內外舞臺上的“小名人”,曾被團市委派到店員工會里教店員們唱抗美援朝歌曲。到了髙中時期,校團委更是直接要他當舞蹈隊隊長。“我至今還保留著揚州市文聯發給我的音樂協會的會員證。”黃琳自豪地拿出已經很舊的古老證書。黃琳熱愛音樂,尤其喜歡在閑暇之余待在家里聽中國古典音樂,沉浸在古琴、簫、琵琶和二胡的世界里是他的一大享受。其中,古琴和簫合奏的《漁樵問答》是他最喜歡的曲子之一。
機遇:讓錢學森20余年不忘的年輕學者
黃琳與錢學森第一次相見是1956年2月,彼時黃琳僅及弱冠,而錢學森已過不惑之年。當時錢學森在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講授“工程控制論”,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抽調了15名學生作為第一屆一般力學的學生前往聽課,正在數學力學系讀大三的黃琳就是這15個人之一。“當時我們十多個學生坐在一群大學老師中間,聽得津津有味。整整半年多,我深深地被這么一門‘有用又‘好玩的學科所吸引。這門課就影響我決定一輩子搞控制科學。”
1959年,在對擬研制的飛機安定性的預研實際工作中,黃琳提出了針對時變系統的多維系統衰減時間問題,并以此為基礎完成了研究生的論文答辯。1961年11月,他帶著這些成果參加了中國自動化學會的成立大會,并成為由15人組成的控制理論首屆專業委員會中最年輕的一員。會后經過推薦和評審,他的成果被正式發表在第二屆國際自動控制大會上。
1962年春,全國一般力學大會籌備召開,黃琳受周培源先生委派作為他的代表參與了籌備工作,并應邀在大會上做了題為“有控系統動力學的若干問題”的大會報告。在大會上,錢學森對黃琳的報告做了肯定的詳細點評,并糾正了他對一美籍華人教授譯名的不當。錢學森對待科學一絲不茍的嚴謹態度,讓黃琳又一次受益匪淺。
會后不久,《力學學報》決定將黃琳的報告發表在該學報上。“當時編輯告知我這一消息,我想應該是錢先生推薦的。”之后,為了解決中國導彈發射因彈性振動而失敗的問題,錢學森專門組織在頤和園龍王廟召開了一次小規模研討會,黃琳也是參會者之一。為數不多的幾次活動讓錢先生記住了這個年輕人。20多年后,黃琳隨王仁院士等人去拜訪錢學森,讓他頗感意外的是,一進門,錢先生便記起他來:“哎呀,黃琳來了,我們好多年不見了。”
“我們雖然交往不多,但印象中的錢先生是能力超群的。比如說,錢先生在美國生活幾十年,回國上課為了照顧學生,除了xyz之外,竟能夠不說一個英文單詞,這確實是常人難以做到的。”黃琳說,給自己影響最大的書,一是錢學森的《工程控制論》,二是錢學森老師的傳記《馮·卡門傳》,他們堅強執著的個人品質和科學精神在黃琳心中刻下了深刻的印記。
堅守:控制科學領域的“個體戶”
20世紀60年代正是現代控制理論在國際上剛剛興起的時期,當時的力學界并不認可控制在力學中的重要作用,這使得黃琳在力學專業環境下做控制研究顯得很孤立。甚至有同事認為黃琳是在“不務正業”,要他改行。他頂著種種壓力,在數學專業程民德教授等人的支持下,憑著一股韌勁在力學環境下硬是把控制理論研究堅持了下來,并帶領兩個六年級的學生在線性二次型最優控制與極點配置方面做出了領先于世界的科研成果。由于當時的環境,文章僅發表在國內,致使這一創造性工作在國際上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留下了遺憾。
2013年7月份,這一科研成果得到國際自動控制聯合會(IFAC)的高度肯定,黃琳當選為國際自動控制聯合會(IFAC)2011-2014年度選出的會士(IFAC Fellow)。時隔半個世紀,中國在控制科學研究領域的貢獻終于受到國際認可。
提起控制科學,黃琳有說不完的話。“控制科學簡單地講,就是給你一個控制的對象,讓這個對象能夠滿足你的要求。比如說一架飛機,大家坐飛機都不希望顛簸,所以就希望能夠設計一個自動駕駛儀,通過不斷地測量飛機的俯仰角度變化,來糾正顛簸。控制科學跟一般的自然科學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它的著眼點在于改造世界。控制科學要解決的就是兩個問題:一個是能不能做,一個是怎么做。這件事情能不能做,根據這樣一些數據,控制器能否設計出來。理論上解決的是可以做,不代表已經做出來了,怎么做法,還有具體的控制器的設計。”
黃琳還認為,控制科學僅僅發展不足百年,但隨著社會和科技的進步,控制科學面臨著新的挑戰。20世紀60年代之前,控制科學是控制單一某個裝置,控制對象比較單純、孤立;但到了60年代以后,控制發展為多角度,控制對象由一個發展為多個,這就誕生了現代控制理論。控制的量從單變量變成多變量,其中計算機的作用越來越大。現代控制領域的關鍵,一是網絡控制。“智能電網”的樣本量極大,既有好處也有一定風險,比如美國加州一次大停電的損失是極大的。二是多智能體控制,比如一次派出去多架飛機參戰,不僅需要中央指揮,還需要互相配合。近年來一些國家研究無人作戰飛機,這種無人機的機群如何協調行動就是一個富于挑戰性的問題。
擔當:憑良知行事的知識分子
“文革”期間,黃琳所在的力學專業于1969年遷至漢中。同黃琳一同翻過秦嶺的,還有一箱箱寶貴的藏書。“當時根本不允許帶書,但我舍不得,就把那些書也帶了過去,以備不時之需,因此受到當時軍宣隊領導的訓斥。”在到達漢中的第一年,他參加挖石頭、抬石頭、修護坡、種樹、平整土地等勞動,還帶過演出隊去大巴山深處演出,所有這些事他都認真負責地完成。1970年底力學專業辦起了射流技術訓練班,黃琳與一些工人師傅一起到寶雞虢鎮的一家無線電廠,搞以射流技術為主的技術革命。在這里,他幫助一位趙姓師傅修復了沖床振動送料器,使其能正常工作。回校以后,他直言事實,反對工宣隊領導炮制的假經驗,并因此遭到工宣隊頭頭的打擊。幸好同去寶雞的老工人趙師傅仗義執言才使他免遭批判。從寶雞返回漢中正值隆冬,領導要求他們由寶雞必須徒步翻越秦嶺,拉練回校以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這次拉練使黃琳發髙燒再度咯血,1971年夏天他又患上黃膽肝炎并發瘧疾,這使得他早已恢復健康的身體又一次受到嚴重打擊。盡管身體不好和備受打壓,但他頂住壓力,為當時留校的紅衛兵大學生奠定了起碼的后續學習與研究的基礎知識。
“‘文革使中國控制科學與國外的差距進一步拉大,我希望盡己所能地彌補這些差距。”整個“文革”的十年中,黃琳接觸到控制只有兩次,一次是1973年海軍的研究單位因慣導不過關而召開了一次研討會,他從漢中趕到天津參加并見到了久別的一些前輩與朋友。另一次是1975年,號稱哈工大四杰的榮國俊來訪,找他討論多輸入多輸出系統的解耦和其他問題。
剛從漢中回到北京時,黃琳一家三口包括才三四歲的女兒就住在一間僅十一二平方米的房子里。“一個知識分子只需要有充裕的時間,一個相對寬松安定的環境,能夠從事自己的研究就足夠了。”他用兩年時間整理了一本《應用線性代數講義》并在國防科大等高校講授,然后在此基礎上又歷經幾年精心修改,以“系統與控制理論中的線性代數”為書名于1984年在科學出版社出版。這在當時的條件下為推進國內控制理論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后來此書還被清華大學等多所高等院校列為控制理論專業的研究生學位課程用書,并被評為1984~1985年度科學出版社優秀圖書。黃琳在回憶中寫道:“當今天一些五六十歲的教授告訴我,這本拙著在幫助他們進入控制領域做研究的作用時,可以說這是對我最大的獎賞和慰藉。”
治學:為人低調的實干派
1985年,黃琳作為訪問學者去了美國,當時美國的大學以為中國訪問學者基礎不夠,遂好意為他安排了不少聽課計劃。而他卻心想,自己早已學習過這些基礎課程,來到美國是希望利用當地條件做科研工作。于是他婉拒了這種安排,堅持與美方合作,在國際上剛興起的具參數不確定性系統的魯棒穩定性分析這一嶄新方向上開展研究工作。功夫不負有心人,很快黃琳通過外事處找到了C.V.Hollot教授,兩人共同研究合作,獲得了包括棱邊定理在內的一系列成果,發表了多篇論文,其中棱邊定理僅在SCI就被引用不下數百次。C.V.Hollot也因與黃琳合作為主的一批成果而獲得了美國總統青年研究獎。他在獲獎之后主動出資邀請黃琳于1989年再次訪美進行合作,后來他們還保持了多年的合作關系。
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控制理論研究面臨諸多困難,在這一情況下黃琳聯合中科院系統科學所、自動化所和清華大學等單位一起爭取到國家八五重大基金項目《復雜控制系統理論的幾個關鍵問題》。他作為第一主持人團結大家一起研究,一方面穩定了一支理論研究隊,同時在現代控制理論的一些新領域做出了重要貢獻。根據我國國防建設的需要,近年來黃琳順利地將他的團隊引領到航天控制的領域。今年他爭取到的重點基金已經是有關臨近空間高速飛行器控制的第二個重點項目。
2011年,“控制學科發展戰略研究項目”成立,黃琳為項目主要負責人。在黃琳的組織與領導下,海內外近百名知名專家參與進來,舉辦了多次科技前沿論壇和發表了近20篇科研方向的綜述論文,順利地完成了發展戰略報告,并計劃結集出書。黃琳曾說:“在科學上做成一件事,世界上如能有1000個人知道,有幾個人完全明白,我就滿足了。”擁有這樣“一覽眾山小”而又安于“高處不勝寒”的氣魄,才能體會科研的孤寂,體會上下求索帶來的樂趣。
育人:學風嚴謹的大師
黃琳研究生畢業后即留校工作,在現代控制理論剛剛誕生之時他就在北大開設了一些反映當時國際水平的控制課程,并指導六年制大學生的畢業論文。他的學生中,直接受其影響搞控制研究的人雖然不多,但改革開放以后由于他們控制學的功底厚實,很快就成為了所在工作單位控制領域的學術帶頭人與骨干。北大在1985年被正式批準建立以控制研究為特色的一般力學博士點,黃琳為創始人。他培養的博士生數量并不多,出色的卻不少。在六零后中有從神舟一號即開始進入研究直至成為神舟系列控制系統副總設計師的胡軍;在七零后中有帶領團隊獲得教育部自然科學一等獎、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的長江特聘教授段志生;在八零后中有全國優秀博士論文和國際專業雜志年度最佳論文獲得者李忠奎。他們是黃琳所帶博士的優秀代表,幾乎都是立志創新、不怕困難而又為人低調的實干派,從他們的身上可以充分看到老師的影響。現在黃琳已退居二線,北大的團隊已經由年輕學者組成。黃琳常自豪地說:“他們干得比我更好。”
黃琳是一個甘于寂寞、堅守科學的人,但他并不希望當代所有的學生都向他學習。“社會是由各種各樣的人才組成的,不要要求大家都去做基礎研究。中國真正獻身科學、獻身基礎研究的人,終究是少數,而且也不應該是多數。”黃琳重視質量而非數量,一年只招兩個博士生。他對學生的要求尤其嚴格,特別是在學風方面。“我的學生絕不會抄襲,因為我出的題目他們聞所未聞,無處可抄。”這樣,在他的周圍就形成了學風嚴謹、且善于提出新問題進行研究的良好氛圍。“當年學生們周末會到我家來一塊做題,我們都直接用油筆寫在玻璃上,隨時修改隨時交流。”這種嚴謹好學的學風從他的求學時代延續至今,孕育出一屆屆優秀的學者。不少的博士生在求學時期有了一點點成果就急于發表,沒有精雕細琢的耐心。黃琳認為,這對科學的進步起不了任何作用,學術研究終究是一個長遠的事情,想要做出成果需要日積月累,若是一味地追求發表文章,中國的學術氛圍就始終無法達到一個耐得住寂寞的境界,而科學的道路恰恰是常有寂寞相伴,只有水滴石穿的韌勁才能磨出經得起時間檢驗的成果。
黃琳出生之時適逢經典控制理論初具規模,到他參加工作時剛好迎來了現代控制理論,可以說他的一生見證了控制科學從誕生、發展到逐步完善的過程。如今,雖然已近耄耋之年,黃琳仍然活躍在包括國防科技在內的學術場合,用他自己的話說:“有時還很忙!”
黃琳這一代人與偉大祖國一起經歷了太多磨礪,在動蕩的年代,黃琳能夠那么從容地在政治斗爭之外生存、思考、科研,并做出驕人的業績,這的確需要過人的智慧與勇氣。不管是在會場做報告,與朋友漫談,還是和家人相處,黃琳身上總散發出一種平靜淡然而又飽滿有力的氣場。(來源:《北京青年報》,2014-01-22,有刪節)
“‘文革使中國控制科學與國外的差距進一步拉大,我希望盡己所能地彌補這些差距。”整個“文革”的十年中,黃琳接觸到控制只有兩次,一次是1973年海軍的研究單位因慣導不過關而召開了一次研討會,他從漢中趕到天津參加并見到了久別的一些前輩與朋友。另一次是1975年,號稱哈工大四杰的榮國俊來訪,找他討論多輸入多輸出系統的解耦和其他問題。
剛從漢中回到北京時,黃琳一家三口包括才三四歲的女兒就住在一間僅十一二平方米的房子里。“一個知識分子只需要有充裕的時間,一個相對寬松安定的環境,能夠從事自己的研究就足夠了。”他用兩年時間整理了一本《應用線性代數講義》并在國防科大等高校講授,然后在此基礎上又歷經幾年精心修改,以“系統與控制理論中的線性代數”為書名于1984年在科學出版社出版。這在當時的條件下為推進國內控制理論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后來此書還被清華大學等多所高等院校列為控制理論專業的研究生學位課程用書,并被評為1984~1985年度科學出版社優秀圖書。黃琳在回憶中寫道:“當今天一些五六十歲的教授告訴我,這本拙著在幫助他們進入控制領域做研究的作用時,可以說這是對我最大的獎賞和慰藉。”
治學:為人低調的實干派
1985年,黃琳作為訪問學者去了美國,當時美國的大學以為中國訪問學者基礎不夠,遂好意為他安排了不少聽課計劃。而他卻心想,自己早已學習過這些基礎課程,來到美國是希望利用當地條件做科研工作。于是他婉拒了這種安排,堅持與美方合作,在國際上剛興起的具參數不確定性系統的魯棒穩定性分析這一嶄新方向上開展研究工作。功夫不負有心人,很快黃琳通過外事處找到了C.V.Hollot教授,兩人共同研究合作,獲得了包括棱邊定理在內的一系列成果,發表了多篇論文,其中棱邊定理僅在SCI就被引用不下數百次。C.V.Hollot也因與黃琳合作為主的一批成果而獲得了美國總統青年研究獎。他在獲獎之后主動出資邀請黃琳于1989年再次訪美進行合作,后來他們還保持了多年的合作關系。
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控制理論研究面臨諸多困難,在這一情況下黃琳聯合中科院系統科學所、自動化所和清華大學等單位一起爭取到國家八五重大基金項目《復雜控制系統理論的幾個關鍵問題》。他作為第一主持人團結大家一起研究,一方面穩定了一支理論研究隊,同時在現代控制理論的一些新領域做出了重要貢獻。根據我國國防建設的需要,近年來黃琳順利地將他的團隊引領到航天控制的領域。今年他爭取到的重點基金已經是有關臨近空間高速飛行器控制的第二個重點項目。
2011年,“控制學科發展戰略研究項目”成立,黃琳為項目主要負責人。在黃琳的組織與領導下,海內外近百名知名專家參與進來,舉辦了多次科技前沿論壇和發表了近20篇科研方向的綜述論文,順利地完成了發展戰略報告,并計劃結集出書。黃琳曾說:“在科學上做成一件事,世界上如能有1000個人知道,有幾個人完全明白,我就滿足了。”擁有這樣“一覽眾山小”而又安于“高處不勝寒”的氣魄,才能體會科研的孤寂,體會上下求索帶來的樂趣。
育人:學風嚴謹的大師
黃琳研究生畢業后即留校工作,在現代控制理論剛剛誕生之時他就在北大開設了一些反映當時國際水平的控制課程,并指導六年制大學生的畢業論文。他的學生中,直接受其影響搞控制研究的人雖然不多,但改革開放以后由于他們控制學的功底厚實,很快就成為了所在工作單位控制領域的學術帶頭人與骨干。北大在1985年被正式批準建立以控制研究為特色的一般力學博士點,黃琳為創始人。他培養的博士生數量并不多,出色的卻不少。在六零后中有從神舟一號即開始進入研究直至成為神舟系列控制系統副總設計師的胡軍;在七零后中有帶領團隊獲得教育部自然科學一等獎、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的長江特聘教授段志生;在八零后中有全國優秀博士論文和國際專業雜志年度最佳論文獲得者李忠奎。他們是黃琳所帶博士的優秀代表,幾乎都是立志創新、不怕困難而又為人低調的實干派,從他們的身上可以充分看到老師的影響。現在黃琳已退居二線,北大的團隊已經由年輕學者組成。黃琳常自豪地說:“他們干得比我更好。”
黃琳是一個甘于寂寞、堅守科學的人,但他并不希望當代所有的學生都向他學習。“社會是由各種各樣的人才組成的,不要要求大家都去做基礎研究。中國真正獻身科學、獻身基礎研究的人,終究是少數,而且也不應該是多數。”黃琳重視質量而非數量,一年只招兩個博士生。他對學生的要求尤其嚴格,特別是在學風方面。“我的學生絕不會抄襲,因為我出的題目他們聞所未聞,無處可抄。”這樣,在他的周圍就形成了學風嚴謹、且善于提出新問題進行研究的良好氛圍。“當年學生們周末會到我家來一塊做題,我們都直接用油筆寫在玻璃上,隨時修改隨時交流。”這種嚴謹好學的學風從他的求學時代延續至今,孕育出一屆屆優秀的學者。不少的博士生在求學時期有了一點點成果就急于發表,沒有精雕細琢的耐心。黃琳認為,這對科學的進步起不了任何作用,學術研究終究是一個長遠的事情,想要做出成果需要日積月累,若是一味地追求發表文章,中國的學術氛圍就始終無法達到一個耐得住寂寞的境界,而科學的道路恰恰是常有寂寞相伴,只有水滴石穿的韌勁才能磨出經得起時間檢驗的成果。
黃琳出生之時適逢經典控制理論初具規模,到他參加工作時剛好迎來了現代控制理論,可以說他的一生見證了控制科學從誕生、發展到逐步完善的過程。如今,雖然已近耄耋之年,黃琳仍然活躍在包括國防科技在內的學術場合,用他自己的話說:“有時還很忙!”
黃琳這一代人與偉大祖國一起經歷了太多磨礪,在動蕩的年代,黃琳能夠那么從容地在政治斗爭之外生存、思考、科研,并做出驕人的業績,這的確需要過人的智慧與勇氣。不管是在會場做報告,與朋友漫談,還是和家人相處,黃琳身上總散發出一種平靜淡然而又飽滿有力的氣場。(來源:《北京青年報》,2014-01-22,有刪節)
“‘文革使中國控制科學與國外的差距進一步拉大,我希望盡己所能地彌補這些差距。”整個“文革”的十年中,黃琳接觸到控制只有兩次,一次是1973年海軍的研究單位因慣導不過關而召開了一次研討會,他從漢中趕到天津參加并見到了久別的一些前輩與朋友。另一次是1975年,號稱哈工大四杰的榮國俊來訪,找他討論多輸入多輸出系統的解耦和其他問題。
剛從漢中回到北京時,黃琳一家三口包括才三四歲的女兒就住在一間僅十一二平方米的房子里。“一個知識分子只需要有充裕的時間,一個相對寬松安定的環境,能夠從事自己的研究就足夠了。”他用兩年時間整理了一本《應用線性代數講義》并在國防科大等高校講授,然后在此基礎上又歷經幾年精心修改,以“系統與控制理論中的線性代數”為書名于1984年在科學出版社出版。這在當時的條件下為推進國內控制理論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后來此書還被清華大學等多所高等院校列為控制理論專業的研究生學位課程用書,并被評為1984~1985年度科學出版社優秀圖書。黃琳在回憶中寫道:“當今天一些五六十歲的教授告訴我,這本拙著在幫助他們進入控制領域做研究的作用時,可以說這是對我最大的獎賞和慰藉。”
治學:為人低調的實干派
1985年,黃琳作為訪問學者去了美國,當時美國的大學以為中國訪問學者基礎不夠,遂好意為他安排了不少聽課計劃。而他卻心想,自己早已學習過這些基礎課程,來到美國是希望利用當地條件做科研工作。于是他婉拒了這種安排,堅持與美方合作,在國際上剛興起的具參數不確定性系統的魯棒穩定性分析這一嶄新方向上開展研究工作。功夫不負有心人,很快黃琳通過外事處找到了C.V.Hollot教授,兩人共同研究合作,獲得了包括棱邊定理在內的一系列成果,發表了多篇論文,其中棱邊定理僅在SCI就被引用不下數百次。C.V.Hollot也因與黃琳合作為主的一批成果而獲得了美國總統青年研究獎。他在獲獎之后主動出資邀請黃琳于1989年再次訪美進行合作,后來他們還保持了多年的合作關系。
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控制理論研究面臨諸多困難,在這一情況下黃琳聯合中科院系統科學所、自動化所和清華大學等單位一起爭取到國家八五重大基金項目《復雜控制系統理論的幾個關鍵問題》。他作為第一主持人團結大家一起研究,一方面穩定了一支理論研究隊,同時在現代控制理論的一些新領域做出了重要貢獻。根據我國國防建設的需要,近年來黃琳順利地將他的團隊引領到航天控制的領域。今年他爭取到的重點基金已經是有關臨近空間高速飛行器控制的第二個重點項目。
2011年,“控制學科發展戰略研究項目”成立,黃琳為項目主要負責人。在黃琳的組織與領導下,海內外近百名知名專家參與進來,舉辦了多次科技前沿論壇和發表了近20篇科研方向的綜述論文,順利地完成了發展戰略報告,并計劃結集出書。黃琳曾說:“在科學上做成一件事,世界上如能有1000個人知道,有幾個人完全明白,我就滿足了。”擁有這樣“一覽眾山小”而又安于“高處不勝寒”的氣魄,才能體會科研的孤寂,體會上下求索帶來的樂趣。
育人:學風嚴謹的大師
黃琳研究生畢業后即留校工作,在現代控制理論剛剛誕生之時他就在北大開設了一些反映當時國際水平的控制課程,并指導六年制大學生的畢業論文。他的學生中,直接受其影響搞控制研究的人雖然不多,但改革開放以后由于他們控制學的功底厚實,很快就成為了所在工作單位控制領域的學術帶頭人與骨干。北大在1985年被正式批準建立以控制研究為特色的一般力學博士點,黃琳為創始人。他培養的博士生數量并不多,出色的卻不少。在六零后中有從神舟一號即開始進入研究直至成為神舟系列控制系統副總設計師的胡軍;在七零后中有帶領團隊獲得教育部自然科學一等獎、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的長江特聘教授段志生;在八零后中有全國優秀博士論文和國際專業雜志年度最佳論文獲得者李忠奎。他們是黃琳所帶博士的優秀代表,幾乎都是立志創新、不怕困難而又為人低調的實干派,從他們的身上可以充分看到老師的影響。現在黃琳已退居二線,北大的團隊已經由年輕學者組成。黃琳常自豪地說:“他們干得比我更好。”
黃琳是一個甘于寂寞、堅守科學的人,但他并不希望當代所有的學生都向他學習。“社會是由各種各樣的人才組成的,不要要求大家都去做基礎研究。中國真正獻身科學、獻身基礎研究的人,終究是少數,而且也不應該是多數。”黃琳重視質量而非數量,一年只招兩個博士生。他對學生的要求尤其嚴格,特別是在學風方面。“我的學生絕不會抄襲,因為我出的題目他們聞所未聞,無處可抄。”這樣,在他的周圍就形成了學風嚴謹、且善于提出新問題進行研究的良好氛圍。“當年學生們周末會到我家來一塊做題,我們都直接用油筆寫在玻璃上,隨時修改隨時交流。”這種嚴謹好學的學風從他的求學時代延續至今,孕育出一屆屆優秀的學者。不少的博士生在求學時期有了一點點成果就急于發表,沒有精雕細琢的耐心。黃琳認為,這對科學的進步起不了任何作用,學術研究終究是一個長遠的事情,想要做出成果需要日積月累,若是一味地追求發表文章,中國的學術氛圍就始終無法達到一個耐得住寂寞的境界,而科學的道路恰恰是常有寂寞相伴,只有水滴石穿的韌勁才能磨出經得起時間檢驗的成果。
黃琳出生之時適逢經典控制理論初具規模,到他參加工作時剛好迎來了現代控制理論,可以說他的一生見證了控制科學從誕生、發展到逐步完善的過程。如今,雖然已近耄耋之年,黃琳仍然活躍在包括國防科技在內的學術場合,用他自己的話說:“有時還很忙!”
黃琳這一代人與偉大祖國一起經歷了太多磨礪,在動蕩的年代,黃琳能夠那么從容地在政治斗爭之外生存、思考、科研,并做出驕人的業績,這的確需要過人的智慧與勇氣。不管是在會場做報告,與朋友漫談,還是和家人相處,黃琳身上總散發出一種平靜淡然而又飽滿有力的氣場。(來源:《北京青年報》,2014-01-22,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