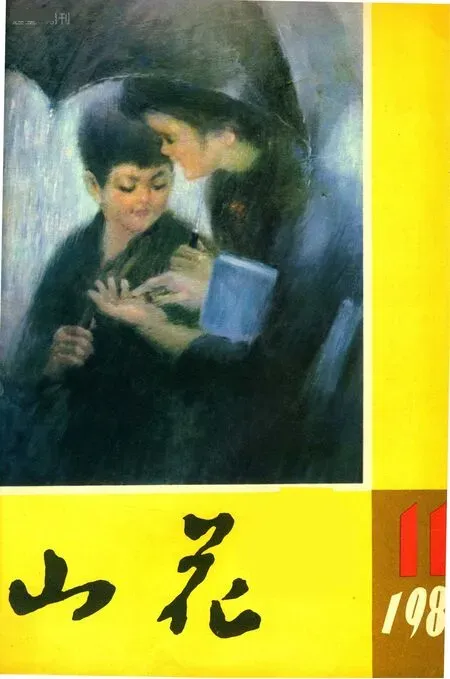喻指視角下托尼·莫里森小說研究
托尼·莫里森,原名柯勒爾·安桑妮·威福爾德,是美國當代文壇一位極富盛名的非裔女作家,也是截至目前唯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殊榮的美國非裔女作家,堪稱美國非裔文學創作的旗手。出身貧寒的莫里森從小目睹了非裔群體生活的點點滴滴,尤其是深切體會了非裔女性在以白人文化為主流的社會里的屈辱掙扎。這種深沉的社會經歷為其文學創作積累了大量鮮活的素材,自從1970年發表小說《最藍的眼睛》以來,先后創作了《秀拉》、《所羅門之歌》、《柏油孩子》、《寵兒》、《爵士樂》、《天堂》、《愛》、《仁慈》等近十部長篇小說。莫里森的這些作品基本都以非裔人物為關注對象,通過細膩的筆觸、豐富的想象力、深邃的洞察力與犀利的批判精神,不僅揭示了美國非裔群體的生存困境,而且展現了20世紀以來美國波瀾壯闊的社會畫卷,特別是以隱喻的手法表達出對族裔文化的敬仰與種族制度的譴責。本文以喻指理論為視角,通過對托尼·莫里森幾部小說的文本分析,對其創作中語言、意象的喻指涵義進行探究,管窺莫里森的獨特創作觀念。
喻指理論概述
在人本主義與科學主義這兩大西方哲學思潮的影響下,西方文藝理論自20世紀以來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其反傳統意識不斷增強,尤其是在經歷了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文學創作階段之后,西方文藝理論有了質的改變,逐步實現了語言學轉向與文化轉向。在這樣的轉向背景之下,美國非裔學者小亨利·路易斯·蓋茨提出了對學界震動頗大的非裔美國文學理論,尤其是其喻指理論對當下非裔文學創作影響甚大。喻指理論主要體現在蓋茨的兩部專注《黑人形象:詞語、符號與種族性的自我》和《表意的猴子:非裔美國文學批評理論》中,這是后殖民主義時期對族裔文學價值的一次嘗試性探討。所謂“喻指”是非裔美國文化中特有的一種語言現象,雖然字面意義較為費解,但是涵義卻極為幽默,是非裔美國人在日常生活與文藝創作中慣用的一種表達方式,諸多文藝批評家及作家如哈羅德·布魯姆、羅杰·D·亞伯拉罕、克勞迪婭·米歇爾·科南、佐拉·尼爾·赫斯頓等分別從不同的視角對“喻指”下了定義,蓋茨在吸取他人理論合理部分的基礎上對“喻指”給出了自己的定義:指黑人英語在標準英語意義表達的過程中由于增添轉義而產生的具有族裔特點的表意方式,是構成美國非裔文學特殊性的重要因素。這種包含眾多修辭方式的“轉義”體現了長期以來非裔群體在奴隸制下掙扎求生的語言技巧,也是非裔美國人智慧與幽默的表現。從來源上來說,喻指理論源于結構主義文藝批評理論和符號學以及文化文論,也就是體現在語言學與文化兩個層面。而在具體的文學創作與文藝批評中,喻指既包含語言喻指(詞匯與意象),又包括文本喻指。該理論的提出一方面批判了長期以來白人主流文化對非裔文學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為非裔文學研究提供了全新視角,特別是對非裔美國文學獨立地位的確立有著極大的理論指導意義。
托尼·莫里森小說中的喻指表現
作為非裔美國文學的重量級人物,托尼·莫里森對非裔美國文化自是有著深刻的了解,因此她在文學創作中使用了大量的喻指,具體來說其小說創作中的“喻指”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語言喻指
漫長的奴隸制度對黑人產生了不可消除的負面影響,其中關鍵的一個就是剝奪了他們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從而使他們幾乎沒有借助書面語言表達情感的能力,這樣,口頭語言便成了他們的主要情感表達途徑。喻指又是黑人口頭語言的主要特征,蓋茨曾經這樣描述:“美國黑人傳統自起始階段起就是比喻性的,否則它如何得以生存至今呢?……黑人一開始就是比喻大師:說一件事而意指另一件事,這是在西方文化壓抑中求生存的一種基本方式。”而托尼·莫里森小說中聚焦的人物往往都是沒有接受良好教育的非裔美國青年或者黑人奴隸,比如《所羅門之歌》與《秀拉》中的主人公是社會青年、《最藍的眼睛》中關注的是貧困的小學生、《仁慈》中的主人公是黑人女奴、三部曲(《寵兒》、《爵士樂》、《樂園》)描述的主要是歷經奴隸制在下層打拼的中年人。他們就用獨特的“喻指”化語言表達了其內心世界以及文化傳統,同時向具有種族歧視的主流社會發起了挑戰。比如在《所羅門之歌》中有一段關于麗芭鉆戒的對話,頗具諷刺意味。在對話中不斷提到“五十萬”,讓大家都以為是鉆戒的價格是“五十萬”,而實際上它只是麗芭走進某一商場的順序而已,這恰巧是她得以幸運贏得鉆戒的原因,諷刺的是麗芭只是要進這個允許黑人如廁的商場方便而已,絕不是為了買東西,甚至連一絲買東西的欲望都沒有。在那個年代,黑人是不允許隨便進入一些地方如廁的,不成想那次經歷讓麗芭得到了一枚鉆戒,但是我們可以想象店老板是多么不愿意把它送給一個只是進入商場如廁的黑人,這以“幽默”的方式映射了種族制度。
除了使用對話形式進行喻指外,托尼·莫里森在小說中使用了不少民間傳說故事,借助非裔美國傳說中的神秘怪誕現象隱喻現實,開創了意蘊深刻的神話敘事新傳統。比如小說《寵兒》一開篇就是關于124號房子的神秘描述,其中“鏡子一照就碎”、“蛋糕里出現的兩個小手印”、“一鍋鷹嘴豆隊在地板上冒煙兒”等現象把一個嬰兒的詛咒彌漫在房子中。在這里莫里森借用了非洲神話傳說中鬼神與人類在異質空間生活并存的觀念,從而把賽斯無法擺脫心理陰影的困境恐怖地展示出來。當然這些怪異神秘的現象并不是簡單地讓故事充滿懸疑色彩,而是喻指歷史中那段恐怖得令人無法忘卻的奴隸制時代。
2.意象喻指
豐富的意象是托尼·莫里森小說創作的重要特征之一,這些意象有來自西方文學經典文庫的,也有源于非裔民間傳說的。經過喻指手法的運用,這些意象除了體現莫里森深厚的語言功底之外,更有深刻的文化寓意。比如小說《柏油孩子》中“柏油孩子”意象的運用就是西方圣經故事與非裔民間故事的融合,故事的人物框架就是以民間故事中“兔子”、“農夫”、“柏油孩子”為原型設計的,但是卻對原有的人物關系重新布局,旨在體現現代非裔美國人在文化繼承與同化中的融合表現。對“柏油孩子”的喻指也許尚存爭論,有的認為是喻指女主人公“雅丹”,因為她接受了混合教育,并且具有強大的吸引力,但是她已經是變味了的“柏油孩子”,因為她骨子里流淌的是白人的血;也有認為“柏油孩子”泛指非裔美國人自身的黑人特性(blackness),即指的是非裔民族具備的具有強烈凝聚作用的民族特性,它是無法抹殺的“內質”,就像雅丹無論如何傾向于白人文化,但最終心底還是皈依于非裔族群。另外在《所羅門之歌》中“飛人”意象貫穿故事全局,這個取材于民間傳說的意象表達了人們對暢游自由天空的向往,而在小說中具有特殊的含義,整體上表現了非裔美國人對“自由”的追求。小說開頭“飛人”羅伯特·史密斯的飛行是為了擺脫黑人暴力組織,而結尾另一“飛人”奶娃的飛行則是為了制止暴力分子,這也是其人生第一次飛翔。不管哪一個“飛人”,他們都是為了追求靈魂的自由。
“柏油孩子”與“飛人”只是莫里森小說中兩個較為典型的意象,她的作品中還有很多涵義豐富的意象,但基本上都是為了突出或喚醒非裔美國人的民族主體意識,比如莫里森還通過特殊的命名進行喻指。在《所羅門之歌》中,莫里森把一個十分殘忍的黑人極端主義組織命名為“七天”,這是有意利用《圣經》內容進行喻指。在《圣經》中我們都知道,上帝用了整整六天創造了世界,第七天完全可以休息了,也被稱之為圣安息日。也可以說“七天”在基督教中意味著新世界的完全建立和新生活的開始,一片美好祥和,充滿希望。但是在小說中,“七天”則完全相反,該組織既不是意在構建新世界,也不是純粹的改革現實,而只是通過暴力手段來毀滅白人以及任何敵對者,旨在發泄種族仇恨。“七天”的行為是非常瘋狂的,比如在其活動期間,必須每天殺死一個包括婦女老幼在內的白人,充分體現了人性的殘忍、愚昧、野蠻等陰暗面。當然,這并不是莫里森要宣揚的要點,她只是通過血淋淋的事實讓世人看到社會的殘酷性和人類的愚昧,因此她通過“七天”這個特殊的名字,讓整個事件充滿荒誕色彩,從而啟發人們的深思,表達出對受害的弱勢人群的同情。這樣充滿荒誕意味的命名在《所羅門之歌》中還有很多,比如主人公的名字為梅肯·戴德,即“Maken Dead”,意為不祥的“讓……死亡”。可以說這樣充滿“厄運”的名字在西方世界姓氏中根本不存在,因此它的出現在怪誕中隱喻出特殊的涵義。小說中,莫里森把這個名字的出現歸因于奴隸解放時期白人官員的筆誤,即在為這個家族登記的時候把姓氏寫為“梅肯·戴德”,這一方面體現了白人對黑人的態度并沒有多大改變,另一方面則與奴隸解放后“重獲新生”的口號宣言形成強烈的諷刺性對比。雖然這個名字是那么地充滿“死亡”意味,但他們還是接受了它,并且堅持傳承下去,從而讓后人記住他們獲取“自由”的艱辛,尤其要記住: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變幻,他們的生命力是頑強的,他們絕不會因為一個名字而停止追求美好生活的腳步,這也正是托尼·莫里森使用特殊名字意象的良苦用心。
結 語
“喻指”是非裔民族語言文化發展的主要特色,它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非裔群體的智慧的濃縮,而托尼·莫里森正是意識到了“喻指”對于非裔美國民族傳統文化發展的重要性,于是借助高超的語言技巧塑造了一個個文學經典。而根據小亨利·路易斯·蓋茨的喻指理論對其小說創作進行分析可謂不錯的選擇,既可以讓我們進一步了解“喻指”的魅力,更可以讓我們領略托尼·莫里森駕馭語言與文化的至深功力。
[1]宗蔚.《最藍的眼睛》中一個黑人家庭的悲劇——美國黑人“兩難”生存困境的真實寫照[J].外語研究,2008(3):89-91.
[2]詹姆斯·費倫.作為修辭的敘事:技巧、讀者、倫理、意識形態[M].陳永國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3]謝群英.莫里森《最藍的眼睛》中的主題與象征意象[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29(6):160-162.
[4]王守仁,吳新云.性別·種族·文化:托尼·莫里森與二十世紀美國黑人文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5]孟慶梅,姚玉杰.莫里森《最藍的眼睛》民族文化身份缺失之悲劇與思考[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40(4):174-176.
[6]甘振翎.民族文化的生存與兩性關系的協調——托尼·莫里森和她的《所羅門之歌》[J].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15(03):76-79.
[7]郭秀娟.隱喻的故事與象征的意味——論喻指理論在莫里森小說《寵兒》中的作用[J].小說評論,2011,(s01):90-91.
[8]朱榮杰.傷痛與彌合:托尼·莫里森小說——母愛主題的文化研究[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
[9]Fisher,Dexter and Stepto,Roboert B.ed.,Afo-American Literature:the Reconstruction of Instruction[M].New York:The Modern Lang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