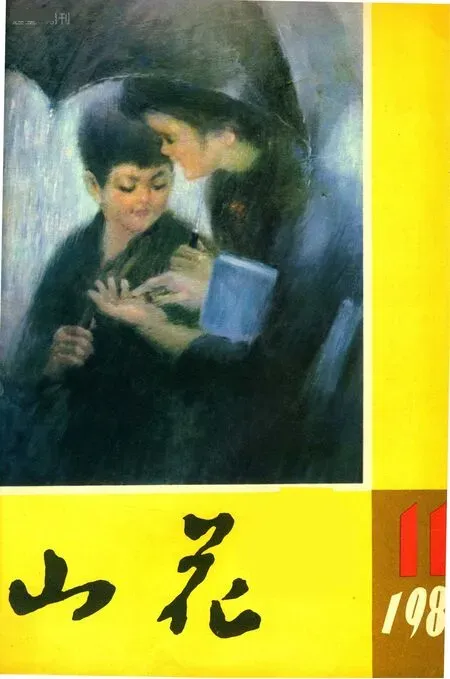到美國去
陳謙
今年2月17日,我來到美國整整二十五年了。
這個(gè)早晨,舊金山灣區(qū)在下雨,我假想我在此刻回望,二十五年經(jīng)過的事,見過的人,果然如風(fēng)雨中的羽毛四處翻飛,有些飄遠(yuǎn),有些沉落,無論在天空還是在泥水里,它們都給染出了雜色。如果我站出去張手接迎,能把握的實(shí)在少得可憐。
更多的時(shí)候,它們存在的影子會(huì)在晴空萬里的日子里突襲而來,這里一片,那里一片,星星點(diǎn)點(diǎn)。那種時(shí)候,我除了注目,從不試圖撿拾。
我離開你們?cè)絹碓竭h(yuǎn)了,你們卻一直在我的呼吸中,那便叫記憶了。
1
1988年11月底,我乘火車來到廣州,申請(qǐng)赴美留學(xué)簽證。
我的行李少得可憐,不及我如今出門時(shí)的一個(gè)零頭。我?guī)е鴲圻_(dá)荷大學(xué)給我發(fā)放的I-20表——我這么一說,所有有過赴美留學(xué)經(jīng)驗(yàn)的人都會(huì)立刻明白它意味著什么。到了今天,所有赴美的自費(fèi)留學(xué)生,還是拿著同樣的表格。
可是,我的表格卻又不是那么普通。在表格的最下端,打著一行字:該錄取只在表格持有人的TOFEL等成績達(dá)到學(xué)校的要求后才正式生效。也就是說,它是一份有條件錄取通知書。在赴美自費(fèi)留學(xué)簽證極不容易獲得的上世紀(jì)80年代,手持這樣一份I-20表格去辦簽證,實(shí)在有點(diǎn)搞笑的。
可直覺告訴我,我會(huì)走運(yùn)的。
我那時(shí)已經(jīng)不上班有好一陣了。因已決定要去美國,就去申辦停薪留職,想學(xué)學(xué)英文——之前,我不知有多久沒看過英文了,突然拿起《新概念英語》第二冊(cè),要看懂竟還得查字典。我那幾年渾渾噩噩,被無窮無盡的青春煩惱折磨著,感覺前途一片灰暗。終于也隨起大流,想出去轉(zhuǎn)轉(zhuǎn),可能也可轉(zhuǎn)運(yùn)也不定。
原單位的頭兒死活就不同意我停薪留職,威脅我說,那么你干脆就辭職。那時(shí)我竟不曾想過要辭職!或說不敢。我天天去頭兒的辦公室磨。那頭兒是五十年代大學(xué)畢業(yè)后從上海分來廣西的上海人,平常看到吊兒郎當(dāng)?shù)奈揖皖^疼。所以我死活想不通,為什么他就不讓我離開。
我找到譚總——我供職的單位所屬的市里主管局里的總工,請(qǐng)他為我想想辦法。譚總在我代單位向他送報(bào)告時(shí)認(rèn)識(shí)我的,曾借調(diào)我到他的辦公室工作過一段時(shí)間,我每日在那里為他寫企劃書,報(bào)表,顯然,他對(duì)我的工作是滿意的。可單位里一直在催譚總讓我回去,理由竟是單位里的革命工作太需要我了。我的天,他們一見我就愁容滿面,頭疼腦熱的,心里卻又是多么擔(dān)心我滑腳跑了呀。
譚總和太太都是湖南人,也是五十年代大學(xué)畢業(yè)后分到廣西來工作的。譚總話很少。他家里三個(gè)兒子,所以他明顯地對(duì)女孩子比較耐心友善。
我站在春節(jié)前的寒雨中,在譚總家的樓下截住了正要出門的譚總。他聽我焦急地訴說了面臨的困境,馬上答應(yīng)幫我試一試。譚總在一個(gè)星期內(nèi)為我找到了愿為我接掛檔案的單位。我在寒雨中的南寧街頭東奔西跑,好不容易跑完接收單位這頭,我的原單位卻不同意放人。這時(shí),若讓主管局的領(lǐng)導(dǎo)譚總?cè)袼麄兎湃耍@然是不很合適的。這時(shí),我決定去見西寧兄。
西寧兄該是五十年代中期出生的,高干子弟。老媽山東人,老爸陜西人。我們算世交。他在七十年代去長沙當(dāng)了工農(nóng)兵學(xué)員回來,在一家很大的國營冶煉廠工作。每個(gè)時(shí)代都有弄潮的時(shí)髦人,西寧兄就是他那個(gè)時(shí)代的弄潮兒。他無論言談舉止還是衣著打扮,都是那個(gè)時(shí)代的時(shí)尚。到了八十年代,他忽然就紅起來,成了市經(jīng)委的領(lǐng)導(dǎo)之一,到處見到他的名字。他那時(shí)儼然政界新星,可惜最終也沒走很遠(yuǎn)。想來可能跟行事過于高調(diào)、鋒芒太過直露有關(guān)。當(dāng)然,是否跟對(duì)了人,更是關(guān)鍵。
我在大年三十的下午找到他父母家中時(shí),他剛和妻子抱著娃娃進(jìn)門,是回家過年了。我們有些時(shí)候未見了,可西寧兄聽我一說情況,手一擺,說,我過了節(jié)就去辦。切,若真是不行,讓你辭職你就辭,怕啥。如果真走不了,我給你再找個(gè)更好的單位!你不要怕!
意氣風(fēng)發(fā)的西寧兄果然節(jié)后就讓他的同事,主管我所在的行業(yè)口的副主任給他過去的老部下、我單位的頭兒去了電話讓放人。等我被蓋章放人的時(shí)候,頭兒說,看你平時(shí)挺老實(shí)的嘛!我很想說,老實(shí)人給逼急了也只能這樣了,但還是因?yàn)槔蠈?shí),沒敢說出口。
如今想到當(dāng)年我在陰雨綿綿的春天里無頭蒼蠅一樣?xùn)|撞西撞的樣子,真真是叫恍若隔世了。我不愿意,也必須很吃力地做著這些到處奔波找關(guān)系的事情。哪怕就是那么一點(diǎn)點(diǎn)小小的愿望,小小的正當(dāng)要求,也需要人如此費(fèi)力奔波啊。它讓初入社會(huì)的我清楚地看到,在那個(gè)地方,一個(gè)小民的生活有多么艱難。
我去了愿意接受我的新單位面談。印象里,他們還讓我考了筆試。我當(dāng)時(shí)只是想,他們?cè)敢庾屛覍⑷耸玛P(guān)系掛著就好了,我真的就想只是停薪留職。接見我的是單位里的第一把手金總,是在德國進(jìn)修過一年的中年知識(shí)分子,江浙人,戴著眼鏡。他跟我說,我們送你去學(xué)英文,工資照發(fā)。我對(duì)年輕人愿意學(xué)習(xí)上進(jìn)是很鼓勵(lì)的。將來能出去,當(dāng)然是好事,可以見見世面;若出不去,學(xué)好英文,對(duì)今后的工作也是有益的。
我大喜過望。我在那一年里,就帶著這個(gè)自己沒上過一天班的單位發(fā)給我的工資,脫產(chǎn)學(xué)英文去了。這家我從未上過一天班的老單位,如今從資料上看效益相當(dāng)好,祝福它。金總該退休了。我跟他就一面之緣。在我拿到簽證就要離開之前,他曾捎話來說要為我餞行,我因行程改變,都未去見成他。這么多年來,我很少想起他,只在此時(shí),當(dāng)我打下這些字,他在我的背景里跳出來。我深深地感激他。
而譚總已退休多年。他年紀(jì)大了,身體不是特別好。我每次去看他們,他和太太都非常高興,譚總還是話很少,我就跟他太太藍(lán)阿姨聊些家常。
他們是我生命中的貴人。
2
我去廣州之前,已經(jīng)報(bào)名參加1989年1月的托福考試。當(dāng)時(shí)心里很有把握。如果按部就班,我就該在拿到正式的TOFEL成績后,再給學(xué)校發(fā)入學(xué)申請(qǐng),我心里最理想的日程,就是能在1989年的秋季入學(xué)。
可是,奮強(qiáng)向我指出了另一種可能性!
奮強(qiáng)是我小學(xué)一直到高中的同學(xué)。他在中學(xué)期間,一直坐在我的身后。他性格溫和浪漫,個(gè)子很高,畫一手好畫,很會(huì)唱歌,寫很華麗的文章,很討女孩子們喜歡的。他大學(xué)學(xué)的是中文,大學(xué)畢業(yè)后開始弄影視攝影。他母親當(dāng)時(shí)在南伊利諾大學(xué)進(jìn)修,為他辦下了南伊大電影系的“有條件錄取”,這家伙TOFEL沒考,就沖到廣州去了,竟然拿到了簽證。我去廣州時(shí),他已到了美國。奮強(qiáng)如今生活在佛羅里達(dá)的奧蘭多,和太太經(jīng)營著一所學(xué)校,發(fā)展相當(dāng)好。他當(dāng)年跟我講到他立志去美國的原因,是“如果人間有天堂,美國就是天堂”——我下次有機(jī)會(huì)再見他,真的該問問他如今是否還這么想。
我聽了奮強(qiáng)的說法,立刻就給當(dāng)時(shí)在愛達(dá)荷大學(xué)讀研的甲去信,讓甲幫我也去向我申請(qǐng)的系里要求發(fā)“有條件錄取”。對(duì)所有的捷徑,我都躍躍欲試。我想我的運(yùn)氣從來都不比奮強(qiáng)差,這竟然就是我的信心來源。
我果然也拿到了跟奮強(qiáng)一樣的有條件錄取的I-20表。
表妹阿紅將我從車站接出。我們坐上公車,沿人民路,一直往南,去向五羊城酒店——我那位從暨南大學(xué)化學(xué)系畢業(yè)的表弟阿光,業(yè)余跟朋友在做公司,專營化工原料,做得有聲有色。公司在五羊城酒店包有套間,我跟阿紅將住在那里。
公車經(jīng)過流花公園對(duì)面的東方賓館。當(dāng)年的美國駐廣州總領(lǐng)事館,就在東方賓館內(nèi)。在公車上,我就已經(jīng)看到了從美領(lǐng)館里排出的長隊(duì),轉(zhuǎn)過街角,蜿蜒而去,非常壯觀。如今聽說簽證要預(yù)約了,想來像當(dāng)年那樣先到先得的排隊(duì)方式,就成了歷史。
廣州美領(lǐng)館管著廣東、福建、廣西三省區(qū)的非移民簽證和全國的移民簽證。我聽過太多關(guān)于它的傳言了。自己忽然就要親自面對(duì)了,心下就有些興奮起來。
我那時(shí)對(duì)廣州是不陌生的。在念大學(xué)的時(shí)候,我和好友曉苒曾在暑假里來廣州投奔她在中山醫(yī)大讀法醫(yī)專業(yè)的表弟乃寧,在中山醫(yī)大的女生宿舍里住了好久,沒事就在廣州城里到處亂逛。大學(xué)畢業(yè)實(shí)習(xí),我也是來的廣州。
乃寧大學(xué)畢業(yè)后去了北京市公安局。他回南寧探親時(shí),就向我們宣稱有空給我們講講現(xiàn)場(chǎng)的故事,“包你聽得耳朵都動(dòng)!”他如今在費(fèi)城的一個(gè)器官移植中心當(dāng)個(gè)小頭目。
乃寧個(gè)子不高,樣子卻很男人。他自幼打羽毛球,哥哥如今都還是廣西隊(duì)的教練。他當(dāng)年是中山醫(yī)大羽毛球校隊(duì)的主力,他們隊(duì)那時(shí)剛拿了廣州高校的冠軍,在學(xué)校里很出風(fēng)頭,我們跟在他身后,出入時(shí)都有學(xué)校里的女孩子來找他傾談。他可能覺得我很傻,就很愛逗我生氣,我們?cè)谝黄鸪3臣堋N夷菚r(shí)非常缺乏幽默感,他開個(gè)玩笑讓我不爽,就會(huì)認(rèn)真生氣起來。弄得溫和的曉苒夾在中間很尷尬。如今他回國見到曉苒,會(huì)說,哎呦,你那個(gè)同學(xué)陳某,好喜歡東寫西寫喔,我在美國的華文報(bào)上不小心就會(huì)撞到這只大頭蝦!(會(huì)廣東話的人都曉得這不是啥妙詞兒)我如今聽了,會(huì)很開心地笑笑。可年輕時(shí),總把人的客氣當(dāng)福氣,曾為了他的一個(gè)玩笑,竟當(dāng)眾將一只臉盆踢飛。我都不能原諒自己的無禮,就已經(jīng)不好意思了這么多年了。
我印象極深的是,當(dāng)我們由乃寧領(lǐng)著在廣州的大街小巷中穿行時(shí),偶爾看到一輛神氣的雅馬哈大摩托,他會(huì)無比神往地說,他這輩子的理想,就是要擁有這樣一輛摩托!我當(dāng)時(shí)聽了就“噗哧”笑出聲來。我們?cè)谀莻€(gè)年代,大把的青春,無限的可能,我哪里肯將眼光落到一件那么具體的物件上!我在心里,就有點(diǎn)看不上這樣的心志。我沒受過餓,也沒吃過了不起的苦,雖然一身青澀,兩手空空,那心思也是不愿意落到地面上扎根的。
因?yàn)橐獙戇@些舊事,我專門上網(wǎng)查了一下我當(dāng)年辦理來美簽證時(shí)住過的廣州五羊城酒店,發(fā)現(xiàn)它的地址在廣州市人民中路322號(hào)。因在2006年全面裝修過,已看不出它當(dāng)年的情景。只有一幅非常小的老照片,還讓人能依稀辨認(rèn)出她當(dāng)年的模樣:小小的門臉,闊大的庭院停車場(chǎng),然后是一棟十幾層高的樓。酒店的門口有一棵大榕樹,一拐出去,就是熱鬧的街市,兩廣特有的騎樓,黑呼呼的一片。街對(duì)面有個(gè)很大的基督堂,婦幼醫(yī)院,酒樓,茶樓,熱鬧非凡,離繁華的上下九路,北京路也不很遠(yuǎn)。
阿光公司包下的是個(gè)大套間,外面是辦公室,我和阿紅就住在里面的客房。我們到達(dá)時(shí),見到阿光和他的朋友,可能還有客戶。他們?cè)谕忾g的沙發(fā)上聊天說笑。見我們進(jìn)來,一一介紹。阿光還是那樣樂呵呵的,問了我的事情,想也沒想就說,你肯定簽得出去的。我說很難的,就是試試,阿光說,我說行肯定就行的。
我心下當(dāng)然高興,謝他吉言。
阿光當(dāng)年是暨大足球校隊(duì)的,身體很壯實(shí),總是笑容滿面。我上回見他,是一年多前的春節(jié),他陪學(xué)校里的一個(gè)南寧女孩子小方回家。我們見過那個(gè)叫小方的人,全都對(duì)她驚人的美貌印象深刻。到了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們談起,還是說那小方的好看,更重要的是氣質(zhì)也很好。我們?yōu)榘⒐鉀]有娶她深感遺憾。小方家里在南寧西郊的一個(gè)學(xué)院里,那年阿光是專程陪她回南寧的,然后帶她到我家里來轉(zhuǎn)了一圈。我們?nèi)叶荚鵀榘⒐鈳砹藗€(gè)那么漂亮有氣質(zhì)的女孩而興奮。
可是,我那日剛坐下,就見一非常時(shí)髦的年輕女子進(jìn)來,已經(jīng)不是小方。一見那女子,表妹阿紅的臉立刻拉下。待他們走后,阿紅開始向我數(shù)落,我雖知道小姑這種角色的特別,但心里卻真為阿光沒跟小方在一起有些難過。阿光做生意,在那個(gè)時(shí)代已開始有錢。
我到廣州的第二天,一早起來就去美領(lǐng)館打聽虛實(shí)去了。現(xiàn)在想起來,我當(dāng)年還算是個(gè)主動(dòng)積極的人。如今讓我天沒亮就爬起床,精神十足地出門辦事,簡直寧愿被揍一頓。
美領(lǐng)館是按美國作息方式辦公的,周六不上班。我去的那日,該是星期五,是想先去看看情況,然后周一再去正式辦理簽證。而且,我還想找一個(gè)在美領(lǐng)館工作的女孩了解一下情況。
我到的時(shí)候,天已大亮。那壯觀的長隊(duì)轉(zhuǎn)出到了街外。我轉(zhuǎn)到靠近簽證部的一處,那里有個(gè)小房間可以領(lǐng)申請(qǐng)表格,我想領(lǐng)了也好,這樣回去填好,周一帶來,不用到時(shí)再填,就上去要了表格。簽證部周邊到處是人,有辦簽證的,更多的是像我這類來打聽的。一群群的,站在一起交流心得。我聽了一下,都很悲觀。這個(gè)被拒,那個(gè)被拒,聽得我有點(diǎn)沒信心了。
我就是在這樣的人群中撞到春寧的。她當(dāng)時(shí)穿一件大紅的薄毛衣,黑色的尼龍健美褲,個(gè)子不高,扎一條長辮,給我的第一感覺是頭很圓。她轉(zhuǎn)過頭來,我發(fā)現(xiàn)她的臉也很圓,眼睛也很圓,皮膚黑紅黑紅的。我忘了我們?cè)趺戳钠饋淼模故悄蠈幠持袑W(xué)的英文老師!
如果不是我們那兒辦了附中,我們?nèi)荚撊ニ缃袢谓痰哪撬袑W(xué)念書的,可見她的單位離我小時(shí)住的地方有多近。又因我過去鄰居的帥哥兒子跟她在同一教研組里,我們一下就聊得很熱火了。
春寧告訴我,她是來辦F-2,也就是探親陪讀的簽證。她的先生喬,是南寧師院物理系的老師,這樣一說,我們的校花就是喬的同事,又拉近一步。喬半年前去了紐約,她的兒子才幾個(gè)月。在那個(gè)年代,自費(fèi)留學(xué)的F-1簽證本身就很難簽,配偶的F-2,就更難了。可春寧卻非常自信,她說,要看看是什么人來簽!美國要的是精英,是良種。我給她逗得笑起來。我的朋友里,是沒人這么說話的,我就想,這女人結(jié)了婚還是蠻嚇人的,再生過了孩子,“良種”就能脫口而出了。
春寧說她不帶孩子去,這樣拿到簽證的可能性就大得多。她聽了我的情況,說,唯一不妙的,是你未婚,這很可能會(huì)有移民傾向嫌疑。而移民傾向,是最忌諱的,只要你的護(hù)照上給蓋上個(gè)“214B”,幾乎就是上了絕路的。見我的情緒給說得有點(diǎn)低落,她趕緊又說,沒問題的,你要有信心。我們?cè)谝黄鹆牧撕靡粫?huì)兒,她非常直爽,而且有那種我還很不熟悉的已婚女子的大嫂味兒,讓我對(duì)她生出了興趣和好感,所以當(dāng)她說到自己住在珠江對(duì)岸的珠江電影制片廠里的友人家中,正為周一如何能一大早趕來這兒簽證發(fā)愁時(shí),我想也沒想,就邀她搬來跟我和阿紅擠一擠,這樣,我們也可有個(gè)伴兒一起來簽證。那時(shí)真是沒一點(diǎn)概念,我要帶人來擠,至少該跟阿紅打聲招呼的。好在阿紅是個(gè)很隨意的人,后來見春寧來,還很熱情招待了。
春寧非常高興。我給了她我酒店房間的電話,她說她星期天夜里來。我們就道別了。我拿好表格,看了看,很容易填的,就放心了。
從亂哄哄的人堆里擠出來,我尋到美國領(lǐng)事館邊上的電梯,乘到東方賓館高層。我來廣州前,老爸的朋友葉叔叔聽說我要去辦簽證,就說,他那學(xué)院里徐老師的閨女,廣州外語學(xué)院畢業(yè)后到了廣州美領(lǐng)館里工作,讓我去找那姑娘打聽一下,看能不能有什么幫助。葉叔叔是徐姑娘父親任教的那所學(xué)院的書記,他跟徐老師又是朋友,所以徐家的閨女也很熟悉他。于是我拿到徐老師寫給他女兒的一封信,就找上門來了。
電梯到頂層,一出來,就見到美國國徽。門口有兩位站崗的中國士兵。我過去跟士兵講,我要找徐姑娘。士兵便打電話進(jìn)去尋人。我站在闊大的通道里,好奇地看著那門后的美國領(lǐng)地。
徐姑娘很快出來了。她應(yīng)該跟我差不多年紀(jì)。燙過的齊肩短發(fā),穿一件白衣,淺灰的百褶裙,戴一幅白框的眼鏡,很斯文。她微笑著,很禮貌。我自我介紹過后,將她爸爸的信給她。她看后折起,問我的情況。我將我的I-20表等遞給她看。她沉吟片刻,說,這好像有點(diǎn)難,有些有獎(jiǎng)學(xué)金的都簽不出呢。言下之意,我這種“有條件錄取”的,呵呵。可我心里竟不很服氣,因?yàn)閵^強(qiáng)簽出去了呀!奮強(qiáng),我們從幼兒園就認(rèn)識(shí)的,我的運(yùn)氣從來不輸他呀!
徐姑娘將文件等還給我的時(shí)候,問,你打算什么時(shí)候來簽?我說,星期一。她說,那好的。我不知道她說的“好的”是啥意思。但也不好多問,就謝過她,兩人別過。
想到徐姑娘都認(rèn)為我的情況很難,心里開始有點(diǎn)煩亂。再走到簽證部時(shí),就想起,按他們介紹的,也可去廣東省教育廳的留學(xué)服務(wù)中心看有什么TIPS。我如今記不得那個(gè)留學(xué)服務(wù)中心具體在哪里,好像離東方賓館并不遠(yuǎn)。那是一個(gè)免費(fèi)服務(wù)的機(jī)構(gòu),我到時(shí),問了一下簽證時(shí)該注意什么,他們讓我將我的情況和準(zhǔn)備的簽證文件拿出來看看,一看,TOEFL都沒考,都說沒戲,百分之百簽不出的。
我出來的時(shí)候,慢慢地走著,心里又想到奮強(qiáng),然后又想到春寧說的,那要看是誰來簽!就笑了起來。心里真的不能相信,奮強(qiáng)做得到的,我會(huì)做不到。
決定周一就去簽證。
3
周日的傍晚,表弟阿光請(qǐng)我出去吃飯。我們?nèi)サ氖悄戏酱髲B邊上的愛群大廈頂樓的旋轉(zhuǎn)餐廳。阿光說,我們轉(zhuǎn)它一圈,轉(zhuǎn)出你的好運(yùn)來。
我們坐在一個(gè)靠窗的位子上,邊聊邊吃,難得有這樣機(jī)會(huì),就我們兩人,可以說說心里話。我們從小來往很多,他的母親秀姨是老師,常在暑假里帶他們兄妹三人到南寧來玩,我們從小就感情很不錯(cuò)。所以我一直相信,小孩子的感情是小時(shí)候玩多了才能建立起來的。
秀姨丈是50年代從馬來西亞歸來的僑生。說起來好笑,姨丈告訴過我,新中國成立時(shí),他們?cè)谀涎蟮娜A僑聽說家家都可分到地,很多人就回國了。他的家里就派了他這個(gè)當(dāng)時(shí)還在上中學(xué)的長子跟著鄉(xiāng)親們一起結(jié)伴回國。地沒分著,他就留在國中上學(xué)。畢業(yè)后也是教書,后來在他們那兒的教育局里工作。姨丈多才多藝,還有偏方治蛇傷。我有年寒假去他們那兒,看他養(yǎng)了很多蛇,真的很可怕。
因姨丈家里的人對(duì)讓姨丈回國很是內(nèi)疚,所以長期在經(jīng)濟(jì)上給他們支持。秀姨家里就有很多僑匯券,那個(gè)年頭,僑匯券特別值錢,可以到僑匯商店買到很多外面買不到的東西。秀姨給我們家里不時(shí)就寄僑匯券來,老媽用它們買了不少東西,如自行車,電飯鍋,熨斗等等。我大學(xué)畢業(yè)后買的那輛非常炫的紫紅色的永久牌26吋女士自行車,也是用秀姨給的僑匯券買的。秀姨還給我寄過很多奇裝異服,讓我在學(xué)校里沒少出風(fēng)頭。
阿光在那個(gè)晚上告訴我,他打算很快就從單位里正式辭職,出來自己做了。我聽了很為他擔(dān)心。那是1988年年底,我那單位的頭兒威脅要我辭職,我是不敢的。所以我讓阿光三思。他說沒啥可思的,這體制外的天地是天高任鳥飛。這樣,我們的話題就轉(zhuǎn)到了那個(gè)我念念不忘的美女小方。他說學(xué)經(jīng)濟(jì)的小方現(xiàn)在在廣東省政府機(jī)關(guān)工作,一切都好,也很安定,也想要安定,很反對(duì)他的這種不安分想法,堅(jiān)決不能同意他辭職到社會(huì)上自己干的。他卻不能放棄自己的理想,也不能保證自己能給小方一份她想要的安穩(wěn)的生活,只能算了。
我說不出話來。我們都在要對(duì)自己的人生作出決定性選擇的時(shí)刻,舉杯祝福,相對(duì)無言。
夜色慢慢降臨。看過了峽谷一樣的街市,遠(yuǎn)處的燈火,太陽沉到珠江里,船,樹木,那些螞蟻般的人。我們離開。
夜里春寧到了。我們聊著天。記得很清楚的是,那個(gè)時(shí)候就老有雞鴨們打旅館房間的電話。阿紅還喜歡跟那些人聊上幾句,逗逗笑。我讓阿紅給總臺(tái)的人打電話,讓人家第二天早早就叫醒我們,
我跟春寧一早就起來了。我那天早晨,穿得非常樸素。這是TIPS之一。他們告訴我,你既是申請(qǐng)留學(xué),就要讓人家看著你是個(gè)讀書人的樣子,是真心想去念書的。那個(gè)時(shí)候的觀念好笑,難道讀書人就不可以衣著時(shí)髦嗎?
當(dāng)時(shí)我已經(jīng)工作了,結(jié)交了我大學(xué)畢業(yè)后最要好的女友華華。我第一次見到她,她站在陽光里,褲線筆挺,穿一件下擺非常時(shí)髦的圓尾的襯衣,我被她吸引住了。她后來跟我講,她看到的是坐在陰影里的我:“這是一個(gè)清秀的女孩,我想,可是,她的褲子沒有熨過”——華華后來告訴我她對(duì)我的第一印象。我們很快就成了形影不離的女友,整日勾肩搭背,出雙入對(duì)。我?guī)郊依铮A華能跟我老爸講湖北話。她的老媽是湖北人。當(dāng)然她的湖北口音很可疑。老爸為我交了個(gè)如此“敦厚”的朋友而高興;我到她家里,跟她的兄妹,父母很快打成一片,常常就坐在她家的餐桌上大吃大喝。她們家的菜真是好吃!燒得那個(gè)講究。華華老爸是廣東中山人,建筑設(shè)計(jì)師;老媽湖北人,跟華華老爸是同學(xué)。奶奶竟是出生在美國的中山富商的女兒;中美建交后,那奶奶立刻去了美國,住不慣又回來了,跟他們住一起。
可以想象,我這種所謂“思想意識(shí)不好”的人,一碰到華華會(huì)是怎樣“臭味相投”。她送我志摩的書,我們換穿衣裳,彼此做對(duì)方的心理醫(yī)生。我搖身一變,成了個(gè)追求時(shí)髦的人,讓我大學(xué)里的同學(xué)在街上撞到,竟不敢相認(rèn)。可是,到了去美領(lǐng)館簽證這天,我必須翻出“老實(shí)的”服裝:一件式樣簡單的米白色夾克衫,里面是件黃底黑格的襯衣,一條黑色的長褲,就這樣了。我想華華若在那天早上見到我,是會(huì)嚇一跳的。
我所有的文件都在前一夜弄好了,早晨再檢查了一遍。I-20表,TOEFL考試報(bào)名回執(zhí)。大學(xué)畢業(yè)證書,學(xué)位證書,經(jīng)濟(jì)擔(dān)保證書。那個(gè)年代,大家都沒錢,所以不需要甚么銀行存款證明,房產(chǎn)證等等。是不是要單位證明,工資單之類,這點(diǎn)我忘了。
我的經(jīng)濟(jì)擔(dān)保是由我曾經(jīng)的數(shù)學(xué)老師原子給簽的。戴維和原子,是我青少年時(shí)代的偶像,我后來,也再?zèng)]見過有另外一個(gè)女士,能有我們?cè)幽菢拥囊懔推磩艃骸K麄兪菙?shù)學(xué)老師,我是數(shù)學(xué)科代表。
原子出生在美國兩顆原子彈在廣島、長崎上空爆炸的時(shí)刻。她是當(dāng)年福州二中的高材生。她的父母在49年前的離亂中帶著她的哥哥逃去臺(tái)灣,將她和襁褓中的弟弟留給了她的祖母。她父母本以為到臺(tái)灣安定下來就可以回來接孩子的,可是,哪里想到一隔就是幾十年!
原子在大學(xué)時(shí)代,跟壯鄉(xiāng)的農(nóng)民兒子戴維碰到了,愛了。他們?cè)撌俏母锴爱厴I(yè)的最后一屆大學(xué)生,一畢業(yè)就留校鬧革命,一年后才分配。她隨戴維回到戴維的家鄉(xiāng)廣西,分配到邊遠(yuǎn)的河池地區(qū)教書。所謂是金子就一定會(huì)發(fā)光,講的就是原子這種人。她在山鄉(xiāng)教書,離開時(shí),鄉(xiāng)里的農(nóng)民排著長隊(duì)送出幾十里地!
原子調(diào)到我們那兒,是因?yàn)槲母锖舐鋵?shí)政策。那時(shí)她不過三十多歲,我一見到她就很喜歡,我的數(shù)學(xué)成績就越來越好。原子和戴維對(duì)學(xué)生非常好,沒有老師的架子。我們?cè)谑罴倮锍5剿麄兗依锿妫奶欤袝r(shí)夜里也去,一群人聊到深夜。我是他們最鐘愛的學(xué)生之一,相處就像朋友。他們?cè)谝痪虐肆隳暌泼衽牌谂诺剑チ嗣绹D菚r(shí),原子的父母早已隨原子的大哥大嫂從臺(tái)灣移民美國。我們?nèi)ニ退麄兊哪莻€(gè)夜晚,大家都哭得像淚人。原子那年三十五歲,戴維三十八,他們的兒子小戈八歲。那個(gè)年紀(jì)到美國白手起家的苦,不須贅言。原子是金子,她在中國最苦的地區(qū)都能閃光,到美國也不可能失色。
他們?nèi)ッ绹螅覀兂D瓯3滞ㄐ拧D菚r(shí),我自幼的密友,她們鐘愛的學(xué)生之一阿康(我們班的物理科代表)已經(jīng)到了加國,她們見面后,給我寄好多照片。都說希望有一天,我們能在北美重聚。所以當(dāng)我需要留學(xué)的經(jīng)濟(jì)擔(dān)保時(shí),當(dāng)時(shí)已是那個(gè)大型的EDS公司軟件工程師的原子,為我簽下I-134表。戴維在電話里跟我說,我們已經(jīng)想過了,實(shí)在需要,我們就供你幾年。
我對(duì)原子和戴維有很特別的感情。在我到美國的第一個(gè)暑假,按我的心愿,他們?nèi)規(guī)覀內(nèi)ビ瘟藮|部各處,然后去到他們底特律的家。后來又專門安排我和阿康到他們家中歡聚。他們的家就像我們?cè)诿绹哪锛乙粯印4骶S曾帶我和阿康到商場(chǎng)里一放,說你們?nèi)タ纯矗矚g甚么衣服就買吧,我給你們買。這不就是老爸的口氣嗎?
如今原子和戴維都已退休,卻一點(diǎn)沒有閑下來。到處旅行,在家種菜,不時(shí)去看兒孫。他們的兒子小戈從麻省理工念了博士,在一個(gè)國防的研究所做事。前幾年小戈結(jié)婚時(shí),我還專程飛到波士頓參加了他的婚禮。每年圣誕,我都能看到他們一家三代六口在圣誕卡里幸福地微笑。我去年夏天再度到訪他們?cè)诘滋芈傻募遥覀冞€不時(shí)在加州、上海、成都、九寨溝等處見面。
他們愛我們大家,有這樣的師長,何等幸運(yùn)。
4
我和春寧在星期一早上來到東方賓館的時(shí)候,天色已亮透了。
因前些天已領(lǐng)好了表格并填好,我們就直接越過了那長長的拐出大門外的隊(duì)伍,直接走進(jìn)遞交表格處。那里也排隊(duì),卻不很長。
這時(shí),我看到領(lǐng)事館門口貼出的感恩節(jié)期間將閉館幾日的通告,慶幸自己挑的時(shí)機(jī)挺好,不致被感恩節(jié)的假期拖延。
沒有想到的是,一大早領(lǐng)事館前面就聚集了那么多閑散的人。廣州本地人居多。那時(shí)美領(lǐng)館還沒有設(shè)限,若你今天被拒簽,明天你就可再來試運(yùn)氣。所以本地人很有優(yōu)勢(shì),出門跨幾步就到,沒事就聚在這兒互相交流,打聽,尋思辦法。廣東省內(nèi)的人也很多,福建人在其次,我的廣西老鄉(xiāng)寥寥無幾。那個(gè)時(shí)代,要從廣西來一趟廣州很麻煩。所以后來當(dāng)我看到那個(gè)早晨我們幾位廣西來簽證的都順利過關(guān),心里就想,是不是老美對(duì)我們這些老實(shí)的邊地人民特別有照顧?
接受表格的是中方的工作人員。他們很快地看了看我遞去的文件:I-20,簽證申請(qǐng)書,經(jīng)濟(jì)擔(dān)保書和護(hù)照。其它的文件資料,我按讀到的指示,并不是必交的證件,我就留在手里,打算在面談時(shí)見機(jī)行事。
交了表格后,就可以進(jìn)入簽證大廳里坐著等著被召見了。簽證大廳也不很大,有一些椅子,人們出出進(jìn)進(jìn)很頻繁,但很安靜。我看到過去只是傳說中的簽證處。那些有機(jī)玻璃的窗子上有小孔讓你對(duì)簽證官員說話,文件則是從窗下的小鐵筒里傳遞。每個(gè)窗子都有麥克風(fēng)。你不知你會(huì)被呼喚到哪個(gè)窗口去面談。我新奇地張望了一會(huì)兒,就疲了。沒人知道何時(shí)能輪到自己。那時(shí)真好,若拿不到簽證就不用交錢的。如今聽說收費(fèi)很貴了,卻是無論是否能獲簽證都要交幾百塊。
這時(shí),我看到了徐姑娘。她手里拿著一大疊表格樣的東西,從外面走進(jìn)了簽證大廳。我們的目光相匯,彼此微笑了一下,并沒有打招呼,更沒有說話。她轉(zhuǎn)到了簽證室里面,跟里面的一個(gè)美國人在那兒交談,過了一會(huì)兒她出來時(shí),又朝我擺了擺手,微笑著點(diǎn)點(diǎn)頭,算是別過了。我不認(rèn)為她為我做了什么。按我今天對(duì)美國國家機(jī)器系統(tǒng)運(yùn)作的理解,我想她也不能做什么的。
簽證的人很多,看起來并不是按先后順序被傳見。每個(gè)人前去,都是很短的時(shí)間,大部分都是被拒簽,出來一臉的沮喪。到了這時(shí),我心里只能想,那是各人情況不同,誰知他們的條件是怎樣的呢?我只跟奮強(qiáng)比。
大半個(gè)早晨過去了。我和春寧都還沒輪到。我開始坐不住,出到簽證大廳外去了。這時(shí)太陽已經(jīng)出來,院子里到處是人。我看到一個(gè)很斯文的女孩子,身邊圍著一圈人。那女孩子個(gè)子挺高,很苗條,也像春寧那樣在腦后扎一條長辮。可見,八十年代末還是蠻流行辮子的。她戴一副眼鏡,穿很長的薄呢裙子,氣質(zhì)很好,是我喜歡的那類女孩子。我就也走過去,聽他們?cè)谥v什么。
那個(gè)斯文好看的女孩子可能跟我年紀(jì)差不多,她來自福州,后來我知道她姓李。說這回已是第三次來簽證了,是要辦去費(fèi)城的學(xué)校留學(xué)。她本科念的是英文。她說自己的護(hù)照上被打了214B,也就是“移民傾向”。大家七嘴八舌地說,那你沒戲了。214B那時(shí)好像倒是有時(shí)間限制的,要過了兩個(gè)月才能再來。李姑娘說那我就兩個(gè)月來一次!從福州坐火車過來,也很久呢。她后來跟我說,她是基督徒,她的一切放在神的手中。她憑信心禱告,并不灰心。
我就這樣出出進(jìn)進(jìn),直等到中午,也沒輪到進(jìn)去面談。
我現(xiàn)在一點(diǎn)也想不起來,我那個(gè)中午是在哪里吃的午餐,或許就是吃的自帶面包?我只記得在東方賓館的花園里跟一些等著下午簽證的人又碰上了。那些人聽起來真是太門清了,對(duì)領(lǐng)事館里的簽證官了如指掌,我聽到人說,最難簽的就是那個(gè)大胡子,在他手下能簽過的人極少。說著,大家就看到午餐后陸續(xù)回來的簽證官們,有人就指著說,就是那個(gè)高高的大胡子!最可怕了。我心里就想,但愿這個(gè)下午,別讓我碰上他啊。
我那個(gè)中午在東方賓館的花園里,還碰到了那個(gè)斯文可人的福州李姑娘。我們也在一起聊了一會(huì)兒。
午休后重新開始簽證。春寧終于被叫到了。很快,我就聽到了我的名字在擴(kuò)音器里響起來。我趕緊按指示走向那個(gè)簽證號(hào)的窗口,腳跟剛站穩(wěn),一看,正是那個(gè)穿著白襯衫,打著領(lǐng)帶的大胡子。他的胡子修理得非常整齊。死定了,我心里想,可是已經(jīng)來了,沒有退路。
你識(shí)講廣東話咩?——大胡子第一句來的是這個(gè),廣東話。
我識(shí)聽嗯識(shí)廣——我硬著頭皮用我那蹩腳的廣東話答。太慚愧了!我自幼生長在人們說粵語系方言的城市,竟不會(huì)講那個(gè)城市市民的語言。我要是春寧就好了,她講得很溜的。
但是,我會(huì)講英語!我靈機(jī)一動(dòng),說了句英文。大胡子一邊低頭在我的簽證申請(qǐng)表上記寫著什么,一邊用英文回:太好了!我真愿意天天都能講英文呢。哦,廣西大學(xué)!——他在讀我填的表,我就將我的畢業(yè)證書等從窗口塞進(jìn)去。他打開,說:很好!我心想,好啥啊?我的心情放松了些。到此為止,我們的互動(dòng)還很友好,可我還沒笑出來,要命的一句來了:你考過TOEFL了嗎?啊!!——這是我最弱的一條。我只得如實(shí)說:沒有,趕忙掏出TOEFL考試中心寄回的報(bào)名考試的回執(zhí),從窗下塞進(jìn)去,心有不甘,又加一句:我已經(jīng)報(bào)了一月去考,我相信我考過沒問題。都說美國人喜歡自信的人,我就自信地說。我這年惡補(bǔ)英文還真是有點(diǎn)用的,聽力和口語都提高了很多,跟大胡子說話很自然,可能給他的印象還行。他拿起那細(xì)長的回執(zhí)條看了,又在那表格上寫著什么。
你——他大概看到我填的“未婚”那欄,就問,有男朋友了嗎?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我是適婚的年齡,卻沒結(jié)婚,還要跑去美國,太可疑了。按大家分析的講法。214B等著了。可這時(shí)我只能說,男朋友有的。他翻個(gè)白眼看看我。我想我都穿了最老實(shí)的衣裳了,頭發(fā)也不像平時(shí)那樣披散開來,而是老老實(shí)實(shí)地用發(fā)夾在頭頂夾牢,真真是素面朝天呢,還戴了個(gè)白塑框的眼鏡,多像一個(gè)好青年啊!他低頭又寫,問:他在哪里?
我心里想,這是我的隱私呢。我修美國文化課,第一堂講的,就是不要隨便問女士的年齡,婚姻狀況——當(dāng)然,我是在申辦簽證,這里沒隱私可言。我只好說:在念研究生。他沒看我,繼續(xù)寫。我想,這也不是關(guān)鍵的,以美國人的概念,男朋友是衣裳啊。要訂了婚的未婚夫才算靠點(diǎn)譜吧。
嗯,你——這時(shí),他抬起頭,拿著我的經(jīng)濟(jì)擔(dān)保書,說:你讓他們將你第一學(xué)年的學(xué)費(fèi),存到你的賬戶上。拿到存款證明后,再來,聽明白了?OK?隨即,將申請(qǐng)表格的復(fù)聯(lián),我的那些文件,從窗口下遞回給我。什么時(shí)候拿到什么時(shí)候回來!好了。
那么,我OK了?!!——聽他們說的,你只要沒拿到214B,只要讓你去補(bǔ)材料,你就過了!!我慌忙地抓起那把文件,謝過大胡子。誰說大胡子最難簽?!大胡子太好簽了!
轉(zhuǎn)身就退到大廳里。春寧已在線外等我:我過了!她高興地報(bào)告。我跟她講我的情況,她拍著我說,過了過了,沒問題了!我說過的,美國不可能拒絕我們這種人的!我們是美女,我們是精英!美國需要我們!我心里想,這回她咋不說她是良種了呢?說著,春寧興奮地抱了我一把。她這時(shí)還沒意識(shí)到,她就要跟她才幾個(gè)月大的兒子分離了!F-2也是很難簽的,甚至比學(xué)生簽證的F-1還難簽,她竟然也很順利過關(guān)。
我們走到門外,那些等在那兒的人們,見人出來就圍上來。我被那些人圍住,問這問那。有人還一把拿過我的文件去看,又叫:離曬譜了!這種條件也能簽哦!
我現(xiàn)在真的懷疑,我能那樣順利地混出來,確實(shí)是因?yàn)槲覀儚V西去的人少吧。你想,如果你是簽證官,一天下來,很難見到一個(gè)廣西人的時(shí)候,當(dāng)他們終于零星冒頭了,你大概真是要對(duì)他們寬松一點(diǎn)的吧?熊貓寶貴,是為什么呢?
黨和國家多年來為安撫我們老(區(qū))少(數(shù)民族)邊(遠(yuǎn))山(區(qū))窮(困)地區(qū)人民所作出的送溫暖的承諾,第一次讓我領(lǐng)受到了。它竟是由美國簽證官大胡子代為兌現(xiàn)的.。
這時(shí)那個(gè)福州的李姑娘也出來了,她又被拒簽了。她說她還會(huì)再來。她讓我留了在美國的聯(lián)系地址,又給我留了她福州家里的地址。我記得她家里是福建土地局的。
我到美國后,大概在1989年的秋天,收到過她寄自費(fèi)城的來信,知道她在歷經(jīng)六次簽證后,上帝終于感動(dòng)了,她如愿來到美國。轉(zhuǎn)眼二十五年過去,我不知道李姑娘如今在哪里了。以我身邊的同學(xué)朋友們的經(jīng)驗(yàn),如今大多該在美國安居樂業(yè)。希望美國沒有令李姑娘失望,她的神時(shí)時(shí)看顧她。
5
從美領(lǐng)館回來,當(dāng)然立刻就去電美國托辦銀行證明的事。
想來那時(shí)美國也很烏龍。我人都沒到美國,卻要開個(gè)有我名字的帳號(hào)!開帳號(hào)要社會(huì)安全號(hào)碼,身份證等,要開辦獨(dú)立帳號(hào),顯然辦不下來。但是,那時(shí)的留學(xué)生都是這招:和人在美國共開一帳號(hào),作為一個(gè)銀行帳號(hào)里的共同擁有者開個(gè)戶頭,存錢進(jìn)去,讓銀行出具存款證明時(shí),只寫你的名字就可以的。這些具體的事兒于我而言,只能望天了。
那時(shí)愛達(dá)荷大學(xué)研究生一年的學(xué)費(fèi)是近八千美元。
那時(shí)的酒店不好掛美國長途。我由阿紅領(lǐng)著,到酒店附近的一個(gè)挺大的郵電局往美國掛電話。那時(shí)打到美國的電話一分鐘幾塊錢,我沒錢,只能打?qū)Ψ礁犊畹碾娫挕L顔沃螅稽c(diǎn)押金,然后坐著等,總歸要十幾二十分鐘才能接通,然后告你到那個(gè)小房間里去接聽電話。
我將簽證的情況通報(bào)了原子他們和甲等。甲幫我在大學(xué)所在地去幫開帳戶。他帶了一位中國女孩子去代我簽的字。說辦好后用國際快遞傳到五羊城酒店,大概得要一周時(shí)間。正好這期間美領(lǐng)館也放假,到它再開館,我就可以再去了。
在等存款證明的那一周,我沒事就跟阿紅出去逛街。我特別喜歡阿紅領(lǐng)我去吃的那些大排檔里的煲仔飯,還記得風(fēng)味茄子煲,臘味煲,都非常夠味兒,真是百吃不厭,特別是在冬天里。廣東人也吃很多米粉,腸粉,可他們的米跟廣西的米很不一樣,所以那河粉的質(zhì)感在我看來是不好的,沒有點(diǎn)韌勁兒,所以我不是很喜歡。冬天夜里,還去吃燉甜品。五羊城酒店在鬧市區(qū),小街巷里很多大排檔的攤位,熱鬧非凡。有時(shí)阿光也領(lǐng)我去他的生意合作伙伴的家里吃飯。
記得那家人住在深深的巷里,典型的廣州人家的天井,青石的老屋。那個(gè)太太不工作,天天在家煲湯做飯,她家男主人跟阿光合作,相處像家人一樣。他們跟著阿光“表姐”長“表姐”短地叫我,做的飯非常好吃。后來他們家里那個(gè)跟阿光跑進(jìn)跑出的兒子去了澳洲,又說澳洲很不好混,再又回了國。
我還跟春寧去了珠江電影制片廠她朋友家。春寧從小生活在中國新聞圖片社廣西分社的院子里,珠影那家人是她父母的朋友,我們?cè)谀莾哼€吃了飯。珠影過去是個(gè)好廠子,我很喜歡他們的一些電影,像《大浪淘沙》等等。它在離市區(qū)很遠(yuǎn)的地方(想來也是因過去交通不便,現(xiàn)在連順德都感覺在郊區(qū)了,所以珠影該不是很遠(yuǎn)的),占地很大。
春寧的簽證簽下了,但要領(lǐng)到簽證,還要等十來天。她開始想念她的兒子,就說想先回家了,讓我到時(shí)幫她領(lǐng)簽證帶回南寧。我應(yīng)下。她就收拾了回家去了。
我還去了在仲愷農(nóng)大的唐阿姨家。唐阿姨跟我老媽在一個(gè)教研室里共事幾十年,是看著我長大的。她當(dāng)時(shí)調(diào)到廣州不久,在那兒當(dāng)系主任。唐阿姨有兩個(gè)女兒,靜和鳴。靜在廣西醫(yī)科大畢業(yè),在當(dāng)醫(yī)師,非常斯文。鳴則念的是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的是鋼琴。鳴是為高考才學(xué)的琴。
我去唐阿姨家時(shí),鳴也跟著調(diào)到廣州,在老媽那個(gè)學(xué)院的團(tuán)委當(dāng)個(gè)小頭目;而靜則留在南寧。她們兩姐妹向來都很時(shí)髦,特別是鳴。唐阿姨和先生郭伯伯見到我很高興,正好老媽他們的老同事,去了香港的陳叔叔那日也到廣州,我們?cè)谔瓢⒁碳遗錾希黄鸪燥埩奶臁:荛_心。他們說,日子過得真是快啊,孩子們一下都這么大了,你都要去美國了!
唐阿姨的哥哥是臺(tái)灣空軍里的一個(gè)將軍,當(dāng)時(shí)已聯(lián)系上。我小時(shí),總是見唐阿姨跟我的好友阿康的媽媽在學(xué)院的牧場(chǎng)里放養(yǎng)水牛,有時(shí)我也跟阿康去找她媽媽。我很怕動(dòng)物,總是離得遠(yuǎn)遠(yuǎn)的,后來在美國,有一次我談到我怕動(dòng)物,對(duì)狗,貓,豬,牛,馬,都很怕,阿康很淡地說一句:我根本不怕。我心下一酸,小時(shí)候,她常陪她媽媽放牛呢,怎么會(huì)怕呢?
阿康的媽媽是金陵女大畢業(yè)的國民黨員,阿康的爸爸在文革中去世。她媽媽拖著三個(gè)幼女,真是可憐。唐阿姨因老哥在臺(tái)灣也罷了,關(guān)鍵是她跟建國初期一件轟動(dòng)全國的匪特案有牽連。那時(shí)剛解放,局面很亂。唐阿姨在上海的姐姐,將一個(gè)朋友的朋友介紹到廣西來找唐阿姨。那個(gè)人卻是個(gè)男扮女裝的流竄的“國民黨特務(wù)”。特務(wù)在南寧時(shí),在唐阿姨家住了好些日子,唐阿姨說,他老穿著旗袍,領(lǐng)子很高的,根本沒看出是個(gè)男人!特務(wù)要去桂林時(shí),唐阿姨又將她介紹給在桂林的妹妹。特務(wù)后來被抓了,說是全國新聞,好像文革后還有作品寫過那個(gè)故事的。唐阿姨算是收藏過特務(wù)的,文革中當(dāng)然過不了關(guān),真的放了幾年牛呢。
唐阿姨前些年因乳癌去世了。我母親去世那年,她正好回南寧養(yǎng)病,住在靜家。靜的家離我父母最后住的地方很近。唐阿姨來家里看望我們,她告訴我,我母親幾乎每天都散步去她那兒聊天說話的啊!她在我準(zhǔn)備回美前,請(qǐng)我到靜家跟他們?nèi)页粤祟D飯。唐阿姨說,你媽媽走得太突然了!她指著廳里的一張小凳子,說,她一來,就坐在那兒的。我聽得說不出話來。唐阿姨那時(shí)自己剛做了手術(shù),看上去恢復(fù)得不錯(cuò)的。我還保留著我們的合影,沒想到,唐阿姨后來也走了。
我回想這些往事,還記得唐阿姨說著一口標(biāo)準(zhǔn)好聽的桂林話,在她廣州的家里談笑風(fēng)聲的樣子。我也有一張我們那日在唐阿姨廣州家中的合影。二十五年就這樣過去了。
那段時(shí)間,阿光用他那該讓乃寧羨慕的摩托車,載著我去了一趟華南植物園。那是我要求的。我非常喜歡那個(gè)亞熱帶風(fēng)情濃郁的植物園。
我們一路出城。去華南植物園要過廣州的銀河公墓的。我是很喜歡坐摩托的,人就在風(fēng)里,跟自然是一體的。銀河公墓那一帶是廣州殯儀館所在地,很是熱鬧。我知道蕭紅墓在那兒,多年來一直想去看看,跟乃寧也提過的,可沒人愿意陪我去,在他們看來這是非常可笑的事情。當(dāng)我坐在阿光的摩托車尾上掠過銀河公墓時(shí),我看到了側(cè)邊安靜冷清的鐵門后的墓地,我想,蕭紅墓大概就在這邊了,但我也沒開口讓阿光停下。感覺是不該和阿光這樣的人去看蕭紅的。
我的銀行存款證明果然在一周后收到。就一頁紙。我看到,上面的存款數(shù)目是八千多美元。我拿到它,第二日就去往東方賓館。又重復(fù)一次,交表遞表。這回多了上次大胡子給我的申請(qǐng)表的副聯(lián),要補(bǔ)的材料等都寫在上面,所以一進(jìn)去,將存款證明一遞,啪啪,那個(gè)簽證官——當(dāng)然不是大胡子了,將大印敲了幾下,就讓我去交錢了!
簽證費(fèi)是八十元。我到交款處交了錢,大功告成。簽證要在十天后來取。走出簽證大廳,我想,說去就要去了!我真的就要去美國啦!這也沒想象的傳說的那么難嘛!
出了東方賓館,我就上了公車,去往離那兒比較近的廣州火車站,因我記得那兒有個(gè)很大的郵電大樓,我要去那兒打電話去美國報(bào)告簽證結(jié)果。火車站前的那個(gè)郵電大樓很大很新,人潮洶涌。我填好表,在那兒等著,忽然,就有人在我身后拍了我一下,我轉(zhuǎn)頭看去,是我大學(xué)同班的同學(xué)阿泉!他鄉(xiāng)遇故知啊!我們一個(gè)勁兒地傻笑。他和女朋友在去往深圳的路途中。他給我介紹了他的女友。其實(shí)我之前已聽說她是華華大學(xué)的同班同學(xué)。他們都是桂林人。那個(gè)女友眉眼非常細(xì)致,好看的,但是表情很淡,很有距離感,一看就比我們成熟。她的年紀(jì)比阿泉大很多歲,非常能干,阿泉對(duì)她是言聽計(jì)從,做牛做馬。可是她對(duì)阿泉好兇。當(dāng)然這些都是聽別人講的。阿泉怎么努力,她都不能滿意。她后來做得非常好,就跟阿泉離了婚。我去年秋天到珠海跟同學(xué)們聚會(huì),阿泉都沒來——他曾在珠海生活過的。聽說他過得不是很開心。
可二十五年前,大家的人生才剛剛開始,在熱戀中奔向前方,哪里知道二十五年后各自的生活會(huì)是什么樣子呢?那時(shí),我看到阿泉跟他的女友在一起,很好看的呢。他笑得那么甜,那么開心的。
阿泉問了我住在哪兒,說要將借我的八十元錢給我送去。他之前曾給我電話,說他在南寧學(xué)習(xí)的表妹的好友出了車禍,有點(diǎn)麻煩,需要八十元錢,他從桂林寄的話,就太慢了,讓我?guī)徒o他表妹送錢去救急。我回家馬上就跟我老爸報(bào)告了。我手頭沒那么多錢,老爸聽了二話沒說,拉開抽屜就給了我八十元,讓我快點(diǎn)給人家送去。我按阿泉講的地址,找到他表妹。小妹說她的朋友騎車撞了人,那人傷了,要她朋友賠錢,要不擺不平。我看那小妹緊張得不行,就讓她快點(diǎn)拿錢去給人家吧。
阿泉在碰到我的第二天,就將錢送到酒店了。我那時(shí)不在,他將錢留給那里的人。去年我在珠海,聽到他們說阿泉借了朋友的錢也沒還等等,我在想,或許他如今真的很有難處了?我愿意他是過得開心的,我們年輕的時(shí)候,他是多活潑的一個(gè)小伙子啊。
因?yàn)樾睦镞€惦記著一月考TOEFL的事,我給家里掛了電話,老媽說那你先回來吧,到時(shí)我去趟廣州幫你取簽證就是了。這就是典型的中國父母了,可那時(shí)并不覺得這有什么不妥。我掛了電話就開始收拾行李回南寧了。
我是乘飛機(jī)回去的,那時(shí)廣州飛南寧的機(jī)票好像是六十元(曾經(jīng)是四十元)。我很討厭坐飛機(jī),因?yàn)闀?huì)暈機(jī)嘔吐。可是想到從廣州到南寧只用飛五十分鐘,就忍下了。飛機(jī)在傍晚起飛。整個(gè)白天,廣州的天空電閃雷鳴,到了下午四五點(diǎn)后,開始放晴。阿紅他們叫了出租車,一路將我送去白云機(jī)場(chǎng)。
巧的是,我在飛機(jī)上的鄰座是一對(duì)北方口音的老夫婦。他們跟我聊起來,說是廣西公安廳的。老爸剛到廣西時(shí),就在公安廳做事,我就提了老爸,想他們都是前后南下的那批人吧。夫婦倆都笑起來,說原來你是他的女兒啊!到了吳圩機(jī)場(chǎng),他們一定要我跟來接他們的車一起進(jìn)城,并將我直送到家門口。我回到家中,告訴老爸我碰到的這對(duì)夫婦,老爸笑說那是公安廳的X(秦?,忘了)副廳長嘛。不知他們?nèi)缃窨珊?年事應(yīng)該相當(dāng)高了。
TOEFL考試是在1989年1月,春節(jié)前考的。考場(chǎng)在廣西大學(xué)里,我碰到很多熟人,我那教室里監(jiān)考的那位外文系的年輕男老師我也認(rèn)識(shí)的,我在他的班上學(xué)過“閱讀理解”。聽說他如今也在美國。也許是廣西人出來得比較少的緣故,在美國碰到廣西出來的人,幾乎彼此都是認(rèn)識(shí)的,大多就是那幾所大專院校里出來的。就算不直接認(rèn)識(shí),也都有共同的朋友。
我的成績是到了美國后才從學(xué)校的檔案里查到的,沒有考得我預(yù)期的那么好,但也大大超過了學(xué)校要求,不需再考或去補(bǔ)習(xí)英文了。我達(dá)到了“條件”,那張I-20表,就由“有條件錄取”變成了“無條件錄取”。我的其它條件在之前已滿足了。這樣,我就成為正式學(xué)生了。
在南寧過了我出國前的最后一個(gè)春節(jié)。我清楚地記得我這輩子和父母一起吃的最后一次年夜飯。有每一年必不可少的香菇燉雞湯,作為湖北人,老爸在廣西生活了一輩子,仍不吃廣西人熱愛的白切雞。那個(gè)年三十,竟然還包了餃子。我在細(xì)雨里出門打醬油的時(shí)候,遠(yuǎn)遠(yuǎn)看到灰朦朦的天空,心里竟有著一種難以言表的感動(dòng)。從那時(shí)起,到如今,整整有二十五年,我不曾再在中國過過農(nóng)歷新年。那清晰的一刀,就切在1989的春天。
1989。
從此去國離家,成了一杯潑出去的茶。
6
前幾年冬天我在上海,夜里冒著寒風(fēng)在外灘瞎竄,一個(gè)老哥指著浦東的高樓大廈對(duì)我說,他當(dāng)年在外灘邊上班,中午常跟同事出來亂逛,他們看著江對(duì)岸浦東的農(nóng)田,說:如果有一天,能讓對(duì)岸也變成像外灘這樣繁華,我TMD就……就甚么?跳黃浦江?……老哥沒說,只是轉(zhuǎn)了話題,說,你看,怪胎,它竟也能干出這等。我看著江對(duì)岸的紅紅綠綠,沒有感覺。
我不記得1989年2月的浦東長什么樣子。2月的上海淫雨霏霏。我看外灘的樓,似曾相識(shí)。廣州沙面?武漢江漢關(guān)蘭陵路一帶?并沒有感覺很新鮮。
我那時(shí)到外灘,是奔波著到中國銀行去按配額換出一些美元。我好像在南寧換了一些的,是不是走后門了?沒在護(hù)照上蓋章,這樣,我還可以多換點(diǎn)?具體細(xì)節(jié)忘了。反正比起那些懷揣二三十美元去美國的故事,我稍好一點(diǎn),好像是帶了四百多美元。那時(shí)是四點(diǎn)七人民幣兌一美元?我一個(gè)月的工資加獎(jiǎng)金,可到近百元?我有點(diǎn)積蓄,加老爸贊助的錢,就換得那么多。
上海各處都是灰白色,還是很樸素的。人們的衣著也是老派的,或灰或藍(lán)。當(dāng)時(shí)間倒遠(yuǎn),我們竟說,我們是懷念那種時(shí)代的,這里面包含太多復(fù)雜的感情。
我是坐火車到上海的。79次普快,到今天還是這趟車來往于南寧—上海之間。父親沒有將我送遠(yuǎn)。關(guān)于這一天,我在《幽幽的桂香》里有過記寫:“我離家的時(shí)候,我的父親沒有說很多的話,他走在來給我送行的我的朋友們中間,我以為他是要和我們一塊兒到火車站的,可到了接近街道的時(shí)候,他突然站住了,微笑著,作了個(gè)手勢(shì),憑著我們父女極深的相知,我明白他送我就是送到這里了,而他的那種手勢(shì),我想就是‘走吧!好好地走吧!那樣的祝福。我也站下來,回頭朝他笑,那時(shí)的父親顯得那么年輕、挺拔,他另一只手瀟灑地夾著一只煙,臉上慈祥的笑意里有一股淡定沉著的安然,他的身后是一棵不很高大的桂樹,它墨綠的枝葉反襯著更遠(yuǎn)處的一堵紅墻,還有父親那身挺刮的衣裝。我也回應(yīng)著朝他招手,我們就那樣隔著距離彼此對(duì)望了一會(huì)兒,然后是我調(diào)頭,給父親留下了他心愛的女兒遠(yuǎn)行離家的背影。八年的時(shí)光如白駒過隙,那樣父女分別的場(chǎng)景就這樣鑲嵌在了記憶的畫版上,愈久彌新。”
那日到車站送我的朋友記得有華華,小燕,專門從北海趕來的蘇,阿文和她新婚的丈夫龍等(華華去年在多倫多因病離世,令人傷心;小燕還在南寧,在大學(xué)里教物理化學(xué);蘇在硅谷;阿文在日本留學(xué)后回國,在廣東中山工作,她和當(dāng)年愛得要死要活的龍?jiān)缫央x婚;龍如今在加拿大)。別的朋友們已經(jīng)吃過飯,道過別了。我上車了,她們開始哭。我忍住沒有哭出來。當(dāng)車子開出車站,我的眼淚才流出來。在這之前,我從來沒有在這個(gè)城市之外的地方連續(xù)生活過一個(gè)月以上。現(xiàn)在,我就要出遠(yuǎn)門了,那么遠(yuǎn),我是有點(diǎn)怕的。
我最后一次坐火車進(jìn)出南寧,大概是十幾年前了。如今為了方便,我若在廣西境內(nèi)跑,都是去坐那種十五分鐘發(fā)一趟車的大巴。我不知如今從南寧火車站出去,車窗外是怎樣的景觀了。我正式向南寧告別的那個(gè)1989年的春天,我看到的是很多五六層的大板房,友愛路郁郁蔥蔥的芒果樹,遠(yuǎn)處南棉的廠房,轉(zhuǎn)過去,人民公園的山,山頂上廣西電視臺(tái)高聳的天線塔,我看著它,笑笑。
我們過去常去在那天線塔下住著的阿江那兒玩,有時(shí)叫不開大門,就翻墻。青年男女,在那廣西電視臺(tái)的機(jī)房重地里炒菜,聊天,鬼混。阿江和那個(gè)大帥哥小袁住在一間巨大的屋里,他們的蚊帳永遠(yuǎn)都是下垂的狀態(tài)。小袁那時(shí)跟臺(tái)里的一個(gè)女孩談戀愛,就老不回來。那個(gè)水磨石地面的大屋里,總是人來人往。有一個(gè)中秋,我們?cè)谀情g闊大的房間里舉行過大型舞會(huì),樓下停滿了自行車,來了那么多的俊男美女,想來是違規(guī)的。
那是多么美好的夜晚啊,天上一輪明月,腳下萬家燈火——這里當(dāng)年是南寧的制高點(diǎn),如今應(yīng)該也還是制高點(diǎn)之一。我們每一個(gè)人,都那么年輕。我第一次看到阿偉的舞姿,那么儒雅迷人——我如今回去還會(huì)去看他和阿柯,那時(shí)阿柯是他的女友。而他們那個(gè)英氣逼人的兒子從英國大學(xué)畢業(yè)了,阿柯呢,捧著大罐的零食幸福地坐在電視機(jī)前,跟我說笑。阿偉做得非常好,這樣的人,不可能不好,只是再不跳舞了。阿江呢,聽說去了北京,前年在北京見到他,他熱情地請(qǐng)我到廣西大廈吃家鄉(xiāng)菜。還是那么瘦,那么高,帶著天真。他離了,又結(jié)了,又離了;在北京見到時(shí),帶來的是那位女友是北京一所大學(xué)里的教授。
我青年時(shí)代的友人,在那日就此正式別過了。再見,就都已到中年。廣西那邊的人,大多是從深圳出境的。因私人感情的原因,我選擇了從上海離境。
谷姐跟我一起去的上海。她在柳州站上車,我們一起換到了臥鋪車廂。到了上海,去找一個(gè)先生在民航工作的大姐。請(qǐng)她先生幫買去美國的機(jī)票。那時(shí)沒有互聯(lián)網(wǎng),沒有預(yù)訂,你如果打民航的電話,永遠(yuǎn)沒有人接,或忙音。一周只兩班飛機(jī)飛美國。你必須找關(guān)系。
那是我第一次到上海。
上海在那之前,于我一直是以物質(zhì)的形式存在的。母親的同事、朋友每年回上海探親,或出差,母親都會(huì)給她們一個(gè)單子,那時(shí)的人真有空,真的都給你去采購的。有丁字皮鞋,翻毛皮鞋,銹花羊毛衫,花型漂亮的的確良布料,中長纖維的格子成衣;漂亮的塑料涼鞋;五香蠶豆,肉松,大白兔奶糖,果香型橡皮擦,神氣的有磁鐵扣的文具盒……后來到我自己也有這個(gè)習(xí)慣,只要有人去上海,我就會(huì)讓人給買衣鞋包什么的。
直到八十年代,我開始跑廣州,覺得上海捎來的東西已經(jīng)不夠時(shí)髦,廣州的舶來貨質(zhì)地比不過上海的,但那款式,那花型,樣樣都代表著另外一個(gè)世界。
我坐火車去廣州;坐船去廣州;坐飛機(jī)去廣州。在那里度暑假、實(shí)習(xí),等簽證。廣州有高第街,到處是香港貨;廣州的男孩女孩個(gè)個(gè)想出國,掙錢。我住在中山醫(yī)大女生宿舍里過暑假,聽那些未來的女醫(yī)生們一大早起來就在朗讀英語,她們都說,我們要去美國——為了更好的生活,她們目標(biāo)明確。
7
79次列車在早晨抵達(dá)上海。
火車進(jìn)站的速度慢下來,我趴在窗口等不及要看那個(gè)物質(zhì)的上海。雨中成片的平房,灰的,黑灰的,木的,棕色的,棕黑的,一片一片,平常百姓的家居生活從一扇扇窗里招搖著衣褲向我致意,跟我的城市看不出區(qū)別。視野里,遠(yuǎn)處有一些樓。不高,更不現(xiàn)代──我在拿它們跟我看過的廣州比。原來上海是這個(gè)樣子的呀,我想。很好奇。
那個(gè)我們?nèi)フ业拇蠼愫孟裨谥幸话偕习唷K缒暝趶V西工作過,所以認(rèn)識(shí)谷姐。她很熱情,讓我們放心,因我們來之前已給過她信,她已安排。果真很快就定下日程,二月十七日乘中國民航經(jīng)洛杉磯入境,轉(zhuǎn)飛舊金山,再轉(zhuǎn)飛華盛頓州的斯波坎。機(jī)票兩千多元人民幣。我一窮二白,老爸贊助了我,那時(shí)他在弄律師事務(wù)所,該是萬元戶。他說:這錢你以后得還啊。
拿到機(jī)票,找到一個(gè)街邊的小郵局給父母掛長途電話報(bào)告離境日程。母親接的電話,說,知道了,一路小心。她從頭到尾,沒有表示過對(duì)我的不舍。年輕人,要出去闖,走得越遠(yuǎn)越好,這是他們對(duì)我講的話。
又給美國方面發(fā)電報(bào),天啊,那時(shí)竟想發(fā)電報(bào)到美國!一想不對(duì),又轉(zhuǎn)而掛對(duì)方付款電話。機(jī)票搞定,離起飛還有三天,可以購物去了。
我那時(shí)住在延安路一家離民航大樓很近的小旅館里,是朋友介紹的。他們出國前到上海,就住那兒,說是離民航近,跑機(jī)票方便。那好像是個(gè)街道辦的旅館?還有地下室,是防空洞里改建出來的。
我手里有好些個(gè)父母的同事朋友叔叔阿姨給寫的介紹信,讓我如果有事,可去找他們?cè)谏虾5挠H朋戚友,中國人就這樣,一出門就想到投親靠友的,這些都是那些叔叔阿姨主動(dòng)提供的。記得其中一位還是牧師呢。我那時(shí)沒這根弦,要不真該去看看那個(gè)時(shí)代的中國牧師是怎樣的。
在火車上認(rèn)識(shí)的一位年輕母親,也給了我她在上海的聯(lián)系方式的。她是從柳州上車的,帶一個(gè)非常漂亮可愛的八歲小女孩。我很快發(fā)現(xiàn),那女孩是個(gè)啞巴,說是小時(shí)用藥弄壞了。那母親說,她們家里是上海支邊到廣西的,在柳州的工廠里。她們的親戚都在上海,常來常往的。小姑娘的爸爸在小姑娘兩歲多時(shí)就到美國探姑媽去了,從此就留在美國。那母親說,孩子爸常來信,說在打工,很辛苦,但他的動(dòng)力就是有一天將女兒接出去,到美國治病。那爸爸相信美國能治好她的。如今那女孩該好大了,不知際遇如何。爸爸接她來美了嗎?病治好了嗎?那真是個(gè)漂亮的小姑娘啊。
買完票,換到四百多美元收好。剩下千來元人民幣,我決定在上海花光它。同去的谷姐說,那就去淮海路吧。街上很多很多的人,比廣州多。
我走上南京路的天橋,下面黑黑的全是人頭!根本看不到水泥地,那么多黑黑的人頭!我呆住了。他們都從哪里來?都在干什么?他們肯定都是我這樣的鄉(xiāng)下人,都說上海人是不大到南京路買東西的。我進(jìn)商店去,給人擠出來,連柜臺(tái)都接近不到。我想我過去真不懂事,讓人家到上海給我買東西!她們都受的這種罪嗎?
我離家的時(shí)候,買了兩個(gè)箱子,里面裝了一點(diǎn)書,其它都是衣物。我?guī)У臅欢啵瑓s有一本<<徐志摩選集>>,那時(shí)深愛志摩。我朋友跟我說,不是去美國嗎?干嘛像是去沙漠?
我不是去沙漠,但是舍不得漂亮的衣裳。那時(shí)我穿蝙蝠衫(去秋今冬美國又流行起來);酷愛高跟鞋(我今天還不喜平跟鞋);長裙,短裙,A型的,連衣的,紅的,綠的,黃的。不停地?fù)Q發(fā)卡;總而言之,燒包,全是跟華華學(xué)的。裝了一大箱。我的那只軟皮的大箱子至今還留著。他們告訴我最好弄個(gè)罩子,要不軟尼龍面會(huì)給勾爛的,華華幫我弄來很長一匹那種做工作服的布,我母親為我車縫了一個(gè)罩子,我至今也將它好好地收著。與它相關(guān)的兩位親友都已離世,它成了紀(jì)念。
我到淮海路買羊毛衫,買全毛的裙裝,買皮鞋,買風(fēng)衣,買絲巾,手套,毛巾被,小禮品。到走的時(shí)候,箱里塞下新舊毛衣十幾件,新皮鞋四五雙,在廣州買的牛仔褲、波鞋,羽絨服等等等等,看得谷姐目瞪口呆。后來到了美國,讓樸素的中國同學(xué)看到我整日花里胡哨的樣子,竟不時(shí)撞過來開玩笑說:你是來上學(xué)的嗎?
那時(shí)的淮海路都是小小的店家,一家接一家,門面不大,店子大多很深。二月的上海一直陰雨,店里亮著暗暗的日光燈。物質(zhì)是很豐富的,像我心中的上海。全是國貨,多還是滬產(chǎn)國貨,質(zhì)量是實(shí)打?qū)嵉暮谩N矣幸患罴t繡花的純羊毛衫至今留著,看著仍象新的一樣。那時(shí)四十多元買的。皮鞋的款式非常多。我買了乳白的,黑的,和紫紅的。價(jià)錢都在三十到三十六七元間。
我并沒有找到去沙漠的感覺,卻把老爸贊助的錢揮霍一空。如果我不出國,按當(dāng)時(shí)的趨勢(shì),大概很快就會(huì)變成啃老族?
我去上海前,了解情況的人都說,要換全國糧票去,那里小吃店都要糧票的。我已經(jīng)很久很久不用糧票了,在我們那兒,你多付一點(diǎn)錢,所謂議價(jià)糧到處都買得到了,副食品都不用票了。
但八九年的上海還要票。他們竟還有半兩的糧票。我用全國糧票去買飯買小吃。吃當(dāng)時(shí)是不重要的。
也許是水土不服,也許是跑得太多。我病了,發(fā)燒,頭暈,嘔吐。谷姐給我喝水,吃藥,頂?shù)降诙欤瑹€不退,吃不下東西。馬上就要上飛機(jī)了,我去一個(gè)區(qū)級(jí)醫(yī)院掛急診,看病的是一個(gè)大學(xué)剛畢業(yè)的女醫(yī)生。我說要不要吊針?她說不用。我就堅(jiān)持要吊針,因?yàn)榈诙炀鸵痫w了,我渾身無力,頭重腳輕,真怕耽誤了行程,如果走不了,改個(gè)機(jī)票,天曉得又有多少麻煩。年輕的女醫(yī)生翻翻白眼,就開了點(diǎn)藥,說回去多喝水,休息就行了。
我回到旅館,又是一番嘔吐,吐完了,休息了一下,突然非常想喝杯糖水。谷姐出門辦事了。我慢慢摸著走到旅館外的街邊的小賣部,想買一兩白糖。人家說,要票!我說我糧票有的,可糖票沒有,我買議價(jià)的吧,我是外地來的,生病了,很想喝一杯糖水。賣東西的人說,沒糖票不好賣的。我走回旅館,轉(zhuǎn)到后面的食堂,問那里的師傅,可不可給我一勺白糖?他說不行!出去小賣部買吧!我說去了,我沒有糖票,人家不賣。我又說我就是病了,特別想喝一杯糖水,我跟你買。他用紙折了一個(gè)小斗,舀了小小的一勺糖,說三毛錢!我給了他三毛錢。
那個(gè)時(shí)候,在南寧,白糖隨便買,一斤七毛錢。那就是一九八九年的上海。她開放的程度遠(yuǎn)遠(yuǎn)比南方滯后,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在2月17日那天一早就叫了出租車去虹橋機(jī)場(chǎng)。谷姐送我去的。虹橋機(jī)場(chǎng)樸素?zé)o華,我排隊(duì)過關(guān),向谷姐招手道別。旁邊有一家父母在送一個(gè)男孩子。那母親哭得像個(gè)淚人,以她的年紀(jì),這個(gè)兒子一定是生得很晚的。她過來跟我說,希望我路上幫忙照顧她的兒子,孩子第一次出遠(yuǎn)門。我點(diǎn)點(diǎn)頭,卻沒有告訴她,我也是第一次出遠(yuǎn)門啊。
飛機(jī)騰空而起時(shí),我看了一眼雨云下的上海。我沒想到我竟然流淚了,我想,我這就走了啊。旁邊的男生也在哭。他是同濟(jì)二年級(jí)的學(xué)生,退學(xué)去加大戴維斯分校。
在1989年,我不讀書,不看報(bào),不學(xué)馬列,深陷在無盡的青春問題中,慵懶,憂郁,厭世。1989年,后來發(fā)生了驚天動(dòng)地的大事件,在那個(gè)早春,我后來認(rèn)識(shí)的那么多朋友,都開始卷入,可我卻與“我”之外的一切無所關(guān)聯(lián)。“我”在那個(gè)時(shí)候,是我前行的道路中,在前方吸引著我所有注意力的一個(gè)路牌。我在1989年的早春忽然得到機(jī)會(huì)踹了它一腳,它應(yīng)聲倒下的時(shí)候,我尋到了去往新大陸的那扇門。
我當(dāng)年親密的友人們大多在那之前都離開了中國,我期待跟他們重聚。
奮強(qiáng)那時(shí)甚至說:如果人間有天堂,美國就是天堂。我其實(shí)并不信這樣的話。但美國在1989年成了一根稻草,我抓住了它。
很多年后,我聽丹青兄說,感謝美國包容他于無形。就是這個(gè)意思,我非常喜歡他的這個(gè)意思。在我人生陷入低潮的時(shí)刻,我選擇了美國。美國也選擇了我——在我兩手空空,連正式的入學(xué)錄取通知書都沒有的時(shí)候,它的廣州總領(lǐng)館向我發(fā)放了通行證。它確實(shí)包容我于無形,讓我獲得了過一種全新生活的機(jī)會(huì),平安度過最危險(xiǎn)的青蔥歲月,變成一個(gè)知道感恩的人。
在感謝所有我該感謝的人之外,我真誠地感謝這個(gè)偉大的國家。
我青年時(shí)代的友人,在那日就此正式別過了。再見,就都已到中年。廣西那邊的人,大多是從深圳出境的。因私人感情的原因,我選擇了從上海離境。
谷姐跟我一起去的上海。她在柳州站上車,我們一起換到了臥鋪車廂。到了上海,去找一個(gè)先生在民航工作的大姐。請(qǐng)她先生幫買去美國的機(jī)票。那時(shí)沒有互聯(lián)網(wǎng),沒有預(yù)訂,你如果打民航的電話,永遠(yuǎn)沒有人接,或忙音。一周只兩班飛機(jī)飛美國。你必須找關(guān)系。
那是我第一次到上海。
上海在那之前,于我一直是以物質(zhì)的形式存在的。母親的同事、朋友每年回上海探親,或出差,母親都會(huì)給她們一個(gè)單子,那時(shí)的人真有空,真的都給你去采購的。有丁字皮鞋,翻毛皮鞋,銹花羊毛衫,花型漂亮的的確良布料,中長纖維的格子成衣;漂亮的塑料涼鞋;五香蠶豆,肉松,大白兔奶糖,果香型橡皮擦,神氣的有磁鐵扣的文具盒……后來到我自己也有這個(gè)習(xí)慣,只要有人去上海,我就會(huì)讓人給買衣鞋包什么的。
直到八十年代,我開始跑廣州,覺得上海捎來的東西已經(jīng)不夠時(shí)髦,廣州的舶來貨質(zhì)地比不過上海的,但那款式,那花型,樣樣都代表著另外一個(gè)世界。
我坐火車去廣州;坐船去廣州;坐飛機(jī)去廣州。在那里度暑假、實(shí)習(xí),等簽證。廣州有高第街,到處是香港貨;廣州的男孩女孩個(gè)個(gè)想出國,掙錢。我住在中山醫(yī)大女生宿舍里過暑假,聽那些未來的女醫(yī)生們一大早起來就在朗讀英語,她們都說,我們要去美國——為了更好的生活,她們目標(biāo)明確。
7
79次列車在早晨抵達(dá)上海。
火車進(jìn)站的速度慢下來,我趴在窗口等不及要看那個(gè)物質(zhì)的上海。雨中成片的平房,灰的,黑灰的,木的,棕色的,棕黑的,一片一片,平常百姓的家居生活從一扇扇窗里招搖著衣褲向我致意,跟我的城市看不出區(qū)別。視野里,遠(yuǎn)處有一些樓。不高,更不現(xiàn)代──我在拿它們跟我看過的廣州比。原來上海是這個(gè)樣子的呀,我想。很好奇。
那個(gè)我們?nèi)フ业拇蠼愫孟裨谥幸话偕习唷K缒暝趶V西工作過,所以認(rèn)識(shí)谷姐。她很熱情,讓我們放心,因我們來之前已給過她信,她已安排。果真很快就定下日程,二月十七日乘中國民航經(jīng)洛杉磯入境,轉(zhuǎn)飛舊金山,再轉(zhuǎn)飛華盛頓州的斯波坎。機(jī)票兩千多元人民幣。我一窮二白,老爸贊助了我,那時(shí)他在弄律師事務(wù)所,該是萬元戶。他說:這錢你以后得還啊。
拿到機(jī)票,找到一個(gè)街邊的小郵局給父母掛長途電話報(bào)告離境日程。母親接的電話,說,知道了,一路小心。她從頭到尾,沒有表示過對(duì)我的不舍。年輕人,要出去闖,走得越遠(yuǎn)越好,這是他們對(duì)我講的話。
又給美國方面發(fā)電報(bào),天啊,那時(shí)竟想發(fā)電報(bào)到美國!一想不對(duì),又轉(zhuǎn)而掛對(duì)方付款電話。機(jī)票搞定,離起飛還有三天,可以購物去了。
我那時(shí)住在延安路一家離民航大樓很近的小旅館里,是朋友介紹的。他們出國前到上海,就住那兒,說是離民航近,跑機(jī)票方便。那好像是個(gè)街道辦的旅館?還有地下室,是防空洞里改建出來的。
我手里有好些個(gè)父母的同事朋友叔叔阿姨給寫的介紹信,讓我如果有事,可去找他們?cè)谏虾5挠H朋戚友,中國人就這樣,一出門就想到投親靠友的,這些都是那些叔叔阿姨主動(dòng)提供的。記得其中一位還是牧師呢。我那時(shí)沒這根弦,要不真該去看看那個(gè)時(shí)代的中國牧師是怎樣的。
在火車上認(rèn)識(shí)的一位年輕母親,也給了我她在上海的聯(lián)系方式的。她是從柳州上車的,帶一個(gè)非常漂亮可愛的八歲小女孩。我很快發(fā)現(xiàn),那女孩是個(gè)啞巴,說是小時(shí)用藥弄壞了。那母親說,她們家里是上海支邊到廣西的,在柳州的工廠里。她們的親戚都在上海,常來常往的。小姑娘的爸爸在小姑娘兩歲多時(shí)就到美國探姑媽去了,從此就留在美國。那母親說,孩子爸常來信,說在打工,很辛苦,但他的動(dòng)力就是有一天將女兒接出去,到美國治病。那爸爸相信美國能治好她的。如今那女孩該好大了,不知際遇如何。爸爸接她來美了嗎?病治好了嗎?那真是個(gè)漂亮的小姑娘啊。
買完票,換到四百多美元收好。剩下千來元人民幣,我決定在上海花光它。同去的谷姐說,那就去淮海路吧。街上很多很多的人,比廣州多。
我走上南京路的天橋,下面黑黑的全是人頭!根本看不到水泥地,那么多黑黑的人頭!我呆住了。他們都從哪里來?都在干什么?他們肯定都是我這樣的鄉(xiāng)下人,都說上海人是不大到南京路買東西的。我進(jìn)商店去,給人擠出來,連柜臺(tái)都接近不到。我想我過去真不懂事,讓人家到上海給我買東西!她們都受的這種罪嗎?
我離家的時(shí)候,買了兩個(gè)箱子,里面裝了一點(diǎn)書,其它都是衣物。我?guī)У臅欢啵瑓s有一本<<徐志摩選集>>,那時(shí)深愛志摩。我朋友跟我說,不是去美國嗎?干嘛像是去沙漠?
我不是去沙漠,但是舍不得漂亮的衣裳。那時(shí)我穿蝙蝠衫(去秋今冬美國又流行起來);酷愛高跟鞋(我今天還不喜平跟鞋);長裙,短裙,A型的,連衣的,紅的,綠的,黃的。不停地?fù)Q發(fā)卡;總而言之,燒包,全是跟華華學(xué)的。裝了一大箱。我的那只軟皮的大箱子至今還留著。他們告訴我最好弄個(gè)罩子,要不軟尼龍面會(huì)給勾爛的,華華幫我弄來很長一匹那種做工作服的布,我母親為我車縫了一個(gè)罩子,我至今也將它好好地收著。與它相關(guān)的兩位親友都已離世,它成了紀(jì)念。
我到淮海路買羊毛衫,買全毛的裙裝,買皮鞋,買風(fēng)衣,買絲巾,手套,毛巾被,小禮品。到走的時(shí)候,箱里塞下新舊毛衣十幾件,新皮鞋四五雙,在廣州買的牛仔褲、波鞋,羽絨服等等等等,看得谷姐目瞪口呆。后來到了美國,讓樸素的中國同學(xué)看到我整日花里胡哨的樣子,竟不時(shí)撞過來開玩笑說:你是來上學(xué)的嗎?
那時(shí)的淮海路都是小小的店家,一家接一家,門面不大,店子大多很深。二月的上海一直陰雨,店里亮著暗暗的日光燈。物質(zhì)是很豐富的,像我心中的上海。全是國貨,多還是滬產(chǎn)國貨,質(zhì)量是實(shí)打?qū)嵉暮谩N矣幸患罴t繡花的純羊毛衫至今留著,看著仍象新的一樣。那時(shí)四十多元買的。皮鞋的款式非常多。我買了乳白的,黑的,和紫紅的。價(jià)錢都在三十到三十六七元間。
我并沒有找到去沙漠的感覺,卻把老爸贊助的錢揮霍一空。如果我不出國,按當(dāng)時(shí)的趨勢(shì),大概很快就會(huì)變成啃老族?
我去上海前,了解情況的人都說,要換全國糧票去,那里小吃店都要糧票的。我已經(jīng)很久很久不用糧票了,在我們那兒,你多付一點(diǎn)錢,所謂議價(jià)糧到處都買得到了,副食品都不用票了。
但八九年的上海還要票。他們竟還有半兩的糧票。我用全國糧票去買飯買小吃。吃當(dāng)時(shí)是不重要的。
也許是水土不服,也許是跑得太多。我病了,發(fā)燒,頭暈,嘔吐。谷姐給我喝水,吃藥,頂?shù)降诙欤瑹€不退,吃不下東西。馬上就要上飛機(jī)了,我去一個(gè)區(qū)級(jí)醫(yī)院掛急診,看病的是一個(gè)大學(xué)剛畢業(yè)的女醫(yī)生。我說要不要吊針?她說不用。我就堅(jiān)持要吊針,因?yàn)榈诙炀鸵痫w了,我渾身無力,頭重腳輕,真怕耽誤了行程,如果走不了,改個(gè)機(jī)票,天曉得又有多少麻煩。年輕的女醫(yī)生翻翻白眼,就開了點(diǎn)藥,說回去多喝水,休息就行了。
我回到旅館,又是一番嘔吐,吐完了,休息了一下,突然非常想喝杯糖水。谷姐出門辦事了。我慢慢摸著走到旅館外的街邊的小賣部,想買一兩白糖。人家說,要票!我說我糧票有的,可糖票沒有,我買議價(jià)的吧,我是外地來的,生病了,很想喝一杯糖水。賣東西的人說,沒糖票不好賣的。我走回旅館,轉(zhuǎn)到后面的食堂,問那里的師傅,可不可給我一勺白糖?他說不行!出去小賣部買吧!我說去了,我沒有糖票,人家不賣。我又說我就是病了,特別想喝一杯糖水,我跟你買。他用紙折了一個(gè)小斗,舀了小小的一勺糖,說三毛錢!我給了他三毛錢。
那個(gè)時(shí)候,在南寧,白糖隨便買,一斤七毛錢。那就是一九八九年的上海。她開放的程度遠(yuǎn)遠(yuǎn)比南方滯后,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在2月17日那天一早就叫了出租車去虹橋機(jī)場(chǎng)。谷姐送我去的。虹橋機(jī)場(chǎng)樸素?zé)o華,我排隊(duì)過關(guān),向谷姐招手道別。旁邊有一家父母在送一個(gè)男孩子。那母親哭得像個(gè)淚人,以她的年紀(jì),這個(gè)兒子一定是生得很晚的。她過來跟我說,希望我路上幫忙照顧她的兒子,孩子第一次出遠(yuǎn)門。我點(diǎn)點(diǎn)頭,卻沒有告訴她,我也是第一次出遠(yuǎn)門啊。
飛機(jī)騰空而起時(shí),我看了一眼雨云下的上海。我沒想到我竟然流淚了,我想,我這就走了啊。旁邊的男生也在哭。他是同濟(jì)二年級(jí)的學(xué)生,退學(xué)去加大戴維斯分校。
在1989年,我不讀書,不看報(bào),不學(xué)馬列,深陷在無盡的青春問題中,慵懶,憂郁,厭世。1989年,后來發(fā)生了驚天動(dòng)地的大事件,在那個(gè)早春,我后來認(rèn)識(shí)的那么多朋友,都開始卷入,可我卻與“我”之外的一切無所關(guān)聯(lián)。“我”在那個(gè)時(shí)候,是我前行的道路中,在前方吸引著我所有注意力的一個(gè)路牌。我在1989年的早春忽然得到機(jī)會(huì)踹了它一腳,它應(yīng)聲倒下的時(shí)候,我尋到了去往新大陸的那扇門。
我當(dāng)年親密的友人們大多在那之前都離開了中國,我期待跟他們重聚。
奮強(qiáng)那時(shí)甚至說:如果人間有天堂,美國就是天堂。我其實(shí)并不信這樣的話。但美國在1989年成了一根稻草,我抓住了它。
很多年后,我聽丹青兄說,感謝美國包容他于無形。就是這個(gè)意思,我非常喜歡他的這個(gè)意思。在我人生陷入低潮的時(shí)刻,我選擇了美國。美國也選擇了我——在我兩手空空,連正式的入學(xué)錄取通知書都沒有的時(shí)候,它的廣州總領(lǐng)館向我發(fā)放了通行證。它確實(shí)包容我于無形,讓我獲得了過一種全新生活的機(jī)會(huì),平安度過最危險(xiǎn)的青蔥歲月,變成一個(gè)知道感恩的人。
在感謝所有我該感謝的人之外,我真誠地感謝這個(gè)偉大的國家。
我青年時(shí)代的友人,在那日就此正式別過了。再見,就都已到中年。廣西那邊的人,大多是從深圳出境的。因私人感情的原因,我選擇了從上海離境。
谷姐跟我一起去的上海。她在柳州站上車,我們一起換到了臥鋪車廂。到了上海,去找一個(gè)先生在民航工作的大姐。請(qǐng)她先生幫買去美國的機(jī)票。那時(shí)沒有互聯(lián)網(wǎng),沒有預(yù)訂,你如果打民航的電話,永遠(yuǎn)沒有人接,或忙音。一周只兩班飛機(jī)飛美國。你必須找關(guān)系。
那是我第一次到上海。
上海在那之前,于我一直是以物質(zhì)的形式存在的。母親的同事、朋友每年回上海探親,或出差,母親都會(huì)給她們一個(gè)單子,那時(shí)的人真有空,真的都給你去采購的。有丁字皮鞋,翻毛皮鞋,銹花羊毛衫,花型漂亮的的確良布料,中長纖維的格子成衣;漂亮的塑料涼鞋;五香蠶豆,肉松,大白兔奶糖,果香型橡皮擦,神氣的有磁鐵扣的文具盒……后來到我自己也有這個(gè)習(xí)慣,只要有人去上海,我就會(huì)讓人給買衣鞋包什么的。
直到八十年代,我開始跑廣州,覺得上海捎來的東西已經(jīng)不夠時(shí)髦,廣州的舶來貨質(zhì)地比不過上海的,但那款式,那花型,樣樣都代表著另外一個(gè)世界。
我坐火車去廣州;坐船去廣州;坐飛機(jī)去廣州。在那里度暑假、實(shí)習(xí),等簽證。廣州有高第街,到處是香港貨;廣州的男孩女孩個(gè)個(gè)想出國,掙錢。我住在中山醫(yī)大女生宿舍里過暑假,聽那些未來的女醫(yī)生們一大早起來就在朗讀英語,她們都說,我們要去美國——為了更好的生活,她們目標(biāo)明確。
7
79次列車在早晨抵達(dá)上海。
火車進(jìn)站的速度慢下來,我趴在窗口等不及要看那個(gè)物質(zhì)的上海。雨中成片的平房,灰的,黑灰的,木的,棕色的,棕黑的,一片一片,平常百姓的家居生活從一扇扇窗里招搖著衣褲向我致意,跟我的城市看不出區(qū)別。視野里,遠(yuǎn)處有一些樓。不高,更不現(xiàn)代──我在拿它們跟我看過的廣州比。原來上海是這個(gè)樣子的呀,我想。很好奇。
那個(gè)我們?nèi)フ业拇蠼愫孟裨谥幸话偕习唷K缒暝趶V西工作過,所以認(rèn)識(shí)谷姐。她很熱情,讓我們放心,因我們來之前已給過她信,她已安排。果真很快就定下日程,二月十七日乘中國民航經(jīng)洛杉磯入境,轉(zhuǎn)飛舊金山,再轉(zhuǎn)飛華盛頓州的斯波坎。機(jī)票兩千多元人民幣。我一窮二白,老爸贊助了我,那時(shí)他在弄律師事務(wù)所,該是萬元戶。他說:這錢你以后得還啊。
拿到機(jī)票,找到一個(gè)街邊的小郵局給父母掛長途電話報(bào)告離境日程。母親接的電話,說,知道了,一路小心。她從頭到尾,沒有表示過對(duì)我的不舍。年輕人,要出去闖,走得越遠(yuǎn)越好,這是他們對(duì)我講的話。
又給美國方面發(fā)電報(bào),天啊,那時(shí)竟想發(fā)電報(bào)到美國!一想不對(duì),又轉(zhuǎn)而掛對(duì)方付款電話。機(jī)票搞定,離起飛還有三天,可以購物去了。
我那時(shí)住在延安路一家離民航大樓很近的小旅館里,是朋友介紹的。他們出國前到上海,就住那兒,說是離民航近,跑機(jī)票方便。那好像是個(gè)街道辦的旅館?還有地下室,是防空洞里改建出來的。
我手里有好些個(gè)父母的同事朋友叔叔阿姨給寫的介紹信,讓我如果有事,可去找他們?cè)谏虾5挠H朋戚友,中國人就這樣,一出門就想到投親靠友的,這些都是那些叔叔阿姨主動(dòng)提供的。記得其中一位還是牧師呢。我那時(shí)沒這根弦,要不真該去看看那個(gè)時(shí)代的中國牧師是怎樣的。
在火車上認(rèn)識(shí)的一位年輕母親,也給了我她在上海的聯(lián)系方式的。她是從柳州上車的,帶一個(gè)非常漂亮可愛的八歲小女孩。我很快發(fā)現(xiàn),那女孩是個(gè)啞巴,說是小時(shí)用藥弄壞了。那母親說,她們家里是上海支邊到廣西的,在柳州的工廠里。她們的親戚都在上海,常來常往的。小姑娘的爸爸在小姑娘兩歲多時(shí)就到美國探姑媽去了,從此就留在美國。那母親說,孩子爸常來信,說在打工,很辛苦,但他的動(dòng)力就是有一天將女兒接出去,到美國治病。那爸爸相信美國能治好她的。如今那女孩該好大了,不知際遇如何。爸爸接她來美了嗎?病治好了嗎?那真是個(gè)漂亮的小姑娘啊。
買完票,換到四百多美元收好。剩下千來元人民幣,我決定在上海花光它。同去的谷姐說,那就去淮海路吧。街上很多很多的人,比廣州多。
我走上南京路的天橋,下面黑黑的全是人頭!根本看不到水泥地,那么多黑黑的人頭!我呆住了。他們都從哪里來?都在干什么?他們肯定都是我這樣的鄉(xiāng)下人,都說上海人是不大到南京路買東西的。我進(jìn)商店去,給人擠出來,連柜臺(tái)都接近不到。我想我過去真不懂事,讓人家到上海給我買東西!她們都受的這種罪嗎?
我離家的時(shí)候,買了兩個(gè)箱子,里面裝了一點(diǎn)書,其它都是衣物。我?guī)У臅欢啵瑓s有一本<<徐志摩選集>>,那時(shí)深愛志摩。我朋友跟我說,不是去美國嗎?干嘛像是去沙漠?
我不是去沙漠,但是舍不得漂亮的衣裳。那時(shí)我穿蝙蝠衫(去秋今冬美國又流行起來);酷愛高跟鞋(我今天還不喜平跟鞋);長裙,短裙,A型的,連衣的,紅的,綠的,黃的。不停地?fù)Q發(fā)卡;總而言之,燒包,全是跟華華學(xué)的。裝了一大箱。我的那只軟皮的大箱子至今還留著。他們告訴我最好弄個(gè)罩子,要不軟尼龍面會(huì)給勾爛的,華華幫我弄來很長一匹那種做工作服的布,我母親為我車縫了一個(gè)罩子,我至今也將它好好地收著。與它相關(guān)的兩位親友都已離世,它成了紀(jì)念。
我到淮海路買羊毛衫,買全毛的裙裝,買皮鞋,買風(fēng)衣,買絲巾,手套,毛巾被,小禮品。到走的時(shí)候,箱里塞下新舊毛衣十幾件,新皮鞋四五雙,在廣州買的牛仔褲、波鞋,羽絨服等等等等,看得谷姐目瞪口呆。后來到了美國,讓樸素的中國同學(xué)看到我整日花里胡哨的樣子,竟不時(shí)撞過來開玩笑說:你是來上學(xué)的嗎?
那時(shí)的淮海路都是小小的店家,一家接一家,門面不大,店子大多很深。二月的上海一直陰雨,店里亮著暗暗的日光燈。物質(zhì)是很豐富的,像我心中的上海。全是國貨,多還是滬產(chǎn)國貨,質(zhì)量是實(shí)打?qū)嵉暮谩N矣幸患罴t繡花的純羊毛衫至今留著,看著仍象新的一樣。那時(shí)四十多元買的。皮鞋的款式非常多。我買了乳白的,黑的,和紫紅的。價(jià)錢都在三十到三十六七元間。
我并沒有找到去沙漠的感覺,卻把老爸贊助的錢揮霍一空。如果我不出國,按當(dāng)時(shí)的趨勢(shì),大概很快就會(huì)變成啃老族?
我去上海前,了解情況的人都說,要換全國糧票去,那里小吃店都要糧票的。我已經(jīng)很久很久不用糧票了,在我們那兒,你多付一點(diǎn)錢,所謂議價(jià)糧到處都買得到了,副食品都不用票了。
但八九年的上海還要票。他們竟還有半兩的糧票。我用全國糧票去買飯買小吃。吃當(dāng)時(shí)是不重要的。
也許是水土不服,也許是跑得太多。我病了,發(fā)燒,頭暈,嘔吐。谷姐給我喝水,吃藥,頂?shù)降诙欤瑹€不退,吃不下東西。馬上就要上飛機(jī)了,我去一個(gè)區(qū)級(jí)醫(yī)院掛急診,看病的是一個(gè)大學(xué)剛畢業(yè)的女醫(yī)生。我說要不要吊針?她說不用。我就堅(jiān)持要吊針,因?yàn)榈诙炀鸵痫w了,我渾身無力,頭重腳輕,真怕耽誤了行程,如果走不了,改個(gè)機(jī)票,天曉得又有多少麻煩。年輕的女醫(yī)生翻翻白眼,就開了點(diǎn)藥,說回去多喝水,休息就行了。
我回到旅館,又是一番嘔吐,吐完了,休息了一下,突然非常想喝杯糖水。谷姐出門辦事了。我慢慢摸著走到旅館外的街邊的小賣部,想買一兩白糖。人家說,要票!我說我糧票有的,可糖票沒有,我買議價(jià)的吧,我是外地來的,生病了,很想喝一杯糖水。賣東西的人說,沒糖票不好賣的。我走回旅館,轉(zhuǎn)到后面的食堂,問那里的師傅,可不可給我一勺白糖?他說不行!出去小賣部買吧!我說去了,我沒有糖票,人家不賣。我又說我就是病了,特別想喝一杯糖水,我跟你買。他用紙折了一個(gè)小斗,舀了小小的一勺糖,說三毛錢!我給了他三毛錢。
那個(gè)時(shí)候,在南寧,白糖隨便買,一斤七毛錢。那就是一九八九年的上海。她開放的程度遠(yuǎn)遠(yuǎn)比南方滯后,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在2月17日那天一早就叫了出租車去虹橋機(jī)場(chǎng)。谷姐送我去的。虹橋機(jī)場(chǎng)樸素?zé)o華,我排隊(duì)過關(guān),向谷姐招手道別。旁邊有一家父母在送一個(gè)男孩子。那母親哭得像個(gè)淚人,以她的年紀(jì),這個(gè)兒子一定是生得很晚的。她過來跟我說,希望我路上幫忙照顧她的兒子,孩子第一次出遠(yuǎn)門。我點(diǎn)點(diǎn)頭,卻沒有告訴她,我也是第一次出遠(yuǎn)門啊。
飛機(jī)騰空而起時(shí),我看了一眼雨云下的上海。我沒想到我竟然流淚了,我想,我這就走了啊。旁邊的男生也在哭。他是同濟(jì)二年級(jí)的學(xué)生,退學(xué)去加大戴維斯分校。
在1989年,我不讀書,不看報(bào),不學(xué)馬列,深陷在無盡的青春問題中,慵懶,憂郁,厭世。1989年,后來發(fā)生了驚天動(dòng)地的大事件,在那個(gè)早春,我后來認(rèn)識(shí)的那么多朋友,都開始卷入,可我卻與“我”之外的一切無所關(guān)聯(lián)。“我”在那個(gè)時(shí)候,是我前行的道路中,在前方吸引著我所有注意力的一個(gè)路牌。我在1989年的早春忽然得到機(jī)會(huì)踹了它一腳,它應(yīng)聲倒下的時(shí)候,我尋到了去往新大陸的那扇門。
我當(dāng)年親密的友人們大多在那之前都離開了中國,我期待跟他們重聚。
奮強(qiáng)那時(shí)甚至說:如果人間有天堂,美國就是天堂。我其實(shí)并不信這樣的話。但美國在1989年成了一根稻草,我抓住了它。
很多年后,我聽丹青兄說,感謝美國包容他于無形。就是這個(gè)意思,我非常喜歡他的這個(gè)意思。在我人生陷入低潮的時(shí)刻,我選擇了美國。美國也選擇了我——在我兩手空空,連正式的入學(xué)錄取通知書都沒有的時(shí)候,它的廣州總領(lǐng)館向我發(fā)放了通行證。它確實(shí)包容我于無形,讓我獲得了過一種全新生活的機(jī)會(huì),平安度過最危險(xiǎn)的青蔥歲月,變成一個(gè)知道感恩的人。
在感謝所有我該感謝的人之外,我真誠地感謝這個(gè)偉大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