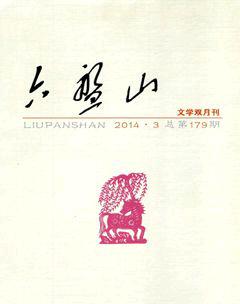宗教意識”中的“死亡關懷”
姜應龍
作為一個出生在鄉村、成長在鄉村,以純潔的眼睛和質樸的心靈審視鄉土生活的“80后”女作家,寧夏回族青年女作家馬金蓮始終以其獨特的視角和細膩的筆觸書寫著西海固這片貧瘠土地上的人情風貌。在她的筆下,西海固生活顯得有些憂傷而又透露著絲絲甘甜,也許正是她的這種獨特經歷才孕育了如此豐富的精神世界,才構成了她“明靜又傷感、好笑又苦澀、艱辛與希望、磨難與堅韌、成長與隱痛交織并存的敘述風格”。小說《長河》(《小說選刊》2013年第10期)以馬金蓮一如既往的視角關注著西海固的鄉土生活,不僅探掘著生存的本質和意義,也以宗教的眼光和審美表現著穆斯林面對無常時獨有的“死亡關懷”和宗教意識。
《長河》以四個篇章描寫了四個生活于西海固底層社會的人們無常的故事。小說始終縈繞著死亡的氣息和無奈的悲痛,然而在馬金蓮的筆下卻顯得溫存而不突兀,平淡卻又偉大。以穆斯林獨有的宗教意識表現著對亡人的另類關懷和西海固人質樸、善良的內心世界。
受傳統社會環境和宗教因素的影響,西海固形成了以男性為社會、家庭中心的地域文化,兒童和女性往往是被社會生活和家庭生活邊緣化的群體,他們沒有重要活動和事件的決策權與參與權。而馬金蓮卻反其道而行之,她的小說大多采用兒童或女性視角作為敘述者,以一種類似于局外人的身份洞察著周邊的一切事物,獲取著更加透徹、細微的信息。兒童率真無邪的天性決定了他們眼中的世界必將回歸原生態,女性細膩而柔軟的內心決定了她們用最豐富、真實的情感看待事物。馬金蓮正是以兒童和女性的視角不斷剖析著西海固的鄉土生活,關照著這片土地上最為原生態和最為純潔的一面,“因而馬金蓮的小說不經意間就像安徒生《皇帝的新裝》中的小孩一樣,說出簡單但被遮蔽的生活真理。”小說《長河》依舊沿用兒童的視角審視著人們無常后的一舉一動,在兒童的眼中,村莊里有人無常了意味著娃娃們的節日到了,“平日里不常見面的人也都能見到了”,而且他們會因為送埋體而得到兩毛或五毛的“海底耶”,以便他們在獨眼那里換取“做夢都想得到的好東西”,還“可以大搖大擺在主人家進進出出地自由活動,到他們的上房、廚房、倉房等平時沒有機會進出的地方游逛一番”。他們單純無邪的眼中真實地再現了亡人的親人們的悲痛和鄉親們臉上的凄然,展現著面對死亡時人們內心深處的純潔和真摯的情感。
從馬金蓮的作品中我們能夠發現,她以獨特的視角關照著西海固地區純潔、質樸的鄉土生活,忠實地記錄著這片土地上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長河》中為了孝敬父母而在挖井吊土時被砸而無常的伊哈,農忙的季節,人們忙于播種、除草、收割、碾打而大半時間都在野外的場景為我們展現了人們生活的苦難,但感受更多的卻是面對苦難時人們所表現出的堅韌與執著,他們秉承著吃苦耐勞的傳統,將內心深處強大的能量發揮得淋漓盡致。
馬金蓮在關注西海固鄉土生活的同時,另一個關注點便是這篇貧瘠土地上女性的生活狀況,通過對女性生存狀況的書寫表達著自己對女性的人文關懷。“我”的母親因癱瘓在床而情緒變得反復無常,面對辛勞的父親她說:“真主呀,這么老實的人咋就攤上了我這樣一個病秧子呢,我們的命真是苦到家了。”這是一個女性面對不堪命運的心聲,也是面對丈夫、兒女和貧苦家庭發出的悲痛呼喚。最終母親選擇了不吃藥,以便為家庭節省開支,更為重要的是她希望早點兒走,不要再拖累丈夫和家人。在馬金蓮的眼中,這些被社會生活與家庭生活邊緣化的女人們承擔了家庭日常生活中的重擔,面對苦難和壓力,她們并沒有氣餒,而是用她們獨有的方式展現著她們身上獨有的堅韌與頑強。
小說《長河》一如既往地堅持了馬金蓮慣常的風格與審美特征,不同的是作品表現了穆斯林面對無常時獨有的“死亡關懷”和宗教意識。寧夏西海固地區是回族的一大聚居區,回族以伊斯蘭教為自己的宗教信仰,在伊斯蘭教的經典教義中,“平等觀、前定觀以及‘兩世吉慶的思想指導和規范著穆斯林的日常行為,這些思想也極大地影響和決定了回族穆斯林的死亡觀及其臨終關懷的形式和內容。”正是伊斯蘭教特有的“生死觀”,回族穆斯林很早便知道珍惜生命,努力生活。同時也能寧靜坦然地對待死亡,接受死亡。
伊斯蘭教認為世界上的一切生命,包括人的生命,都是真主安拉創造的結果。《古蘭經》中記載:“我們確是真主所有的,我們必定只歸依他”。小說《長河》中,因為挖井吊土而意外無常的伊哈、因心臟病而無常的小姑娘素福葉、因常年癱瘓最終無望治療選擇不吃藥而無常的“我”的母親、活到了九十一歲終因壽限已到而安詳無常的穆薩爺爺,他們的“歸真”(回族穆斯林把死亡稱作“歸真”)給親人和鄉親們帶來了痛苦和緬懷,但卻沒有人因此說出一句怨天尤人的話來,穆斯林們知道這些都是真主的安排。回族穆斯林有六大信仰,即信安拉、信使者、信經典、信天使、信后世以及信前定。前定是指真主的安排,“不得真主的許可,任何人都不會死亡;真主已注定各人的壽限了”(《古蘭經》)。有了“前定”信仰,回族穆斯林便認為安拉決定著人類生命的長短,人是無法改變它的,“人人都要嘗死的滋味”(《古蘭經》)。因此,回族穆斯林把死亡看成是生物的必然現象、人的必然歸宿。
回族穆斯林認為現世生命是有限的,“其實,后世是更好的,是更久長的”(《古蘭經》)。與后世相比,“今世生活,只是欺騙人的享受”(《古蘭經》)。人活著不僅要實現現世生命的價值,更要追求后世生命的價值。而且伊斯蘭教認為今世的宗教修行以及對真主的虔敬與否決定著后世的價值,也決定著生命的永恒價值。不論富裕還是貧窮,只有虔信真主的人才能進入天堂。伊哈是個孝子,為了給雙親打一口井,徹底解決吃水難的問題,最終喪命,“無常”后連一塊用來包裹埋體的潔凈的羊毛氈都沒有,更沒有在送埋體時散海底耶;素福葉是一個擁有清瘦小臉,兩彎兒細溜溜的眉毛,明亮羞怯的眼睛被癩頭稱為“仙女下凡”的純凈的小姑娘,她離死亡很近很近,正因為此,她更能體會生的意義,終因追尋馬蘭花而心臟病發無常在了山坡上;“我”的母親常年癱瘓在床,受盡了身體與精神上的苦難,為了不拖累丈夫和家人最終放棄了治療,選擇了早點兒“走”;活到九十一歲的穆薩老人一輩子沒干過歹事,老了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無常了照舊受人尊敬,“無常”后的埋體送得非常好。在馬金蓮的眼中,他們都是虔信真主的人,他們在生前是心安的,無論“歸真”的原因如何,是否突然,馬金蓮相信他們的來世是幸福的,因為美好幸福的“天堂”正在等著他們。
回族穆斯林非常重視靈魂歸宿的終極關懷。終極關懷主要是指信仰的關懷,它包括明醒“伊瑪尼”、請阿訇念“討白”和要“口喚”。同時也貫穿在送埋體、親人送別等一系列送別儀式中。《長河》中“德高望重的鄉老馬三立老漢向來是料理喪葬的帶頭人”,他總是能做到神態安詳、穩重,處事不驚的帶頭和大伙商議送葬的具體事宜;阿訇大聲誦念清真言為亡人明醒“伊瑪尼”念“討白”和要“口喚”;村莊里的男女老少都來為亡人送埋體,并評述著亡人生平的點點滴滴,為亡人的“無常”表達內心深處的惋惜;伊哈家因貧困拿不出一張潔凈的羊毛氈時,鄰居“王老漢趕緊跑回去抱來了他家的一頁新氈,”;“我”的母親無常后,“姐姐拿著一些白線,給每個女人散一束白線幾苗針,意味著我們的母親生前可能借過別人的針頭線腦而忘了歸還,我們借著送埋體一并給人家歸還了,這樣在后世的母親就不會欠著別人的賬債了”;穆薩老爺爺的葬禮很隆重,“男人們集體行動,掃開了村中主干道上的積雪,為穆薩老漢準備葬禮”,“大伙都來了。臉上掛著笑,樂呵呵打著招呼,互相問候著,不無喜悅地贊嘆著這一場好雪”。穆薩老人一輩子經歷的世事很多,是“村莊里最受尊重的人家。”他在年輕時冒險解救五八年“社教”中不堪凌辱而上吊的柯家老阿訇并把自己的小女兒許給了柯家孫子,后來柯家老奶奶無常的時候給兒孫交代,“要世世代代記著馬家穆薩的恩情”。正因為穆薩老人的為人,“真主是不會虧待忠厚老實人的”,穆薩老人“老了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無常了照舊受人尊敬”。
從《長河》中我們能夠看到回族穆斯林的信仰,使他們對死亡采取了客觀從容的態度,認為死亡是一種自然規律,是真主的安排,一個人的生命是短暫的,而死亡是永恒的。正因為如此,在馬金蓮的筆下,西海固這片貧瘠純凈的土地上,人們坦然、達觀、從容不迫地面對死亡,使死具有了崇高的意義。他們的“死亡觀”使生者受到了極大的震撼,讓他們懂得了珍惜前世的點滴;讓亡者得到了安息,能夠平靜祥和地尋找真主為他們建造的“天堂”。
“一個人只有坦然洞察生死的奧秘,獲得生死的大智慧,才能提升生的質量,消解死的恐懼,平抑死的悲傷,最終超越死亡”。作為一個回族穆斯林,一個出生并生長于西海固回族聚居區的青年作家,馬金蓮正在試圖洞察生死的奧秘,堅守著一個穆斯林的宗教信仰,懷揣著純凈高尚的“死亡關懷”書寫著屬于西海固獨特的生命圖景。當眾多作家和讀者將目光聚焦在都市生活上時,馬金蓮卻始終堅持著自己內心的那一片熱忱與虔誠的信仰,堅持著對社會底層和鄉土生活的書寫,猶如一汪清泉讓我們再度重新審視自我,尋找內心中純潔而又質樸的一面。
參考文獻:
王永軍:個性固化與模式超越——青年女作家馬金蓮小說創作總論。
王興文:寧夏回族女作家馬金蓮的小說創作論略。
嚴夢春:回族的死亡觀與臨終關懷傳統。
買麗萍:回族穆斯林的“死亡關懷”及其積極意義。
【責任編校 單永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