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夜晚用于相思
◎ 安 頓
四個夜晚用于相思
◎ 安 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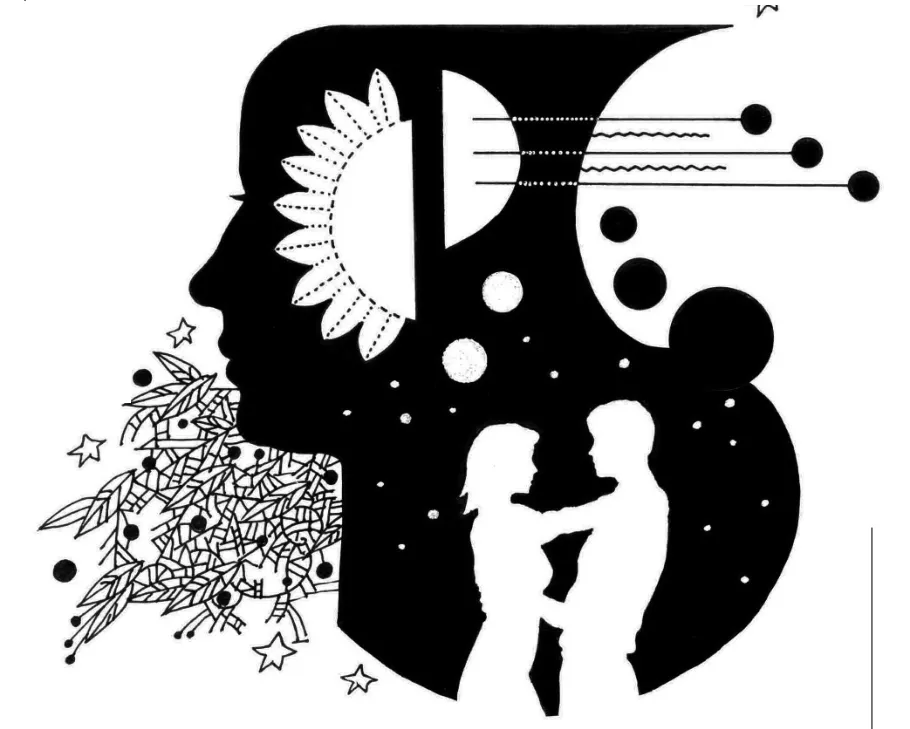
飛機收起起落架的時候,機身猛地一震,我急速地右傾。“不要緊,就這么一下。”一只手溫和、有力地拉住了我的胳膊。這聲音來自我身邊的一位白發老婦人。她穿著灰色羊絨衫、毛呢長褲,顯得十分干練,白發卷曲,一雙灰色的眼睛毫不因年邁而渾濁。
“您的北京話很像我外婆講的那一種,現在不大有人這么說話了。”我試探著說。老人的臉上涌起一種祥和 :“那是我 20 歲開始學的中文口音,1936 年,還沒有開始抗日。”我飛快地算出老人的年齡——80 歲。但她不像 80 歲的女人。
飛機慢慢爬升,老人如自言自語般輕聲講述起自己的故事:她的家鄉在德國法蘭克福,父親是一位建筑學教授。當時父親有一位學生,一個英俊的湖北小伙子,他講一口流利的德文,常常出現在她家的客廳里,在和父親討論問題的時候偶爾會偷偷看她,那時她 17歲。兩年后,25歲的湖北小伙子回國前留下一封信,信里有一張中德文對照的地址卡片:中國·武漢。這個地址,她只用過一次,用于給他發一封簡短的電報:“將來武漢結婚,請等待。”
兩人結婚后一直在中國生活,1966 年丈夫去世之后,她便定居北京。60年的時光已經讓她完全中國化了,她穿過列寧服,拿過紅寶書,有中國人手一頁的戶口卡片,用過各種糧票、布票、肉票……她講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話。她每年回一次武漢,在她的觀念里,丈夫的家就是她的家。
從她的講述中,我算出一個數字——30年,一個德國女人為一個中國建筑師守寡 30年。老人的敘述中沒有任何愁苦,她完全沉浸在少年夫妻的甜蜜之中。
飛機開始降落。“我可以知道怎樣在北京找到您嗎?”我小心地問。“5天以后我返回北京,咱們要是有緣,還可以碰上。”她笑著說。
在武漢找到一家酒店住下來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訂下5天之后返京的機票,只為與她重逢。因為這個老人,我開始無法抑制地想家。而事實上,從我做記者的那一天起,就已經習慣和丈夫分離。
我撥通家里的電話,是丈夫的聲音:“就知道是你。”于是我給他講起那個老婦人,丈夫靜靜地聽著。“我知道你是欣賞我的。”相隔千里,我忽然有了表達的沖動,這是平日里的我不會做的。
丈夫笑了,但他的話依舊淡然:“我在洗衣服、床罩還有窗簾,你想想,一個老婆出差了的男人,除了這樣消磨時間還能怎樣?”這是丈夫一貫的表達方式,我似乎只有在異地的夜空下才能感覺到其中的深意。
5天的時間很快過去,在離開武漢前的最后一個上午,我找到一間休閑裝專賣店,給丈夫買了件毛衣。這是我若干次出遠門中唯一一次帶禮物回家。
我提前一個半小時到達機場,逡巡在換登機牌的地方,等待那個令我難以忘懷的老婦人。當灰色的身影出現在視線中,我們相視而笑。老人拉住我的手:“下了飛機有人接嗎?”我搖頭:“我丈夫今天下午的班機,出差。”老人笑了,雙眼瞇成一條縫兒:“聚少離多,我們當年也這樣。你丈夫一定很不希望你出差。”我點頭,說不出話,忽然很想哭。“因為有分離,才顯得在一起的時候很寶貴。”老人拍拍我的手,“我們在一起30 年,之后我有 30 年的時間用來回憶。你離開家5天,有4個夜晚用于相思,很充實,對不對?”
我的眼淚落下來,打在她皮膚有些松弛的手背上。
我們仍然在機場告別。她鉆進計程車之前很認真地問我:“你知道婚姻是什么嗎?”我一時語塞。
老人粲然一笑:“婚姻就是把穩定送給你愛的人,把浪漫留在你心里。”
回到家,看到丈夫留的字條:“我會用魂斗羅第六代的速度快去快回。”桌布、床罩和窗簾都是新換過的,屋子里飄著淡淡的姜花味道。我抱著那件新毛衣坐在地板上,把柔軟的大毛衣貼在臉上,想著老人說的話。(摘自《絕對隱私——當代中國人情感口述實錄》 北京出版社 圖 / 傅樹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