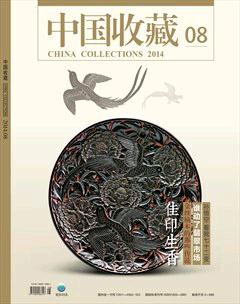疏可走馬 密不透風
劉賁



中國的文化理想是“和”為貴的,文化核心是大“中”至正,其審美方式是仰“觀”俯察,最終達到一種審美主體構成的“知足常樂”,而篆刻藝術的整體布局就正是一個融合以上思想的最精煉的視覺物化形態。印章,以文字為主要表現手段,自古以來就可按照用途劃分為“實用印章”和“藝術印章”。而這兩者,無論單字、兩字、多字乃至百字,都是一個整體。方寸之間,氣象萬千。章法的結構編排是篆刻的萬法之源,印章布局要經由多次安排推敲、一審再視,才能看出其謀篇布局。所謂“疏可走馬、密不透風”正是篆刻藝術謀篇布局的一個動靜、縱橫、輕重、展束和盼顧的對比協調問題。
事實上,初學篆刻者,往往必須掌握與理解一種橫平豎直、方圓互補、左右對稱的結字技巧。這種技巧力求將每一個字安排妥帖、布白勻稱,排列規范入印。是從單純走向自然,從質樸轉化為華贍,從曠達顯示出勁健的基礎。因此,印文分朱布白之間,強調內容與形式和諧表現,既要發揮每個字的內涵特色,又要協調整個印面的布局安排,是一種相互獨立“自治”,局部又相互制約統一的“聯邦”式整體。
篆刻藝術為了強調這種動靜顧盼對比,避免填鴨式的呆板空間,就要變化,即“疏可走馬、密不透風”。以此攪起方寸布局的隨字、隨勢、隨興、隨形的參差撅挺、氣串意新。而所刻內容結字之間粗細、正斜、長短、波折、挫頓等的相輔相成,相映成趣,則使原有動靜筆畫得以適當的夸張和變化,使印面空間沖破平淡和板滯。
讓我們舉例說明,傳世最著名的戰國古璽“日庚都萃車馬”(圖1)即是“疏可走馬、密不透風”的典型。此璽鈕部中空,可安裝木柄,為戰國時期燕國官方烙馬的鐵質專用章(烙馬印),十九世紀末出土于河北易縣。其形制較大,邊長7厘米左右,印面六字,兩行朱文排列,為戰國璽印中最大者。出土后被古文字學家王懿榮用600兩白銀購得,可惜于20世紀初被日本人藤井善助購去,現藏于日本京都有鄰館。
“日庚都”為戰國時燕國地名,“萃車”是指副車,全文翻譯過來就是指所烙之馬為日庚都官署副車所用的馬。該印印面六字布局高渾典博,沉穩而不失峭拔, 挪讓而不失瀟灑。體勢疏密呼應,超詣純熟,藝術審美價值極高,常為后世篆刻追隨者所臨摹借鑒。
此印文緊靠分布在四周,中間呈空虛狀,相互揖讓,巧妙布白。最大限度地達到中空的狀態。這種“疏可走馬、密不透風”布局方式猶如高山叢林,環抱一泓清泉碧池,給人感覺古雅凝重,富有詩情畫意。
傳統印章的章法布局為我們提供了一定的標準或模式,并且隨著歷史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后繼的篆刻者們,特別是明清以降,當篆刻成為文人案頭玩物之后,這種超越歷史的時空的視覺物化藝術形式,更綻放出一種現實的生命力。雖然印章的形式和材質在演進和轉型。但借印抒情,張揚活力,打造趣味的審美風尚 并沒有變。
近代以來,齊白石以詩、書、畫、印“四絕”聞名,其印章呈現為多字白文,大刀闊斧的單刀刻法主要得益于《天發神讖碑》的影響,縱橫平直,不加修飾的印風高立現代印壇。筆墨當隨時代”,其“人長壽”、“湖南長沙湘潭人也”、“大匠之門”、“悔烏堂”、“三百石印富翁”等印集中反映出了他的時代心聲。其印面鐵筆線條排列滿目縱橫、波瀾起伏,長豎、長橫韌勁支撐印面,自然節律天成,空間塊面分割的耐人尋味,常有絕岸頹峰之勢,臨危據槁之形,在險絕、矛盾與沖突之中,復歸平整,必欲仔細品鑒而后快。他曾有詩云:“做摹蝕削可愁人,與世相違我輩能。快劍斬蛇成死物,昆刀截玉露泥痕。”他沒有把自己的審美定在一尊,拘于一律,把握時代之脈,重視藝術多元化吸收和借鑒。他以其自身的創作體驗去介入時代審美氛圍,轉化意識、傳統取經、大膽探索。
再例如下面這一枚齊白石1935年作“黃庭堅詞句四面印”,此印印文乃黃山谷畫堂春詞(一說為秦少姑作),四個印面如同大型抒情樂曲的四個樂章一樣,是一個和諧的整體。“東風”一印以舒張的字法為主,沖刀直走,線質剛柔相濟,威猛恣肆中不乏溫婉的情致。“雨余”一印則奇正相生,益為奔放,留紅大膽自然,“雨”字獨到的字法使畫意盎然。“杏花”、“畫屏”兩印均有十七字之多,鼓刀耘石,如同書寫于紙面一樣,意到之處,刀亦隨之,用刀輕重和石面自然崩裂形成的塊面變化富有生動的節奏感,莫可端倪,讓人領略到星列河漢的妙趣。此整體方圓、離合、疏密、虛實、陰陽等形體美感有機整合在在一起,于舒朗處見飄逸,密集處致幽邃,面積比例富有節奏,筆畫輕重粗細變化多姿,以“斷”言說“續”,以“分”強調“合”,以“動”寓言“靜”的處理手法,形成了氣脈貫注的動態性張力,主次有別,主輔安閑相依,顯示出高古軒昂而又值得品鑒的無窮魅力,賦予印面以極高的品位,使觀者視覺上為之一亮。而這種筆意疏密參差變化生動,穿插自然而恣肆縱橫,也是“疏可走馬,密不透風”的藝術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