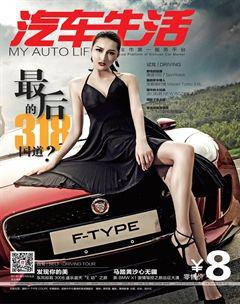遠方在,318就不會消失
劉曉夫

登巴大叔告訴我,后天他又將離開成都。我問下一站是哪,他竟然說還沒決定。登巴客棧出品過一張《藏地旅行地圖》,封面印著“我的心如流云在天空漫無目的,但只要聽到你的召喚,我將即刻啟程”——出自登巴大叔的詩歌《生命歸去》“我將即刻啟程”,登巴大叔及眾多318行者的生命狀態,以此句刻畫,足矣。
墨爾多自生塔與南木克老人
在丹巴,流傳著一個關于自生塔的傳說——墨爾多神山上有一處天然的自生塔群,發現之人叫南木克,1957年他在家里找到了一本有關墨爾多神山的藏文經書,在經書里發現了自生塔的秘密。他便每年上山兩三次尋找,終于在1978年找到了自生塔,并在自生塔旁邊住了下來。
2003年冬,登巴大叔從莫日村出發,上山尋找這座自生塔。傍晚時分,登巴大叔見到了南木克與他的女兒班馬初,那時南木克病得很重。南木克睡后,登巴大叔與班馬初徹夜長談,“我問她如果你爸爸走了,你怎么辦呢?她說我爸爸不會走的,我就在這一直陪著他。”就是這樣一句話,讓登巴大叔無數次反思生命的狀態,“這是最簡單最深刻的回答”。
兩天之后,在登巴大叔離開之時,班馬初讓他帶信給她哥哥上山準備后事,“我身上隨時備著一瓶重感片,離開時我隨手留下了一瓶,沒想到兩個月之后,班馬初在丹巴打電話告訴我他爸爸吃了我的藥病好了。”
這次奇遇,登巴大叔突然發現內心之門被打開,觸摸到了生命的本原,找到了自己。
318國道改變中國
采訪登巴大叔的一周前,登巴大叔在“甘孜州走進北大分享會”上分享了他背包十多年的故事,其中包括他在墨爾多的奇遇。“我在北大問那些學生,‘不知你們坐在這里感受到沒,但我在康定,在318國道上,感受到這個社會正經歷著這樣一種變化——從趨同化到多元包容再到簡單的生活狀態。”
十多年背包生涯,登巴大叔看到了318國道上發生的改變——“十年前騎行318國道還是非主流,總是遭到家人反對,五年前家人開始默認了,到現在318國道上出現了父母帶著孩子騎行的。”
2005年,登巴大叔第一次徒步搭車到拉薩,在布達拉宮前流下了激動的淚水。“后來我每年都去,每次行走都能遇見不同的人,聽到不同的故事,對自己有不同的認識。”在318國道上,登巴大叔見到了72歲的老人,見到了高中輟學沿著318國道流浪到尼泊爾的17歲小姑娘,見到了在暴雨中堅持推車15公里而不愿搭車的五位車手,“我到現在都沒買車,今后也不會買,我搭車是為了與更多陌生人溝通交流。”
登巴大叔認為,318國道在改變中國,不管是騎行、搭車還是徒步,這些人最大的特點選擇了互相信任、包容,還有最核心的——簡單的狀態。
詩和遠方的家
從2010年起,登巴大叔開始連載《登巴客棧的故事》,最近一篇的標題是《詩和遠方的家》,寫詩是登巴大叔的愛好,而遠方的家,指的便是登巴客棧。
在甘孜徒步多年,登巴大叔在路上認識很多朋友,每次路過康定,朋友們都會叫他幫忙訂房,“2006年,偶然一次聊天,朋友說我經常幫忙訂房,干脆開個客棧好了。”于是,在康定的一間小木屋里,登巴客棧誕生了。
從此,登巴客棧在318國道上遍地開花,瀘定、丹巴、新都橋、日喀則、拉薩……今年還開到了首爾和清邁。我問登巴大叔有沒有什么成功秘訣,他只是說受到了很多人幫助。
之所以得到幫助,是因為這些人認同登巴客棧的價值觀——在《詩和遠方的家》,登巴大叔寫道“陽光、音樂、饅頭、書籍,這一切都平分給大家,沒有了高低貴賤之分”——這不就是家的感覺嗎?登巴大叔告訴我,在登巴客棧十周年,他會離開,對于我的驚詫,他苦笑道:“現在我的生活越來越被登巴客棧包裹了。”
“離開之后,你會做什么?”
“寫詩,繼續徒步旅行。”
遠方,是我們內心的憧憬和努力的方向——登巴大叔《詩和遠方的家》。
只要遠方還在,就不會有最后的318國道。
他們眼中的318國道
登巴客棧創始人 登巴大叔
Q:提到318國道,你最先聯想到哪三個詞語?
A:險峻,故事,風景
Q:對于318國道修路,你怎么看?
A:對背包客來說多少有些遺憾,但能讓更多人走進它,感受它,這種改善是件好事。
Q:路修好了,你還會上318國道嗎?
A:會,并且我們還可以選擇去318國道旁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