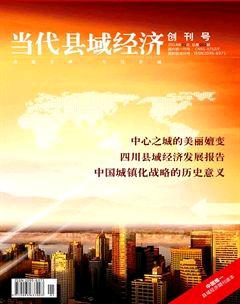讓農民的財產成為能下蛋的母雞
【人物名片】
鄭風田,經濟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副院長。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科基金同行評審專家,財政部、教育部、科技部、商務部、農業部等部委項目評審專家。主要研究領域:"三農問題",食品安全,農村產業集群與創業、企業與環境關系等。
單就土地而言,目前我國農民擁有的建設用地與所有城市建設面積相當,都是2.5億畝。每年的全國財富榜上多次出現城市地產商的名字,而大都市的普通居民因為擁有幾套房子也成了過去做夢都不敢想象的百萬、千萬富翁,城市的土地成為能下金蛋的母雞,給城市居民帶來巨量的財富。而擁有同樣面積土地的農民其年收入剛過6千元,每年土地給農民帶來的財產性收入不足3%,2.5億畝的農村土地成為一個不會下蛋的母雞。不過,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把束縛在這只母雞身上的諸多枷鎖卸掉。如果制度設計得當,未來這只巨大的母雞也能給農民兄弟下出諸多金蛋來。
政策紅利之一:
5000萬畝的農村建設用地直接入市
《決定》規定,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縮小征地范圍,規范征地程序,完善對被征地農民合理、規范、多元保障機制。
過去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既不能抵押,也難以進入市場進行交易。而城市土地沒有多少限制而身價百倍,同權不同利現象嚴重。不少地產商買到土地后,拿土地作抵押獲得資金,既可以建設商業設施獲得收益,也可以建工廠進行產品生產。雖然早在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上,中央就提出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但5年過去了,基本上原地踏步。原因很簡單,目前的征地是壟斷制度,農村土地要想搞建設就必須征地,地方政府低價拿地高價賣出獲得土地財政,農地直接入市首先會動了地方政府的奶酪,如果沒有上級的統一布置,單純靠地方政府推動會很難。所以,必須出臺中央層面更具體的操作規則,才能讓政策紅利落地。另外,目前的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界定也是不清楚,要防止各個上級以集體領導的名義把農村建設用地低價拿出,成為變相的征地。應該建立透明的制度,讓農民有參與權與表決權,讓農民以土地入股,保證土地增值收入中農民的利益。
政策紅利之二:
18億畝承包地的抵押、入股、轉讓權
《決定》規定,賦予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
這次把耕地的抵押權終于給了農民,是個了不起的進展。通過確權頒證,我國目前已為進一步放開三權(處置權、抵押權和轉讓權)奠定了基礎。全國18億畝耕地的抵押權很重要。我國城鎮居民靠房產證抵押可以很容易得到貸款。最近看一篇經濟學頂級期刊發表的論文,研究結論是1993年中國城里的房改政策讓城市居民獲得了房屋產權證。緊接而來的效果就是城市創業的迅猛發展,居民可以用房產抵押得到的資金來創業。遺憾的是,我國目前的相關法律卻不允許農民用承包地來進行抵押貸款,農民由于沒有可低押的物品,也使現代金融無法流向農村。我國一些地方已經試點,效果很不錯。例如吉林等地探索設立物權公司,通過制度創新來規避法律限制,讓農民用土地承包證獲得貸款。如果每畝地每年獲得3萬元的貸款,全國18億畝耕地,每年就有54萬億的資金進入農村,這該是多大的一股新鮮血液啊。雖然目前中央財政每年投入到農村近萬億元,與54萬億相比,還只是杯水車薪。
入股權、轉讓權也很重要。以轉讓權為例,目前,全國有2.6億農民外出打工,農民如果把自己承包的耕地出租轉讓,既可以獲得收益,避免拋荒,讓寶貴的土地得到有效的利用,也為留守在農村的農民擴大土地規模經營提供了條件。構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服務,家庭農場、種糧大戶、養殖大戶、專業合作社的規模經營擴大,其實都離不開農民承包地的轉讓權。
承包土地抵押權雖然農民獲得了,但是否有足夠多的金融機構愿意下鄉,則是農民能否獲得收益的最大障礙。另外,對農民土地承包權究竟該如何評估,如何保證農民把投資用好,如果降低投資風險等等,都需要相應的配套制度。
政策紅利之三:
2億畝宅基地試點抵押、退出、轉讓權
《決定》指出,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保障農戶宅基地用益物權,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選擇若干試點,慎重穩妥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探索農民增加財產性收入渠道。建立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推動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公開、公正、規范運行。
全國有2億多農戶,每戶農民都在農村有宅基地,這樣算來,全國有近2億畝宅基。但這個宅基地既不可抵押,又不能退出,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兩只老鼠的理論折射出流動農民工的悲哀:農民工在農村老家的房子讓老鼠住,自己在城里打工卻只能住老鼠窩。城市房價遠超出大部分農民工的購買力,而老家的宅基地卻無法退出變現成資本。我國臺灣當年的城鎮化得益于農民把家鄉的土地與房屋買掉后可以在城里買到房子。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要試點建立農民宅基地的抵押、退出、轉讓機制,允許農民在其他農村獲得宅基地,這應該是一個大的制度創新。
如果允許農民宅基地可以抵押貸款,以此為支點,可以撬動我國農村的內需市場,從而換回國家整體經濟再快速增長30年。我國農村的農民一生中投資最大的一筆應該是住房,占他們一生投資的60%。如果農民可以用自己所建房子進行抵押貸款,靠月供來償還貸款,農村的內需也就可以撬動了,他可以每年能夠拿出一部分錢來干除了攢錢建房以外的事了。
總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的確確賦予農民足夠多的財產權利。如何用好用足這些權利,讓這些權利逐步成為會下蛋的母雞,切切實實給農民帶來益處,需要相應的配套,也需要中央層面的具體指導意見,以防止政策在基層懸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