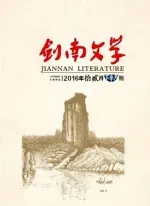從三部作品看新時期文學女性意識的發展
■崔菲菲
《愛,是不能忘記的》、“三戀”、《私人生活》清晰地體現了新時期女性意識的發展變化。它們強調性別的差異與對立,站在女性的立場上反對男性中心主義,抗拒父權制,可以說是非常好地體現了新時期女性文學女性意識發展的三個階段,顯示了女性文學中女性意識的復蘇到發展。
在《愛,是不能忘記的》之中,受制于當時的歷史條件,作者筆下的愛是深情而令人絕望的,只是因為鐘雨所愛的人是有婦之夫,雖然他們之間沒有愛情,但是鐘雨卻固執地認為自己與他不能結合。傳統的道德告誡她不能破壞另一個女人的家庭,更不能毀掉老干部的聲望和名譽。因此鐘雨一直孤獨地封閉自己,竭力掩飾那個被愛情焦灼的、痛苦的心。她苦苦地想忘掉他,她竭力地躲避著他,她總是害怕,怕把持不住自己,會說出那可怕的、折磨了她多年的三個字 “我愛你”。她躲進自己所營造的心靈的牢籠中。其實,她是陷進了傳統男權編織的道德網羅之中,在這一方面,張潔的反抗意識并不自覺。
王安憶筆下的“三戀”,對男權社會的反抗更多地表現在對男權社會下舊道德原則的反抗。在男權中心社會中,社會規則是男人們制定的,是服從男人的利益和要求的,而這些規則有時對于女性來說卻是不公平的壓迫和捆綁。男人們可以“三妻四妾”,而女性卻要遵從“三從四德”。在“三戀”中,女性主人公卻通通沖出了傳統男權社會所設定的道德羅網。《荒山之戀》中金谷巷的女孩小小年紀便讓男孩子們又愛又恨,欲罷不能,不同于才子佳人小說中的書生負心的橋段,金谷巷的女兒才是愛情中真正的掌舵者。而她對于有婦之夫“假戲真做”,更是不能被世俗和倫理所容的。《小城之戀》中的她盡管只有十幾歲的年齡,卻順從自己的身體欲望,偷嘗禁果……到了《錦繡谷之戀》,平淡的生活和不甘平淡的心都給她提供了出軌的契機,終于,一次外出讓她在自我的體內完成了對于傳統道德規范的摒棄與超越。
王安憶在這幾個文本中可以說是一種“超道德寫作”,這種超道德的寫作,表現在不用傳統的倫理道德來審視評價其筆下的女性。不同于《愛是不能忘記的》中的鐘雨,在情愛與道德的邊緣痛苦躊躇,王安憶有意忽略掉”婚外情”、“第三者”、“出軌”等道德界限。她要表現的,更多的是對自由情愛乃至性愛的追求,對固有道德規范進行超越。
在《私人生活》之中,陳染對父權社會的反抗來得直接而猛烈,倪拗拗的成長過程便是與父親所代表的“男權話語中心”不斷抗爭的過程。在小說中,父親一開始就是作為被排斥的對象登場的:“他是一個傲慢且專橫的不很得志的官員,多年來他一直受著抑制和排擠,這更加劇了他的狂妄、煩躁與神經質。”他左右家庭的心情,驅趕年邁的保姆,他讓母親流淚傷心。因此,對于父親,“我”厭惡,仇恨,甚至產生了弒父的心理。作者假借幻覺和夢境的描寫,完成了對父親的排斥與驅逐:“一眨眼的工夫,那輛小汽車就變成了一輛氣喘吁吁的警車,我父親一晃,就成了一個身穿褐色囚衣的囚犯,他的手腳都被鐐銬緊緊束縛著,他正在用他的犟脾氣拼命掙脫,可是他依然被那輛警車拉走了。拉到一個永遠也不能回家的地方去了……”當父親驅趕奶奶時,“我”發誓:“等我長大了,……我要報仇!”總之,陳染的小說《私人生活》是一種女性意識的另類書寫,小說中的“我”以女性的目光審視外部世界,寫出了在男權社會中,“我”不甘于被男性統治,大膽地向男性挑戰,顛覆父性權威的反抗。
美國的伊萊恩肖瓦爾特曾說過:“婦女的小說總是不得不對那些使婦女的經驗降到次要地位的文化和歷史的勢力作斗爭。”通過對新時期以來以上具有代表性意義的女性小說發展過程的梳理,我們看到女性意識在與男權社會的博弈中愈走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