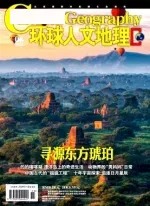關于使鹿鄂溫克族生態移民與文化變遷的綜述研究
梁雪萍
(吉林農業大學,吉林 長春 130118)
一、關于使鹿鄂溫克族歷史發展脈絡與民族傳統文化的研究
1859年,清代學者何秋濤在沙俄入侵之際潛心研究實時務,在其所著80卷本《北檄匯編》中的《索倫諸部內屬述略》記述了明清之際索倫諸部的分布及清初的經營和統一,介紹了鄂溫克人的民族源流及遷徙過程,是較早研究我國索倫諸部以及使鹿鄂溫克族歷史地理的代表性著作。
新中國成立后出版的《內蒙古自治區額爾古納旗使用馴鹿的鄂溫克人的社會情況》、《鄂溫克人的原始社會形態》等著作對當時該民族原始而艱苦的生活現狀進行了詳細的描述。秋浦(1961)清楚的描述了原始社會晚期的生產生活方式:“每個家庭公社之內都分成若干個小家庭。鄂溫克人把家庭公社這樣的家庭組織稱之為‘烏力楞’,‘烏力楞’是以一些有血緣關系的人們所組成的,并且全體成員在一起勞動,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生活資料則按戶來平均分配。這種家庭公社是鄂溫克人生產、消費的單位”。
20世紀80年代以后,呂光天(1981)、孔繁志(1994)、烏熱爾圖(1995)、等學者出版了一系列分析使鹿鄂溫克民族社會、歷史、文化、生活的研究性著作,對使鹿鄂溫克人的起源背景、歷史發展脈絡、文化歷史根基及其特點、社會形態、游獵生產方式和社會變遷歷程等都做了較全面的論述,對研究使鹿鄂溫克族的歷史脈絡和社會發展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除了悠久的歷史之外,使鹿鄂溫克民族還擁有馴鹿文化、薩滿文化、樺樹皮文化、狩獵文化、獸皮文化等豐富的傳統文化,這些寶貴的傳統文化與獵民的生產生活息息相關,密不可分。但由于長期生活在原始森林里,與其他民族交往較少,對外界保持著神秘感,直到20世紀80年代,隨著學者們的廣泛關注和一批有價值的學術著作的發表,該民族的傳統文化才逐漸揭開神秘的面紗,被外界所了解。卡麗娜(2006)從宏觀的角度闡述了該民族文化整體性、地域性、民族性、傳承性、變異性等特點,依據文化人類學與民族文化學的理論視角提出了關于文化發展的思考,包括盡可能整地記錄那些即將消亡的民族文化事象,開設傳統文化和技能課程,實施馴鹿業的科學化改造,合理科學的劃定馴鹿飼養牧場,開發民族鄉的旅游資源等。還有一些學者從微觀的角度對不同文化進行了具體研究,比如任國英(1994)闡述了馴鹿鄂溫克人是一種以馴鹿文化為其“文化核心”的文化系統,分析了鄂溫克族馴鹿文化在社會變遷的進程中出現的困境和問題,并提出建立馴鹿生態保護區以及協調自然生態使用權的建議;杜·道爾基(2002)和汪立珍(2002)介紹了鄂溫克人信仰薩滿的根源、薩滿法術儀式過程以及與薩滿有關的神話故事,薩滿文化也是使鹿鄂溫克族的精神追求和情感寄托,曾經一度代替法律成為處理氏族內部事務的準則;卡麗娜(2004)詳細介紹了樺樹皮制品的種類、使用價值及其特征;陳柏霖(1999)指出鄂溫克族的傳統狩獵方式是其對長期狩獵生產實踐的科學總結,也是一種文化積累,從中可以看出鄂溫克族覓食方式和謀生手段的不斷提高,充分顯示出鄂溫克人的聰明才智,也從中可以窺視出原始人類的生存狀況和文化形態。
二、關于少數民族生態移民與文化變遷的研究
在生態移民的過程中,由于與其他民族的接觸而引起自然生活環境的變化及社會文化環境的變化,正是文化變遷的外部原因,因此,從生態移民的背景出發來研究少數民族的文化模式與形態的變遷以及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是很有必要的。社會學學者李培林(2013)指出:從世界范圍看,很多國家以政府主導的移民工程來實施移民,通過對遷入地的科學選擇和規劃,生產生活設施的精心設計和建設,移民社區的有效組織和安置,使移民工程具有穩定發展的可能。而在政府主導的移民工程中,人們又進一步劃分了因生態環境惡化而進行的移民和以生態環境保護為目的而進行的移民,從嚴格意義上講,后者被稱為生態移民。該著作是在實地調查與案例分析的基礎上,對寧夏生態移民工程這一世界移民史上成功的經典案例進行全面考察和評估,指出標準化的安置方式難以滿足移民的差異化需求,在移民的過程中充滿了利益沖突和博弈,很容易引起社會矛盾,而生態移民工程的評估,其成果最終還要看移民滿意不滿意。同時李培林認為移民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文化素質與移民社會發展一般呈正相關關系,重視文化建設,增進文化認同和社會融合是寧夏生態移民建設的重要舉措之一。要使移民社會穩定,就不能就移民問題談移民問題,要系統的考察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各方面的問題。荀麗麗(2012)強調國家自上而下的“現代化規劃”始終包含著對草原生態秩序和社會秩序的“病理化的診斷”,自然之“失序”與社會之“失序”是相互建構的,她致力于回歸文化多樣性的觀照和社區集體規范與認同的再創造,認為這是實現生態脆弱地區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在關于敖魯古雅使鹿鄂溫克生態移民的文化傳承的發展方式存在兩種不同觀點的交鋒:內蒙古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長白蘭認為:“鄂溫克的狩獵、馴鹿文化沒有和其他文化碰撞和融合的機會,她要么生,要么就是死。”“所有的一切給予了敖魯古雅使鹿鄂溫克一種外力的干預,所以這個文化將不可避免地有她的硬傷。”而根河市人大副主任、敖魯古雅鄂溫克文化研究學者孔繁志則堅持另一種觀點:“只有生命得到保證,文化才能得到傳承。總不能因為要保留傳統文化而讓一個民族永遠生活在一個社會形態中。”余吉玲(2009)的觀點與孔繁志相似,她認為文化的變遷引起文化的適應,也必然引起一部分傳統文化的流失,引起部分民族心理的失落,而文化也是在適應、互動、調試、交融、碰撞中前進的。謝元媛(2005,2011)則持一種折中的理性態度,對生態移民后敖鄉面臨的生產生活困境和文化選擇壓力以及經濟發展困境進行了持續的關注,指出文明的責任更多地體現在對有限資源使用的權力分配上,意味著理性感召而不是標簽化處理,意味著人文關懷而不是簡單的“一刀切”,從而化解不必要的沖突。
三、國外學者的相關研究
就國外而言,研究我國使鹿鄂溫克民族以及少數民族生態移民的資料并不多。俄國著名民族學家、人類學家C.M.希羅科戈洛夫(中文名史祿國,1984)通過在后貝加爾和我國東北地區田野調查搜集了豐富的材料,他將我國大小興安嶺的鄂溫克族和鄂倫春族通稱為北方通古斯,將使鹿鄂溫克民族成為滿洲馴鹿通古斯,用較大篇幅闡述了通古斯家庭的形成、機能及其發展變化,對氏族制度進行了比較詳細的研究并對氏族名稱的含義以及親屬稱謂問題作了記錄,論述了該民族和鄰族的關系以及內部集團之間的關系,值得我們在研究我國的鄂溫克族和鄂倫春族社會歷史時當作參考。
美國學者凱若琳·漢弗瑞(Caroline Humphrey)與戴維·史尼斯(David Sneath)(1999)致力于剔除對草原畜牧非定居的種種偏見和刻板印象,通過對中亞地區的俄羅斯、蒙古、中國三個國家的草原生態區的比較研究,分析了草原移民定居對環境和地方文化的影響,作者認為盡管牧民渴望著城鎮化的現代生活,但城鄉一體化過程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同時,與草原生態特點相契合的地方文化的衰微與環境的惡化密切相關,一方面是地方知識精英在積極地致力于文化復蘇,另一方面是新的外來文化價值觀的沖擊,這些都是移民定居所要面對的問題。
小結:綜上所述,對于使鹿鄂溫克民族的研究,古代史料提及的只有點滴,近代僅僅了解了該民族的生活生產狀況和衣食住行情況,現代學者的調查和研究取得比較突出的成果。但國內外學者對敖魯古雅使鹿鄂溫克民族的研究,更多是從民族學和人類學的視角出發,多側重于歷史、族源、生活生產方式、民族傳統文化和風俗習慣等社會歷史發展和社會文化形態的研究。生態移民后,很多學者注重生產生活方式變遷、人口發展、民族融合、民族文化特點、社會發展困境的研究,致力于探尋出一條符合該民族實際情況的社會發展模式,也有一些學者分析了生態移民過程中傳統文化的流失以及文化變遷的表現。
以上查閱的文獻資料有很多可借鑒之處,但是關于文化變遷的研究中,很少有將其放入生態移民這個特殊社會變遷歷程中進行考察,缺少從移民規劃與現實需求脫節的現狀和生態移民后再社會化的要求出發闡述文化模式的變遷以及文化困境的表現。
隨著生態移民工程的順利開展,敖魯古雅使鹿鄂溫克民族的生產水平和生活環境得到充分改善,但這次生態移民也使民族傳統文化模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獵民與外界交流日益增多,其他民族的生活習慣和民族風俗大量涌入,產生文化震驚和文化墮距;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逐漸代替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本民族傳統文化模式中的語言、飲食、民族服飾、交通工具等面臨著被同化的危機;本民族內部代際間也發生了分歧,兩代獵民的生活態度存在顯著差異,年輕獵民愿意到城里生活、學習,而老一輩的獵民則對下山后的生活感到失落和不適應;民族風俗和信仰也正面臨著消亡的危機,如樺樹皮船的制作技藝在失傳,馴鹿不再作為主要的交通工具而是供游客欣賞,薩滿教隨著敖魯古雅鄂溫克最后一個薩滿妞拉的去世而失傳,越來越多的年輕鄂溫克人不會說本民族語言等等。這些文化困境與生態移民這個特殊的社會變遷背景是密不可分的,對此進行深入的分析并找到符合該民族實際情況的文化傳承的可持續發展道路是必要且緊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