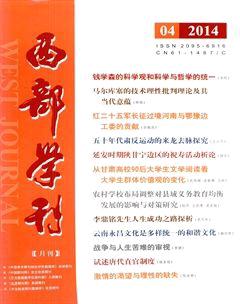激情的渴望與理性的缺失
摘要:《包法利夫人》描述了平民女子愛瑪一味地追求激情、浪漫的情感生活而最后身敗名裂、服毒自殺的悲劇。本文作者分析了包法利夫人的悲劇認為:艾瑪追求激情的滿足并沒有錯,錯就錯在她為達目的置理性與不顧,暫時的缺失理性的滿足,換來的卻是理性永恒的懲罰,最后只得以付出生命為代價。文章認為:“包法利夫人既不是一個壞女人,也不是一個圣潔的女人,她是一個現實生活中的女人。”作品告訴人們,生活中不能沒有激情,也不能沒有理性,二者不可排斥,不可缺失。
關鍵字:《包法利夫人》;悲劇;激情;理性
中圖分類號:I106.4
一、包法利夫人的悲劇
《包法利夫人》是一部不同尋常的小說,寫一個女子“紅杏出墻”的老套故事,但卻能不落俗套,以至于每一部談論法國文學的著作都會提及。它引起了法國正統文學觀念的強烈反彈,被認為是一部不道德的書,宣傳墮落,有誨淫之嫌。包法利夫人作為已婚女子、有夫之婦,她的悲劇是不顧家庭和情人私通,最后聲名狼藉、債臺高筑,無奈之下自殺身亡。
我們統觀包法利夫人的一生,不難發現,愛瑪的悲劇是注定的,從女兒時的漫天幻想,到嫁給了穩如磐石的丈夫,再到為了釋放炎炎欲火而產生的兩次婚外情,一步一步陷入絕望的深淵。
我們先看包法利夫人尚未出閣之前,對“歡愉、熱情、迷戀這些字眼”充滿癡迷,“她覺得那樣美”,“她狂熱而又實際,愛教堂為了教堂的花卉,愛音樂為了歌的詞句,愛文學為了文學的熱情刺激,她反抗信仰的神秘,院規同她的性格格格不入……”[1]像愛瑪這樣一個渴望刺激與激情的女子,若能如愿以償的嫁給一位“騎黑馬的白羽騎士”,悲劇或許不會發生。造化弄人,充滿激情的愛瑪,偏偏嫁給了毫無激情的查爾·包法利。“談吐竟像人行道一樣平板,見解庸俗,如同來往行人一般,衣著平常,激不起笑或者夢想”。[1]愛瑪巴望著浪漫的愛情“活像廚房桌子上一條鯉魚巴望水”[1],“她以為愛情應當驟然來臨,電光閃閃,雷聲隆隆顛覆生命,席卷意志”[1],欲火灼燒著愛瑪。庸俗的包法利,滿足不了愛瑪情感欲求,為此她陷入了婚外情之中。為了約會打扮自己她揮霍著丈夫的微薄收入;為了送給情人禮物,她不惜借高利貸,愛瑪甚至準備與羅道爾夫私奔。一個被愛情沖昏頭腦的女人,孤注一擲地追逐著轟轟烈烈的愛情,而最后卻被情人拋棄、高利貸商人逼迫,萬般無奈選擇自殺。
由此可見,包法利夫人的悲劇是一個人渴望激情、追逐激情、不顧一切滿足激情而導致的悲劇。
二、分析包法利夫人悲劇的原因:人性中情與理的沖突
每一場悲劇的發生都有多種多樣的原因,包法利夫人的悲劇原因也復雜多樣,我們僅從人性化中情與理的沖突角度進行探究。
所謂人性,從西方文化對“人”的認識來看:認為人性內涵中包括物質方面的欲望,和情感或精神方面的欲望,人對激情的渴望屬于情感或精神需求。理性是人的本質屬性,是人之所以為人而有別于普通動物的根本所在,“唯有以理性的目的為目的的活動才是真正完全屬于人的活動,理性的目的構成了人自身存在的真正意義和目的。”[2]39通俗講理性是指從理智上控制行為的能力,它把握人生的方向與平衡。理性既內指為人的理智,又外化為社會的各種規范,倫理、道德、風俗、習慣、法律、宗教等無不是理性的外化。
首先,激情和理性的關系。史鐵生承認有個問題他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人生應該更崇尚理性還是更尊重激情?”“沒有激情人原地不動成了泥胎,連理性也無法發展;喪失理性,人滿山遍野地跑成獸類,連激情的美妙也不能發現、不能享受了”。[3]激情是一種強烈而激動的情感,激情往往可以作為一個人前進的動力,而理性則是把握前進的方向,使其不至于偏差。激情需要理性的約束與指引,但如果只有理性,缺少了激情,那人生只剩條條框框、枯燥乏味,所以激情又是人生所需要的因素。包法利夫人正是因為激情與理性的天平失去平衡,才換來了自我了結的悲劇。
其次,激情和理性的博弈。激情與理性是人性中必不可少的兩個方面,忽視其中任何一方都會造成悲劇。愛瑪不滿足平庸的生活,一直期待意外的發生,干涸的情感世界,渴望激情的填充,婚外情便“理所當然”地發生了。
在與羅道爾夫的婚外情中,對激情的渴望得到了滿足。她精神煥發“像服過什么仙方一樣,人變美了……開始自言自語,一想到自己有一個情人,就心花怒放好像剎那間返老還童了一樣”[1]。愛瑪盡情享受這種樂趣,完全失去了理智。她不顧丈夫的發覺,大膽與羅道爾夫相會;為了長久在一起,甚至拋棄父親、丈夫、女兒,精心籌備私奔,遠走天涯。在愛瑪的精神中,只有情感在跳動,思維、理智、責任統統拋開。欲望瘋狂地燃燒,激情永無休止地釋放,墮落的步伐也越來越快。如果說在與羅道爾夫的婚外情中包法利夫人只是為了滿足饑渴的感情,那么與萊昂的婚外情就是她徹底拋棄一切、肆無忌憚地自我放縱。剛開始“她怕人看見,一般不走近的路”,后來,“她和他在街上散步,仰起頭來,不怕出事”甚至直接跑到律師所去找萊昂;為了包裹她的愛情,愛瑪一連串說謊;有時偷情達到歡愉,愛瑪徹夜不歸;“衣服,說脫就脫……一看門關好了,一下把衣服脫得一絲不掛……”[1]包法利夫人為了維持奢靡的生活,為了送給情人禮物,她不停地賒購;為了還錢她揮霍掉包法利微薄的積蓄,繼而寫信向病人索要診費,變賣田莊家產。一切可以想到的辦法,她都在瘋狂地使用。約會、肆意賒賬、盡情揮霍這些毫無理智的舉動為她的悲劇埋下了種子。
包法利夫人的激情達到了巔峰,而理性處于永恒的缺失狀態。在她縱情于欲望時,她的理性是空白的,生不出愧疚與反思。在激情與理性的博弈中,激情完全壓倒了理性,包法利夫人肆無忌憚地追求激情的生活,她被激情燃燒到瘋癲,完全失去了理智。只求激情的滿足,而缺失了理性節制,這是包法利夫人悲劇的主要原因。
最后,激情與社會規范的沖突。除了自身的情與理的矛盾外,人還要受社會規范的制約,而所謂社會規范,恰恰是外化的理性。它包括倫理、道德、風俗、習慣、法律、宗教等,每一個人都要受到外化理性的約束。當自身行為尚處于理的容納下,我們既是自由的,又合乎理性規范,而一旦超越了這個范圍,則悲從中來。包法利夫人的悲劇就是為了激情的滿足而無視社會規范的結果。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為追求激情生活,不顧忌社會輿論。包法利夫人的偷情幾近瘋狂,她“縱情聲色、積習難返肆無忌憚,言語也更放肆;她甚至甘冒不韙與羅道爾夫一起散步口噙香煙,旁若無人”;在與萊昂的相處中,只要她想見到他,便直接奔到萊昂的事務所,毫不顧忌社會輿論的批評。
第二,為了滿足自己的情感需要,不顧念人倫和親情。在家庭關系中,愛瑪對丈夫是責備、厭煩、嘲笑與譏諷。愛瑪看他越來越有氣,“世上會有這種人!會有這種人!”,反感至極,何談夫妻間相濡以沫、相敬如賓;對女兒也是愛搭不理,缺乏一個母親應該有的關愛;與婆婆關系更是劍拔弩張,大吵大鬧,讓婆婆“滾出去”,愛瑪沖撞了家庭倫理觀念中孝、親、婦道等信條,苦果終是自己吞下。
第三,偷情通奸、婚外生活與社會習俗、觀念格格不入 。愛瑪愿捐棄一切來換取一次約會,社會習俗不允許這種態勢繼續發展。鄰人給萊昂的母親寫信,警告她,“他與一位有夫之婦相好,前途堪憂”;老太太眼前影影綽綽出現一位敗家精,立刻斥責萊昂,并求助于他的老板杜包卡吉律師,希望他懸崖勒馬,認清這種曖昧行為將給事業帶來的損害。偷情、通奸這些字眼,勢必影響一個男人的前途,因此必須斬斷;而偷情的女子,則是敗壞名聲勾引他人的丑惡女人。情感世界里愛瑪全力以赴,但改變不了業已形成的社會習俗觀念,一旦二者沖突達到頂峰,悲劇的結局就到了。
第四,欠債不還受到法律的追究。為了維持體面的約會,愛瑪不惜傾其所有買衣服飾品、租旅館、贈送情人禮物,這種奢侈的生活,大大超出了丈夫的支付能力。為此她賣掉父親送的結婚禮物,典當掉祖傳的田地,借債揮霍達到頂峰,日積月累使她陷入勒樂的圈套欠下重金,無能力償還:欠債不還,受法律追究。
第五,縱欲偷情違背了宗教的信條,因而是一個有罪的女子。宗教主張禁欲,節制欲望,而愛瑪無休止地釋放欲望,觸犯了教條。包法利夫人與羅道爾夫決裂后,曾經試圖懺悔,“愿變成一位圣者,買念珠戴符咒,床頭掛一個圣骨匣,每天夜晚親吻”;當生命即將結束時,她看到了教士的紫飄帶,感到了無限平靜“好像懺悔儀式醫治好了她一樣”,畢生的罪過一洗而盡。即使是縱欲到毫無理性的愛瑪,也無不受宗教的約束。她沖撞了這些信條,受到了處罰。
家庭倫理規范、社會習俗觀念、法律、道德宗教等等,當我們行為在許可的范圍時,感覺不到壓抑束縛;而一旦觸及了底線,將無可避免受到懲處。
三、《包法利夫人》包孕的悲劇精神
悲劇是古希臘美學中的一個經典概念,由悲劇意識和悲劇精神組成。由人的“原欲”而造成的悲劇、悲劇精神是《包法利夫人》這部書所滿蘊的精神價值,而恰恰是濃郁的悲劇精神成為該書名傳后世、屹立于文學之林的重要因素之一。
當代歐美悲劇理論家柯列根認為:“悲劇精神不是叫人逆來順受無所作為,而是一種抓住不放棄斗爭到底的精神”。通俗地講是指建立在對現實中的悲劇性進行清醒把握的悲劇意識基礎上,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抗爭與超越精神,面對生命的極限情況時必須堅定地做出選擇,正是對災難的勇敢承擔而顯示出高貴的悲劇精神。所以俄狄浦斯王雖竭盡全力反抗命運的安排而最終難逃悲劇便包孕了濃郁的悲劇精神,而一個逆來順受不思進取的人如阿Q則無從論及悲劇精神。
原欲是精神分析學說創始人弗洛伊德于《性學三論》中提出的,特指無意識層面的性的原始驅動力,泛指人的性本能沖動,并且可以直接發泄和滿足,甚至以勢不可擋之勢席卷并戰勝理性,往往是明知觸犯規定、人倫,而一意孤行。如同《安娜·卡列尼娜》拋下丈夫與兒子飛蛾撲火般投入沃倫斯基懷抱,《哈姆雷特》其叔父殺兄娶嫂更是原欲控制下的無可自拔。
包法利夫人出于原欲即“里比多”的支配,通過追求“性”、“愛情”、“激情”“狂熱”丟棄了倫理、道德、宗教、理性的約束,由與羅道爾夫私會偷情再到明目張膽得和萊昂出出入入毫不避諱,直至自我了結,走完了其悲劇一生。
平心而論,愛瑪力求擺脫平庸的家庭生活遵循自由意志,進行自由選擇,追求有滋有味的愛戀本沒有錯,但忽視理性的約束成為悲劇的根源。人生本不完善但卻一心期待幸福完美,這種無束縛的激情與精神性的理想分道揚鑣,“欲”與“理”形成二律背反的沖突態勢,她以犧牲者的姿態向理性發出挑戰,并勇敢地承擔了屬于自己的悲劇、苦果,這份脫離正常軌道后盡情灑脫的傷痛最終以愛瑪的吞食砒霜自盡結束。
原欲與理性在愛瑪身上的沖突雖是個案但亦有共性,法國作家左拉的《戴蕾絲·拉甘》中孤女戴蕾絲、日本渡邊淳一筆下的凜子、中國古代的潘金蓮、現當代的鄧幺姑、繁漪無不是忍受“里比多”與“理性”的抗爭,并且無一例外地選擇原欲,挑戰理性權威力求激情的滿足,以或瘋或自殺而結束生命。她們抗爭命運但超越不了命運,雖貴為“萬物之靈長”在抗爭之后歸為悲劇,因而其悲劇精神也凸顯出來。
福樓拜懷著復雜的心情完成了《包法利夫人》的寫作,他既嚴厲地懲罰了愛瑪,又懷著憐憫之心來寫這個縱情縱欲的女子。正如他自己所說“我愿意理解你的痛苦,你的可憐的隱蔽心靈……”愛瑪追求“性”的滿足并沒有錯,錯就錯在為達到需求,置理性于不顧。縱使暫時地激情得到滿足,換來的卻是理性永恒的懲罰。愛瑪被圍困在婚姻的城堡里,始終逃脫不出,但圍不住那顆騷動不安的心。“包法利夫人既不是壞女人也不是圣潔的女人,而是一個現實生活中的女人”。[4]360
參考文獻:
[1]福樓拜.包法利夫人[M].李健吾,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
[2]王海明.人性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3]史鐵生.靈魂的事·私人大事排行榜[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
[4]李云峰.福樓拜的藝術視覺與道德氣質[C]//邊國恩.外國文學論文集.北京:文藝出版社,1985.
作者簡介:倪金艷(1984—),女,河北滄州人,青海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少數民族文學。
(責任編輯: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