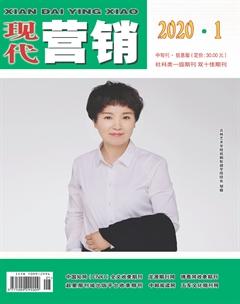鐵路基層干部心理健康素質提升策略探析
朱珠 閆肅
摘 ?要: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指出:“要真情關愛干部,幫助解決實際困難,關注身心健康,對基層干部要給予更多理解和支持。”當前,是中國鐵路實現三個“世界領先”和三大提升的最后沖刺年,完成這一艱巨任務,需要有一支意志堅定、精神向上、身體健康,能打持久戰的基層干部作為堅強保障。因此,在鐵路企業實施好健康戰略,提升基層干部的心理健康水平,是鐵路企業保證企業改革發展穩定的一項重要課題。
關鍵詞:心理健康;鐵路;基層干部
一、主動學習心理健康知識
在中央《關于加強心理健康服務的指導意見》的文件中指出:“倡導‘每個人是自己心理健康第一責任人的理念,引導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識地營造積極心態,預防不良心態,學會調適情緒困擾與心理壓力,積極自助。”由此可見,提升心理健康素養的關鍵在個人。每位基層干部都要認識到這一關鍵問題,不能將心理問題的原因推脫給單位、家人,更不能聽之任之,不作處理。
基層干部學習心理健康知識,首先要對什么是心理健康,有所認識了解,理解心理不健康不是有精神問題,更不是什么見不得人的“疾病”,它只是與身體不健康相對應的概念,是個體健康的組成部分。要認識到心理健康知識是一個系統、科學的知識體系。其次要學習保持心理健康的有效辦法,比如:心理教練技術、合理情緒療法、感恩訓練法、正念冥想法、腹式呼吸法、運動減壓法等。這些辦法可以有效降低基層管理者的焦慮情緒,緩解壓力,幫助其提升幸福感,更高效率地完成工作任務,而不是帶著情緒、帶著抱怨,帶著安全隱患進行每天的工作。
二、積極應用心理減壓工具
不同于哲學等社會科學,心理學雖然屬于社會科學分類,但是保持心理健康卻是一項“脖子以下的學問”。基層干部要想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就需要積極在工作生活中加以實踐。
一方面因為人們的思維習慣存在固化,需要刻意練習思考方式,調整行為習慣。比如:受到領導的批評時不要一味找理由推脫責任,而是采取建設性的行動;發現職工違章違紀時,不是一味責備,考核扣錢,而是幫助職工揪出違章違紀的心理根源,啟動努力工作的動力源;遇到難以解決的問題時,不會一直陷入消極懈怠的想法中,而是努力看到事物積極的一面,從各個方面尋求辦法。
另一方面根據行為強化原則,人們在采取一個行動后得到了希望的結果或者獎勵時,會再次重復這一行為,以便獲得獎勵。即只有通過堅持實踐心理減壓辦法,切實感受到減小自身壓力,提升工作能力、工作效率的效果后,才會更愿意堅持下去,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如果一直不去實踐這些辦法,知道而做不到,感受不到效果反饋,那么心理健康素養只能是停留在原有水平,無法得到提升。
三、積極維護社會支持系統
社會支持系統是個體通過與環境中人物的互動,所建立的一種關系網絡,個體能從中獲取情緒情感心理的支持,能夠緩解心理壓力,提高自身對環境的適應能力和對變化的應對能力。日常生活中的社會支持系統主要包括家人的支持、朋友的支持和單位同事的支持三個部分。
要使社會支持系統發揮提升心理健康素養的功能,就要積極維護這一系統。對待家人,要學會使用“愛的語言”經營夫妻關系、掌握孩子成長規律保持親密的親子關系;對待朋友,要真誠友善,不要以利益交換為前提;對待單位同事要互相尊重,不要媚上欺下、欺軟怕硬。沒有付出一味索取的關系是不存在的,只有不斷在情感賬戶中“存錢”,關鍵時刻才能從這一系統中“取錢”。遇到困難,出現焦慮情緒時,多與他們溝通交流,通過家人支持、朋友的幫助、同事關心渡過難關,解決問題。
四、用工企業協助健全機制
固然心理健康的第一責任人是本人,但是由于鐵路行業的特殊性,安全生產紅線不可觸碰,需要保證旅客運輸安全萬無一失,基層管理人員不僅要在白天工作8個小時,還要在周一至周日晚上輪流值班盯控生產維修,更要在法定節假日雙人雙崗,全天盯控作業,就算回到家中,手機也要保持暢通,24小時隨時待命,隨時接聽電話,不敢有絲毫松懈。這樣的工作性質使得企業制度建設的科學與否、人性與否,與基層管理人員的心理健康有密切的關系。
首先根據企業自身特點提供適合鐵路職工的EAP服務。《關于加強心理健康服務的指導意見》中指出:要在全社會建立健全心理健康服務體系,其中對企業的要求就是要設立心理健康輔導室,培養心理健康服務骨干隊伍,配備專(兼)職心理健康輔導人員。這些服務內容就是建設EAP服務中的重要部分。
其次優化基層領導工作權責劃分。各級組織的工作任務,工作落實最后幾乎都要由基層領導負責執行。這就意味著基層領導責任重大,但是從目前制度來看,他們既沒有選人用人權,也沒有獎金二次分配權,調動職工工作積極性的“兩大法寶”都處于失效狀態,這就給管理帶來了困難,加重了工作壓力。為此,上級組織要充分信任基層管理者工作能力,在選人用人和獎金分配方面給予一定的自由裁量權,更好地履行管理職責,減輕工作焦慮,提高幸福感。
再次建立科學獎懲機制。由于站段中的一些獎懲機制設置不科學,使得出現“多干多錯、少干少錯、不干不錯”的現象,這大大抑制了一些基層干部,尤其是年齡偏大的干部的工作熱情。為此,要科學設計獎懲機制,使基層管理者“多干多得、少干少得、不干不得”,激發工作熱情,提升工作動力,改善工作倦怠。
參考文獻:
[1]常秀芹.高校青年教師專業發展的社會支持系統構建與加強[J].高等農業教育,2012(06):3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