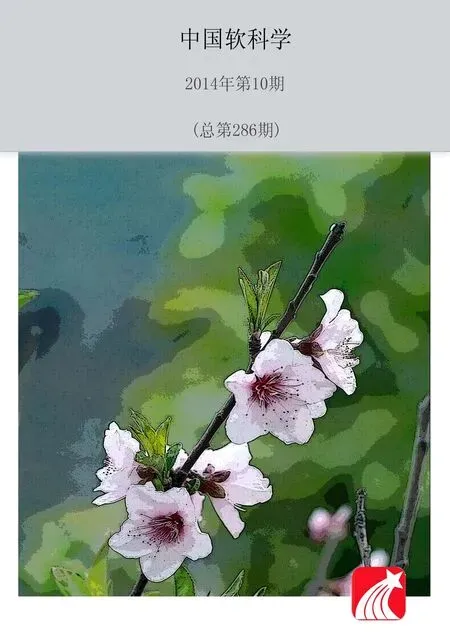協同創新網絡、法人資格與創新績效
——基于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的實證研究
林潤輝,謝宗曉,丘 東,周常寶
(1.南開大學 商學院,天津 300071;2.北京科技大學 東凌經濟管理學院,北京 100084)
一、問題提出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①中強調了“建立產學研協同創新機制”的重要性,并要持續推進“建設國家創新體系”。協同創新可以認為是協同理論和創新理論的結合應用[1]。Chesbrough在2003年明確提出“開放式創新”的概念,陳勁和陽銀娟[2]在深入分析協同創新和開放式創新的異同后,把協同制造與開放式創新一并列入協同創新的前范式,認為協同創新是一種更復雜的創新組織形式,是“通過國家意志的引導和機制安排,促進企業、大學、研究機構發揮各自的能力優勢、整合互補性資源,實現各方的優勢互補,加速技術推廣應用和產業化,協作開展產業技術創新和科技成果產業化活動,是當今科技創新的新范式(PP.162)”。 和開放式創新的本質不同是,開放式創新強調對外部參與者與資源的利用[3—6],協同創新則關注“協同效應”,通俗講就是“1+1+1>3”的非線性效應[7—8]。
我國的產學研協同創新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9],最具里程碑性質的事件是1993年國家科委公布的《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暫行管理辦法》,其中明確指出要“建立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探索科技與經濟結合的新途徑”,而這個載體就是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和美國的工程研究中心(ERCs)、澳大利亞的合作研究中心(CRCs)、新技術孵化器(start-ups incubator)以及科技園區(science park)等類似,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是協同創新的重要組織形式[10],也是“國家重大創新基地和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探索科技與經濟結合的新途徑,加強科技成果向生產力轉化的中心環節,提高科技成果的成熟性、配套性和工程化水平,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技術創新支撐”*引用自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信息網,http://www.cnerc.gov.cn/index/centers/index.aspx。。
本文以在協同創新網絡中處于主節點位置的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為研究對象,探討如下問題:(1)網絡規模對創新績效的影響;(2)網絡多樣性對創新績效的影響;(3)現有的管理機制,本研究中關注是否具有法人資格在協同創新網絡和創新績效的關系中的影響,即法人資格的調節效應。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協同創新網絡
通過協同創新的定義可知,協同的含義不是簡單的兩兩組合,而是一種網絡組織。一般認為,網絡組織能有效促進組織間協同創新。林潤輝等[11]在分析了166篇1973—2012年間的相關論文后甚至將網絡組織列入了協同創新的必要前提之一。協同創新網絡正成為在不確定性市場和技術條件下的戰略選擇,其不僅包括產業鏈上正式的產業和經濟網絡,還包括了社會網絡和企業家個人的關系網絡等非正式網絡[12]。
協同創新網絡主要從兩個方面促進創新績效:
(1)資源效應,協同創新網絡可以突破組織自身資源的限制,在這點上,與開放式創新存在相同之處。在開放式創新領域,Laursen和Salter[13]的實證研究得出更廣泛更深入的搜索外部資源的企業更具有創新性。企業為了獲取自身缺乏的資源或技能而產生的協同會提高其創新績效[14],Becker和Dietz[15]認為這相當于利用外部資源補充自身能力的不足,即“取長補短”,大量的研究都得到了類似的結論,例如:Miotti和Sachwald[16]以及Faems等[17]等。
(2)協同效應,協同創新網絡中節點之間的相互合作和相互摩擦所產生的增效效應。網絡合作有利于不同創新主體間的信息交流、技術知識的傳播、轉移和共享,從而加快知識的積累和能力的提升[11]。
下面主要從網絡規模和網絡多樣性兩個維度考察協同創新網絡對創新績效的影響,其中網絡規模強調網絡的資源效應,網絡多樣性強調網絡的協同效應。
(二)網絡規模對創新績效的影響:資源效應視角
資源依賴理論認為,維持組織的運行需要多種不同的資源,而這些不同資源不可能都由組織自己提供。作為開放系統視角的組織,與環境的交互不僅是創新的需求,更是生存需要[18—19],相關研究顯示協同網絡是獲取關鍵資源的重要途徑[20]。一般而言,更大的網絡規模會增加知識庫的大小,也增加了潛在的合作者,而合作者又意味著更多的知識資源。在快速變化的環境中,組織試圖擁有創新所需要的所有知識和能力既不現實,也不經濟[21]。
Cohen和Levinthal[22]首次將創新研究的吸收能力從個人層次上升為組織層次,認為一個企業如果能意識到外部信息的重要性并將其內化和應用在其商業活動中,對創新能力非常重要,這實際和個體認知的邏輯保持了一致。該觀點在Chesbrough[3]的開放式創新論述中變得更為清晰,即組織應該“利用更廣泛的外部參與者和資源來幫助其獲得和維持創新能力”。
資源依賴論認為組織環境并不僅是一個客觀存在,而是組織及其管理者通過自己的選擇和參與而產生出來的,是組織和環境交互作用的一系列過程的結果[18,23]。組織通過網絡獲取所需要的資源,同時也通過網絡轉移自身所能夠提供的資源,由此形成“共贏”的狀態,這個狀態強化了組織與網絡(組織環境的組成部分)的依賴關系。過度對外界環境的依賴將帶來相應的風險。Nieto和Santamaria[14]認為更大的協同網絡意味著更大的合作風險,這將考驗組織間的協調能力。
協同創新網絡的規模會促進組織的創新績效,這種積極作用隨著網絡的增加而增強,但是同時限于自身的網絡管理能力[24—25]和制度性因素等,超過該臨界點之后,這種積極作用會逐漸減弱直至成為負向作用,也就是說,協同創新網絡與創新績效之間呈現的關系不應該是線性的,而應該是一種“倒U型”關系。Vanhaverbeke[26]發現在網絡中直接聯系的數目與創新績效呈“倒U型”關系,而間接聯系的數目與創新績效則成正相關關系,這說明管理能力是有限的情況下,可能會面臨規模過度所導致的不經濟。綜上所述,提出假設1:
H1a:網絡規模與創新績效(專利)之間呈現倒U型關系。
H1b:網絡規模與創新績效(獲獎)之間呈現倒U型關系。
(三)網絡多樣性對創新績效的影響:協同效應視角
協同理論認為開放系統在與外界有物質或能量交換的情況下,通過自己內部協同作用,產生整體價值大于各部分之和的協同效應[1,27]。林潤輝等[11]認為在協同創新網絡內,主體間的聯系促進了創新要素在不同主體間的共享,進而實現創新要素的整合和互動,提升創新主體以及網絡整體的創新績效,從而實現了網絡的協同效應。
網絡多樣性也稱為異質性,是指協同創新網絡內節點的多樣化程度,在本研究中特指與研究中心有直接聯系的組織類型的多樣化程度。和網絡規模等表征網絡特征的指標類似,網絡多樣性被認為是影響創新績效的屬性之一[11]。多樣性能夠為企業提供更多的機會[28],與不同類型的類型組織,可以促進彼此的摩擦性創新。Powell等[29]研究證明網絡節點多樣性能夠有效促進網絡整體的創新性和適應性。Powell和Giannella[30]指出協同創新網絡內成員如果是處于不同地理位置的企業間的技術人員,相比于都是同一企業內的技術人員,更能夠提高網絡成員的多樣性,進而獲得更高的創新績效。劉志迎和單潔含[31]則在組織層次發現技術距離對大學和企業之間的協同創新績效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也就是說節點之間的技術異質性對創新績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Rodan和Galunic[32]的研究結論表明通過網絡去獲取異質性(多樣性)知識對于創新的影響比管理水平提高對創新績效的影響更大,這更說明了多樣化的重要性。
這些研究從不同的角度表明節點的多樣性有助于實現網絡的協同效應,此外,節點的同質性也會導致創新主體之間不能形成資源互補,從這個意義上講,資源效應和協同效應是相輔相成,互相依存的關系。
對網絡內的每個節點而言,選擇合適的協同對象至關重要,不同的協同對象會導致不同的結果,不同的協同對象可能導致不同的管理模式,帶來不同的資源,伴隨著不同的風險[33]。例如,Zeng 等[34]發現中小企業與其他企業、中介組織、政府機構以及研究機構之間的協同,企業間協同對創新績效的影響最顯著,與政府協同則影響不顯著。Powell等[29]認為與其他組織共享資源決定于權衡協同所帶來的風險與預期的結果。網絡多樣化程度太高,會導致資源的復雜性與過高的管理成本,同時伴隨的風險也會加大,因此網絡多樣化與創新績效的關系應該是“倒U型”,Duysters和Lokshin[35]和Lin[36]等的實證研究都驗證了這個結論。基于此,提出假設2:
H2a:網絡多樣性與創新績效(專利)之間呈現倒U型關系。
H2b:網絡多樣性與創新績效(獲獎)之間呈現倒U型關系。
(四)法人資格的調節效應
《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暫行管理辦法》中規定研究中心的經費“國家撥款、銀行貸款、主管部門或依托單位自籌各1/3”,在隸屬關系上“研究中心與依托單位、上級主管部門的隸屬關系不變。經濟上實行獨立核算,獨立帳戶,可與依托單位共有一個法人代表”。在訪談中,對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的這種制度設計存在完全不同的兩種態度,例如:(1)中心不具備獨立法人資格,我們的依托單位也不具備法人資格,在運行體制和機制上存在很大制約,例如,我們想與國外研究機構建立研發中心,最后就不了了之了。(2)根據《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現代農作物種業發展的意見》,事業單位面臨從教學科研單位剝離的困境,面臨很大的挑戰。
實際上這是許多研究機構所面臨的共同問題,獨立法人單位依法享有法人權利,履行法人義務,非法人單位則沒有法人單位所具有的權利和義務。獨立法人單位可能有更大的自主權,更容易與其他組織建立合作關系明確的協同研發中心,但是同時面臨更大的競爭和風險,從創新的資源依賴角度而言,有依托單位的組織會獲取更多的資源,可以共享更大的協同創新網絡,而不需要額外的網絡選擇和管理能力。因此,提出假設3。
H3a:法人資格在網絡規模與創新績效(專利)的關系中起調節作用。
H3b:法人資格在網絡規模與創新績效(獲獎)的關系中起調節作用。
H3c:法人資格在網絡多樣性與創新績效(專利)的關系中起調節作用。
H3d:法人資格在網絡多樣性與創新績效(獲獎)的關系中起調節作用。
(五)本文的研究模型
因此,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研究模型
三、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的分析數據為2007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的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的運行數據,來源主要為:(1)訪談數據,研究者訪談了63家研究中心,積累了約300小時的現場訪談資料,整理出近70萬字的訪談記錄;(2)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信息網(http://www.cnerc.gov.cn/)所公布的數據;(3)科技部科技評估中心網站(http://www.ncste.org/);(4)各研究中心及其主管部門的官方網站。
以下數據源主要用來校對因變量:(5)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工作辦公室官方網站,關于科學技術獎勵的統計數據(http://www.nosta.gov.cn);(6)國家知識產權局官方網站,關于專利統計的信息(http://www.sipo.gov.cn/tjxx/);(7)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檢索數據庫(http://www.sipo.gov.cn/zljs/)。
截至2010年底,共有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264家,包含分中心在內為277家。其中108(12+27+36+33)家是2007—2010這4年之間成立,而數據以4年為一個周期,因此這期間成立的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數據不全,還剩169個樣本,另有40家因各種原因數據缺失,能計入分析的共129家,表1為樣本的統計特征。
(二)變量及其測量
1.因變量
本研究中對創新績效的測度采取兩個指標:專利分數和獲獎分數。
用專利或知識產權作為創新績效的測量是已有文獻中比較常見的方式[37]。Ahuja和Katila[38]認為專利是與創造力直接關聯的詞匯,而且與其他的創新績效測量也高度相關,例如,新產品數量和發明數量等。當然,用專利測量創新績效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不同行業在專利申請和授權方面具有很大的差異性,例如,2007—2010年間,根據IPC分類*IPC(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指國際專利分類,共有8個大類。國家知識產權局官方網站有據此統計的所有專利申請即授權統計信息,http://www.sipo.gov.cn/tjxx/。,H04電信技術共申請了58340項專利,C40組合技術卻只申請了13項。其次,很多專利并不具備經濟價值,據統計大約45%~49%的專利最終沒有轉化為新產品[39—40]。此外,有些創造性的設計并不能申請專利,而只能以技術秘密或科研文獻的形式存在,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2008年修正版)第二十五條規定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方法以及動物和植物品種均不能授予專利。
針對以上3個缺點,本文中采取了如下途徑彌補其不足之處。
(1)用專利的相對數量代替專利絕對數量,從而解決行業間差異。根據研究中心的行業特征與所申請的專利進行IPC子類映射*由于研究中心的分類并不是按照IPC,因此需要映射,但映射關系不是一對一。例如:農業領域對應A01農林牧漁;材料領域則根據具體單位到對應C07有機化學、C08有機高分子化合物、C09染料;涂料;拋光劑等、C22冶金學;合金或有色合金、B22鑄造;粉末冶金。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舉,如有興趣,請與本文作者聯系。,計算2007—2010年間該IPC子類的所有授權專利數量。
(2)專利按成熟度分為4類:A.實驗室成果或設計方案;B.小試成果或有機樣;C.中試成果或能小批量生產;D.能批量生產。將其分別賦權值1,2,3,4。結合(1)的IPC分類映射,將專利分數轉化為在該領域內的相對比例。
該公式用專利成熟度賦值解決專利是否能作為創新的代理變量的問題,除以同行業專利授權總數,轉化為相對數,從而消除行業之間的差異。
(3)國家科學技術獎5大獎項*國務院設立的5大國家科學技術獎項為: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技術發明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幾乎無一例外的都要求“技術創新性突出”且“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顯著”,因此本文中將國家級與省部級科學技術獎項也作為因變量。以國家科技進步獎為例,分為3個等級,特等獎、一等獎和二等獎,科技部和財政部從2005年開始將獎勵金額分別調整為100萬元,20萬元和10萬元*國家科技獎獎勵細則,規定2005年起,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獎金為100萬元,國家自然科學獎、技術發明獎以及科技進步獎一等獎獎金由9萬元調整為20萬元,二等獎獎金由6萬元調整為10萬元。。結合其他獎項的特點,本次調查中將獎項分為國家級三個等級和省部級三個等級,參考獲獎數量和獎勵金額,分別賦值為:50,20,10,5,2,1。
2.自變量
本研究中自變量為網絡規模和網絡多樣性。其中網絡規模定義為與研究中心有合作關系的所有組織數目。
Jacquemin和Berry[41]的熵指數(entropy)是測量網絡多樣性(異質性)的最常見方法之一[36,42],Palepu[43]在測量戰略多樣性時對熵指數做了更為詳細的論證。本文和Lin[36]等研究一樣,也沿用了這個方法。
協同對象的類別別沿用了Asakawa等[44]和Nieto和Santamaria[14]等研究的分類:高校、研究機構、企業和國外機構。
3.調節變量
法人資格為本研究中的調節變量。在本文中將A.依托單位內部二級機構與B.與依托單位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兩種情況都映射為無獨立法人資格,賦值為0。而將C.獨立法人和D.多單位聯合組建的法人組織,賦值為1。
4.控制變量
如上文因變量討論中所述,所屬領域與專利授權數量和國家科技獎授予數量有關系,因此納入控制變量。楊典[45]發現雖然企業沒有行政級別,但企業隸屬的各級政府的行政級別越高,業績表現越好。因此,本研究中將依托單位性質和主管部門性質均列入控制變量。行業類型和依托單位性質。其中主管部門,研究者根據其官方網站的介紹依據表1重新進行了類型映射。從正式掛牌時間到2010年的時間間隔則定義為建立時長,建立時長可能表征了研究中心的規范化程度。從組建到正式掛牌的時間間隔在本研究中定義為籌備時長,以表征其籌備的充分程度。因此,建立時長與籌備時長作為控制變量。Chen和Huang[46]研究表明人力資源實踐對創新績效存在顯著影響,本研究將單位總人數,業務總人數和青年骨干人數列入控制變量。諸多關于科研績效評價的研究都標明研發投入與研發產出存在顯著的相關[47]。研究中心承擔的開發項目按照來源分類:國家級、省部級、橫向、自選和國際合作,均列入控制變量。

表2 變量定義與數據來源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模型設計
為了驗證假設,本文構建了以下計量模型:

模型一:log(1+專利分數)=β0+β1網絡規模+β2網絡規模2+β3建立時長+β4籌備時長+β5單位總人數+β6業務帶頭人數+β7青年骨干人數+β8國際級課題+β9省部級課題+β10橫向課題+β11自選課題+β12國際合作課題+∑所屬領域+∑依托單位+∑主管部門+ε1模型五:log(1+專利分數)=λ0+λ1網絡規模+λ2網絡規模2+λ3是否法人+λ4(是否法人×網絡規模)+λ5(是否法人×網絡規模2)+λ6建立時長+λ7籌備時長+λ8單位總人數+λ9業務帶頭人數+λ10青年骨干人數+λ11國際級課題+λ12省部級課題+λ13橫向課題+λ14自選課題+λ15國際合作課題+∑所屬領域+∑依托單位+∑主管部門+ε5
其他回歸模型的構造與模型一和模型五類似,只是需要替換不同的變量。
根據Wooldridge[48]的建議,由于斜率系數不隨測度單位變化,而且嚴格為正的變量,其條件分布常常具有異方差性或偏態性,取自然對數后,即使不能消除這兩方面的問題,也可以使之有所緩和。在本研究中,專利分數和獲獎分數均非負且包含較少0值,因此取log(1+y)的形式。
(二)描述性統計
自變量網絡規模標準差為104.580,可見不同的研究中心協同創新網絡的規模具有顯著的差異,兩個因變量專利分數和獲獎分數在未對數化的原始值也存在顯著的差異,其中專利分數達到186.876。專利分數和獲獎分數的相關系數顯著(0.685,P<0.01),符合模型的預期。自變量網絡規模和專利分數以及獲獎分數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820(P<0.01)和0.790(P<0.01),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自變量網絡多樣化和專利分數以及獲獎分數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519(P<0.01)和0.608(P<0.01),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除了平方項與交叉項,在同一個回歸方程中的自變量、調節變量與控制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普遍比較弱,一般不會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
但為了更好地診斷自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本文還是沿用Lin[36]和Surroca和Zahra[49]等做法在表3標識了方差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縮寫VIF)值。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與VIF值見表3。由于VIF值大小決定于自變量與其他自變量之間的回歸系數,因此本研究中雖然用了兩個因變量,但只需標識一列VIF值。最后一列的VIF值有些是缺失的,因為:(1)兩個因變量不涉及共線性問題;(2)根據Jaccard和Turrusi[50]的建議,交叉項與二次項不需要考慮共線性問題,除非“共線性高到足以破壞電腦代數運算的設計,使統計軟件無法分離相關的標準誤(PP.294)”。
(三)回歸結果及分析
1.網絡規模對創新績效的影響分析
假設1提出網絡規模與創新績效的倒U型關系,通過模型一與模型三的回歸結果得到驗證。網絡規模對專利分數和獲獎分數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812(P<0.01)和1.270(P<0.01),同時,平方系數為負值,分別為-0.571(P<0.1)和-0.779(P<0.01)。觀察兩者的轉折點區別如圖2所示。

圖2 不同因變量的比較(網絡規模)
可見獲獎的轉折點更大一些,變化的速度也更快。雖然也有Freel和De Jong[51]等少數研究結果顯示創新網絡的大小與創新績效成線性關系,但是更多的研究還是與本文基本保持了一致,例如Grimpe和Kaiser[52]、Leiponen和Helfat[53]和Chen等[54]等。
這個結論意味著,研究中心需要根據自己的管理能力選擇恰當的網絡規模規模。同時,籌備時長與獲獎分數的相關系數顯著,這可能是由于科技獎更偏好重大的工程性項目,而這類研究需要則需要更長的籌備時間,例如搭建試驗環境。與平時的理解不同的是,各類課題投資對創新績效的影響不顯著,這可能由于行業投資的差異所致,例如,與中醫研究相比,航天項目可能需要更高的研究經費投入,而在本文中并未對該控制變量做相應的行業處理。詳細數據如表4所示。


表4 主效應檢驗結果
注:***P<0.01;***P<0.05;*P<0.1;括弧內為t值。
2.網絡多樣性對創新績效的影響分析
假設2提出網絡多樣化和創新績效的關系呈倒U型,該假設未通過模型二與模型四的回歸結果得到驗證。如表4所示,“倒U型”關系在網絡多樣化與專利分數之間成立,即假設2a成立。網絡多樣化與獲獎分數之間的倒U型關系不成立,即假設2b不成立。重新構造線性回歸模型四#,模型四中的二次項去掉,發現網絡多樣化與獲獎分數之間的線性關系成立(Beta=0.470,P<0.01)。兩者的區別如圖3所示。

圖3 不同因變量的比較(網絡多樣性)
該研究結論與Duysters和Lokshin[35]和Lin[36]等不完全一致,出現這種結論可能由于以往的研究中,并沒有將國家科技獎等獲獎內容作為因變量。在“倒U型”的邏輯中,很重要的因素是管理成本。對成本而言,專利顯得更敏感,而獲獎甚至關注“創造顯著社會效益”,有一些關系國計民生的項目甚至不計成本或者在國家的資助下完成,因此許多科技獎項對成本并不敏感,而專注于創造性。從這個角度講,以獲獎作為因變量不會出現預期的拐點。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以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作為樣本研究網絡多樣性,在整體上尚未到達拐點,加上本研究中所限定的協同對象分類限制了網絡多樣性的程度,導致在模型擬合的過程中近乎直線。在后續的研究中,可以考慮采納開放式的協同對象分類,以更清晰的觀察網絡多樣性的作用。
3.法人資格的調節效應分析
調節效應的檢驗沿用了Lin[36]和Gilsing等[55]的方法。結果如表5所示。

表5 調節效應檢驗結果
注:***P<0.01;***P<0.05;*P<0.1;括弧內為t值。
模型五和模型七的交互項系數支持了本文的假設3a與3b。是否法人×網絡規模的一次交互項系數分別為:-0.875(P<0.01)和0.672(P<0.1)。是否法人×網絡規模2的二次交互項系數分別為:0.670(P<0.1)和-0.462(P<0.1)。繼續以“是否法人”拆分樣本做分組回歸*在IBM SPSS Statistics 20.0.0中,以“法人資格”將樣本分為兩組,重新做回歸,限于篇幅,本文未給出所有分類回歸的具體數據以及模型的相關參數,若有興趣,請與本文作者聯系。,更深入的探討其調節方向與強弱,結果如圖4所示。

圖4 調節效應(網絡規模)
如圖4右所示,以獲獎分數作為因變量時,當研究中心有法人資格時,網絡規模與獲獎分數的“倒U型”關系彎度更大,也就是變化速度更快。如圖4左所示,以專利分數作為因變量恰相反,即無法人資格時,曲線變化速度更快,有法人資格相對變化緩慢。這符合本文的理論分析,因為對獲獎而言,需要更多的投入和創造性,有法人資格的組織,自身需要承受更多的風險,導致其變化更敏感(斜率大),也會更快的到達拐點。
模型六與模型八是對假設3c和假設3d的檢驗,從表5的回歸數據看,模型八的兩個交互項均不顯著,假設3d不能成立,結果如圖5右所示,兩條曲線無顯著區別,在此基礎上去掉二次項,做線性模型四#的調節檢驗,是否法人×網絡多樣性的交互項系數值為:-0.074(P>0.1)*研究者刪掉二次項,重新構建模型探討調節效應,發現是否法人在網絡多樣性與專利分數的關系中調節效應顯著,在網絡與獲獎分數的關系中調節效應不顯著。由于也不是本文的研究重點,因此未給出更詳細的數據匯報,若有興趣,請與本文作者聯系。,也不顯著,說明研究中心是否具有法人資格對獲獎調節效應不顯著。從分類回歸的兩條曲線分析來看是否具有法人資格,網絡多樣性都難以出現拐點,近似于圖3中的線性關系。這也佐證了主效應的結論,即網絡多樣性對獲獎分數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
以專利分數作為因變量時,是否法人×網絡多樣性的一次交互項系數顯著(-0.990,P<0.1),是否法人×網絡多樣性2的二次交互項系數不顯著(0.532,P>0.1),假設3c也不成立。如圖5左所示,雖然法人資格的調節導致曲線方向發生變化,但有法人資格的曲線,其模型F值不顯著(1.433,P=0.253>0.1)*在分組回歸中,有法人資格和無法人資格的分組分別匯報F值,由于樣本量變小,會導致分組后的回歸模型F值不顯著,但這并不影響調節作用的檢驗,因為本文中調節作用的驗證主要依據交互項,分組回歸旨在更深入的揭示調節作用的方向和強弱。,因此不具備太多的解釋意義。

圖5 調節效應(網絡多樣性)
(四)穩健性檢驗
本研究中利用VIF值檢測自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如表3最后一列所示,各自變量的VIF值均小于5,說明可以接受。采用D-W值(Durbin-Watson)對自相關性進行檢驗,值均在1.4~2.3之間,不存在顯著的自相關性。此外,采用殘差散點圖分析回歸模型是否存在異方差,本研究中回歸模型的殘差散點圖均不存在明顯的規律,因此不存在異方差問題。以上模型有效性檢驗以及回歸都在IBM SPSS Statistics 20.0.0中完成。
此外,本研究在設計階段就選取了兩個可以替代的因變量測度(專利分數和獲獎分數)來表征創新績效,這相當于穩健性檢驗中的替換變量。最后,研究者還將專利分數和獲獎分數公式中的權值進行了不同的賦值(所有值均保證其權值是有序的,即獲獎級別越高,賦值越大,專利成熟度越高,賦值越大),重新做回歸,回歸結果亦無實質差異。
五、結論與討論
(一)研究結論
本文從資源依賴理論和協同創新理論出發,以研究機構為樣本,探討了協同創新網絡(網絡規模與網絡多樣性)法人資格和創新績效(專利分數與獲獎分數)的關系。主要結論如下:(1)網絡規模對創新績效(專利分數與獲獎分數)的影響呈“倒U型”關系;(2)網絡多樣性對專利分數影響呈“倒U型”關系,而對獲獎分數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3)法人資格在網絡規模與創新績效(專利分數與獲獎分數)的關系中起調節作用,在網絡多樣性與創新績效(專利分數與獲獎分數)的關系中調節作用不顯著。
(二)理論貢獻與管理啟示
基于以上結論,本文的主要貢獻點及管理啟示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1)目前已有的文獻,絕大部分都是以企業作為樣本,本文是目前首次以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作為樣本的研究,這為協同創新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即站在研究機構的視角探討協同創新的作用。
(2)驗證了網絡規模與創新績效的倒U型關系,這與開放式創新領域對于知識搜索的研究結論保持了一致,例如,Katila和Ahuja[56]得出“過度搜索”會降低創新績效,Laursen和Salter[13]建議應注意搜索的性價比。本研究支持這個結論在協同創新領域的延伸,適當規模的網絡能夠取得最好的績效,但是過度的協同會降低創新績效。
(3)本文中首次將創新績效分為兩個維度:專利和創新。研究結果標明,網絡多樣性與專利的關系呈現“倒U型”結構,這與現有的諸多研究保持了一致。但是同時得出網絡多樣性對獲獎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未能驗證假設中所提出的“倒U型”,這說明高度創造性的創新與普通創新成果存在不同的規律,這不僅為多樣性與創造力的研究提供了佐證,也為科研機構(關注突破性的創造)和企業(關注一般性的創新)在戰略決策方面的異同提供了指導。
(4)法人資格在網絡規模、網絡多樣化和創新績效的關系中起不同的調節作用,這對現在的研究機構治理有很大的參考價值。由于工程中心大多來自高校和研究院所(包括轉制院所),來自企業的僅占23.26%(表1),但僅有少量研究關注大學治理[47],專門關注研究機構治理的文獻則幾乎沒有。本研究的結果顯示法人資格存在不同的調節效應,國家主管機構應根據研究機構設立的目的設計合理的治理結構。
(5)此外,本研究提供了更合理的創新績效測量方法,通過用專利成熟度防止專利授權中存在的僅僅關注“新穎性”而不是“創新性”,用專利相對數代替絕對數解決行業間的差異,用國家科技獎等作為另一個因變量解決有些創新無法申請專利的問題。
(三)局限與研究展望
當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由于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數量的限制,本研究的樣本量偏小。隨著發展,截至2012年底,研究中心增至327個,包含分中心在內為340個,以后可以加入2011—2014年的數據之后,模型可能會變得更穩健。其次,本研究僅選用了2007—2010年度的橫截面數據,沒有采用時間序列數據,后期可采用面板數據對結論進行進一步驗證。最后,在國家創新系統中,制度性因素起著重要的作用。但本研究中只驗證了制度性因素中是否具有法人資格的作用,在后續的研究中可以加入更多的制度性因素。
參考文獻:
[1]張瓊瑜.高新技術產業集群協同創新網絡與創新績效研究[D].江南大學,2012.
[2]陳 勁,陽銀娟.協同創新的理論基礎與內涵[J].科學學研究,2012,30(2):161-164.
[3]CHESBROUGH Henry W.The era of open innovation [J].Sloan Management Review,2003,44(3):35-41.
[4]ALMIRALL E,CASADESUS-MASANELL R.Open versus closed innovation:A model of discovery and divergenc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0,35(1):27-47.
[5]王 雎,曾 濤.開放式創新:基于價值創新的認知性框架[J].南開管理評論,2011,14(2):114-125.
[6]陳 勁.新形勢下產學研戰略聯盟創新與發展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7]陳 勁.協同創新與國家科研能力建設[J].科學學研究,2011,29(12):1762-1763.
[8]冉 龍,陳曉玲.協同創新與后發企業動態能力的演化——吉利汽車1997-2011年縱向案例研究[J].科學學研究,2012,30(2):201-206.
[9]何郁冰.產學研協同創新的理論模式[J].科學學研究.2012,30(2):165-174.
[10]郭 斌,等.知識經濟下產學合作的模式、機制與績效評價[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11]林潤輝,張紅娟,范建宏.基于網絡組織的協作創新研究綜述[J].管理評論,2013(6):33-48.
[12]CAMAGNI R.Innovation networks:Spatial perspectives[M].London:Beelhaven-Pinter,1991.
[13]LAURSEN K,Salter A.Open for innovation:The role of openness in explaining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mong U.K.manufacturing firm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6,27(2):131-150.
[14]NIETO M J,SANTAMAR?A L.The importance of diverse collaborative networks for the novelty of product innovation[J].Technovation,2007,27:367-377.
[15]BECKER W,DIETZ J.R&D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on activities of firms-evidence for the german manufacturing industry[J].Research Policy,2004,33:209-223.
[16]MIOTTI L,SACHWALD F.Co-operative R&D:Why and with whom?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of analysis[J].Research Policy,2003,32:1481-1499.
[17]FAEMS D,VAN Looy B,DEBACKERE K.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innovation:Toward a portfolio approach[J].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05,22:238-250.
[18]PFEFFER J,SALANCIK GR.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M].New York:Harper&Row,1978.
[19]SCOTT WR,DAVIS GF.Organizations and organizing rational,natural,and open system perspectives[M].高俊山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20]JENSSEN JI.Social network,resource,and entrepreneurship[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 ship and innovation,2001,2(2):103-109.
[21]JENSSEN JI,NYBAKK E.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 and innovation in small,knowledge-intensive firms:A literature review[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2013,17(2):1-27.
[22]COHEN W M,LEVINTHAL D A.Absorptive capacity: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J].?1990,35(1):128-152.
[23]林潤輝,范建紅,趙 陽等.公司治理環境、治理行為與治理績效的關系研究[J].南開管理評論,2010.13(6):138-148.
[24]冉 龍,陳 勁,董富全.企業網絡能力、創新結構與復雜產品系統創新關系研究[J].科研管理,2013,34(8):1-8.
[25]SALMAN N,SAIVES A L.Indirect networks:An intangible resource for biotechnology innovation[J].R&D Management,2005,35(2):203-215.
[26]VANHAVERBEKE W,BEERKENS B,DUYSTERS G.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technology-based alliance networks[J].Academy of Management Proceedings,2004.
[27]ANSOFFHI.Corporate strategy:An analytic approach to business policy for growth and expansion[M].McGraw-Hill,1965.
[28]BURT R.Structural holes.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29]POWELL W,KOPUT K,SMITH-DOERR L. Interorga-
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the locus of innovation:networks of learning in biotechnology[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6,41(1),116-146.
[30]POWELL W W,GIANNELLA E.Collective invention and inventor networks[M]//HALL B, ROSENBERG N.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innovation.Elsevier,2010.
[31]劉志迎,單潔含.技術距離、地理距離與大學-企業協同創新效應——基于聯合專利數據的研究[J].科學學研究,2013,31(9):1331-1337.
[32]RODAN S,GALUNIC C.More than network structure:How knowledge heterogeneity influences managerial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venes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4,25(6):541-562.
[33]WHITLEY R. Developing innovative competences: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J].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2002(11):497-528.
[34]ZENG S,XIE XM,TAM CM.Relationship between cooperation networks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SMEs[J].Technovation,2010,30(3):181-194.
[35]DUYSTERS G,LOKSHIN B.Determinants of alliance portfolio complexity and its effect on innovative performance of companies[J].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11,28(4):570-585.
[36]LIN J.Effects on diversity of R&D sources and human capital on iindustrial peroformance[J102].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2013. http://dx.doi.org/10.1016/j.techfore.2013.08.010.
[37]Wang F,et al.The effect of R&D novelty and openness decision on firms’ catch-up performance:empirical evidence form China[J].Technovation.2014, 34:21-30.
[38]AHUJA G,KATILA R.Technological acquisitions and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acquiring firms: A longitudinal study[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1,22(3):197-220.
[39]COHEN WM,LEVINTHAL D.Innovation and learning:The two faces of R&D[J].Economic Journal,1989,99(397):569-596.
[40]GRILICHES Z.Patent statistics as economic indicators:A survey[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0,28(4):1661-1707.
[41]JACQUEMIN AP,BERRY CH.Entropy measure of diversification and corporate growth[J].Th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1979,27(4):359-369.
[42]周浩軍.搜索優勢與轉移問題:弱聯系、結構洞和網絡多樣性對創新的曲線效應[D].杭州:浙江大學,2011.
[43]PALEPU K.Diversification strategy,profit performance and the entropy measur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85,6(3):239-255.
[44]ASAKAWA K,NAKAMURA H, SAWADA N.Firms’ open innovation policies,laboratories’ external collaborations,and laboratories’ R&D performance[J].R&D Management,2010,40(2):109-123.
[45]楊 典.公司治理與企業績效——基于中國經驗的社會學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13(1):72-94.
[46]CHEN CJ,HUANG JW.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practices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The mediating role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capacity[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09,62(1):102-114.
[47]官海濱,武德昆.中外高校科研績效評價理論比較[J].中國高校科技,2013(1/2):112-114.
[48]WOOLDRIDGE JM.Introductory ecnometrics:A modern approach(4th edition)[M].費劍平,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181-182.
[49]SURROCAJ,TRIBJA,ZAHRASA.Stakeholder pressure on MNEs and the transfer of socially irresponsible practices to subsidiaries[J].Academy Management Journal,2013,56(2):549-572.
[50]JACCARD J,TURRISI R.多元回歸中的交互作用,收錄于:線性回歸分析基礎[M].蔣 勤,譯.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51]FREEL M,DE JONG JP.Market novelty,competence-seeking and innovation networking[J].Technovation,2009,29(12):873-884.
[52]GRIMPE C,KAISER U.Balanc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knowledge acquisition:The gains and pains from R&D outsourcing[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10,47(8):1483-1509.
[53]LEIPONEN A,HELFAT C E.Innovation objectives,knowledge sources,and the benefits of breadth[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0,31(2):224-236.
[54]CHEN J,CHEN Y,VANHAVERBEKE W.The influence of scope,depth,and orientation of external technology sources on the innovativ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firms[J].Technovation,2011(31):362-373.
[55]GILSING V,NOOTEBOOM B,VANHAVERBEKE W,et al.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novel technologies:Technological distance,betweenness centrality and density[J].Research Policy,2008,37(10):1717-1731.
[56]KATILA R,AHUJA G.Something old,something new:A longitudinal study of search behavior and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2,45(6):1183-1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