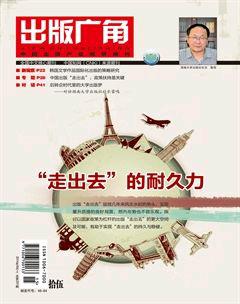中國圖書“走出去”如何鍛造真金
武靜
對國外讀者來說,他們關心的是看到什么樣的圖書;對國內出版社來說,他們關心的是如何借助國家的渠道將圖書輸出海外。因此,我們只有擴寬出海的渠道,才能讓文化的交流順利到達大洋彼岸。
在2014年7月剛剛結束的第21屆東京國際書展上,中國展團共輸出版權75項,創參展以來的最好成績。近年來,隨著國內外出版界交流和合作的深入,我國出版企業也頻頻出現在國際書展中,并逐步取得顯著成績,贏得更多的國際話語權。
值得注意的是,在由美國《出版商周刊》、英國《書商》、法國《圖書周刊》、德國《圖書報道》等多家世界出版行業媒體共同發布的“2014全球出版業50強排行榜”中,中國出版集團公司和中國教育出版傳媒集團分列第14位和21位,名次較2013年有不少提升。與之相對應的是,中文圖書海外市場影響力逐年擴大。
中國圖書走向世界,是中國出版人的理想和追求。中國圖書“走出去”,通過優秀作品回答國際上關注的中國問題,傳播中國精神,使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進程做出國際社會廣泛認同的重要貢獻,增強中華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響力,最終使我國的對外文化傳播能力與綜合國力相匹配。
十年耕耘,摸著石頭過河
“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已經實施10年,在提高中國圖書版權輸出的數量和質量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其中版權輸入輸出比例發生革命性變化,從10年前的15∶1縮小到1.76∶1;輸出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對西方發達國家的版權輸出逐年遞增,一批反映中國模式、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圖書進入西方主流圖書市場;語種的數量也有了很大變化,實現了英語、法語、西班牙語、俄語等多種語言全面推進;出版物的形態多樣化,積極開拓數字版權輸出,并取得明顯成績。在國家的重視下和出版社的努力下,中國圖書版權輸出逐年上升,輸出選題類型逐年豐富。除了中醫藥圖書、對外漢語教材、中國文化圖書等帶有明顯中國特色的選題,少兒圖書、學術圖書、文學圖書成為版權輸出的新力量。
第一,中國文化點亮西方讀者。《于丹〈論語〉心得》堪稱近年來“走出去”中的經典案例。截至目前,《于丹〈論語〉心得》已經簽約海外32個國家和地區,共譯有28個語種、34個版本,海外發行60多萬冊。《于丹〈論語〉心得》在中國的持續熱銷以及“于丹現象”和“國學熱”引發的各種爭議,引發了國際出版界和新聞界的濃厚興趣,這是其通向海外的重要砝碼。西方讀者對東方文化很感興趣,這也是《于丹〈論語〉心得》法文版上市之后便創下近8萬銷量的原因。《于丹〈論語〉心得》之所以能在西方引起注意,得以進入主流市場,是因為這本書雖然是寫給中國人的,但其哲學思想對西方人同樣具有參考價值。如在《于丹〈論語〉心得》一書中,于丹引用了大量西方素材來論證孔子的思想,其中包括許多西方民間傳說和黑格爾哲學。
第二,科技圖書打造私人訂制。自2009年開始,浙江出版聯合集團借助浙商在非洲的基礎和人脈,與非洲出版界合作,開創了私人訂制的“走出去”模式。在搭建與非洲各國的版權輸出平臺上,浙江出版聯合集團重點針對醫療保健、農業技術、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政治經濟等非洲國家相對亟須的圖書選題進行合作。其中,浙江科技出版社與馬里撒哈拉出版社合作出版法語版《非洲常見病防治讀本》,圖書由中國援非醫療隊總結40多年醫療實踐寫成,受到當地讀者歡迎。國務院新聞辦已多次采購該書分發給非洲各使館,有的使館一次訂書達2000冊。目前該系列已出版馬里、坦桑尼亞、赤道幾內亞等多個國家版本,涉及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和斯瓦希里語四個語種。該系列圖書的出版模式為由我國醫療隊撰稿,我國負責翻譯、印刷,當地出版社負責審稿和出版,以贈送為主,并進入當地發行渠道。
第三,童書“走出去”新版圖。在引進版童書不斷受到國人追捧之時,中國的原創童書也逐漸走向世界,這是因為兒童圖書最容易跨越不同文化背景。而且少兒圖書很多是圖文并茂的,圖畫和音樂一樣,是世界的語言,在彼此了解的過程中少了很多障礙。近年來,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就以博洛尼亞兒童書展為平臺,為中國搭建了一條通向世界的童書出版橋梁,改變了以往坐等的戰略。其中,高洪波的《快樂小豬波波飛》、曹文軒的《羽毛》的版權備受歐美國家關注,《羽毛》一書更是得到“安徒生獎提名獎”的巴西插畫家羅杰·米羅為其畫插畫。在更多出版社的努力下,中國童書走向世界并非夢想。
華麗轉身,從內容到品牌
隨著十八大報告提出的“中國夢”,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坐標系中構建主體性的意識漸強,中國出版“走出去”力度日益加大。經過了10年摸索的圖書“走出去”工作也有了新的風向,各方機構正在合力讓“中國品牌”順暢地走向世界。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國圖書“走出去”實現了華麗的轉身,已經轉變了初始的單本內容輸出方式,升級為文化品牌輸出和與國外出版商強強聯手打造學術品牌兩大方式。
第一,從單本圖書輸出到文化品牌圖書輸出。中國圖書“走出去”迅速發展,說明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高,尤其是作為綜合國力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文化,受到普遍重視。在中國文化魅力和影響力大幅提升的今天,我們不僅需要簡單便捷地宣傳介紹中國的讀物,更需要將圖書品牌集體推向世界。原新聞出版總署2009年啟動了“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以下簡稱“經典中國”),采用項目管理方式資助外向型優秀圖書選題的翻譯和出版,有效推動中國圖書“走出去”。“經典中國”的重要資助對象包括 “中國學術名著系列”和“名家名譯系列”等能夠代表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系列圖書,其覆蓋哲學、政治、法律、軍事、文藝理論、詩歌、小說、戲劇等社會和人文學科領域。2013年還增加了“名家名作”的“走出去”這一子版塊,莫言的《蛙》《酒國》,劉震云的《溫故一九四二》《我叫劉躍進》,余華的《兄弟》,曹文軒的“大王書系列”《青銅葵花》《細米》,沈石溪的《刀疤豺母》《會貿易的狐》等名家的70余種圖書入選。通過“經典中國”的資助,許多中國圖書得以“走出去”,大大降低了圖書海外出版發行的商業風險。
第二,跨國合作,彰顯學術品牌力量。由于學術圖書內容高度專業化,篇幅相對較長,翻譯周期長、難度大,這就對學術圖書“走出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政府的支持和幫助下,我國許多大學出版社通過與國際學術出版商合作實現共贏,按照國際出版規律和學術出版規范來組織實施“走出去”戰略,并穩步推進。如由外語研究與教學出版社和施普林格出版集團的“中華學術文庫”(英文叢書)項目,華語教學出版社與耶魯大學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對外漢語教材《環球漢語——漢語和中國文化》,五洲傳播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多家國內出版社和劍橋大學出版社合作的“劍橋中國文庫”等。這些深層次的“走出去”合作,最終目的都是將中國學術成就及時介紹給國外讀者,不僅有利于世界各國人民更完整、更真實地了解中國,也有利于促進中西方之間的學術交流和互相理解。雖然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學術出版還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與國外出版社合作的方式,為中國學術品牌“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思路。
世界接軌,我們還缺什么?
距離“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工作小組的第一次工作會議,已經過去10年了,我國“走出去”工作邁上了新的臺階。我們開始對產業發展有了更深入的促進作用,企業也從被動、觀望向主體化、特色化運作轉變。經過10年的發展,各出版企業在機制體制、框架搭建上有了更清晰、更完善的設計,并取得市場實效。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我國的“走出去”工作仍是困難重重,仍有許多問題亟須解決。
第一,翻譯問題如何解決。中國圖書、中國文化“走出去”,翻譯是第一道關。表面上看,翻譯的是文字,實際上翻譯的是文化。讓一個文化產品被對方接納,實際上是在進行一種文化轉化工作,通常是要依靠翻譯者對兩種不同文化的理解才能完成這個轉化過程。目前,“走出去”工作中的翻譯問題已成為亟須解決的問題,尤其是我國的小語種翻譯人才匱乏。我國的翻譯行業,尤其是筆譯,待遇低、工時長、出名難,這就導致很多人不愿意從事這方面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很多翻譯工作者缺乏西方讀者的思維,在翻譯過程中習慣采用中國人的邏輯方式,這就使得外國讀者對格格不入的中國作品難以產生興趣。許多著名國際出版機構對譯者十分挑剔,要求譯者的母語必須是出版機構所在的國家,像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的出版機構都有如此要求。在未來的“走出去”工作中,政府機構、出版集團、出版社能否有計劃地組建翻譯人才團隊是關鍵。我們在“走出去”的模式上已經不斷創新,而在最基礎的問題上卻不牢固,中國文化走向世界解決不了基礎問題,恐怕一切都是空想。
第二,完善的渠道建設如何解決。在“走出去”工作中,渠道建設發揮著重大作用。近年來,隨著在北美的中國移民和留學生人數的增加,北美的中文圖書市場需求逐漸增大。2011年,在原新聞出版總署的推動下,中國最大的圖書出口企業中國國際圖書貿易集團公司與全球最大網絡圖書零售商美國亞馬遜公司達成協議,開設中文圖書銷售頻道——亞馬遜“中國書店”。值得注意的是,在亞馬遜“中國圖書”里,不論是中文圖書,還是英文圖書,都是中國出版的,都由中國國際圖書貿易集團負責提供,所有上線圖書的簡介和圖片都翻譯成英文。這樣的在線營銷效果,為中國出版物的全球傳播探索出一種新模式,開辟了一條新渠道。
然而,從目前國內圖書輸出到海外的現狀來看,真正可用的渠道還很少,若是政府沒有足夠的力量支持、政策引導,再強大的出版集團也難以獨自出海。對國外讀者來說,他們關心的是看到什么樣的圖書;對國內出版社來說,他們關心的是如何借助國家的渠道將圖書輸出海外。因此,我們只有擴寬出海的渠道,才能讓文化的交流順利到達大洋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