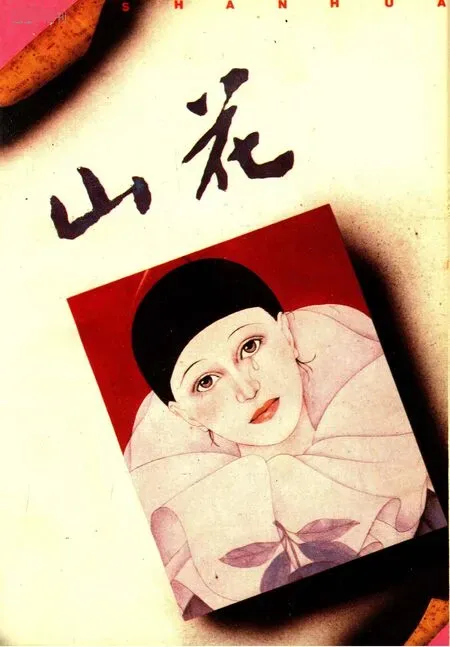《一千英畝》中人與土地關系的倫理研究
簡·斯邁利(Jane Smiley, 1949—)在小說《一千英畝》中通過女主人公金妮的視角著力展現了澤倫縣人與土地之間的復雜關系。從土地倫理的角度分析小說《一千英畝》,可以發現該作品中人地關系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爭奪土地,爭奪財富和地位;向荒野進軍,擴張人類利益;殘害動物生命,喪失生態良知;毒害土地健康,毒害人類自己。
爭奪土地,爭奪財富和地位
數千年來,土地既是人類生存的根基,又是人類竭力爭取的對象,土地在人們眼里成為了財富、地位、尊嚴和權威的象征。如同小說所說的那樣,“土地面積和財力在澤倫縣如同姓名和性別一樣都是基本的事實。”[1]在澤倫縣,幾乎每一個人都十分看重土地面積,甚至已非常富裕并已有了很多土地的人仍覬覦得到更多的土地,他們對土地的貪欲從未減少過,對土地的戰爭也從未停止過,“每一英畝都是垂涎的對象。”[1]
文中,拉里·庫克(金妮的父親)和哈羅德等人只從經濟和實用的角度來看待土地。拉里以“得到的就是你應得的”為座右銘,[1]竭力爭取到了一千英畝土地,這給他的家族帶來了繁榮。與拉里相比,埃里克森家并不那么幸運,僅“有370英畝土地,并且還背著抵押貸款,” 所以當埃里克森家“最終失去抵押貸款時,”[1]拉里常常和哈羅德商量誰應該接手他家的土地,最后拉里以低價購買了埃里克森的土地而不是在對方困難時給予幫助。此外,拉里買了一輛別克汽車后,他家的孩子可以舒服地坐在車里,“能很好地防止灰塵”,而埃里克森家的孩子只能坐在一輛農車的后面,這輛別克汽車“可以準確地衡量出640英畝土地與300或500英畝的差距。”[1]
向荒野進軍,擴張人類利益
庫克家祖輩四代人幾乎都是步步在向荒野進軍,他們只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待土地,缺失對土地問題的倫理和美學考慮,他們通過抽干原野上的水而徹底毀掉了充滿生機的土地,結果,“現今草沒了,沼澤地和潮濕大草原也沒了。”[1]澤倫縣最初的時候是荒野或沼澤,基本被水覆蓋,但人類的到來改變了這里的一切。在1890年春天,金妮的外婆的父母(塞姆和阿拉貝拉)第一次來到澤倫縣時,“看到他們已買的土地中有一半幾乎都看不見,都在兩英尺的水下,另有四分之一的土地是潮濕的。”[1]約翰·庫克(金妮的爺爺)是一個無所畏懼并愛讀書的人,他對最新的農業和工業設備發明感興趣,并說服塞姆和阿拉貝拉購買了工具、磚頭和水管等材料。他們一起在土地中安置了一個永久的抽水系統,這個抽水系統“‘吸引’著水,溫暖著土壤,使人很容易在其上工作,使人可以帶著自己的機器在最大暴雨后一天24小時進入田地里……最終,約翰、塞姆,還有我父親花了一代人25年的時間,才鋪成水管線,挖好了抽水井和水池。”[1]抽水系統抽干沼澤中的水后,人們通常種植一些對人類有利可圖的農作物,而不是一些像香蒲花一樣“無用的”植物,這給人們帶來了經濟上的繁榮,正如金妮所說,“最奇幻的是,水管帶來了繁榮——每年每英畝土地產生了更好且更多蒲式耳的莊稼。”[1]“一旦那些寶貴的排水管線出現,土壤就會產生人類陰謀策劃要獲得的財富。”[1]
為了獲得更多耕地,拉里等人甚至把美麗的天然池塘也給毀了。天然池塘是金妮過去常常去那兒沉思冥想的地方。金妮回憶道,“在我們小時候,羅斯和我通常去農場池塘游泳……這個池塘是在農場以前就有的一個壺穴,它非常大,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在這個池塘里,金妮和妹妹羅斯度過了快樂的兒童時光,“過去羅斯和我在池塘所做的只是仰面浮游數小時,吸收著涼爽的水,生活在藍色的天空下。”但不幸的是,“在母親去世不久后,父親抽干了池塘,摧毀了池塘周圍的樹及其殘余部分,以便能更有效地經營那片土地。”[1]而今,“池塘,還有房屋,農場花園,井,谷倉的地基,所有這一切都沒了”[1],最終“沒有一個可以讓一個人私下獨自陷入沉思冥想的地方了。”[1]
在人類中心主義者面前,土地變成了供人類消遣和享樂的工具。在派克游泳池邊,金妮評論說,“甚至在我父親年輕的時候,在澤倫縣有許許多多的湖和壺穴狀的池塘,以至于想建一個游泳池的想法在當時都是滑稽的。但現今任何大小的鎮子要么已經建了一個游泳池,要么想要建一個。縣報紙把三個平臺狀且有九個洞的高爾夫球場說成‘澤倫縣許多娛樂設施中的一些。’”[1]人類就這樣為了自身的享樂把原有的土地變成了游泳池和高爾夫球場等娛樂設施。
人類對土地的亂墾導致了水體的嚴重污染。金妮記得,現今的水變成了“褐色和黑色”,更不能潛入里面游泳了,通常可以從水中打撈出“輪轂罩,錫罐,打壞的油桶”,“混濁的水一動不動……有一部分垃圾埋在了周圍的雜草中,這部分垃圾埋的時間如此長,以至于道路都繞過了它……”[1]即便在下雨后,水也不會變清,因為農業和工業廢物被帶入了水中,“有些日子,水是藍的,但是其中卷入了很多的廢物。”[1]
殘害動物生命,喪失生態良知
小說中,人類喪失了生態良知,忘卻了自己在共同體中簡單而普通的成員身份,更忘卻了作為公民對共同體應盡的義務。他們進軍荒野,富裕了自己,但卻剝奪了眾多水生動植物的生命和家園。90年前,當金妮的祖父們第一次來到澤倫縣時,整個土地完整、穩定與美麗,許多水生動植物棲息于此,例如,“數萬計的塘鵝在香蒲花中筑巢。但是自60年代年早期以來,我從未見過一只塘鵝了。”[1]人類缺失對土地共同體的倫理關懷,導致了荒野的破壞,進而造成了塘鵝大批死亡。
對于拉里和哈羅德等人來說,他們褻瀆和殘害共同體中其他和人類平等的成員和公民。拉里“不怎么喜歡不能被馴服的自然”[1]。他“每年都殺害田地里的動物”[1]。金妮從杰西那兒得知,田地“周圍有很多漂亮的蛇。乳蛇和游蛇很美麗”[1],但是拉里卻殘忍地“殺害它們”[1]。此外,拉里甚至嘲笑熱愛動物的埃里克森家。在拉里看來,那些不專心耕種土地卻一心照顧動物的農民不是好農民而是大傻瓜。對于哈羅德來說,他用現代機械殘酷地殺害動物。一次,哈羅德駕駛玉米收割機,在看到臥在玉米地里的一只小鹿后,沒有繞個彎躲過小生命或者把車停下來先把它趕走,而是徑直地開車從其身上軋過去。尤其是,在小鹿嚴重受傷后,哈羅德對它無動于衷、放任不管,讓其在痛苦中慢慢死去而不是給它一個很快的死法。哈羅德就這樣無情地奪取了一個“公民”的寶貴生命。
毒害土地健康,毒害人類自己
土地健康是土地倫理的重要目標和土地共同體“完整、穩定與美麗”的重要前提。為了協調好土地利用和土地保護之間的關系,利奧波德在其兩篇文章中創造性地提出了“土地健康”的概念,一篇為“荒野:科學的實驗室”[2];另一篇為“保護整體還是部分”[3]。在利氏看來,保護不單單是保護土地共同體中單個的個體,更重要的是,要保持“土地的健康狀態”,“土地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動物,但健康不單單是這些組成部分數量的充足。健康既是每個組成部分自我更新的活力狀態,也是所有部分整體性的自我更新的活力狀態。”[3]
利奧波德把人與土地視為“兩個均受到人類干涉和控制的有機體”[4],就像人生病一樣,土地喪失健康后,也會“生病”。在利氏看來,由于現代社會過于重視經濟的發展,結果導致土地“生病”,經濟社會的發展是以土地健康的喪失為代價的。利氏還認為,如果通過不可持續的機械或科技手段來發展農業,就會破壞土地健康,例如,人們不正當地利用乃至濫用化肥、殺蟲劑、除草劑等化學品,不僅會不知不覺地使動物趨于滅絕,也會從根本上危及土地健康,更會危害人類自己的健康。利氏把土地生病歸因于錯誤的社會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僅把自然看作是支離破碎的個體或者僅供人類利用的資源,更把人與土地的關系錯誤地理解為人類有權使土地商品化、工具化,并可以遞增性地利用土地的工具價值。
在小說中,人類借助排水管線征服荒野和沼澤,雖然獲得了暫時的繁榮,但留下了潛在的危機。這些排水管線抽干了水,剝奪了土地的生機與活力。年復一年,莊稼在土地上生長,不斷地吸干其中的營養,慢慢地,土地不能再為莊稼提供足夠的營養。正如文中所說,“小山頂上的土壤如此暗淡無力以至于矗在其中的谷物如同站在沙礫中一般,因為這些谷物不能從土壤中汲取任何營養了。”[1]從澤倫縣土壤肥力喪失可以推測出那兒的土地已經“生病”了。
在小說中,毒藥和毒素成為小說一個主題,有關“毒藥”的詞匯反復出現。作者寫道“農場富含各種毒物,盡管許多的毒藥的作用不是快速”[1]。文中給出了在澤倫縣涌現的很多毒藥的名字:氯丹(一種強力殺蟲劑)、砷、殺蟲劑、煤油、汽油、涂料稀釋劑、鐳、氣霧劑、脫脂劑、車用機油、阿特拉津(一種除草劑名)和氟樂靈,等等。在庫克家拍賣地產的那天,金妮注意到在谷倉里堆滿了罐裝滴滴涕(DDT,一種殺蟲劑名)。此外,作者經常提到農田上有許多裝滿化學肥料的大容器。澤倫縣農藥之多令農民們對其危害幾乎熟視無睹、麻木不仁,“每個農民都知道化學物銷售商代表會示范性地把某些要推銷的化學劑當作母乳來喝掉。”[1]作者肆意渲染毒藥數量之多,實際上是在警告人類,四面埋伏的毒藥已經對土地共同體中的所有生命構成了潛在的威脅,人類很難逃脫其害。
曾經帶來繁榮的排水管線成為了毒藥散播的渠道。當金妮長大成人后,她承認排水管線僅僅“與自然形成暫時脆弱的休戰”[1]。“暫時脆弱的休戰”意味著排水管線僅會給農民帶來暫時的繁榮,但也意味著一場自然向人類報復的大戰正在醞釀。金妮注意到,“排水管線把水排到了排水井里。這些井延伸到地下約300英尺,并星羅棋布于小鎮中,在我們農場四周就有7個排水井。”[1]金妮總覺得“在堅固的土地下有種東西在移動,從一個地方轉向另外一個地方。總是存在著某種神秘”[1]。這種移動的神秘物可能就是毒素。被化肥、農藥等污染的水一旦流進了土壤,就很有可能通過排水管線、排水井等設備傳遞、散播,這就意味著所有生命每天喝的水都不是干凈的水,意味著所有生命都在受到毒素的毒害。
化肥和毒藥的利用不僅毒害了土地,更毒害了女性。“現今存在一個普遍認可的事實:女性是環境災難的最大受害者。”[5]作者把對土地健康的擔心和對人類健康的擔心聯系在了一起,認為毒害土地和毒害人類尤其是女性是一體的,正如法雷爾(Farrell)所認為的那樣,“《一千英畝》努力探討了土地與人類身體的關系,這種關系在歐美文化中……尤其表現在對女性身體的催逼方面。”[6]“斯邁利的《一千英畝》描寫了生病的土地對人類身體的毒害,并使得人類的身體成為不生育的荒地。”[6]小說中的女性幾乎沒有一個能擺脫毒藥的危害。金妮一直渴望著懷孕,但毒素使她五次流產,最終剝奪了她的生育能力。當金妮向杰西講述自己五次流產的經歷時,杰西變得異常氣憤,原因是無人告訴她那個專家們至少都知道十年的事實:井水中的硝酸鹽會導致嬰兒的流產和死亡,“十多年來,人們早已知道井水中的硝酸鹽可以導致流產和嬰兒的死亡。難道你不知道化肥殘留物流入了蓄水層嗎?”[1]在文中,作者也寫到化學物對女性母乳的污染:“我現在已染上了有毒化學物。它們已經——通過空氣、水和食物鏈——到達了我身上的秘密渠道。”[1]
作者在批判人類通過濫用農藥和化肥等方法破壞土地的同時,還通過介紹杰西的有機種植方法為受毒害的土地和人類指出了一線生存的希望。杰西倡導有機種植,因為有機種植能夠保證人與土地的共同健康和繁榮,“自1964年以來,他就從未在土地上用過化學物。他72歲,但看起來像50歲……他們獲得了大量的收成!他僅僅利用綠色肥料和動物糞肥。植物園就像一個非雜交品種博物館……他在自己的果園有20種不同的應用品種……他們都如此開心。”[1]這個有機農場與拉里的機械農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或許它沒有拉里的一千英畝土地面積大,或許也沒有其產量高,但是,有機種植有更好的未來,因為它是以一種合作和對生命負責的態度來耕耘土地。換句話說,有機種植在“耕耘土地”時,實際上是在“耕耘未來”,“耕耘未來”要求人們在利用土地時要對后代人負責,所以部分農民開始對這種農作方式感到開心。
在1949年,利奧波德開創性地提出了土地倫理,并十分擔心現代社會缺失土地倫理,“至今,仍沒有任何倫理是處理人與土地關系的。”[4]在1991年,斯邁利在小說《一千英畝》通過對荒野消失、農藥污染、物種滅絕、水源枯竭和草原退化等環境問題的揭露,批判了人類無視土地倫理的態度和行為。可惜的是,利奧波德60多年前的擔憂的問題現今依然存在,從內心接受土地倫理的人數很少,能夠踐行的更少。當今社會,生態危機愈演愈烈,人地矛盾日益尖銳,迫切需要我們樹立和實踐土地倫理,但樹立和實踐土地倫理是一項艱難的過程,需要社會各個成員和各個機構共同參與。作為土地共同體中的一公民,我們每個人都有義務培養生態意識,塑造生態良知,保持土地健康,接受和實踐土地倫理,保護和恢復土地共同體的“完整、穩定與美麗”。
[1]Smiley, Jane.A Thousand Acres[M].Thorndike, Maine: Thorndike Press, 1992.
[2]Leopold, Aldo.“Wilderness a Land Laboratory”[A].Flader,SL, Callicott,JB , eds,The River of the Mother of God and 0ther Essays by Aldo Leopold [C].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 287-89.
[3]Leopold, Aldo.“Conservation: In Whole or In Part?”[A].Flader,SL, Callicott,JB,eds, The River of the Mother of God and 0ther Essays by Aldo Leopold [C].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1:310-19.
[4]Leopold, Aldo.A Sand Almanac With Essays on Conservation form Round River[M].New York:Ballantine,1970.
[5]Plant, Judith.Healing the Wounds:The Promise of Ecofeminism[M].Philadelphia:New Society Publishers,1989.
[6]Farrell, S.Jane Smiley's A Thousand Acres[M].New York, London: Continuum,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