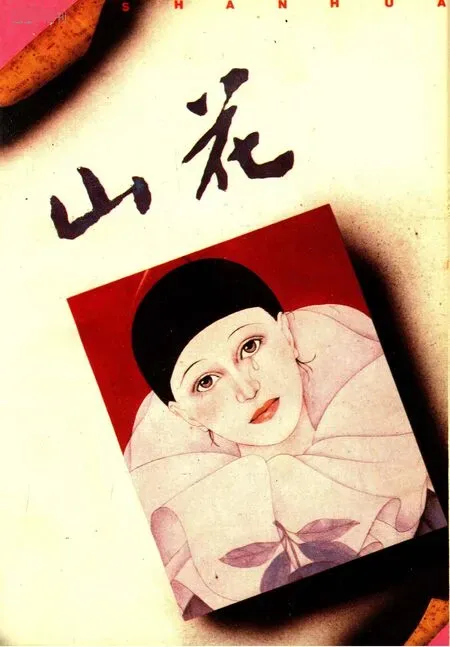《達洛衛夫人》中陌生化技巧的運用
夏增強
弗吉尼亞·伍爾芙(1882-1941)是20世紀現代主義公認的先鋒人物。她在小說藝術領域的大膽創新為20世紀的文學帶來了一股清風,讓我們在傳統的文學氛圍中聽到了其細膩而又深邃的聲音,感受到了其獨特而又雋永的精神世界。《達洛衛夫人》作為其早期的意識流作品,其新穎的藝術構思一直以來備受評論家和讀者的關注。本文采用俄國形式主義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論來分析該小說是如何在行文結構、敘事視角以及語言運用這三個方面來進行陌生化處理,從而達到深化主題,拓展行文的藝術效果。
行文結構的陌生化
《達洛衛夫人》的故事結構的陌生化是通過其時間安排的陌生化來實現的。由俄國形式主義發展演變而來的法國結構主義的代表人物托多洛夫指出,敘事時間包括作品講述的時間對事件時間的壓縮和延伸,還包括“連貫”、“交替”和“插入”。“連貫是并列幾個不同的故事,上一個故事結束,又開始下一個故事;插入是把一個故事插入到另一個故事里去,形成故事套故事的結構;交替是同時敘述兩個故事,頭一個故事還未完,就中斷了去講第二個故事,第二個也未講完,中斷了去續講頭一個,交替進行。”《達洛衛夫人》里,一直有兩條并行不悖的主線貫穿全文:一條是對達洛衛夫人一天的心理和行為描述;另一條則是對賽普蒂默斯·史密斯臨死前一天的心理活動描述。以這兩條主線為軸,伍爾芙加入了兩個主角在這一天之外的大量的回憶,穿插進許多不同的故事,從而使得全篇小說顯得行文飽滿、視野開闊而又意義深刻。這種故事的穿梭就是托多洛夫的“交替”和“插入”的最好體現。
達洛衛夫人和史密斯是兩個原本互不相識的陌生人。共同點也只有兩人都生活在倫敦。小說是從講述達洛衛夫人清晨出門買花開始的。當達洛衛夫人在花店中因街上傳來的一聲巨響而吃驚時,正在路邊公園里的史密斯也同樣吃了一驚。這一聲巨響成了一條故事線索跳到另一條故事線索的紐帶。也因此展開了史密斯的故事。而在隨后的故事情節中,我們也逐漸發覺史密斯其實就是達洛衛夫人的影子。他們倆身世迥異,經歷不同,性格懸殊,也從未相遇。但是他們對生活中公開的或潛在的恐懼的反應卻是驚人的一致。這樣一種故事的跳躍和情節的安排是現代以前的傳統小說所罕見的。這種插入故事時間從而實現故事套故事的結構加深了對該小說理解的難度,延長了讀者審美的感受,并因此達到了陌生化的目的。
另一方面,伍爾芙不僅僅滿足于兩個故事的相互融合,她還更深入地分別在這兩個故事里又加入故事,形成了故事套故事,故事交替故事的結構形態,使原本簡單明了的幾個故事交織在一起,進一步加深了整部小說的非尋常化,以及在理解上的難度,達到結構陌生化的效果。在達洛衛夫人自己的這一條故事線里,伍爾芙穿插進去了達洛衛夫人對過去的回憶和對自己當前的臆想、她的舊情人彼得的回憶、她的丈夫理查德的回憶等。這些回憶和臆想都是圍繞達洛衛夫人而展開,形成了這一條將當前和過去,自己和周圍人的回憶相互纏繞的模式。而在史密斯的那條線里,同樣也交叉著別的故事:史密斯好友伊萬斯的去世、對戰爭的回憶、妻子對意大利生活的回憶等。和第一條主線一樣,這條主線也是以史密斯一天的活動為軸,以圍繞他的其他回憶為徑,實現故事和故事的嵌套。而這兩條主軸又作為小說的主線和支撐,讓我們似乎看到了兩棵并排的大樹各自出枝長葉,而彼此的枝葉又相互交結,枝葉交錯繁茂的景象。
在伍爾芙的丈夫倫納德·伍爾芙為其妻子去世后編輯的伍爾芙日記選中曾記有這樣一段:“今天下午我終于設想出一部新小說的新表現手法。假如在小說中,一個事件可以從另一個事件中脫胎而出,演繹出不止10頁,而是200頁或更多一些的篇幅來,這不是可以顯示出這樣一種形式嗎?即結構松散,可以包容一切,同時更接近主題,卻又能保持形式和節奏的不變。而這種形式正是我所企求的。”
由此可見,結構的變化和陌生化也是伍爾芙本人追求的。她開創的這種非常見的故事敘述模式不同于傳統的結構模式。如果按照傳統的方式,按事件的先后順序來安排的話,該小說就不可能達到這種新穎的效果。也正是這種使小說結構陌生化的技巧的使用,讀者在閱讀的同時延長了欣賞時間,加深了審美感受,《達洛衛夫人》也因此從眾多作品中脫穎而出,成為了現代主義與傳統文學劃分界限的最好證明。
敘事視角的陌生化
“敘事視角即敘事人是站在何種角度、以什么方式來敘事的著眼點。按美國學論家艾伯拉姆斯的定義,敘事視角是指‘敘述故事的方法——作者所采用的表現方式或觀點,讀者由此得知構成一部虛構小說的敘述里的人物、行動、情境和事件’。”“敘事視角在作品中有一個基本定位,但它也可以有變動游移,使敘事有一種更廣角的攝取故事內容的角度。”
《達洛衛夫人》中,伍爾芙采取的就是這種變動游移的敘事視角。小說一開始,作者用的是一種傳統的全知全覺的敘事視角。這種傳統敘事方式可以為我們展示作品中人物所無法講述的內容。同時,這種全知的敘述也能夠更客觀地為我們講述事件的發展而不摻雜太多的主觀成分,使小說敘事更可信,更有說服力。
然而,隨著情節的展開,我們不難發現在小說的行文中經常可以見到以達洛衛夫人、史密斯等人為敘事視角開始講述或回憶。在對史密斯在公園里的一段思緒的描述中,伍爾芙這樣寫到:
“然而,他自己仍待在嵯峨的巖石上,仿佛一個遇難的水手趺坐在礁石上。他尋思:我把身子探出船外,掉入水里。我沉入海底。我曾經死去,如今又復活了,哎,讓我安息吧,他祈求著。(他又喃喃自語:這太可怕了,太可怕啦!)恍惚在蘇醒之前,鳥語嚶嚶,車聲轔轔,匯合成一片奇異的和諧;繁音徐徐增長,使夢鄉之人似乎感到被引至生命的岸邊,賽普蒂默斯覺得,自己也被生活所吸引,驕陽更加灼熱,喊聲愈發響亮,一樁大事行將爆發了。”
我們看到就在很自然的移動中,我們從敘述者的角度轉移到了史密斯的視角,讀到了他的內心活動。這種意識流的運用也正是伍爾芙嘗試并孜孜不倦地進行實驗的寫作技巧。意識流的采用為我們展示了達洛衛夫人、史密斯、彼得等人的內心世界。讓我們站在他們的角度來思考他們的問題,使我們因此了解了達洛衛夫人和彼得的過去;達洛衛夫人和彼得彼此現在的感覺;史密斯精神錯亂的原因;史密斯對世界和生活的認識,等等。通過他們自己的語言,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們思緒的流動和變化,使我們更真切地體味他們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
在小說里,伍爾芙并不是單一地采用一種視角,而是將二者相互結合,相互滲透。使全知敘述者在滲透一切客觀事物的同時也將人物的主觀內心世界聯系起來,展現出一個主客觀交融的生活場景,讓讀者能在更大程度上理解該小說。這樣一種敘事視角也是反傳統的。它讓讀者在習慣了客觀描述的同時,一下走進了人物的內心深處,在不斷流動的意識世界中漂浮,前進,從而更深刻地感受小說人物的心靈變換和思想更替,加強了理解難度和認知程度,從而達到陌生化的效果。
語言運用的陌生化
小說作為藝術的創作,要實現陌生化首先要實現語言的陌生化。在《達洛衛夫人》中,伍爾芙靈活地采用了自由間接式敘述話語。自由間接式敘述話語通常省掉了引導語,人物語言不加引號并且十分自然地融入小說的原來的敘述話語之中。這種敘述方式能最大限度、最自然地將人物語言和內心活動融入到小說整體的敘述節奏中,給人一種渾然一體的感覺。例如在達洛衛夫人經過花店附近公園時就這樣對自己說道:
“她向邦德街走去,捫心自問:她必然會永遠離開人世,是否會覺得遺憾?沒有了她,人間一切必將繼續下去,是否會感到怨恨?還是欣慰,想到一死便可了結?不過,隨著人事滄桑,她在倫敦的大街上卻能隨遇而安,得以幸存,彼得也活過來了,他倆互相信賴,共同生存。”
這里,達洛衛夫人自己的語言突然就插入了作者安排的第三人稱的全能的敘事語言中,而不帶有一絲呆板的痕跡,一切都顯得自然而又流暢。這種自由的插入和轉換給了作者極大的自由度在小說各個人物之間轉換,在各種不同的世界觀不同的人物感受之間隨意移動游走,從而更好地為讀者展現一個更全面、更生動以及更具包容性的文本世界。
雖然自由間接式敘述話語的運用能讓人物和整體敘述達到渾然一體的效果,但是對讀者來說,這種安排卻加大了理解的難度。引號的省略使讀者往往得仔細地去分辨哪里是小說敘述者的語言,哪里是小說人物的語言。也正因為如此,意識流類型的小說,例如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伍爾芙的《海浪》、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等意識流經典之作,總會讓讀者有種受挫、費解、想要逃避的感覺。因為它們的人物內心話語的流動是無拘無束、隨感覺而延續的、流淌的。因此對讀者來說,它們的語言是高度的陌生化的語言,必然加大了讀者閱讀的難度。
作為意識流小說和現代主義小說的代表人物,弗吉尼亞·伍爾芙對小說陌生化的處理也是不遺余力。《達洛衛夫人》里她在行文結構、敘事視角以及語言運用的陌生化處理方面表現出精湛的藝術技巧和別致的藝術獨創性。在她反對傳統創作方式以及主張小說創新道路的創作生涯里,她也不斷地對藝術技巧以及多樣性的人生進行求知和探索,為我們展現出一個別樣的多彩的世界。
[1]Virginia Woolf.Mrs. Dalloway[M].London:Random House,1928.
[2]Raman Selden.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M].Kentucky: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6.
[3]弗吉尼亞·伍爾芙著.達洛衛夫人[M]. 孫梁,蘇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
[4]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5]弗吉尼亞·伍爾芙著.伍爾芙日記選[M].戴紅珍,宋炳輝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
[6]安德魯·桑德斯.牛津簡明英國文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