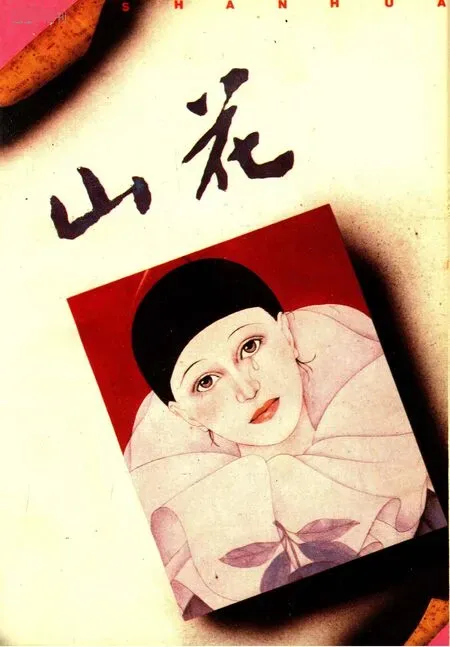鄉村發廊
黃水成

平寨村趕集這天,來趕集的四方鄉鄰都被“東芝發廊”給電了一下。
一間普普通通的“先東理發店”,怎么一夜間就變成了“東芝發廊”呢?被吸住的目光恨不能透過那低垂的珠簾再拐個彎兒,好看清這粉紅色發廊屋里的主人還是不是原來的那個剃頭匠——先東。
慶華叔是個受人尊敬的退休老教師,這天他也來趕集。他趕到集市時,太陽已在鷓鴣山頭一丈高了,他掏出手帕拭去額頭的汗水。鄉村集市不大,近年來,鄉下的年輕人開始往城里跑,集市也日漸萎縮,從早先的大榕樹下一直萎縮到橋頭。如今只剩下橋頭這一段是集市。集市雖小,卻依然是十里八鄉最重要的交易場所,市場上照樣擺滿了雞鴨鵝豬狗貓的攤子,有些人連牛羊都牽來了,街上連同那些賣斗笠的、賣鋤頭鐮刀扁擔的、還有賣那些花花綠綠的衣服首飾的,各種叫賣聲此起彼伏,和公路上的塵土一塊飛揚。
不斷抬手和鄉鄰們打招呼的慶華叔走到發廊門口,扶一下老花鏡才看清“東芝發廊”這塊招牌,他回過頭來問:“這不是先東理發店嗎?”所有看他的人都含笑對他回答說:“對,就是這間。”
慶華叔掀起珠簾徑直走了進去,看他進去的人看到,先東先迎向慶華叔點了頭哈了腰,慶華叔好像也點了一下頭。墻上的那面大鏡子還在,原先那張木制的大轉椅不見了,旁邊那張長條凳也不見了,連那個鐵皮桶和桶下那個洗發池也不見了。慶華叔低頭尋來一張粉紅塑料椅子,他拎過來在美容鏡前坐下來。要在往日,這時先東就會過來,先幫他解開中山裝外套和襯衫的第一個扣子,把領子窩進去,圍上一條毛巾,再披上大布,扎好,就開始理發。慶華只要坐在椅子上,后背往椅子上一靠,就可以舒舒服服地享受半個多鐘頭。慶華叔每次來先東理發室都有這個感覺。
先東是集市上最好的一名理發師,手藝是家傳的,那年高考落榜后跟父親學了這門手藝。手藝學成半年后,他父親中風走了,這間店就傳到他的肩上了。先東性子好,老少無欺,大家都上他這里來理發。別看他年輕,理發技藝一點不比父親差。他可以拿面鏡子放在后腦勺外,自己給自己理發。他幫人剪的平頭像用尺子量過一樣,平整得很。無論是頭頂還是發墻,他剪過的地方,沒有一絲不妥帖、不齊整。頭發剪好洗凈后,先東一踩開關,把人放下來,半躺在椅子上,開始細致地打磨客人的臉。有時他還和前來理發的人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話,說著說著,客人就睡著了。到他這來理發的人多半是睡著的,先東需要修右臉,他就把轉椅往左邊轉個角度,把客人的右臉挪過來;要修左臉,就把椅子往右邊轉個角度,再把客人的左臉挪過來,客人一點動靜都沒有。舉手投足之間,毫厘不差,鬢毛、汗毛、胡須、眉毛,甚至鼻毛,一把剔刀外加一把剪子,他就能把一張臉一一幫你收拾得光滑油亮。最享受的是掏耳朵,一把細細的小刮刀,他能恰到好處地伸進耳朵里,不深不淺,像個小陀螺一樣,一圈一圈地轉起來。那種似乎疼又似乎癢,酥酥的,麻麻的,酸酸的,拿捏得那個準呀,增一毫則疼,減一毫則癢,那舒服勁無法言說。天大的煩惱被他一掏耳朵就掏沒了。老人們尤其信賴他的技藝,就是為了這個,也會來這里。理過發后很多熟客都朝先東豎大拇指,下次還一定來他這里理發。盡管如此,先東卻常感慨:“唉,也就換碗飯糊口罷了。”
開始,大家以為他只是說說罷了,這種小營生不就是養家糊口而已,難道還指望它發財。誰知先東真的去了特區。這可急壞了他的那幫老顧客,除了他這家,誰也不掏耳朵,要么是掏不好,要么就是不會掏。大家開始等,特別是像慶華叔這樣上了年紀的人,無一不在等他。好在他沒讓大家等得太久,也就兩個月光景,就回來了。見他回來,大家都急著要上他這來,誰知,他回來不重操舊業,卻開起了發廊。集市附近人家都知道他開的是發廊,再沒人來。慶華叔不知道,他只聽說先東回來了,又碰上趕集,就急著要把長了兩個月的頭發理了。
慶華叔坐下,先東只在一旁搭話。慶華叔說:“來吧!”
集市上發出一種低低的笑,這笑如同那晃蕩的珠簾還沒停歇下來,一個女孩子端杯水就向慶華叔走過來了。人群中又發出“哇”的一聲驚嘆。那女孩涂脂抹粉,燙個卷發,長筒黑襪,皮短裙。集市上的眼睛又被“電”了一下,都等著看慶華叔他接下來的內容。她請慶華叔向店里深處走去。
“聽不清,好像是……”
游手好閑的半丁捂著嘴巴向大家傳話,他剛從賭場回來,耳朵貼到門柱上聽里面的動靜。他希望聽出一些動靜好跟大家傳話,脖子還往前伸,慶華叔剛好撩開珠簾,差點和半丁撞個照面。慶華叔“哼”了一聲大步跨出發廊。大家看他醬紅著臉,低低地會心一笑。慶華叔一轉身,指著“東芝發廊”大罵一聲:“傷風敗俗!呸!”消失在人群中。
“老頭子速度太快了吧!”半丁對著他的背影朝大家扮鬼臉說,人群中終于發出響雷般的笑聲!
挑著一籠雞來賣的馮友三跟半丁打賭說:“你要是敢進去,我馬上送只雞給你補補。”
“我才不稀罕呢?”
“不是不稀罕,而是不敢。”
“誰說不敢,我進給你看。”半丁抬起一只腳又縮了回來,“我才不上你的當呢。”
人群中又一陣哄笑。馮友三說:“你不是不敢,你是不會,人家慶華叔是只雄雞,你是‘閹雞,不然到三十多歲都不想娶老婆。”半丁不理會馮友三,他可是遠近聞名“大炮”嘴,誰也斗不過。
半丁走了,慶華叔又折了回來。大家看他手里拿著米糊和紅紙徑直走到“東芝發廊”門前,直接把紅紙糊到“東芝發廊”上,紅紙上寫著:傷風敗俗!
慶華叔的紅紙還沒糊好,先東就沖出來了,他一把撕下剛糊上去的“傷風敗俗”,沖著慶華叔大吼一聲:“你這是干什么,我礙你什么事,啊,我偷你還是搶你啦?”
“反正就是傷風敗俗。”慶華叔一臉憤怒地拾起一根扁擔要捅下“東芝發廊”這塊招牌。
“小妹,接客!”先東朝里面喊了一聲,馬上跑出剛才給慶華叔端水的那個女孩,不由分說地要拉慶華叔進去。慶華叔一甩袖,落荒而逃。先東這才朝各位鄉鄰一拱手說:“各位鄉親,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咱們各謀生路,誰也不礙著誰,不然休怪我翻臉。”endprint
慶華叔沒走遠,他覺得今天沾了晦氣,先東是他教過的一個好學生,他不相信他會墮落到這般田地,所以他才一心想砸了他的招牌,好讓他回到正道上來。慶華叔又走了回來,他搬把椅子在“東芝發廊”對面的阿胖飲食店坐下來,他對四方趕集的鄉鄰說:“我看誰進去,我就記下他來,然后把海報貼到各村頭去,看他有何臉面做人?”
大家聽了又哄堂大笑:“是是是,慶華叔你做得對!”慶華叔見大家幫腔,越發抬高嗓子說:“大家伙兒知道什么叫發廊嗎?告訴大家,人家城里人叫雞店,過去書上叫青樓,又叫窯子。”說著他一指馮友三的雞籠子說:“干那營生的叫什么知道吧?就是那東西,人家大城市是十里洋場,有這東西不稀奇,你看那后生干什么營生,啊,去了幾天特區,連把推子剪子都拿不起來了,耍起花花腸子來了,想吃軟飯,賣祖宗臉面呀!”慶華叔唾沫星四濺的演說,所有人都聽得有滋有味,正說著今天趕集太有意思了,只見慶華叔的老伴春花婆匆匆趕來。可能有人告訴她慶華叔進了雞店了,還被人拖過,這還得了,她男人一生清白還得了,跳進三河壩也洗不清了。
你看她哭喪著臉,捶著胸,“雷打的呀,天沒長眼是吧,竟欺負一個老頭子。”說著從路邊角落便桶處,舀了一勺尿就要去潑“東芝發廊”。先東站出來迎向春花婆說:“你要是敢潑下去,我讓你家連只跳蚤都養不活,地里別想長一粒糧食,統統藥死,統統掃光。”春花婆還真被他給唬住了。慶華叔走上前來拉了一把老伴說:“你來湊什么熱鬧。”轉身沖著“東芝發廊”說:“完了,沒救了!”就和老伴一塊消失在回家的鄉村小路上。
集市一散,“東芝發廊”的名聲就傳遍了十里八鄉,甚至更遠的地方。
過了很多天,慶華叔又來趕集,看“東芝發廊”沒有開門,他問對面飲食店的阿胖說:“關了?”
“我哪知道。”阿胖說。
“你撒謊,誰半夜到你店里吃過點心你會不知道?”隔壁裁縫店阿芬揭穿阿胖的鬼話。
阿胖臉一紅說:“我哪知道他們從哪來?”阿芬繼續刮自己的臉在羞阿胖。
阿胖和阿芬從小就是一對歡喜冤家,阿胖明顯在撒謊,他哪不知道,本地的,外地的,都來。現經阿芬一搶白,他脖子陡然粗了起來:“我才不管那些鳥事呢,開發廊有什么,省得那些沒老婆的人老到寡婦店里去守夜。”
阿胖這話刺了阿芬的心,他男人剛走半年,半丁就常坐到半夜不走,她沉下臉說:“哇,好福氣喲!對面搬來好鄰居,一個好吃,一個好賣,得了便宜還賣乖。”
阿芬的話得到左右鄰居的幫腔,她隔壁的梅花嬸說:“這成何體統,還真有那些不要臉的人敢上那兒去,就他一家,就把我們一條街的腰都給閃了,慶華叔,你該管一管,都什么世道。”
“我們大人倒沒什么,我就擔心把孩子給教壞了,你看一天到晚,孩子們來來回回地往里瞧,還編著歌唱:發廊,發廊,夜夜新娘。惡心哪!”鞋店的友仁叔也氣憤地向慶華叔倒苦水。大家越說越氣憤,原本很平靜的集市,被這家發廊一攪,弄得大家神經都脆弱起來,還沒人管。大家嘰嘰喳喳地議論開來。
“什么亂七八糟的,我要去找派出所。”慶華叔氣沖沖地找派出所去了。“還是慶華叔受人尊敬。”友仁幾個朝他遠去的影子說。
半天后,大家看見慶華叔垂著頭回來了。他從集市上走過時,先東剛好開門撞見,先東說:“慶華叔,進來放松放松,我讓小妹動作輕點兒。”慶華叔氣得身子發抖,剛才派出所的人也這么對他說的,還說什么這是改善招商引資的軟環境。他朝派出所的人啐了一口說:“招商引雞,缺德。”掉頭就往回走。現在他朝先東也啐了一口走了,身后傳來一陣怪笑。之后,慶華叔來趕集明顯少了。
半年后,先東得了怪病,全身浮腫,“東芝發廊”關了。集市好像又回到原先那樣子,一條塵土飛揚的公路,除了雞鳴,就剩狗跳。那天,慶華叔還拄著一根拐杖到“東芝發廊”店前放了一串鞭炮,走了。之后,慶華叔來集市越發少了。“東芝發廊”關了三個月后,人們才重新見到慶華叔的身影,他的背明顯駝了,但步子還是邁得很有精神。慶華叔走到原先的“東芝發廊”停了一下,看見“東芝發廊”旁邊竟一下冒出“小妹發廊”、“小妮發廊”、“纖纖發廊”三家發廊出來。慶華叔給電了一下,竟呆住了,待他回過神來,掉頭從另一條小路繞過集市。往后,就沒見他來趕集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