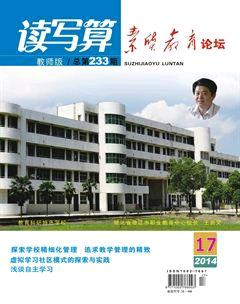論文學作品藝術闡釋的未定性
原曉蕓
中圖分類號:G63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661(2014)17-0002-02
文學藝術世界是一個恢弘博大的世界,它包含了作者的人生體驗和審美追求,成為讀者作無限品味的自由廣闊的天地。古人云:“聲無聽一,物無文一,味無果一”(《國語?鄭語》)今人曰:“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萊特。”精確地闡釋之于文學藝術何其難矣!對文學作品作藝術的把握,是一個復雜的審美過程,文學作品的典型形象的復雜性、主題意蘊的模糊性、審美個體的差異性決定了藝術闡釋的未定性。傳統闡釋中的那種章句訓詁式的抱殘守缺,狹隘單一的明白無誤,只能肢解、扭曲作品的審美價值,誤導讀者,銷蝕掉文學作品無限的豐富性、生動性及深刻性。研究文學作品的藝術闡釋的未定性,正是為了使讀者從評論家的視野中跳出來,在由讀者積極參與的閱讀過程中進入作品無限豐富的自由天地。從而深刻地把握美感效應的多樣性,更好地發揮欣賞主體的主觀能動性,最大限度地發揮文學作品的美感因素。
形成文學作品闡釋的未定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從典型形象、主題意蘊、審美個體幾個方面予以論述。
1.典型形象的復雜性
文學作品中的典型形象是作家對現實生活藝術發現的結晶,是作品處于最高審美層次的藝術形象,是“理想藝術表現的真正中心”。它除了一般藝術形象的特點外,還具有高度的審美獨創性和豐富多彩的個別性。關于藝術典型復雜性,歌德精粹地概括為“單一的雜多”。在中國古典典型理論中,脂硯齋最是反對“惡則無往不惡,美則無一不美”的單薄淺顯。成功的典型形象,總是呈現出多側面的立體結構,表現出“單一雜多”,人物的性格以復雜性、流動性、以至于矛盾的對立性而存在。普希金曾將莎士比亞和莫里哀創造的人物形象作比較道:“莫里哀的慳吝人只是慳吝而已;莎士比亞的夏洛克卻是慳吝、機靈、復仇心理重,熱愛子女而銳敏多智。”
《阿Q正傳》是中國文學史上也是世界文學史上的“一座高高矗立的豐碑”。但對阿Q這一文學典型的爭議,也是文學史上最為罕見的。解放后,數十位文學家為此撰寫了二百多篇分析評論,不少高等院校曾舉行過阿Q典型性問題的討論,眾說紛紜。綜合起來,有以下幾種:“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國民族所特有的,似乎是人類普遍的弱點的一種,至少,在“色厲內荏”這一點上,寫出了人性的普遍弱點來了。(茅盾《讀〈吶喊〉》)阿Q性格的特殊并不在于他所代表的農民以外的人群而言,而是就在于他所代表的農民中,他也是一人特殊的存在。(周揚《現實主義試論》)阿Q的精神勝利法是奴隸的失敗主義精華,奴隸的被壓迫史,才正是阿Q主義的產生史。(馮雪峰《過來的時代》)對阿Q的“大團圓”的結局,至少在人格上不統一,似乎是兩個(鄭振鐸《吶喊》)當前,文藝研究者認為阿Q是一個呈對立統一的圓形結構系統。他在性格上是一個具有兩重人格的復合體:既樸質愚昧而又圓滑無賴,既率直任性而又正統衛道,既自尊自大又自輕自賤,既爭強好勝而又忍辱服從,既狹隘保守而又盲目趨時,既排斥異端而又向往革命,不安于現狀又安于現狀,憎惡權勢又趨炎附勢,蠻橫霸道又膽小怯懦,敏捷而又健忘等等。對這樣一個復雜而深刻的典型人物,闡釋為“尚未覺悟的貧苦農民”,“破產農民”⑤是“一個物質上受到殘酷剝削,精神上受到嚴重摧殘的農民典型”⑥,遠遠不能準確地闡釋出魯迅創作這一形象的目的和態度(“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靈魂來”,“是想暴露國民的弱點的”⑦)也不能幫助讀者認識作家塑造藝術典型具有的高度的審美的獨創性,豐富多彩的個別性以及人物的復雜性。
2.主題意蘊的模糊性
藝術的本質,是人對世界掌握的一種方式和對自身的肯定。文學藝術的活動,一方面要獲得對于客觀世界真理性的人識,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顯示自己的智慧和理想,以至于實現自己的品格和個性,滿足于審美的需要。文學家對客觀世界的真理性的認識,表現出與哲學家的不同,“一個是證明,一個是顯示。”這種以形象思維為主要特征的圖情再現,必然表現出不確定性、多義性、甚至模糊性。優秀的文學作品,決不會“把個人變成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總是把“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同莎士比亞劇作的情節的生動性和豐富性的完美的融合。”恩格斯甚至說:“作者的見解愈隱蔽,對藝術作品來說就愈好。”文學作品不等于宣傳品,不是那種朝生暮死的東西。經典作品的主題意蘊有著超越時代的永恒與隨世推移的變更出新,在巨大的歷史內容中隱藏著較大的思想深度。不同時代、不同的欣賞主體對作品的理解就會發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現象 。作為對作品闡釋的評論家,不能是僅僅幫助讀者去尋找概念、抽取意義,而是要引導讀者在欣賞藝術形象的過程中,潛移默化的、多維多向地理解作家的美學情趣,理解作家對客觀世界的理解評價,從而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作家在作品中所散發的思想感情。
李商隱的《錦瑟》一詩,辭彩華誕,形象鮮明。但主旨為何,一千多年來眾說紛紜,見解各異。有愛情說的:錦瑟是令孤楚家中的一個女子的名字,李商隱愛慕過她,寫此詩以寄情(劉攽《中山詩話》);有悼哀說的:是悼亡妻王氏(馮浩《玉溪生詩箋注》);有詠物說的:是寫錦瑟這種樂器的,中國四句寫適、怨、請、和中種聲調(《彥周詩話》);有“自傷”說的,抒寫自己落拓失意,“美人遲暮”之感(張采田《玉溪生年譜會箋》);還有人說是傷唐室殘破的,真是“一篇《錦瑟》解人難”,其實我們只要透過那華麗的詞藻,富于暗示的形象,抓住“思華年”這條追憶的線索,去咀嚼詩中間四個典型情境,就可通過字面而進入詩的意境。“莊生曉夢迷蝴蝶”,是夏夜,是喜;“望帝春心托杜鵑”,是春夜,是怨;“滄海月明珠有淚”,是月夜,是悲;“藍田日暖玉生煙”,是秋日,是歡樂,它們交織出當年一年四時的朝、暮、日、夜的喜、悲、怨、歡,表出對逝去的美好年華的回憶,一種纏綿繾綣的情思。我們大可不必解得太實,說得太破。從而增強詩作的暗示性,給讀者更大的想空間。
3.審美個體的差異性
在藝術闡釋過程中,由于個體感受的差異性,形成了所謂“慷慨者逆聲而擊節,蘊籍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的現象。差異的存在一方面給藝術探索提供了多側面多層次的可能,給欣賞者的自由活動提供了無限廣闊的空間,另一方面也導致了藝術闡釋的見仁見智或偏執一端,使藝術闡釋顯現不確定性。生活經驗、學識修養、人生態度及審美情趣的不同,表現在藝術闡釋中就形成欣賞的側重點不同與欣賞效果的差異。
(1)生活經驗的影響。王安石讀到李賀的詩:“黑云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認為不可思議:方黑云壓城之時,焉有向日之甲光耶?楊慎卻認為這是狀物的佳句,譏笑“宋老頭巾不知詩”,因為他曾在云南目睹過這種奇異的景象。
(2)文學功底修養不同。《祝福》,“我”與“四叔”見面后,“談話總是不投機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個人剩在書房里。”對這個“剩”字,汪曾祺解釋道:假如要編一本魯迅字典,這個“剩”字將怎么注釋呢?除了注明出處,標出紹興話的讀音之外,大概只有這樣寫:“剩是余下的意思,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孤寂之感,仿佛被世界遺棄,孑然地存在著了。而且,連四叔何時離去的,也都未感覺,可見四叔既是不以魯迅(原文如此)為意,魯迅也對四叔并不挽留,確實是不投機了。四叔似乎已經走了一會了,魯迅才發現只有自己一個人剩在那里。這不是魯迅的世界,魯迅只有走。”
(3)審美層次的高下。杜甫《江南逢李龜年》:“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吳功正從社會歷史意識層面予以審美闡釋:表面看來,這是詩人寫他晚年和著名歌手李龜年的會見。但在深層結構里,“世運之治亂,華年之盛衰,彼此之凄涼流落,俱在其中。”(孫洙評)岐五宅里,崔九堂前,頻頻相遇,李龜年已是名重歌壇,詩人也已嶄露頭角在文壇。美妙動聽的歌喉和詩人少年浪漫意氣,都是跟烈火烹油的開元盛世相聯結的。往事如煙,過眼即逝,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盛況只能留嵌在記憶中了。而時過了幾十年,他們偶然邂逅,不是在岐王宅里、崔九堂,卻是在“江南”、“落花時節”。好景不再,透露出傷感。其間的幾十年,杜甫如轉蓬也似的離蜀、入鄂,輾轉漂到潭州。而李龜年也流落江南。其間的飄零各地,有幾多家國興亡,身世淪落;于晚年窮途相見,又有幾多感傷,詩人卻不正面置一詞,全部凝聚在今昔相逢如此不同空間地點、“落花”這一具有象征意味的時節之中。在詩的深層次中是安史之亂的國破愁、家世悲,如黃生《杜詩說》所言:“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絕。見風韻于行間,寓感慨于字里,即使龍標(王昌齡)、供奉(李白)操筆,亦無以過。”
由上可見,文學作品的藝術闡釋呈現出開放性、多義性和未定性,任何評論分析都有其相對的局限性。優秀的文學作品的思想意義。審美價值永遠不可能被什么人一次完整地感知。只有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積極地參與作品所敘述的事件,作品的審美效果才得以形成,藝術闡釋者不應以全知全能的身份去教導讀者,積極引導讀者去挖掘,發現文學作品的豐富寶藏。總之,更好地發掘文學作品的美感因素的無限豐富性。使讀者不必凝滯于評論家的既定模型,去獨立地發現文學作品的新的審美價值。這就是探究藝術闡釋的未定性的意義。
(責任編輯 全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