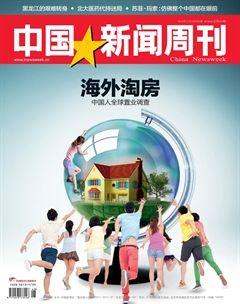“呼格案”內參記者:一場冤案的非典型平反
蘇曉明
在“左”與“右”之間,湯計有些搖擺。他說:“我不喜歡這樣的劃分,如果非要站隊,我寧愿站在中間。”
湯計身高1米83,身材健壯,聲音洪亮。作為“呼格吉勒圖案”再審的主要推動人,他最近聲名鵲起。
呼格吉勒圖案發生在1996年。嫌疑人呼格吉勒圖被懷疑犯有流氓罪和殺人罪,抓捕、取證、審問、公訴、一審、二審,所有司法程序在62天內進行完畢。呼格吉勒圖被判死刑。那時他只有18歲。
出于偶然,新華社內蒙古分社記者湯計得知此案,了解到呼格吉勒圖可能是被誤判,而真兇另有其人。從2005年起,他連續發了5份內參,借著新華社獨有的管道,直接向中央反映此案,每份都得到了中央高層的批示。
堅持9年后,今年11月20日,呼格案終于宣布啟動重審程序。本月初,內蒙古高級人民法院宣布了重審結論:呼格吉勒圖無罪。

湯計。圖/CFP
“我覺得當記者的第一要務是解決問題,這比報道新聞重要。”湯計說,9年來,呼格吉勒圖案成了他的心病,如果最終未能平反,他可能用整個余生來譴責自己。“9年的心血不能最終只畫了個‘逗號或者‘省略號,這不符合我的性格。”
“那些終歸都是物質,不是命”
湯計今年58歲。他從小家境貧寒,父母都是農民,目不識丁,因此讀書一直是他的夢想。但時運不濟。文化大革命斷送了他的學業。1971年,湯計年僅15歲,托關系進入天津大港油田。在人事關系上,他是一名鉗工。但他的真實工作,是在體工隊打排球。
沒有完成學業一直是他的遺憾。因此,1978年高考恢復以后,他就想方設法考進了新華社主辦的中國新聞學院。畢業后,他順理成章進入新華社山西分社,之后又調到內蒙古分社,專做政法報道,一干就是20多年。
他自信做過許多擲地有聲的報道,但無疑,只有“呼格吉勒圖案”的平反堪稱他事業的頂峰。
2005年,呼格吉勒圖已去世9年。他的父親李三仁和母親尚愛云,仍然生活在為有個強奸殺人犯兒子而無法抬頭的恥辱中。這一年10月,警察帶著一個新的“兇手”去當年的案發地指認現場。目擊這一場景的老鄰居將此事告訴了尚愛云。“你兒子可能是冤死的。”他們說。
尚愛云哭了一宿,第二天就去了公安局,滿心認為可以為兒子討回清白。
等待他們的卻不是清白,只有互相推諉。他們被區公安局推到市公安局,又被推到自治區公安廳。有的地方連門都進不去。老兩口從滿懷希望墮入走投無路。
別人告訴他們,伸冤要找律師。他們因此找到了內蒙古何洋律師事務所主任何綏生。“他是呼和浩特很有名的律師,希望能為我兒伸冤。”尚愛云說。
何綏生了解案情后,認為呼格吉勒圖案確實有問題,但考慮到一審二審的主要司法機關負責人仍然在位,而呼格吉勒圖卻已被槍斃,想要通過個人力量、依靠申訴來翻案,他認為不太現實。他支了一招——找記者,找媒體。
尚愛云和李三仁就這樣找到了湯計。
湯計還記得第一次見到李三仁和尚愛云的感受:“看到老兩口老實巴交的,立刻就體會他們老來喪子的那種痛。”
多年做政法報道積累的人脈此時派上了用場。湯計證實了老兩口聽到的消息,公安部門確實抓獲了一個殺人狂魔,而此人正與呼格吉勒圖案有關。
“你想想,當初被槍斃時,呼格吉勒圖剛滿18歲,被五花大綁,要被當做兇手槍斃,但案子不是他干的,他該多么無助。”湯計說。
這么多年,他見過無數求助者,有的被騙,有的家被強拆,但沒有一件像呼格吉勒圖案這樣讓他受到觸動。他說:“那些終歸都是物質,不是命。”
“不是依靠我一個人的力量走到今天”
作為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的那代人,一個普通農民家的兒子,湯汁身上仍有鮮明的時代特征。說到剛從中國新聞學院畢業的心情時,他會說,“就是想做個對國家有用的人”;談到作為一名新聞老兵的體會,他說“首先要在黨的領導下”。
這種復雜的情感,在湯計為“呼格案”平反的工作中顯得更加矛盾:呼吁平反本身,是對現有公、檢、法系統的挑戰;而他所能依靠的,也是公、檢、法內部“有良知之士”。
最早的消息來自時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長赫峰。赫峰向他證實,確實抓獲了一個系列命案的嫌疑人趙志紅,此人的供述中有1996年的毛紡廠命案。
湯計馬上派了一名年輕記者到毛紡大院還原趙志紅指認現場的經過,自己直接去了趙志紅專案組。專案組有人告訴他,內蒙古公安廳已經成立呼格吉勒圖案復查組,然而有些領導不愿再翻這樁舊案,復查難度極大。
2005年11月,湯計發送了第一篇內參《內蒙古一死刑犯父母呼吁警方盡快澄清十年前冤案》。內參很快得到中央有關領導批示。2006年3月,內蒙古政法委正式成立“呼格吉勒圖流氓殺人案”復查組。當年8月,湯計得到消息,復查已有結論:當年判處呼格吉勒圖死刑的證據明顯不足。
一位自治區政法委領導告訴他:這是冤案,但不能由政法委改判,需要走法律程序。政法委會要求自治區高級法院復查,向最高人民法院匯報,兩家成立復查組,依法再審。
然而,2006年11月28日,突然有人向他傳遞消息說:趙志紅案已完成一審,但沒有公開審理,趙供述的10件命案,只起訴9件,惟獨沒有與“呼格案”相關的毛紡廠命案。
一年多來,湯計已搜集到了趙志紅的幾份口供筆錄,警方復核組、檢方領導、政法委領導及復核組成員的一些重要談話信息。這些材料都指向一點:“呼格案”或許是冤案。然而趙志紅的起訴中沒有涉及此案,是否意味著情況有變?
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湯計立即寫了第二篇內參《呼市“系列殺人案”尚有一起命案未起訴讓人質疑》。很快,這篇內參也受到了批示。
巧合的是,批示做出后不久,趙志紅在看守所里寫下了一封寄給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檢察院的“償命”信。
信中寫道:“我是‘2·25系列殺人案嫌犯趙志紅,我于2006年11月28日已開庭審理完畢。其中有1996年4月18日(準確時間是4月9日)發生在呼市一毛家屬公廁(的)殺人案,不知何故,公訴機關在庭審時只字未提!因此案確實是我所為,且被害人確已死亡!”他向檢察院申請派專人重新落實、徹查此案,“還死者以公道!還冤者以清白!還法律以公正!還世人以明白!讓我沒有遺憾的(地)面對自己的生命結局!”
一位看守所的警察把這封申請書的復印件親自送到了湯計手里。
湯計并不認識這位警察。他走進湯計的辦公室,先掏出證件證明身份隨后把申請書的復印件交給了湯計。他說擔心這封申請書最終無法到達高層,希望能通過湯計讓“大領導”看到。
沒有再多說一句話,這個警察就轉身離開了。他轉身走出辦公室那一刻,湯計說他非常感動。他從這名警察身上看到了一種發自內心的使命感,以及強烈的責任心。
來不及多琢磨,湯計為這份《償命申請書》加了一頭一尾,當天就寫成了一篇加急情況反映《“殺人狂魔”趙志紅從獄中遞出“償命”申請》,發往北京。
此后,湯計的焦慮便鎖定在趙志紅身上。趙志紅已審理完畢,盡管少了一件命案,依法仍能判處死刑。然而趙志紅一死,“呼格案”可能便永無大白天下之日。
幸運的是,趙志紅案沒有繼續進行。自寄出那封償命申請書后,他已在看守所等待了8年。
湯計覺得,這是來自冥冥中的神助。“如果這個案子不是遇到那么多有良知的警察,不是遇到政法委書記宋喜德、常務副書記胡毅峰的開明領導,可能從一開始就被壓下去了。所以,并不是依靠我一個人的力量,才走到今天。”
“嚴打有缺點,但不能把辦錯案都推到嚴打上”
湯計說,他的報道原則是“有喜報喜,有憂報憂”。不過,他多用內參來傳遞“憂”,公開報道中更多地報“喜”。“面對社會公眾時,媒體還是要更多報道正能量,看到這個社會好的一面。”
于是產生了一個有趣的反差。為“呼格案”伸冤,依靠的是法律、證據和程序正義;而談到為何選擇內參的形式時,湯計說,“因為領導的批示比外部輿論更有力量。”在談到如何依靠媒體輿論監督執法者時,他認為“媒體和執法者不應成為對立關系”。 “不要光盯著他們的缺點,他們也是人,你和他有什么不同?”他擲地有聲地說,“媒體應該和他們交朋友。”
他甚至也會通過內參為他們排憂解難。
比如,2009年時,湯計了解到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存在干警嚴重老化的問題,平均年齡達44.6歲,并且由于城市擴張,人口膨脹,原有的干警編制已明顯不足。基層警察長時間得不到休息,有的還得了抑郁癥。
湯計為此寫了內參。中央增加了1萬個文職政法編,警力不足得到極大緩解。
不過,他的另一則頗有份量的內參,恰恰也針對內蒙古公安系統的。
大約在2003年,湯計得知,包頭市公安局有一起極其惡劣的私設行刑室事件,主人公是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刑警三中隊原隊長李建華。李建華私設的行刑室里,有手銬、腳鐐、大頭針、手搖電話機等特制刑具,大頭針用來插指甲縫,老式手搖電話機則用來上電刑。通過這間行刑室,李建華常常不立案就抓人,用刑逼迫對方送錢,錢一到,就放人。包頭市大大小小“混混”,或有過犯罪前科的人,只要聽到“李建華”的大名,就會毛骨悚然。
湯計立刻核實情況,寫成內參。2013年底,李建華因犯有受賄罪、非法拘禁罪和徇私枉法罪,獲刑17年。案件審判后,湯計才轉為發表公開報道。
有時,他還充當不收傭金的“中間人”。
大約三年前,一個18歲的賣淫吸毒女“二進宮”,勞教戒毒所為節省經費,沒有例行體檢,但女孩事實上已經懷有宮外孕,不久便突發大出血,最終搶救無效死亡。
家屬到戒毒所討說法,又找到湯計維權。湯計沒有報道,而是直接從中斡旋,最后戒毒所賠付了20萬元,事情平息。
湯計同意是戒毒所的疏忽導致女孩死亡,但他認為戒毒所并非有意為之,女孩懷有宮外孕是任何人都沒想到的意外。在他的判斷準則里,“這是可以被寬恕的”,所以他選擇不報道,但要為雙方“解決問題”。
家長觀念、“善猜公權”以及傳統的善惡因果觀,統一在體制內媒體記者這個社會角色身上,湯計形成了自己的正義觀——對主觀動機看得極為重要。
比如,在呼格吉勒圖案復查過程中,他一直善意地認為證據丟失,系搬家時無意所為。然而對于“呼格案的錯誤部分系當時的嚴打政策造成”的議論,湯計卻十分不齒。“嚴打是要求從嚴、從重、從快,但沒讓亂打。”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據我了解,呼格案的二審審判長,沒有看卷就判案,甚至簽字都不是本人,這也是嚴打讓做的?嚴打有缺點,但不能把辦錯案都推到嚴打上;總批評制度,但再好的制度,執行的人不好,一樣會出問題。”
“體制內體制外,又能有多大區別?”
加急的情況反映“償命申請”發出后,再獲中央批示。但內蒙司法系統果然沒有收到趙志紅寄出的原件。
湯計還曾為此找到時任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邢寶玉,說:你那里有“腸梗阻”啊!
為了再有所推動,2007年,湯計系統地梳理了之前的材料,寫了第三篇內參:《死刑犯呼格吉勒圖被錯殺?——呼市1996年“4·09”流氓殺人案透析》,由于內參通常不宜過長,此文分為上下兩篇。
但收效甚微。經過了解,湯計認為案件重審進程卡在了自治區高院。“政法委開會研究(呼格案),高院派來的代表就是當年的審判長,他本應回避才對。”
湯計找到邢寶玉檢察長討論。湯計問:你怎么不抗訴?后者回答:如果檢察院抗訴,高院維持原判,這案子就沒救了。湯計說,那怎么辦?刑寶玉給出的辦法是:能拿出內蒙就有戲。湯計就此寫出了第四篇內參《內蒙古法律界人士建議跨省區異地審理呼格吉勒圖案件》。
此時,是2007年11月。緊接著,內蒙古領導班子換屆。之前主導復查此案的領導中,檢察長刑寶玉和政法委副書宋喜德退休,政法委副書記胡毅峰調任自治區人大常委會秘書長,新任領導都對這塊“燙手山芋”避而遠之。
湯計說那段日子最難熬。內參寫多了,領導也頭疼;他于是開始聯絡市場化媒體,尋求體制外媒體的支持。他認為這是一種戰術安排:內參領導直接批復,就形成自上而下的要求,對執行者的壓力更直接,也更有力;外部輿論形成的壓力,則是配合內力,內外呼應,缺一不可。
“我是打排球出身,輸了一定要贏回來。”湯計說。他想了很多辦法,還鼓勵李三仁夫婦去上訪。但他叮囑兩位老人:“上訪只是一項工作,千萬不要鬧,要快樂上訪。”
于是,每年1月初,內蒙古自治區兩會召開,湯計都能看到李三仁老兩口身影。那也是內蒙天氣最冷的時候,室外常常低達零下二十多度,老兩口就站在會場大院門口,瘦小的身軀,單薄的衣服,不哭也不鬧。每次見到,湯計心里都很難受,但又不能對他們說“在這站著沒用,回去吧”。他總是鼓勵他們要抱有希望。
老兩口持續上訪,市場化媒體的跟進,終于使此案在網絡上形成了一定的輿論熱度。湯計據此寫了第五篇內參:《呼格吉勒圖案復核六年后陷入僵局,網民企盼真兇早日伏法》。

12月15日,呼格吉勒圖的父母李三仁、尚愛云聽到再審結果后與新華社記者湯計相擁。圖/新華
恰好此時,胡毅峰從自治區人大調到內蒙古高院擔任院長,作為曾經推動此案復核的領導人之一,胡毅峰推動內蒙高院成立了復核小組,案件復核進入新的階段。
隨著四中全會發布《依法治國若干問題的重大決定》,呼格吉勒圖案再次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再審程序順利啟動。“這是全國媒體共同監督的典范。”湯計說。
12月19日,湯計受邀參加財新峰會“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分論壇”。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主任田文昌,最高人民檢察院理論研究所副所長謝鵬程等學者都在會上發言,認為當前中國需要司法獨立。可作為“呼格案”重審的主要推動者,湯計拋出觀點卻是:中國目前的國情還不適合司法獨立,更適合人治。
他后來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說:“法治社會是我們共同追求的目標,也是我向往的。”不過他說,他對公檢法系統了解得太深,因而缺乏足夠的信心。“司法獨立需要一代人接著一代人的普法教育才能做到,可能需要50年后甚至更久。”
對于體制內媒體人的說法,他也頗為不解:“體制內體制外,又能有多大區別?”他自認為堅持為呼格吉勒圖伸冤,靠的不是身在體制內,而是基本的同情心。“一個記者只要是好人,就會有同情心,有了同情心,就會有明辨是非的思想和能力,也就有了做事的動力。”
“既然如此,您認為法律存在的真正意義是什么?”
“懲治真正的惡。”湯計語氣堅定。
“什么是真正的惡?”
“比如明知是冤案但不作為,明知辦錯了案而不糾正。”
再審判決書送達時,湯計就在李三仁夫婦家。他說沒想到自己會哭,但老兩口抓住他的手一哭,他的眼淚也掉了下來。
尚愛云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些年來最擔心的事情不是案子無法再審,而是湯計被調走,“他走了這案子就沒人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