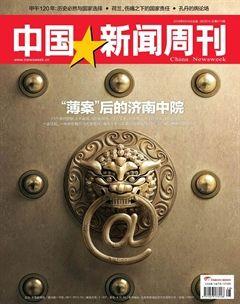政府不應該做什么
鄧聿文
有關政府與市場的話題,一直爭論不休。但一個基本的共識是,政府該做自己能夠做而企業和市場無法提供的事,企業和市場可以做的,政府無需做也不能做。
在前不久召開的經濟形勢座談會上,格力集團董事長董明珠當著總理李克強的面說,“現在最迫切的問題不是給錢,而是企業要協助政府,共同營造一個規范的經營環境。”她直截了當表示,“我們不需要國家的產業政策扶持!”“只要有公平競爭的環境,企業自己就可以做好!” 董明珠之所以能在其他企業都嘆苦的情況下講這樣的硬話,自是她的企業做得好。但別忘了,格力集團也是一家國企,而且是處于空調行業這個競爭最激烈的領域。
在此次座談會上,身為民企的東方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行也表達了和董明珠一樣的看法,“我們不需要政府補貼,我們就希望公平。希望國家有更嚴格的行業標準限制,讓市場主體發揮作用。”可見,在需要一個公平規范的市場環境上,國企和民企有著相同的感受。
對于兩位企業家的建議,總理認為“很有啟發”,要求現場相關部委負責人,都應該“聽一聽”。這個“聽一聽”,其實也有講究,是要這些部委負責人,明白企業真正需要什么。因為在中國,打造公平競爭的市場和政策環境,真正的推手是這些部委。國務院只負責宏觀政策的制定和決策,具體執行與監管是各級部門。它們肯不肯放手,決定著中國市場環境的好壞。
從中國發展市場經濟的經驗看,要政府為企業和市場主體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與政策環境,須力戒三種傾向:一是政府對企業大包大攬的父愛主義;二是地方保護主義;三是壟斷和尋租腐敗。
父愛主義來自匈亞利經濟學者科爾奈。用一句通俗的話說,“管你,是為你好”。這個詞雖是舶來品,但于中國卻有著根深蒂固的傳統。所謂“父母官”就是對它最好的說明。而在計劃經濟時代,父愛主義更是泛濫。改革后,雖然市場經濟的交換關系發展了起來,不過,由傳統和計劃時代養成的父愛主義思維卻被保留了下來,例如,不少政府部門及其官員總覺得自己比企業站得高看得遠,或者比企業更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仿佛他們不替企業做主,企業就不會做生意一樣。長久而言,它會產生兩個弊端,一是造成企業對政府的依賴性,企業一有問題,就會想著找政府解決。而對政府來說,并非所有企業都一視同仁,最受政府父母寵愛的,仍是國企,政府會給國企很多超經濟待遇,這是國企競爭力不強的一個主因。一些大的民企,也常受政府眷愛。二是導致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大。因為要為企業解決問題,需要相應的手段和資源,如果不賦予政府更多權力,政府就沒辦法實施父愛。所以,父愛主義的政府,一般都權力很大,且時時蘊含著擴權的沖動。這與市場經濟要求的簡政放權背道而馳。同時也是歷次政府改革成效甚微的一個因素。
此外,就是地方利益和保護主義在中國的市場環境里也大行其道,甚至愈演愈烈。地方政府動用行政權力設置市場壁壘,制造地區封鎖,有意分割市場,從而嚴重影響到統一市場的形成與發展。
從產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動來看,是需要一個統一、完整的國內市場的。但在中國,由于政企職能沒有完全分開,地方負有扶持本地企業和產業發展的責任,再加之央地事權和財權關系劃分不明確,中央下放的很多權力被地方截留,致使從市場角度看,中國形成了很多國中之國,一個統一的大市場被地方政府人為地分割成眾多的小市場,人為設置的行政壁壘、市場壁壘、技術壁壘、消費壁壘和采購壁壘,加劇了市場分割和地區封鎖。為保護本地利益,地方政府甚至呈現出對中央的疏離態勢,國家的宏觀調控每每遭遇到地方或明或暗的抵制。
上述二者外,壟斷和腐敗更是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的市場需要排斥的。通常而言,凡是非由市場自然競爭形成的壟斷,一般都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或賦予其市場準入權,或授予其市場定價權,或是動用其他政策資源扶持企業發展。壟斷的結果就是造成市場不公平的競爭。中國在國際上爭取市場經濟國地位,首先就需在國內打破壟斷。
壟斷總與各種尋租和腐敗相關。一個市場只要有尋租與腐敗,就不可能是公正的。
以上三者經常混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尋租和腐敗事實上充斥于政府給予企業的父愛關懷和地方保護中的,而地方利益從理念來說,它其實是另一種父愛主義。這些都會極大破壞市場的公平與公正。
簡政放權,清理負面清單,必須搞清政府不應該做什么。
在政府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的問題上,要有明確的認識,并在該放手的時候,堅決不伸手,做不到這點,就不可能有現代市場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