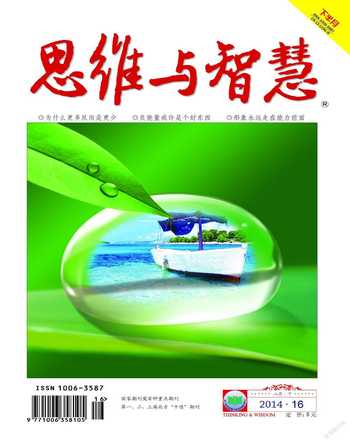紀曉嵐戲臺楹聯
鄭琦
紀曉嵐曾經擬寫過一副戲臺長聯,膾炙人口,傳誦甚廣。其聯曰:
二帝生,三王凈,五伯七雄丑末耳。漢祖唐宗,也算一時名角。其余拜將封侯,不過掮旗打鼓跑龍套;
四書白,六經引,諸子百家雜曲也。李白杜甫,能唱幾句亂彈,此外咬文嚼字,總是沿街乞討耍猴兒。
可以說,在中國汗牛充棟的楹聯寶庫中,此聯上下千古,聲大而宏,目光如炬,異趣天成。非紀曉嵐者,斷乎創作不出這樣精彩的作品來。
試讀上聯,作者將“二帝”——伏羲和神農(一說為堯帝和舜帝),比作舊戲中的行當“生”;將夏禹、商湯、周武等“三王”,比作“凈”(花臉);而春秋時五個強大的國君(即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戰國時的七個強大的國家(秦、楚、齊、燕、趙、韓、魏)——這“五伯七雄”,只是傳統戲劇中的“丑”(三花臉)和“末”(胡子生)。史上赫赫有名的“漢祖唐宗”,在作者的眼里,僅為“一時名角”。既然如此,其余“拜將封侯”者,充其量也“不過掮旗打鼓跑龍套”了。
下聯,繼續發揚蹈厲,議論風生。封建時代的經書“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只是“白”(戲劇中的念詞),“六經”:《春秋》《詩經》《書經》《易經》《禮記》《樂經》,僅是“引”(傳統戲劇時,角色出場的念詞);而從先秦到漢初各派學者及其作品——“諸子百家”,無非是“雜曲”(樂府歌曲,后也泛指戲劇的唱曲),李杜詩作,不外是“亂彈”(戲曲腔調名)。這么一連串地類比下來,其他“咬文嚼字”者,當然只能比作“沿街乞討耍猴兒”的流浪藝人了。
舞臺與生活的距離,歷史與當世的空間,是異質的,紀氏將之雜糅于一體,處理得了然無痕,隱喻、象征、反語、逆說,多種修辭方法并用,妙語如珠,寓莊于諧,遂使此聯有了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中國古代文論中,常常可以見到涉及對句的言論。《文心雕龍》把對句的形式分為“言對、事對、正對、反對”,后代文士則根據不同的表現形式分為“二十九種對”,林林總總,不一而足。
這一副聯語,運用了“緊句直對”、“出句直對”、“壯句直對”的多種形式。緊句直對,如——“二帝生,三王凈”對“四書白,六經引”;壯句直對,如“五伯七雄丑末耳”,對“諸子百家雜曲也”;出句直對,如“其余拜將封侯,不過掮旗打鼓跑龍套”,對“此外咬文嚼字,總是沿街乞討耍猴兒”。另外,從修辭的角度上說,它運用了“數目對”、“疊韻對”等技巧,擺脫了長聯對句平面、羅列的局限,使人覺得耳目一新,天高地闊。
學富五車、主持編纂《四庫全書》宏大文化工程的紀曉嵐,在這副聯語中,可謂小試牛刀,將中國舊文人吟詩作對的才華顯露得淋漓盡致!
(張建中摘自《潮州日報》2014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