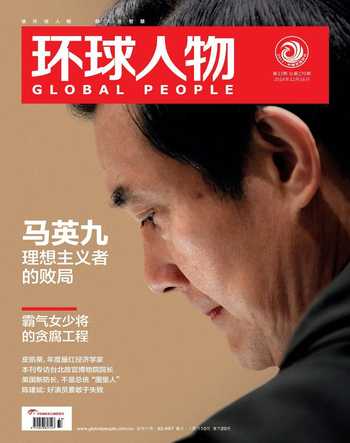陳建斌:好演員要敢于失敗
尹潔


個人簡介:陳建斌,1970年出生于新疆烏魯木齊,1998年研究生畢業于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憑借《結婚十年》《喬家大院》等作品獲得多個表演獎項。2011年在《后宮甄嬛傳》中飾演雍正,引起巨大反響。2014年憑借首次自編自導自演的作品《一個勺子》,獲得第五十一屆臺灣電影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和最佳男主角獎。
采訪開始前,陳建斌戴上了一副墨鏡,配上他穿的連帽衫,就像一個要去晨跑的運動員。“可能早年看東西太多,我的眼睛現在有點怕光。”他對環球人物雜志記者說,隨即露出一絲笑意,“然后就有很多(報道)說我怎樣怎樣……”
到底是“怎樣”,陳建斌不解釋。對于自己不擅長的領域和事情,他覺得沒什么可說的,“但談藝術、創作、戲劇方面的,我還挺能說的”。在不久前舉行的第五十一屆臺灣電影金馬獎上,他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一個勺子》拿下了最佳男主角和最佳新導演兩個重要獎項,人們仿佛在一夜之間意識到陳建斌的導演才華。說起這部作品以及與表演相關的話題,陳建斌根本停不下來。
《一個勺子》中的“勺子”是西北方言,諧音“傻子”。電影中男主人公拉條子是個牧羊人,有天在街上碰到一個傻子,拉條子給了他一點吃的,結果就被傻子跟上了,如影隨行。“好人難做”的拉條子為了幫助,也為了擺脫傻子,發生了一連串的故事。電影原著名為《奔跑的月光》,是河北作家胡學文寫的中篇小說。去年6月,陳建斌在《人民文學》第6期上第一次看到它時就激動不已。 “我很早就想導演一部電影,一直沒找到合適的劇本。直到看到這篇小說,特別吻合我的想法,能把我思考的問題都放進去。”陳建斌迅速買下版權,今年2月在甘肅省景泰縣開機,只用了一個月就拍完了。
陳建斌覺得生活里有很多和電影相似的故事:“拉條子想盡各種辦法要把傻子甩掉,都沒成,傻子成了他的包袱和痛苦,但時間長了,又變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當傻子離開的時候,拉條子悵然若失。這個過程我很喜歡,就像生活中一樣,我們身上有一些自以為或別人以為不好的個性、特點、習慣,很多人到三四十歲的時候會自我反思,想扔掉它們,但非常困難,因為這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扔掉后就不是你了。”
另一方面,是“好人難做”的現實困境,本是舉手之勞的善念變成一種負擔,并因此導致自我懷疑。 “我很小的時候,父親對我說要力所能及地幫助別人,比如街頭救助、給乞丐錢什么的。但前些年發生的一些事讓人們開始否定這一切。等紅綠燈時看到乞丐,以前我會毫不猶豫地給他們點零錢,現在卻開始糾結要不要這樣做?一個人倒在那兒要不要去幫他?我覺得比你沒幫他更糟糕的一件事,就是你在為這件事犯嘀咕。本來是天經地義、自古以來都很正常的好事,為什么到了現在會害怕擔憂?”
原本很正常的事情變成不正常,這讓陳建斌覺得悲哀,但他也無法提供解決問題的答案。他覺得唯一的辦法就是讓人們都開始思考這個問題。“不管你在CBD做白領,還是在農村放羊,對世界的感受是相通的。故事發生的地點、人物身份都是表象,今天各個地域的人們面臨的處境都有相似之處。看過這部電影的人,哪怕能有兩分鐘的思考,我就非常滿足了。”
為了把思考表達得更好,陳建斌把故事背景從河北搬到了西北,那是他從小生長的環境,西北人的特點他最熟悉。
1990年,陳建斌從新疆老家考入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他所在的班叫“新疆班”,是中戲專門為新疆話劇團培養人才的。四年后,別的同學都當了“北漂”,只有他一個人老老實實地回了新疆。兩年后,在大學老師的鼓勵下,陳建斌再一次考回中戲,念一個此前十幾年沒有招過生的表演碩士。“沒有人愿意念這個專業的研究生,大家都去拍戲了,但我挺喜歡讀書的。”陳建斌對記者說。
上大學前,他當了多年影迷,在很長時間里,他覺得自己不像是能當演員的樣子,但他仍然熱衷于參加各種文藝活動。“我就是喜歡這行。上大學的時候,老師教的,自己學的,沒有摻雜別的東西,能干這一行就非常高興了,其他的都是后來才有的。我也分不清藝術和商業,覺得能拍自己喜歡的戲就很滿足了。”
畢業后,陳建斌留校當過老師,演過多部孟京輝的實驗話劇。在話劇《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中,陳建斌飾演了一個瘋子,他先鋒的表演形式和臨場反應使這個角色成為了一個經典。2000年,在獲得了話劇“金獅獎”后,陳建斌逐漸遠離了話劇舞臺。
接下來是電視劇時代。2005年的《喬家大院》讓他獲得了第23屆金鷹獎“觀眾喜愛的電視劇男演員”,同時也認識了妻子蔣勤勤。2011年,導演鄭曉龍找他演《后宮甄嬛傳》里的雍正,陳建斌覺得劇本不錯就接了,他說自己沒看原著小說,人物資料都是從歷史書里查的。當時誰也沒想到,這部戲能火成后來的樣子。
20年的演員生涯,給了陳建斌很多創作的機會, 創作中矛盾總是免不了的,他覺得這最正常不過了。“按部就班,啥也不說,那不叫創作;只有大家坐在那里七嘴八舌,忘了誰是領導誰是員工,討論得熱火朝天,那才是創作。”拍《喬家大院》時,媒體爆出所謂陳建斌“耍大牌”的內幕,他自己是幾年之后才聽說的,“我當時一門心思在演戲,人特別投入地干一件事情的時候,根本不知道周圍發生了什么。過了些年跟別人聊天才知道,啊,當時你們是這么說我的啊。”
陳建斌不善于交際,“娛樂圈的事情我不太了解,當然應酬每個人都有,在我這個年紀,那是生活的一部分,必須得去的場合我會去,就在那坐著唄,但我不是那種呼朋引伴、扎堆攢局的人。我從來沒有為拍戲的事去應酬過,以后也不會,這不是我的生活。”
粉絲數量和收視率也不是他考慮的事。“我就是一個普通演員,做自己喜歡做的事,至于別人喜不喜歡跟我沒多大關系。說實話,能把演員這個職業做好對我來說已經很難了。”
陳建斌的碩士畢業論文題目是《試論演員的理解力》。在他看來,做這個行業的先決條件是有天賦,然后通過不斷地學習,才能把天賦發揮到極致。“演員的力量來自于表現力和理解力,為什么這樣表現來自于你對人物、生活、歷史背景的理解,理解到位了表現出來的自然也就到位了。”
在他看來,如今大部分演員都是本色演員,塑造所有角色都是一個模式。“能塑造不同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的演員非常少,因為首先要有天賦,然后努力學習,還要不斷實踐。但最關鍵的是要敢于失敗。他要把演上一個角色的所有方法扔掉,像丹尼爾·戴—劉易斯(三屆奧斯卡影帝)這樣偉大的演員也有很多角色是不成功的,但他敢于一次次嘗試,才能留下那幾個最經典的角色。而大多數演員別說沒有這個能力,就是有也根本不敢。一兩個角色演砸了,演藝生涯可能就毀了,誰敢拿自己的事業開玩笑?”
導演的才能同樣源于天賦加努力,用陳建斌的話說:“一個鏡頭背后是導演所有生活修養的積累。”他把自己的導演能力歸結為做演員學到的一切。“上學的時候,我們的學習方式就是大家互為導演,后來我又拍了好多年戲,接觸過形形色色的導演和班底。其實真正在現場拍戲的時間很少,演員大多數時間是在等待拍戲,看劇組如何準備,觀察他們怎么拍。”等到一切就緒,陳建斌便轉身進入了他的“導演時代”。
“錢不是一個大問題。現在很多年輕人什么作品都沒有拍過,也能找到錢拍戲。真正的問題是你能不能找到一個好劇本、好創意,以及做這件事的激情,只要有了這些就不會遇到什么困難。”陳建斌真心覺得現在是拍電影最好的時候。第一不缺錢,第二膠片時代已經過去,數碼時代大大降低了拍電影的門檻和制作成本。“不用考慮片比,想拍幾遍就拍幾遍,這還不夠好嗎?”他記得自己第一次拍電影是在1997年左右,當時的片比是一比一,就是每個鏡頭只能拍一條。“導演、攝影師、演員,都緊張得要命,一個鏡頭要提前排練很多遍,生怕這條拍壞了。在那種情況下不可能拍好,搞藝術還是要放松的狀態。”
不差錢,那為什么好作品那么少?“最重要的還是我們缺乏創意。技術花錢就能做到,可想象力和創造力我們太缺了。需要運用腦力和智慧去寫的劇本,中國有多少?創作者本身對電影、對生活、對藝術的理解,各個方面思考得不透徹,或者說沒有沉下心去做研究,可能大家把注意力都放到別的方面了吧。”
“藝術創作者不要給自己找借口,” 在陳建斌看來,被圈內人詬病已久的審查和監管并非問題所在。“你要不行,把你放到好萊塢,拍出來的一樣是爛電影;把卡梅隆放到中國,一樣能拍出好電影。從某種程度上說,藝術是毀于自由,而生于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