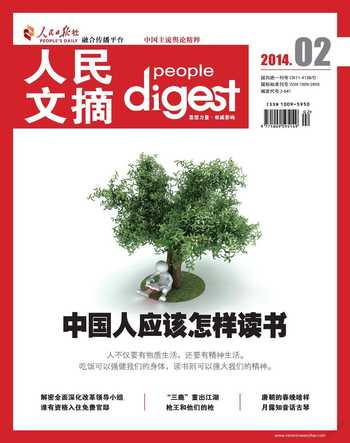“殺馬特”,讓我慢慢靠近你
王潔

優酷網上有一個視頻叫做《殺馬特遇見洗剪吹》,內容是一個長腿女生改編了韓國流行歌手“鳥叔”樸載相的歌曲《紳士》,被觀看了超過240萬次。在微博上,“殺馬特”一直是一個高頻率用詞,但是,它幾乎都是作為審丑狂歡下的貶義詞而存在。他們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群體?今天,讓我們慢慢走近“殺馬特”。
不懂英文也算“殺馬特”
早上6點,王健從西北旺的出租屋中起床,穿著睡衣褲到走廊里的公共衛生間洗漱。他一邊哼著《最炫民族風》,一邊蘸著自來水打理著才染成黃色的頭發,準備開始一天的生活。
王健今年23歲,從安徽蕪湖來北京快4年了,換了七八個工作,干過發廊、做過保安、當過司機,曾自己開過小飯館,如今在西北旺一家洗車行工作。
在北京這四年時間,王健雖然還說了一口標準的普通話,但已逐漸變成一個標準的“殺馬特”,雖然他自己還不是很明白“殺馬特”的確切含義。因為他的英文程度僅限于說“拜拜”和“三克油”,他怎么會明白這個音譯于“托福”單詞的詞匯已經變成自己的代名詞?“殺馬特”其實音譯于英文smart,意為時尚的、聰明的。但由于文化知識精英的話語壟斷與價值重構,讓“殺馬特”從“smart”一翻譯成中文,就成為了其反義詞。
王健的中專都沒有畢業,小學時也曾考過90分以上,但到了初中因為抽煙、逃學,學習成績逐漸滑坡,勉強上了當地的技校,家里還指望他能學一技之長,但是生性不愛學習的他因為一次打架,被學校除了名。一氣之下,王健決定自己到北京發展。
“殺馬特”的群畫像
在人們的眼中,“殺馬特”們是這樣一個群體:留著怪異發型,穿著夸張,佩戴古怪,濃妝艷抹,氣質詭異,來自農村或城鄉結合部的90后青年。
王健和他的朋友很符合“殺馬特”的這些特征。在西北旺的出租屋里,有不少王健的朋友,他們一樣染著五顏六色的頭發、穿著動物園淘來的“時髦”衣褲,閑了就鉆網吧,除了打游戲,最喜歡做的是整理自己的QQ空間,把蹲廁所時的一系列自拍,從山寨手機上傳進QQ空間。有時通過視頻聊天認識新朋友,就約到附近的大排檔吃個烤串、喝點啤酒,或者打打紙牌,樂得悠閑自在。
“殺馬特”,其實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青年亞文化現象。這些“殺馬特”青年們,與近年流行起來的“洗剪吹組合”形象一起,構成了當下中國一個值得關注的群體:新生代農民工。
一眼可以看穿的“殺馬特”
王健和朋友們有著類似的經歷,從學校走出后,直接離開了家里人,進入了鄉鎮以上的中小城市或大城市的城郊,租住價格較低的民房或地下室,且是多人合租。他們都是理發店員工、保安、餐館服務員、富士康的工人,也不排除在一些灰色和黑色地帶的工作。和他們父輩很多都從事建筑業的苦活累活不一樣,他們很難承受如此高強度的體力活。他們這個略顯焦急的圈子,也是以同齡的老鄉為主。當然,也延伸到網絡世界,通過玩勁舞、QQ視頻等,結識同齡的同興趣愛好的網友。他們在身份層次與文化價值觀上,有著較為顯著的特征。各種網絡口水歌是他們的最愛。
當王健得知自己被稱作“殺馬特”時,難免吃了一驚。來到北京后,他一直努力構建一個自己心目中理解的城市人形象。他試圖模仿,這在他們的群體中是一種風潮。他和朋友們一直在試圖接近城市文化,成為他們的一員。然而,他們的自認的流行時尚,在眾多城市人看來,卻是驚悚、夸張、土氣。性質是穿著劣質西裝配著運動鞋的農民,只不過是另外的一種鄉土氣息。在這個消費社會,他們成為了審丑狂歡的消費品。
改變“殺馬特”的生活狀態更重要
百度詞條顯示,“殺馬特”潮流據稱開始于1999年,是對某些日本年輕人非傳統穿著的片面模仿。但是“殺馬特”在中國面臨了特殊的挑戰。城市年輕移民不太可能獲得父母監管或社區支持,以讓他們脫離下層階級。這就是中國年輕職場人士和受教育的精英階層毫不留情地任意嘲笑“殺馬特”的部分原因。
社會工作者袁力敏認為,“殺馬特”一族沒有城市人才有的消費條件,也沒有城市人特有的文化氛圍。“這不是他們的錯,他們的舉動已經顯示出他們對進步的渴望。”
如果有足夠的經濟條件,“殺馬特”們也會選擇高檔公寓、香奈兒、古馳、蘋果,但大城市的生活壓力讓他們無法實現夢想。“殺馬特”們并非天生就沒品位,也并非主動選擇“沒品位”。“殺馬特”的人多了,城鎮化進程會更難。
“殺馬特”更多是一種經濟地位,人們無須從生活狀態、精神生活上對他們指指點點。“殺馬特”們的父輩們為中國的城鎮化奉獻了青春,多數人只能回到農村或生活在城市的邊緣。相反,隨著城鎮化的推進,解決“殺馬特”的經濟地位問題、城市待遇問題已經擺在眼前,這是一個數量巨大的群體,他們的未來也是我們這個國家的未來。
不考量“殺馬特”的經濟地位問題,人們會永遠戴著有色眼鏡旁觀這個無辜的群體。“殺馬特”的父輩們是失去的一代,“殺馬特”們也有“將要失去”的趨勢,我們是否該想想如何讓“殺馬特”們過上真實殷實、“smart”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