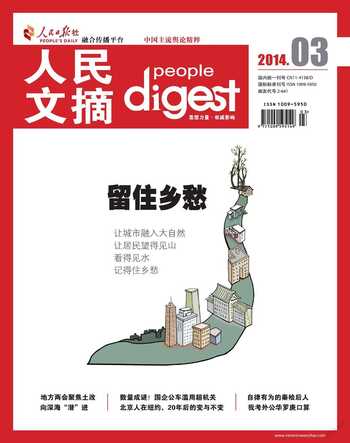詩人余光中的鄉愁
李元洛 趙新兵
小時候
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
我在這頭
母親在那頭
長大后
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
我在這頭
新娘在那頭
后來呀
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
我在外頭
母親呵在里頭
而現在
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
我在這頭
大陸在那頭
——余光中(中國臺灣)
選自《白玉苦瓜》,臺灣大地出版社1974年版
鄉愁,是中國詩歌一個歷久彌新的主題,余光中多年來寫了許多以鄉愁為主題的詩篇,《鄉愁》就是其中情深意長的一曲。
正像中國大地上許多江河都是黃河與長江的支流一樣,余光中雖然身居海島,但是,作為一個摯愛祖國及其文化傳統的中國詩人,他的鄉愁詩從內在感情上繼承了我國古典詩歌中的民族感情傳統,具有深厚的歷史感與民族感,同時,臺灣和大陸人為的長期隔絕、漂流到孤島上去的千千萬萬人的思鄉情懷,客觀上具有以往任何時代的鄉愁所不可比擬的特定的廣闊內容。余光中作為一個離開大陸多年的當代詩人,他的作品也必然會烙上深刻的時代印記。《鄉愁》一詩,側重寫個人在大陸的經歷,那年少時的一枚郵票,那青年時的一張船票,甚至那未來的一方墳墓,都寄寓了詩人的也是萬千海外游子的綿長鄉關之思,而這一切在詩的結尾升華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而現在/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有如百川奔向東海,有如千峰朝向泰山,詩人個人的悲歡與巨大的祖國之愛、民族之戀交融在一起,而詩人個人經歷的傾訴,也因為結尾的感情燃燒而更為撩人愁思了,正如余光中自己所說:“縱的歷史感,橫的地域感。縱橫相交而成十字路口的現實感。”(《白玉苦瓜》序)這樣,詩人的《鄉愁》是我國民族傳統的鄉愁詩在新的時代和特殊的地理條件下的變奏,具有以往的鄉愁詩所不可比擬的廣度和深度。
余光中1928年出生于南京,祖籍福建永春。母親原籍江蘇武進,故也自稱“江南人”。余光中1949年離開大陸,3年后畢業于臺灣大學外文系,先后在數所大學任教、創作,也曾到美國和香港求學、工作。已出版詩集、散文、評論和譯著40余種,他自稱是“文學創作上的‘多妻主義者’”。文學大師梁實秋評價他“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成就之高一時無兩”。
“從21歲負笈漂泊臺島,到小樓孤燈下懷鄉的呢喃,直到往來于兩岸間的探親、觀光、交流,縈繞在我心頭的仍舊是揮之不去的鄉愁。”談到作品中永恒的懷鄉情結和心路歷程,余光中說,“不過我慢慢意識到,我的鄉愁現應該是對包括地理、歷史和文化在內的整個中國的眷戀。”
20世紀60年代起,余光中創作了不少懷鄉詩,包括爭誦一時的“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與黃河之間/枕我的頭顱/白發蓋著黑土/在中國/最美最母親的國度……”20世紀70年代初,余光中創作了《鄉愁》,他說:“隨著日子的流失愈多,我的懷鄉之情便日重,在離開大陸整整20年的時候,我在臺北的舊居內一揮而就,僅用了20分鐘便寫出了《鄉愁》。”
余光中說,這首詩是“蠻寫實的”:小時候上寄宿學校,要與媽媽通信;婚后赴美讀書,坐輪船返臺;后來母親去世,永失母愛。詩的前三句思念的都是女性,到最后一句我想到了大陸這個“大母親”,于是意境和思路便豁然開朗,就有了“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一句。
余光中在南京生活了近10年,紫金山風光、夫子廟雅韻早已滲入他的血脈;抗戰中輾轉于重慶讀書,嘉陵江水、巴山野風又一次將他浸潤。“我慶幸自己在離開大陸時已經21歲。我受過傳統‘四書五經’的教育,也受到了‘五四’新文學的熏陶,中華文化已植根于心中。”余光中說,“如果鄉愁只有純粹的距離而沒有滄桑,這種鄉愁是單薄的。”
《鄉愁》是臺灣同胞、更是全體中國人共有的思鄉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