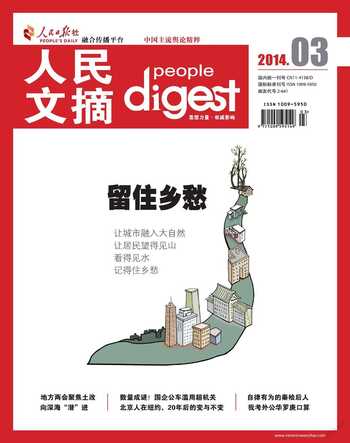“大樹進城”是錯還是對
沈立
最近,鄭州“綠博園”中被發現上千棵移植栽種的珍貴樹木死去,“大樹進城”再次成為熱議話題。
樹木是城市之“肺”。大樹吸收二氧化碳、制造氧氣的功能是草坪的5倍,吸塵量是草坪的3倍,成片樹蔭下的氣溫比草坪綠地氣溫低5攝氏度左右。大樹構成都市綠色的骨架,帶來生命的詩情畫意,它在改善城市生態與綠色人文環境方面的優越性能是小樹或幼苗難以比擬的,在城市生態系統中起著巨大作用。沒有樹的世界是一個死寂的世界——即使在沙漠里,也會有頑強的胡楊。生活在現代化城市里的人不能沒有樹。
然而,所謂“十年樹木”,一棵大樹的成長往往伴隨著數十年的時間,城市現在沒樹怎么辦?我們是應該種一棵樹苗等它長成參天大樹,還是干脆到鄉村挖來參天大樹一下子讓我們的城市綠樹成蔭呢?
移植栽培,成功率偏低
所謂“人挪活,樹挪死”,大樹移植的技術難度是相對較大的。生長幾十年、上百年的大樹可謂根深葉茂,與生長地形成了一種較好的適應關系,若要將它移栽成活,多數需要去其根系、刪其枝葉,以保證它上下水的平衡。然后再是經過長途運輸,能成活者可謂大幸。
2012年,《中國園藝文摘》刊登過一篇名為《“大樹進城”引發的問題及對策》的文章,對國內多個地方的移植大樹生存狀況做了統計。結果表明:一般近距離移植且技術到位的情況下,大樹成活率在60%左右。2002年武漢某公園樸樹的成活率為72%,2005年北京清華東路白蠟樹的成活率則僅為47.3%,2006年長沙城區香樟樹的成活率也只有62%。“技術不到位,一般能活30%就不錯了。”一位負責移栽的技術人員說道。
過去,城市綠化常用幼樹,這些幼樹由于處于生長旺盛期,可塑性強,對移植后的新環境有較強的適應能力,因此死亡率較低,十分易于移植,而且成活后樹勢旺盛,壽命也較長。而成年大樹,可塑性下降,適應能力低,在移植過程中,主根和根系以及主枝樹冠大部分被切斷,樹體受到嚴重傷害,如果水土不服,移植技術不過關,管理不善,極易造成大樹的迅速死亡。這些大樹即使在3至5年內確定成活,也大多在幾年、十幾年內變成缺乏生機的老樹,逐步喪失環境生態功能。
每一棵大樹都是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經過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生長后,它們與周圍的土壤、土中的生物、樹下的地被、樹上的鳥獸昆蟲,形成了良好的依存關系。大樹一旦被移走,不但方圓幾米樹冠下的生物群落隨之遭到破壞,大樹自身也很可能因為失去共存的環境而使健康受到影響甚至死亡。
大樹進城,誰是誰非
事實上,對于大樹進城,起初就有兩種不同的聲音。
一方面,各地政府普遍認為,大樹進城有利于創造最佳人居環境,是為民辦實事的具體體現;傳統的小苗定植培育時間長,護理難度大,設計的景觀效果不易實現。大樹進城一次成林、一次成景,一步到位;大樹進城為農民脫貧致富創造條件,把樹農閑置的樹木資源變成現金收入,可以幫助農村致富,也有利于提高農民種樹的積極性。
另一方面,也有相關的專家對這種算賬的方式表示不以為然,認為移植大樹還得算幾筆賬:首先是大樹原生存地生態破壞賬。大樹移植有悖自然生態規律,會對大樹原生存地生態造成破壞,這種損失是難以估量的;其次是綠色資源浪費賬。假設移植大樹的成活率是80%,移入10萬棵大樹,這意味著其中的2萬棵要“死于非命”,這將造成綠色資源的極大浪費。另外,即使大樹都能成活,修剪后的樹干也需要至少二三年的時間才能恢復到原來的枝繁葉茂狀態,同樣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綠色資源的浪費問題;最后還要算財政投入的浪費賬,大樹移植往往還會給部分貧困地區的財政帶來不小的壓力。
不但價格高昂,還需后續維護
2010年,珠海市投資800萬元,在市內移植了31株羅漢松大樹。對于城市來說,建設綠化本應是好事,但消息一出,馬上引來群眾的紛紛質疑,爭議的關鍵在于800萬元只種了31株樹。很多市民認為,這是一種奢侈綠化行為。
誠然,隨著各城市經濟實力的全面提升,對城市綠化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城市要綠化也要美化,植樹種草作為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一部分也應該不斷提高檔次。但問題在于,“十年樹木”本是自然規律,“一日成景”的急功近利式綠化是否可取呢?
此外,城市引進大樹、引進名貴樹木不光是引種時的巨額投資問題,還要考慮后期的養護和防偷盜等問題。如此珍貴的樹木如果在移植和栽培上的工作做得不夠,很可能出現使大樹長勢趨弱或者死掉的后果,損失巨大。珠海市有關部門為了防止羅漢松被偷盜還專門進行了樹木的GPS定位,如此一來,古樹的養護和防盜成本之高可想而知。
為何屢禁不止,關鍵還是利益
大樹進城屢禁不止的根本原因也許還是利益的驅動。“沒有買賣,就沒有盜采,也不會有大樹進城。”我國著名植物學家蔣高直言,在大樹進城熱潮的背后,隱藏著一條灰色的利益鏈:從鄉下農民到大樹販子,到園林施工負責人,再到園林設計者,都是其中的環節。
一些城市為了追求任期內的政績,盡快在新城建設或舊城改造的過程中增加城市綠化率,選擇直接從外地批量購買大樹。同時,城市購房者偏好大樹多的居住小區也成為大樹進城的推波助瀾者之一。
廣東省陳村鎮就是華南地區花木交易有名的“老字號”。在大樹進城的整個環節中,它可謂一個中途“驛站”。一棵兩百多年樹齡的羅漢松,造型成功后,售價在130萬元。高約4米的羅漢松,被栽種在特制的“花盆”里“待字閨中”。在陳村鎮,這條古樹苗圃街正是3年前“瘋炒”羅漢松留下來的產物。“這棵羅漢松的進價大約是70多萬元,能賣出去,就是對半賺。”年輕的園林老板坦言,園里存活下來的有幾棵80年樹齡的香樟樹,均從廣西運來,售價在8萬~13萬元;從韶關運來的一棵百年以上的橘樹,并不是稀有品種,價格也在3萬元左右。
保護林木生態,還得依賴法律武器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業標準《城市綠化工程施工及驗收規范》(CJJ/T82-99)中規定:“移植胸徑在20厘米以上的落葉喬木和胸徑在15厘米以上的常綠喬木,即視為大樹移植。大樹移植應建立技術檔案,包括移植方案、移植時間、地下情況、根部情況、施工記錄、養護管理技術措施、驗收資料、照片或影像資料。”
如此看來,當下很多城市從自然林地和原始森林中采挖大樹的做法,顯然不符合規范。不過,有專家表示,反對盲目的“大樹進城”雖正確,但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因為并非所有移植都該禁止。以下幾種特殊情況則是應該鼓勵樹木進行移植的:首先,在城市建設中,一些地段被征用,這些地段上的古樹(樹齡在100年以上)名木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這些古樹名木應該帶全冠異地種植;其次,在小城鎮林地中,當種植密度過高時,應對苗木進行適當疏苗,此疏苗是指移栽到其他適合綠化的地方;再次,水庫、道路和工廠等重要基礎設施周圍的大樹移植是必要的;最后,搶救珍稀瀕危植物所進行的樹木遷地保護。
4800歲的狐尾松瑪士撒拉樹,長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東部。據《圣經·舊約》所說,瑪士撒拉是最長壽的人,活了969歲。瑪士撒拉的孫子諾亞建造了方舟,拯救了世界。為了保護這棵古樹,防止被人肆意破壞,當地林業部門從未對外透露過瑪士撒拉樹的確切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