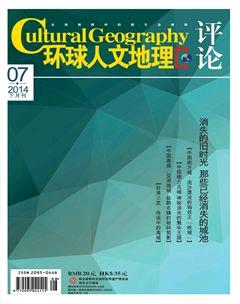伊特魯里亞錢幣漫談
楊揚
摘要:伊特魯里亞是意大利早期文明的代表,但卻無經典文獻傳世,且文字未能釋讀,考古出土的錢幣承載了豐富的歷史信息,成為了解這一文明的重要途徑。通過分析伊特魯里亞錢幣的樣式、幣制,可以看出該文明既受到古代希臘、羅馬的影響,又形成了自己與眾不同的特色。
關鍵詞:伊特魯里亞;錢幣;幣制;銘文;樣式
近日,由意大利特拉維索卡薩德·卡拉雷茲博物館(Casa dei Carraresi Museum, Treviso)、佛羅倫薩國家考古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rcheology, Florence)和錫耶納考古博物館(Museum of Archeology, Siena)聯合舉辦的“曙光時代:意大利的伊特魯里亞文明”展正在湖北省博物館、浙江省博物館、廣東省博物館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巡展[1]。本文希望籍此展覽掀起的熱潮,以錢幣為切入點,勾勒出伊特魯里亞歷史的一個側面,使我們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去了解這個曾經無比輝煌但又最終失落的古老文明。
伊特魯里亞(Etruria)文明是意大利早期文明的代表,因其在歷史上的獨特成就和深遠影響,更被譽為羅馬文明的曙光。雖然這個文明沒有經典文獻傳世,而且我們至今仍然無法釋讀其文字,但是考古學卻揭示出她對羅馬乃至西方文明的深遠影響。錢幣是出土文物當中常見物品之一,它承載了豐富的歷史信息,往往是一個文明社會的見證,能夠幫助我們探尋那段因文字亡佚而早已湮沒的燦爛文明。有關伊特魯里亞的錢幣學研究,歐洲學者顯然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尤其是意大利的學者,他們進行了深入和系統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的專著和論文[2]。目前,國內錢幣學界僅有李鐵生先生的論著當中有部分內容涉及到這一領域,但是尚未見到專門研究伊特魯里亞錢幣的論著[3]。
公元前12世紀到公元前1世紀,伊特魯里亞文明在意大利中西部亞諾河與臺伯河之間興盛。伊特魯里亞是古羅馬人對意大利托斯卡納,翁布里亞、拉齊奧、拉丁姆北部等地區的統稱,這一地區的人們自稱羅散納人(Rasenna),而古希臘人則稱他們為第勒尼安人(Τυρρηνο?)。伊特魯里亞肥沃的土地、曲折的海岸線提供了豐富的食物,同時,該地蘊藏大量的銅、鐵、錫等礦藏,這促使他們掌控了地中海世界的冶煉業,并隨之形成了一個影響整個地區的貿易網。他們在與希臘、腓基尼、迦太基等文化接觸的過程之中,手工業、商業逐漸興盛,其生產的布凱羅黑陶、青銅器和金銀器遍及地中海沿岸[4]。
公元前1000 年左右,伊特魯里亞人已經制作出鐵器和精美的工藝品。公元前6 世紀時,伊特魯里亞人控制了第勒尼安海一側的亞諾河與臺伯河地區,建立起松散的城邦聯盟,勢力達到頂峰,幾乎橫跨整個亞平寧山脈,羅馬王政時代的后三位國王均出自伊特魯里亞人。此時,伴隨著海上貿易的發展,這一地區出現了最初的錢幣,它們很有可能是受到希臘式錢幣的影響,早期是在波普羅尼亞(Populonia)和烏爾奇(Vulci)等地區打制而成。到了公元前4世紀和公元前3世紀,其他伊特魯里亞各城邦也開始廣泛使用。早期的伊特魯里亞錢幣上面大多刻有銘文“ΘEΖI”,同時還有戈爾貢、斯芬克斯或是各種獅子的形象。另一方面,在沃爾泰拉(Volterra)和塔爾奎尼亞(Tarquinia)等城邦也出現鑄模制造的錢幣。
最早期的伊特魯里亞金幣標準基于尤庇亞-敘拉古的銀幣體系,即單個重量約為13.5克[5]。早期的銀幣似乎是源自“卡爾西迪式”(Chalcidian)的銀德拉克馬,其單個重量約為5.8克[6]。此外,青銅也被作為輔助交換的準貨幣單位,這種準貨幣被稱之為“粗銅”(Aes rude),拉丁語意為“未經加工的銅塊”。此后,伊特魯里亞的錢幣逐漸開始標注其面值。波普羅尼亞很有可能是首個將幣值標注在錢幣上的伊特魯里亞城邦,這種做法可能是受到公元前5世紀敘拉古及其他西西里鑄幣的影響[7]。首個(Metus)系列錢幣重量的標準則引入了科林斯的斯塔爾制(stater)或雅典的德拉克馬制,理論上的單個重量為8.6克。
伊特魯里亞錢幣上的銘文引發了諸多討論。不過毫無疑問的是,許多伊特魯里亞城邦的錢幣上都打制了它們各自的名稱。錢幣上的銘文“Pupluna”代表波普羅尼亞、“Vatl”和“Vetluna”代表維圖羅尼亞(Vetulonia)、“Velathri”代表沃爾泰拉、“Cha(mars)”代表卡馬爾斯(Camars)、“Tla(mun)”代表特拉蒙(Telamon)、“Velsu”和“Velznani”代表沃爾西尼(Volsinii)等不同城邦[8]。伊特魯里亞的金幣和銀幣采用了十進制的幣值,這與希臘德拉克馬的十二進制不同,而這種計算體系顯然又影響了羅馬。通常情況下,金幣的面值表明等值的白銀,而銀幣的面值則標志著等價的青銅。一般來說,黃金和白金的兌換比值為15:1。
伊特魯里亞錢幣幣值銘文對照表
伊特魯里亞錢幣的樣式大部分是采用希臘式錢幣風格,不過錢幣上的圖案常常體現伊特魯里亞自身的文化和風情。具體到錢幣上的圖案來說,車輪、戈爾貢和牛頭可能與太陽和月亮崇拜有關。火神和工匠之神伏爾甘(Vulcan)拿著錘子和鉗子使人想到波普羅尼亞等地的金屬鑄造。其他諸如海馬、海豚和船首等樣式的錢幣標志著海洋對伊特魯里亞的影響。另外,各種錢幣上哈德斯、刻耳柏洛斯、格里芬、斯芬克斯、喀邁拉等神話人物和動物以及祭司的頭像則與伊特魯里亞人的宗教世界有關。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伊特魯里亞部分的金幣和銀幣只是一面有圖案,另一面卻為空白,這種樣式在其他古代地中海地區的錢幣上可謂鮮見。
伴隨著公元前6至5世紀伊特魯里亞人在與希臘人爭奪地中海霸權的戰爭中多次失敗,羅馬人在公元前509 年放逐了伊特魯里亞人國王,結束了王政時代。羅馬在意大利的擴張意味著伊特魯里亞文明的衰落。公元4 世紀,伊特魯里亞人屢次敗于羅馬的武力之下。公元前280 年,伊特魯里亞城邦成為羅馬的盟邦,與羅馬風格融合在一起,最終消失于羅馬文明奪目的光輝之中。自此,伊特魯里亞遵循羅馬的“重銅阿斯”(Aes grave)幣制標準,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雙方實力的此消彼長。最終,伊特魯里亞的貨幣也完全改用羅馬的第納爾(Denarius)幣制。
參考文獻:
[1] 黃丹彤、宋敏:“311件意大利文物在省博物館等著你 展現伊特魯里亞文明”,《廣州日報》,2014年05月15日,A16版。
[2] 相關論著詳見Fiorenzo Catalli, Monete Etrusche, (2 ed.), Rome: Istituto Poligrafico e Zecca dello Stato, 1998; Keith N. Rutter, Greek coinages of Southern Italy and Sicily, London, Spink, 1997; Keith N. Rutter, Historia Nummorum:Italy,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1; Italo Vecchi, Etruscan Coinage. Part 1. A corpus of the coinage of the Rasna, Milano, 2012.
[3] 李鐵生先生在北京出版社的《古希臘羅馬幣鑒賞》、《古希臘幣》、《古羅馬幣》等一系列著作當中涉及到了伊特魯里亞的錢幣。
[4] 湖北省博物館:《曙光時代:意大利的伊特魯里亞文明》,文物出版社,2013年。
[5] Sambon, Monnaies de la Presqu'ile italique, Naples, 1870.
[6] N.F. Parise, ‘La prima monetazione etrusca: fondamenti metrologici e funzioni, in Il commercio etrusco arcaico. Atti dellincontro di studio, 5-7 dicembre 1983, Roma, 1985, pp.257-261.
[7] Società Archeologica Comense, Como,1986.
[8] Ernst Justus Haeberlin, Die Systematik des ?ltesten r?mischen Münzwesens, Berlin, 1905.endprint
摘要:伊特魯里亞是意大利早期文明的代表,但卻無經典文獻傳世,且文字未能釋讀,考古出土的錢幣承載了豐富的歷史信息,成為了解這一文明的重要途徑。通過分析伊特魯里亞錢幣的樣式、幣制,可以看出該文明既受到古代希臘、羅馬的影響,又形成了自己與眾不同的特色。
關鍵詞:伊特魯里亞;錢幣;幣制;銘文;樣式
近日,由意大利特拉維索卡薩德·卡拉雷茲博物館(Casa dei Carraresi Museum, Treviso)、佛羅倫薩國家考古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rcheology, Florence)和錫耶納考古博物館(Museum of Archeology, Siena)聯合舉辦的“曙光時代:意大利的伊特魯里亞文明”展正在湖北省博物館、浙江省博物館、廣東省博物館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巡展[1]。本文希望籍此展覽掀起的熱潮,以錢幣為切入點,勾勒出伊特魯里亞歷史的一個側面,使我們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去了解這個曾經無比輝煌但又最終失落的古老文明。
伊特魯里亞(Etruria)文明是意大利早期文明的代表,因其在歷史上的獨特成就和深遠影響,更被譽為羅馬文明的曙光。雖然這個文明沒有經典文獻傳世,而且我們至今仍然無法釋讀其文字,但是考古學卻揭示出她對羅馬乃至西方文明的深遠影響。錢幣是出土文物當中常見物品之一,它承載了豐富的歷史信息,往往是一個文明社會的見證,能夠幫助我們探尋那段因文字亡佚而早已湮沒的燦爛文明。有關伊特魯里亞的錢幣學研究,歐洲學者顯然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尤其是意大利的學者,他們進行了深入和系統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的專著和論文[2]。目前,國內錢幣學界僅有李鐵生先生的論著當中有部分內容涉及到這一領域,但是尚未見到專門研究伊特魯里亞錢幣的論著[3]。
公元前12世紀到公元前1世紀,伊特魯里亞文明在意大利中西部亞諾河與臺伯河之間興盛。伊特魯里亞是古羅馬人對意大利托斯卡納,翁布里亞、拉齊奧、拉丁姆北部等地區的統稱,這一地區的人們自稱羅散納人(Rasenna),而古希臘人則稱他們為第勒尼安人(Τυρρηνο?)。伊特魯里亞肥沃的土地、曲折的海岸線提供了豐富的食物,同時,該地蘊藏大量的銅、鐵、錫等礦藏,這促使他們掌控了地中海世界的冶煉業,并隨之形成了一個影響整個地區的貿易網。他們在與希臘、腓基尼、迦太基等文化接觸的過程之中,手工業、商業逐漸興盛,其生產的布凱羅黑陶、青銅器和金銀器遍及地中海沿岸[4]。
公元前1000 年左右,伊特魯里亞人已經制作出鐵器和精美的工藝品。公元前6 世紀時,伊特魯里亞人控制了第勒尼安海一側的亞諾河與臺伯河地區,建立起松散的城邦聯盟,勢力達到頂峰,幾乎橫跨整個亞平寧山脈,羅馬王政時代的后三位國王均出自伊特魯里亞人。此時,伴隨著海上貿易的發展,這一地區出現了最初的錢幣,它們很有可能是受到希臘式錢幣的影響,早期是在波普羅尼亞(Populonia)和烏爾奇(Vulci)等地區打制而成。到了公元前4世紀和公元前3世紀,其他伊特魯里亞各城邦也開始廣泛使用。早期的伊特魯里亞錢幣上面大多刻有銘文“ΘEΖI”,同時還有戈爾貢、斯芬克斯或是各種獅子的形象。另一方面,在沃爾泰拉(Volterra)和塔爾奎尼亞(Tarquinia)等城邦也出現鑄模制造的錢幣。
最早期的伊特魯里亞金幣標準基于尤庇亞-敘拉古的銀幣體系,即單個重量約為13.5克[5]。早期的銀幣似乎是源自“卡爾西迪式”(Chalcidian)的銀德拉克馬,其單個重量約為5.8克[6]。此外,青銅也被作為輔助交換的準貨幣單位,這種準貨幣被稱之為“粗銅”(Aes rude),拉丁語意為“未經加工的銅塊”。此后,伊特魯里亞的錢幣逐漸開始標注其面值。波普羅尼亞很有可能是首個將幣值標注在錢幣上的伊特魯里亞城邦,這種做法可能是受到公元前5世紀敘拉古及其他西西里鑄幣的影響[7]。首個(Metus)系列錢幣重量的標準則引入了科林斯的斯塔爾制(stater)或雅典的德拉克馬制,理論上的單個重量為8.6克。
伊特魯里亞錢幣上的銘文引發了諸多討論。不過毫無疑問的是,許多伊特魯里亞城邦的錢幣上都打制了它們各自的名稱。錢幣上的銘文“Pupluna”代表波普羅尼亞、“Vatl”和“Vetluna”代表維圖羅尼亞(Vetulonia)、“Velathri”代表沃爾泰拉、“Cha(mars)”代表卡馬爾斯(Camars)、“Tla(mun)”代表特拉蒙(Telamon)、“Velsu”和“Velznani”代表沃爾西尼(Volsinii)等不同城邦[8]。伊特魯里亞的金幣和銀幣采用了十進制的幣值,這與希臘德拉克馬的十二進制不同,而這種計算體系顯然又影響了羅馬。通常情況下,金幣的面值表明等值的白銀,而銀幣的面值則標志著等價的青銅。一般來說,黃金和白金的兌換比值為15:1。
伊特魯里亞錢幣幣值銘文對照表
伊特魯里亞錢幣的樣式大部分是采用希臘式錢幣風格,不過錢幣上的圖案常常體現伊特魯里亞自身的文化和風情。具體到錢幣上的圖案來說,車輪、戈爾貢和牛頭可能與太陽和月亮崇拜有關。火神和工匠之神伏爾甘(Vulcan)拿著錘子和鉗子使人想到波普羅尼亞等地的金屬鑄造。其他諸如海馬、海豚和船首等樣式的錢幣標志著海洋對伊特魯里亞的影響。另外,各種錢幣上哈德斯、刻耳柏洛斯、格里芬、斯芬克斯、喀邁拉等神話人物和動物以及祭司的頭像則與伊特魯里亞人的宗教世界有關。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伊特魯里亞部分的金幣和銀幣只是一面有圖案,另一面卻為空白,這種樣式在其他古代地中海地區的錢幣上可謂鮮見。
伴隨著公元前6至5世紀伊特魯里亞人在與希臘人爭奪地中海霸權的戰爭中多次失敗,羅馬人在公元前509 年放逐了伊特魯里亞人國王,結束了王政時代。羅馬在意大利的擴張意味著伊特魯里亞文明的衰落。公元4 世紀,伊特魯里亞人屢次敗于羅馬的武力之下。公元前280 年,伊特魯里亞城邦成為羅馬的盟邦,與羅馬風格融合在一起,最終消失于羅馬文明奪目的光輝之中。自此,伊特魯里亞遵循羅馬的“重銅阿斯”(Aes grave)幣制標準,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雙方實力的此消彼長。最終,伊特魯里亞的貨幣也完全改用羅馬的第納爾(Denarius)幣制。
參考文獻:
[1] 黃丹彤、宋敏:“311件意大利文物在省博物館等著你 展現伊特魯里亞文明”,《廣州日報》,2014年05月15日,A16版。
[2] 相關論著詳見Fiorenzo Catalli, Monete Etrusche, (2 ed.), Rome: Istituto Poligrafico e Zecca dello Stato, 1998; Keith N. Rutter, Greek coinages of Southern Italy and Sicily, London, Spink, 1997; Keith N. Rutter, Historia Nummorum:Italy,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1; Italo Vecchi, Etruscan Coinage. Part 1. A corpus of the coinage of the Rasna, Milano, 2012.
[3] 李鐵生先生在北京出版社的《古希臘羅馬幣鑒賞》、《古希臘幣》、《古羅馬幣》等一系列著作當中涉及到了伊特魯里亞的錢幣。
[4] 湖北省博物館:《曙光時代:意大利的伊特魯里亞文明》,文物出版社,2013年。
[5] Sambon, Monnaies de la Presqu'ile italique, Naples, 1870.
[6] N.F. Parise, ‘La prima monetazione etrusca: fondamenti metrologici e funzioni, in Il commercio etrusco arcaico. Atti dellincontro di studio, 5-7 dicembre 1983, Roma, 1985, pp.257-261.
[7] Società Archeologica Comense, Como,1986.
[8] Ernst Justus Haeberlin, Die Systematik des ?ltesten r?mischen Münzwesens, Berlin, 1905.endprint
摘要:伊特魯里亞是意大利早期文明的代表,但卻無經典文獻傳世,且文字未能釋讀,考古出土的錢幣承載了豐富的歷史信息,成為了解這一文明的重要途徑。通過分析伊特魯里亞錢幣的樣式、幣制,可以看出該文明既受到古代希臘、羅馬的影響,又形成了自己與眾不同的特色。
關鍵詞:伊特魯里亞;錢幣;幣制;銘文;樣式
近日,由意大利特拉維索卡薩德·卡拉雷茲博物館(Casa dei Carraresi Museum, Treviso)、佛羅倫薩國家考古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rcheology, Florence)和錫耶納考古博物館(Museum of Archeology, Siena)聯合舉辦的“曙光時代:意大利的伊特魯里亞文明”展正在湖北省博物館、浙江省博物館、廣東省博物館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巡展[1]。本文希望籍此展覽掀起的熱潮,以錢幣為切入點,勾勒出伊特魯里亞歷史的一個側面,使我們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去了解這個曾經無比輝煌但又最終失落的古老文明。
伊特魯里亞(Etruria)文明是意大利早期文明的代表,因其在歷史上的獨特成就和深遠影響,更被譽為羅馬文明的曙光。雖然這個文明沒有經典文獻傳世,而且我們至今仍然無法釋讀其文字,但是考古學卻揭示出她對羅馬乃至西方文明的深遠影響。錢幣是出土文物當中常見物品之一,它承載了豐富的歷史信息,往往是一個文明社會的見證,能夠幫助我們探尋那段因文字亡佚而早已湮沒的燦爛文明。有關伊特魯里亞的錢幣學研究,歐洲學者顯然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尤其是意大利的學者,他們進行了深入和系統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的專著和論文[2]。目前,國內錢幣學界僅有李鐵生先生的論著當中有部分內容涉及到這一領域,但是尚未見到專門研究伊特魯里亞錢幣的論著[3]。
公元前12世紀到公元前1世紀,伊特魯里亞文明在意大利中西部亞諾河與臺伯河之間興盛。伊特魯里亞是古羅馬人對意大利托斯卡納,翁布里亞、拉齊奧、拉丁姆北部等地區的統稱,這一地區的人們自稱羅散納人(Rasenna),而古希臘人則稱他們為第勒尼安人(Τυρρηνο?)。伊特魯里亞肥沃的土地、曲折的海岸線提供了豐富的食物,同時,該地蘊藏大量的銅、鐵、錫等礦藏,這促使他們掌控了地中海世界的冶煉業,并隨之形成了一個影響整個地區的貿易網。他們在與希臘、腓基尼、迦太基等文化接觸的過程之中,手工業、商業逐漸興盛,其生產的布凱羅黑陶、青銅器和金銀器遍及地中海沿岸[4]。
公元前1000 年左右,伊特魯里亞人已經制作出鐵器和精美的工藝品。公元前6 世紀時,伊特魯里亞人控制了第勒尼安海一側的亞諾河與臺伯河地區,建立起松散的城邦聯盟,勢力達到頂峰,幾乎橫跨整個亞平寧山脈,羅馬王政時代的后三位國王均出自伊特魯里亞人。此時,伴隨著海上貿易的發展,這一地區出現了最初的錢幣,它們很有可能是受到希臘式錢幣的影響,早期是在波普羅尼亞(Populonia)和烏爾奇(Vulci)等地區打制而成。到了公元前4世紀和公元前3世紀,其他伊特魯里亞各城邦也開始廣泛使用。早期的伊特魯里亞錢幣上面大多刻有銘文“ΘEΖI”,同時還有戈爾貢、斯芬克斯或是各種獅子的形象。另一方面,在沃爾泰拉(Volterra)和塔爾奎尼亞(Tarquinia)等城邦也出現鑄模制造的錢幣。
最早期的伊特魯里亞金幣標準基于尤庇亞-敘拉古的銀幣體系,即單個重量約為13.5克[5]。早期的銀幣似乎是源自“卡爾西迪式”(Chalcidian)的銀德拉克馬,其單個重量約為5.8克[6]。此外,青銅也被作為輔助交換的準貨幣單位,這種準貨幣被稱之為“粗銅”(Aes rude),拉丁語意為“未經加工的銅塊”。此后,伊特魯里亞的錢幣逐漸開始標注其面值。波普羅尼亞很有可能是首個將幣值標注在錢幣上的伊特魯里亞城邦,這種做法可能是受到公元前5世紀敘拉古及其他西西里鑄幣的影響[7]。首個(Metus)系列錢幣重量的標準則引入了科林斯的斯塔爾制(stater)或雅典的德拉克馬制,理論上的單個重量為8.6克。
伊特魯里亞錢幣上的銘文引發了諸多討論。不過毫無疑問的是,許多伊特魯里亞城邦的錢幣上都打制了它們各自的名稱。錢幣上的銘文“Pupluna”代表波普羅尼亞、“Vatl”和“Vetluna”代表維圖羅尼亞(Vetulonia)、“Velathri”代表沃爾泰拉、“Cha(mars)”代表卡馬爾斯(Camars)、“Tla(mun)”代表特拉蒙(Telamon)、“Velsu”和“Velznani”代表沃爾西尼(Volsinii)等不同城邦[8]。伊特魯里亞的金幣和銀幣采用了十進制的幣值,這與希臘德拉克馬的十二進制不同,而這種計算體系顯然又影響了羅馬。通常情況下,金幣的面值表明等值的白銀,而銀幣的面值則標志著等價的青銅。一般來說,黃金和白金的兌換比值為15:1。
伊特魯里亞錢幣幣值銘文對照表
伊特魯里亞錢幣的樣式大部分是采用希臘式錢幣風格,不過錢幣上的圖案常常體現伊特魯里亞自身的文化和風情。具體到錢幣上的圖案來說,車輪、戈爾貢和牛頭可能與太陽和月亮崇拜有關。火神和工匠之神伏爾甘(Vulcan)拿著錘子和鉗子使人想到波普羅尼亞等地的金屬鑄造。其他諸如海馬、海豚和船首等樣式的錢幣標志著海洋對伊特魯里亞的影響。另外,各種錢幣上哈德斯、刻耳柏洛斯、格里芬、斯芬克斯、喀邁拉等神話人物和動物以及祭司的頭像則與伊特魯里亞人的宗教世界有關。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伊特魯里亞部分的金幣和銀幣只是一面有圖案,另一面卻為空白,這種樣式在其他古代地中海地區的錢幣上可謂鮮見。
伴隨著公元前6至5世紀伊特魯里亞人在與希臘人爭奪地中海霸權的戰爭中多次失敗,羅馬人在公元前509 年放逐了伊特魯里亞人國王,結束了王政時代。羅馬在意大利的擴張意味著伊特魯里亞文明的衰落。公元4 世紀,伊特魯里亞人屢次敗于羅馬的武力之下。公元前280 年,伊特魯里亞城邦成為羅馬的盟邦,與羅馬風格融合在一起,最終消失于羅馬文明奪目的光輝之中。自此,伊特魯里亞遵循羅馬的“重銅阿斯”(Aes grave)幣制標準,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雙方實力的此消彼長。最終,伊特魯里亞的貨幣也完全改用羅馬的第納爾(Denarius)幣制。
參考文獻:
[1] 黃丹彤、宋敏:“311件意大利文物在省博物館等著你 展現伊特魯里亞文明”,《廣州日報》,2014年05月15日,A16版。
[2] 相關論著詳見Fiorenzo Catalli, Monete Etrusche, (2 ed.), Rome: Istituto Poligrafico e Zecca dello Stato, 1998; Keith N. Rutter, Greek coinages of Southern Italy and Sicily, London, Spink, 1997; Keith N. Rutter, Historia Nummorum:Italy,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1; Italo Vecchi, Etruscan Coinage. Part 1. A corpus of the coinage of the Rasna, Milano, 2012.
[3] 李鐵生先生在北京出版社的《古希臘羅馬幣鑒賞》、《古希臘幣》、《古羅馬幣》等一系列著作當中涉及到了伊特魯里亞的錢幣。
[4] 湖北省博物館:《曙光時代:意大利的伊特魯里亞文明》,文物出版社,2013年。
[5] Sambon, Monnaies de la Presqu'ile italique, Naples, 1870.
[6] N.F. Parise, ‘La prima monetazione etrusca: fondamenti metrologici e funzioni, in Il commercio etrusco arcaico. Atti dellincontro di studio, 5-7 dicembre 1983, Roma, 1985, pp.257-261.
[7] Società Archeologica Comense, Como,1986.
[8] Ernst Justus Haeberlin, Die Systematik des ?ltesten r?mischen Münzwesens, Berlin, 1905.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