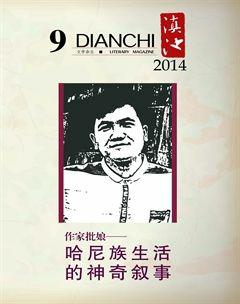走到另外一天去
陳危
楊:
現在,燈光鏤空夜色,霧霾充斥著鼻腔與喉道,就像人群涌入逼仄的走廊,讓我對事物的嗅覺混合著它們體味的基調。我的自我警惕并不能確保這些向你趨近的詞,不附帶別人的聲帶;即便剔得只剩下骨頭,也難逃前人造化賦形的框架,這是我的局限。無奈只好奢求我們那耗時已久的鏡臺,能讓閃碎的月光成為真正的銀子。
請原諒我的信件將先于這九位良師益友的詩作抵達你。同樣的事物因之出場的角度和順序的不同,往往具有不同的價值。比如徐蕭的《雪加速的姿態》,如何安排雪加速落下時的姿態和時空層次,在行文構建過程中,這首先是一件技術活。
你的上一封信中,從《伊利昂紀》講到古羅馬三詩人,從但丁講到莎士比亞掩蓋了多少人的光芒,還有席勒與拜倫,一直提到艾略特、薩特、中世紀東方文學和夏目漱石;你還列舉了不少中國當代詩人,你說“卻怎么都觸動不了靈魂”。這致使我感到窘迫、尷尬、無力。作為僅有幾年詩歌寫作經驗、擱筆一年有余的80末后生,在一個富有鑒賞素養與閱讀經驗的讀者那里,如何向樸素證明復雜的合法性,同樣也是一件技術活。
當我們覽閱詩歌時,我們是在覽閱什么?“立場,早已成為楔入/語言的裝置,你想到什么,它們先說。”(徐蕭《松軟》)如果你認可“立場”往往蠻橫無理地先于“理由和合法性”而存在,那么你一定能夠諒解我為何執拗地要站在踐行者的立場,提及時空層次與視場等詩藝。這并非華山之巔的“劍宗”與“氣宗”孰輕孰重的評判問題,而是創作者落筆時如何從第一個詞開始,通過一段生長、蓬勃,或者跳躍、泅渡的歷程,歸宿于最后一個詞。這個歷程構成了一首詩的本體,是詩之所在,這個歷程溶解并直觀反映著我們的立場與視角,邏輯和想象,感知與思考。
我想借助“你看到花朵呈現‘美麗,/然后產出可以吃的果實,似乎被覽閱就是它們/全部的掙扎”(徐蕭《松軟》),或“沒什么可以通過自身走出自我”(徐蕭《雪加速的姿態》)來提醒你把視線落在鏡面上,而非總是落在鏡后那層水銀鍍層的成像上。讓詩歌中的事物主動或被動地呈現其自身,這種呈現即空間拓延過程(無論向內剖掘,還是向外開拓),是由干癟的實心點漸而演變成一個實體并占據一定空間的過程,即“掙扎”。在一定程度上,掙扎的內涵指向,即掙扎的過程本身,無它。詩歌如果情愿成為附庸,刻意成為某種廣泛已知之物的轉述,或者某種老掉牙的觀點的轉譯,并非不可,但極不光彩。
通過精心謀劃的對“語言鏡像反應功能”的毀壞,而迫使讀者關注鏡面本身,對漢語詞匯及其編排布局進行更新,重塑詩性語言的“思想本體性”,是一件偉大而漫長的苦差事。這絕非單純地將語言去工具化,而是除舊革新。敲擊、破除籠罩在詞匯外圍的舊感官體驗與舊觀念的堅殼,將詞匯的種子與時代土壤進行綁定,是對舊詞匯的提升與再造,我稱之“救贖”,肖水謂之“清洗”。肖水等人對于漢語詞匯的清洗,在清洗內容及踐行方式上,可能同當代詩歌絕大多數其他向度的探索一樣都偏于個體化與小眾化,但誰也不能斷然否定他們不會踩到詩歌發展進程中的大動脈與大神經,這是一條有所傳承、有所建構之路,是對事物進行精準刻畫的必然要求。因此,“去工具化”僅是特征之一,肖水的探索是“骨子里的先鋒,正統的先鋒”。肖水的探索意義是雙重的:在攀爬與踏步推進的過程中,始終抓住詞匯的藤蔓不放,這是寫作策略;自覺為現代漢詩——這座根部瘦削的錐立城樓——的成長積累嶄新的中國(本土)表達。
楊,矛盾的是,如果真有人把詩歌當作各類器官堆砌而成的冰涼肉體去看待,沒有哪個作者情愿。我們希望有人能看見我們作品背后鮮活而完整的東西,仿佛我們早已預設了它的具體存在。不過,但凡有創作經驗的人都知道一個隱情:一首詩的誕生過程,往往是一些局部且細碎的靈感的有機(不乏偶然)融合。不乏一些同代作者,自覺、執拗地讓作品成為一種“現象或符號”的拼畫,等待著把脈與破解。當你問我“如果真有東西要表達,為什么不直說?”時,我想借助詩句“愛一個人,是多么中空又惡劣的勞動。/但美麗只被‘不合時宜、‘一意孤行一生維護。”(肖水《眾生界》)來表達我無言以對的無奈;無言以對的,還有這“初冬的天空,像一枚凍結的陀螺。光之生處露出/鋸齒般的細縫。”(肖水《天工開物》),它不表達、只呈現。這些潛在而基礎的困惑,仿佛一根啃不盡的老骨頭,每次刁難它我都感到不自信,卻又欲罷不能,正是創作方法論問題的攔截,阻滯浪潮,并只將浪尖上的少數水滴提升至高處。
太多的同代詩人,他們“……依舊需要弓著背脊,進到他人的夢里/去借取一斗稻種”(肖水《天工開物》),太多拙劣的重復和無效的寫作,“在羅網中編織的羅網,罩住發霉的草垛。”如何在“他人”陳舊霉變的羅網中突圍?我們首先應該把話題引向詩歌的“當下性、現時性”。具有當下性的詩歌,其形式上至少應當體現出詩人對當下的時空結構的辨識、邏輯觀念的把握、提煉、趨近,甚至是更新和對未來的預示。而針對多時空維度的現實碎片的集納與捕捉手法、延拓節奏及思維偏好,都可以明顯地反映出一個詩人是否帶有某種綜合且系統的(復雜而有序的)、開放的現代思維(有別于古典、傳統的思維)。這些應該成為也必將固化為現代詩藝的一部分。
肖水的《鹿角餐廳》中,出現兩組對峙的意象“性感、救生圈、沙發”和“柳枝、桌腿、嘴唇”,前組偏于現代,后組偏于傳統;相互對峙的意象相互關聯、共存于同一句詩之中,不僅是此樣本,事實上肖水的詩作大量使用該手法,這是他對詞匯的“清洗、救贖、再平衡”方式之一,他對詞匯力度的平衡是精細的;“桌腿因之救生圈而預設了它的復活,踏進傳統曖昧(性感)之水用現代的手攀折柳枝”這更像是肖水對寫作的自我評價。《在此城》中的形而上(傳統)之“鹿群”與世俗(現代)之“車流”,近乎于一對“對立物”,它們如何在此城中“虛實交融、新舊共存”,肖水提供了一個空間圖景。《末日》中“郊外的寺廟”、“頸脖”與“水草叢”,“臉”與“天鵝”均存在對應,在內容上存在精致的對仗。肖水的語言是調合的,詞與詞之間存在力場,微觀精確而宏觀龐博。不同詞匯間的跨度越大,表達的舞臺也相對較大。endprint
“順著田埂走上一整天,才能走到另外一天去。”(肖水《天工開物》)中隱含著飽滿的悲憫與抱負。換來新的一天,我們需要以耗盡“一整天”為代價,這不可或缺、無法規避的“一整天”,猶如舟楫承載我們,猶如風沙席卷著一整座村莊,猶如一條決絕之路走到盡頭才能走上新路。借肖水之言“在‘本土性之上建設漢語詩歌的‘現代性……當代詩歌寫作其核心不僅要關照當下,更要將視野和靈魂引向整個歷史性的整體;它關照的也不僅是西方主導的現代性,還應該有詩歌的本土性、中國性”,那些存在已久的珍貴之物即便近在咫尺,倘若不帶有我們的體溫,也只能算作廉價與遙不可及的生冷之物。這是一條復興之路,肖水的自我辨識是清晰的,難能可貴。楊,之所以我不樂意如此解讀詩歌,是因為詩歌文本是“存在的”,而對內容的解讀更是“發生的”,比如《在此城》是具有與某些大現實暗自吻合的強大潛質的,至于是何種大現實,也許正在發生尚未完結,也許大過我們絕大多數人(包括作者)的視野,我不愿意由于暫時的局限解讀而降低了詩句在現實(更是未來)面前的姿態,當前的“不及物”,有可能及“未來之物”。我不習慣從詩人的只言片語中,就評判出他具有了某種精神意識;也不習慣將幾個修辭上升到哲學論斷;我也絕不會像一些同齡作者那樣,在詩歌中轉述高蹈的哲學命題,用著粗糙干癟的材料,一首詩像一根瘦骨嶙峋的竹竿。如同使用了代表現代焦慮的詞匯的人,不見得寫出了焦慮,唯有用焦慮的方式去寫,才是自覺與純粹的。
歷時已久我總被這樣的問題困擾:在削去波峰與波谷之后,詩歌該如何展現余下的“白噪聲”與“基調”——這平淡無奇的現實日常,這非事件、非典型的主體,像是醞釀風暴的溫床,這種更為持久、廣泛(猶如大合唱)、平庸、笨重卻極具慣性的無形無名之物,“這個丟了身份證的流民”(曹僧《邢建國》)該如何原汁原味卻新鮮地顯現?曹僧在《邢建國》中所展現的詞匯(意象)選用與布局,如“回鍋肉、無門廁所、淘寶、盜版、煙頭、加油站、周黑鴨、擤鼻涕、電視頻道、泡面”與“金草地、木屋、斜陽、青海湖、山谷、經聲、羊群、墓群、明長城、脊梁”,雖然也存在對立(混合、消解、平均),但只是“集合與集合的對立”,并非微觀的“元素與元素之間的對立”,有別于肖水的作品。我將停止對詞匯的談論,將目光鎖定在“片段與鏡頭”上。曹僧通過“終將、更何況、若無其事、終于、而、最后還是、但、直到、并不算”這些詞語將“白噪聲”中的局部片段“提高其頻率、密度與程度”,制造局部的褶皺(峰谷)來打亂平靜(連續),我稱它為“局部加速”。徐蕭在《靜安寺觀雨》中,通過引入“一本寫滿事物的書”作為一枚楔入墻縫的鐵釘,來使整個平白場景受力、受牽連,懸掛于之上,我稱它為“關聯至局外的峰谷”。砂丁的《理發師》、《吃葡萄》、《車過鎮坪路》則是通過在平靜的河面上,選擇多個不同(交錯)的潛水點,進而展現出河床的錯落與矛盾。陳汐的《海棠飯店》和《在冗長車程的后半段》猶如在捶打一塊鋼板,敘事方式硬朗、果敢、毅然決然,而總在鋼板邊緣的刃部剛剛卷起的時刻(大鏡頭剛剛完成切換,初現端倪時),戛然而止。
徐蕭的作品表現出的敘述速度較高,在《雪加速的姿態》中,“并非、才是、不過是、并不、無關、仍然、不能、沒什么”等使得詩句猶如汽車頻繁急剎車、轉彎和調頭,呈現“折線”。徐蕭直率、大膽地(依靠廣博、模糊、想象的知性)對事物作定義、評判、界定,來“剎車、終結”,由此將產生定向的精確感和啟示效應。而洛盞、趙燕磊的作品,敘述推進得較為緩慢、浸潤,猶如旋放的玫瑰,詩句每行進一小段,就持續卷入新事物,以物彰顯物(而非通過評判來勾勒輪廓),他們的“嗜物”表現得很明顯,如“原野被伐倒的身高恰隨日落鋪在平坦的揚場里”(趙燕磊《晚來歸》),“往事是熄火的魚雷,吃力地匍匐在/修辭豐富的水花中”(洛盞《涌動》),婉轉、潤滑,呈現“弧線”,洛盞、趙燕磊的作品的精確性更多地是依靠不同意象在感官直覺上的互通、相互牽連來體現。相對而言,洛盞更是“細嚼慢咽”型的,耐性較大,作品細小處飽滿,通篇航道明確,詩中的“我”主動性、參與性較強;趙燕磊詩中的“我”,則是敲響外物之后,又迅速回歸自己體內去聆聽回聲。洛盞詩歌中存在諸如“甲胄、鞣制、昏憒、綿密、黥面、翕動、帷幔”的詞匯,像一枚枚浮子,對所述之物有托舉、提拉的作用(但也有造成局部窒息的隱患),肖水則較少使用這些密度較大的詞匯(尤其是形容詞)。顧不白的抒情短詩《落燈花》和《巴基斯坦》空靈、清秀、延綿,他把落足點選在溫良的田園中,詩中在場之人表現出對承載人的某種恒久的大氣候(氛圍、境界)的順從、敬畏,他的詩也許是在探求人該以何種姿態叩問那喑啞不語的永恒慣性,該如何處理沉悶的回應。張定浩所持的話語模式明顯有別于其他幾位詩人,《聽斯可唱歌》和《死亡不該被嚴肅地談論》是相對典型的經驗寫作的文本,刻畫手法樸實而經驗鮮活。
楊,請原諒我用“匠人”的口吻向你介紹他們的詩歌,若要從注重體驗與超驗的詩中剖析出我們已知的生活經驗(現實意義),前提是我們具備強大的從現實中提煉經驗的能力,這又是我(或者包括涉世不深的成長中的同齡作者)的局限。近年來我反省自己的寫作,面對血肉飽滿的當下經歷,我的詞語紛紛卷刃,難以長驅直入,總是旁擊側敲、隔靴搔癢。既對未經“救贖”的詞匯敬而遠之,又匱乏“清洗”之后的詞匯,我窘迫得寸步難行。長久以來,我寫不出一句爽快利落的句子,事實上我也未能厘清多少現實脈絡。以現代方式處理詞語微元,雖不是新鮮事,但踐行的詩人(如肖水)極少;沒有新的話語模式(有別于翻譯體詩歌的),整個冬天我說出什么,就不是什么。而我所見的多種的話語(思維)模式,在處理復雜經驗時,在從日常經驗向詩學經驗轉化的環節,常常又是“非當下、模式化、守舊”的。
日常經驗與詩學經驗之間的差別,是質與質之間的差別,假若二者能相減,也一定是得到“質”而非“量”;這首先意味著在詩歌中大量堆積弱相關的日常經驗并非有效之舉,其次我們對待二者應有兩種相異的創作方法論與價值評判,不可等量齊觀。在這樣的時代越來越少的新生之物的首秀需要通過詩人的直接感官來顯現,而當作者滿足于在詩歌中利用語言的工具性去表達日常感官時,我并不情愿稱其為詩。在語言的思想本體性中投入我們的感官體驗,而利用語言的工具性來展示我們的“掙扎”成果,這也許是一條將日常經驗上升為詩學經驗的有效途徑。讓感官不表達感官,讓它專注于顯現自己的“形體”而非裂解散亂,仿佛給了它自由而完整的手足,我們便可利用它來表達那些亟需我們處理的經驗及其成果。而我們的同齡人當中,不乏有人總有一股迫不及待、唯恐不與那些正統的看似笨重、緩慢的東西決裂的風氣,沉浸在那些繁冗、破碎的表象中狂歡,從未深刻揭示,只作重復無效的拙劣轉述。這也值得更多的人自省。讀者希望在作品中“撈到干貨”,而作者有時又刻意制造出閱讀障礙、形成“湯水”,無論二者對立多么鮮明,于一位好的作者自身而言二者最終是能夠協調統一的,具有一致的評判標準。
在他們本次的詩作樣本中,“而科馬拉像墳墓那樣揪住我的尾巴/父親也不愿意我走得太遠/……/我記得或是因為看不清,彼此才變得親近……”(趙燕磊《霧中》)、“向你靠近之人,終將與你相斥”(曹僧《邢建國》)、“那情形,/似乎是我擁有某種特權”(洛盞《寫作》)等經驗意味較濃的詩句含量不高(這又是許多讀者寄予厚望的),然而生活經驗的豐富向度不同必將引起創作指向的不同,創作也不因選擇體驗、經驗、超驗式寫作中的哪一條道路而削減其光輝,他們的作品初現復合體態的端倪,但如果按照上述的觀念模型做苛刻審查,部分作品確有薄弱與非典型之處。同時,我也自問是否需要某一環節的廣泛探索與積累(他們的自覺與自信值得我欽佩),漢語詩歌才能躍入新進程中?
如果我凌亂的贅述能為你的閱讀做些有用的鋪墊,是我的榮幸。請原諒我在詩歌群落的寫作圖景及當代詩歌的整體把握方面,尚無概括能力,或因其自身游散、尚未抵達需被概括的聚合程度和高度。從上文中你也感受到近期困擾我的,是具體的創作方法論。楊,現在夜晚朝向自己的腔體坍塌,月亮荒謬至極,凡照耀到的,都成為反例。愿你早日找到那條恢弘、客觀、絕對、公正而不可逆轉的河流,因果清晰的河流,泥沙俱下的盲視的河流,偶然與必然的河流,你接近它,就會成為它永恒不滅精神的短暫寄居的肉身。祝健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