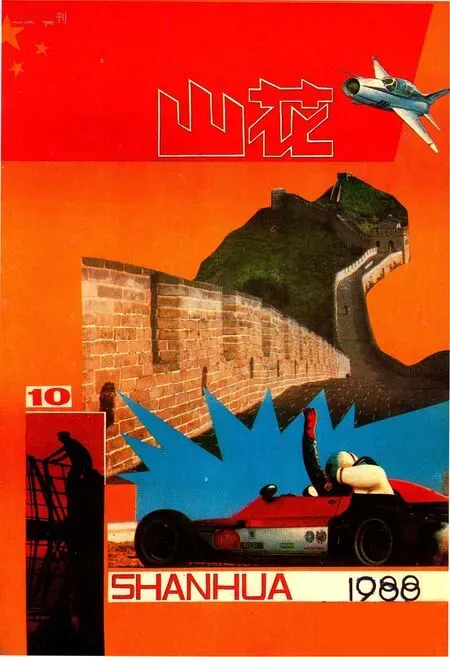新世紀以來德國君特·格拉斯研究概論
從1959年憑借小說處女作《鐵皮鼓》在德語文學界嶄露頭角,到1999年榮膺諾貝爾文學獎,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以其小說獨特的魅力成為德國戰后文學的旗手。進入新世紀以來,德國的君特·格拉斯研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出版的相關專著就達50余部。相對于以作家論為主、以單個文本為對象的早期研究,這一時期的格拉斯研究開始將作家的整體創作納入研究視野,在研究方法上逐漸打破傳統作家論模式,呈現出將作家小說文本置于跨文化、跨學科的廣闊背景之下進行考察的新趨勢。從研究方法來看,新世紀以來的德國君特·格拉斯研究大致從傳記研究、社會歷史、比較文學、文藝詩學四個方面展開,這四個方面互相補充,共同促進了格拉斯研究的深化。
傳記研究
作家傳記研究是德國文學研究的傳統方法之一,它建立在以作家人生經歷為出發點,將作品看作作家生活的外在呈現這一基礎之上。這一研究方法著重從作家生活體驗和文學思想出發,根據作家的世界觀、人生觀特別是人生態度、政治意識、倫理傾向、哲學思想來探索作品的意義。在這一點上,新世紀以來的格拉斯傳記研究可以說比較深入地考察了作家小說創作的時代背景以及其小說文本濃厚的政治意味。
作為格拉斯的同時代人,海因里希·福姆韋格的《君特·格拉斯》(2002)在分析與格拉斯相關的大量訪談資料的基礎上,對其至2002年為止的生活經歷、文學創作背景、小說主題等內容進行了詳細考察,認為格拉斯將自己的人生經歷等內容均以不同方式呈現于文學創作之中。小說《鐵皮鼓》中許多細節如主人公出生地、殖民地商品店等,均與作家本人的經歷吻合,從而使小說帶有濃厚的自傳色彩。但奧斯卡出生日期與格拉斯不同,福姆韋格認為,其原因在于奧斯卡所代表的不是個人,而是與格拉斯同樣出生于20世紀20年代的德國人,特別是男性。他還指出,格拉斯早期的文學創作有三個重要推動力:一是反對對過去保持沉默,代之以勇敢直面歷史的現實生活方式;二是對內心壓抑和對人們由于經濟復蘇而產生的新的過度自我的憤怒;三是故鄉的喪失。《比目魚》中,作者“我”和敘述者“我”自由地互相轉換,以此避免了“我”僅僅作為個人、作為普通市民的單一視角的敘述。小說導入了涉及整個人類歷史的材料,使“文本的不同層面松散但卻合乎邏輯地彼此交織在一起”,[1]從而使小說遠遠超出了小說所借鑒的《漁夫和金魚的故事》這一傳統童話本身的意義。格拉斯沒有在極其局限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內講述,而是在浪漫主義的整體中加入了奇幻元素,形成了其獨特的小說整體觀。20世紀80年代末,在德國統一的呼聲高漲之時,格拉斯發出了不同的聲音,他所贊成德國人的統一并不是政府合二為一,甚至認為保持兩個政府有利于中歐的安全穩定,這一點在小說《遼闊的原野》中得到了充分的表達。可以說,福姆韋格的傳記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挖掘了許多有關作家的最新研究資料,并將之與作品闡釋完美結合起來,很好地實現了對傳統格拉斯傳記研究的繼承和發展。
沃爾克·諾伊豪森的《君特·格拉斯:作家·藝術家·同時代的人》(2012)從文學寫作、藝術創作和政治參與三個角度梳理了作家從出生直到2012年的生活和創作狀況。作為多部君特·格拉斯研究專著的作者和格拉斯全集的出版人,諾伊豪森高度評價了格拉斯的創作,認為他是繼歌德和托馬斯·曼之后小說處女作一發表就享譽世界,其后的作品全集更加令世界矚目的第三位德國作家。諾伊豪森指出,格拉斯的自傳元素幾乎在其全部作品中都有所體現,他認為,“事實上,20世紀是‘他的世紀’,格拉斯的生活可以被當作這個世紀的代表,格拉斯的傳記是典型的德國人的傳記”。[2]新世紀以來,格拉斯將目光投向文學自傳,創作出了“回憶三部曲”。回憶的第一部將回憶比喻為使人流淚的并且有時是痛苦的剝洋蔥的過程,在《盒式相機》里他選擇了童話的形式,《格林詞語》作為它的補充,則主要采用了雜文和報道的混合形式。其中,童話受到格拉斯格外的推崇,他之前的小說如《鐵皮鼓》、《狗年月》、《比目魚》、《母老鼠》等作品都或多或少采用了這種表現手法。《盒式相機》中猶如童話般虛構的那位父親的八個孩子的談話,使小說符合歌德所說的“詩”的范疇;《格林詞語》主要描寫了格林兄弟的生活、歷史貢獻,是作家格拉斯具有公共影響力的寫實作品,是“真”的體現。諾伊豪森認為,格拉斯既是一位著名作家,同時又擁有藝術家天賦。作為藝術家,格拉斯的繪畫和雕塑對其文學作品闡釋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具有與文學作品同等的表現力。諾伊豪森從作家經歷出發考察了作家小說的自傳色彩,對他藝術體驗與小說創作的關系的梳理為格拉斯小說的跨媒介敘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社會歷史視角
社會歷史研究的特點就是挖掘作品所反映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文化內涵,并通過將作品置于具體的社會歷史語境中進行解讀。由于格拉斯文學從一開始就關注社會現實,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色彩,這一方法被廣泛運用在格拉斯研究中。
哈羅·齊默爾曼的《德國人中的君特·格拉斯——關系的編年史》(2006)按照時間順序考察了1955—2005年這50年間的君特·格拉斯作品和公共言論。在這部長達600多頁的著作中,齊默爾曼在對大量翔實的各類材料分析梳理的基礎上,通過將格拉斯文學創作和文學影響置于文化史、文學史的時代背景中進行考察,詳細探討了格拉斯和德國人,尤其是與知識分子之間政治上的爭論、文化上的辯論等充滿沖突的社會關系。齊默爾曼指出,在20世紀60年代初分裂的柏林,格拉斯以具有自我意識的公民的形象公開亮相時,他在藝術上的國際聲譽就被附加了政治性。格拉斯沒有像許多德國人那樣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保持沉默,而是作為一個有政治抱負的知識分子致力于研究奧斯維辛集中營對人類文明的摧殘問題。此后,他開始利用自己的文學聲望介入一些政治問題,從參與維利·勃蘭特的競選到對紅綠聯盟的態度,再到對德國重新統一問題的認識。齊默爾曼認為,“只有君特·格拉斯這個粗暴的批判的語言藝術家的出現,政治文化社會的一個新的理性化才成為可能”。[3]齊默爾曼的研究探討了格拉斯小說濃厚的政治色彩和歷史文化意蘊,描繪出作家通過文學積極介入社會的創作姿態。
薩賓納·摩澤的《君特·格拉斯——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2000)從宏觀上把握了格拉斯1959—1995年的長篇和短篇小說。摩澤將格拉斯的小說創作分為“與德國過去的對立”、“轉入全球主題”和“德國統一”三個階段,從作品創作過程、歷史背景、文學主題、文學接受等方面探討了《鐵皮鼓》、《狗年月》、《比目魚》、《母老鼠》和《遼闊的原野》五部小說,揭示了各個小說的特征及其在格拉斯小說創作中的地位。摩澤指出,德國的罪責(問責第二次世界大戰)是1959至1972年格拉斯作品的中心主題,《鐵皮鼓》成為作家此后作品評價的一個標桿。“《鐵皮鼓》是格拉斯對最早在《文化批評與社會》一文中指出‘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的德國哲學和社會學家特奧多·阿多諾富有詩意的回應。”[4]主人公奧斯卡打破時間界限的擊鼓是小說的典型場景,《洋蔥地窖》一章中的擊鼓使人們內心被壓抑的情感得到宣泄,達到了一種精神治療的效果。奧斯卡的擊鼓不是闡釋過去,而是以具體事物的形式展示被淹沒了的“真理”。摩澤指出,20世紀80年代,格拉斯創作了《母老鼠》,開始將視野轉向核威脅、環境破壞和人口過剩等世界共通的主題。在德國重新統一后,他通過《遼闊的原野》表現出反對遺忘與消弭,反對將罪惡累累的過去看作業已結束的時代這一歷史反思姿態。可以說,摩澤將格拉斯的創作與不同時期的歷史、時代背景聯系起來,全面、深入地描繪出格拉斯小說創作主題嬗變的軌跡。
比較文學視角
進入新世紀以來,出現了將格拉斯文學置于世界文學背景之下進行考察的新趨勢。的確,格拉斯不斷吸收西方文藝理論以及世界文學、文化方面的理論成果,并靈活地將其用于自己的小說創作,這為運用比較文學方法研究格拉斯文學提供了廣闊的探索空間。
海瑪·埃爾·瓦爾迪的《童話和童話元素在君特·格拉斯和拉菲克·沙米與政治相關的作品中》(2007)分析了格拉斯和用德語寫作的敘利亞作家拉菲克·沙米20世紀七八十年代文學作品中童話元素的功能。作者指出,格拉斯將童話視為德國文學最重要的敘述形式之一,他通過將童話元素導入小說的主題、結構,來探索被現實所壓制的歷史真實。在小說《比目魚》創作的20世紀七八十時代,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共產主義兩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對抗中,格拉斯看到了世界末日預言的即將來臨,他通過小說中渴望第三個乳房的女廚師奧阿這一人物形象表達了自己對第三種可能性的探索。拉菲克·沙米在他創作于20世紀80年代的早期帶有童話元素的作品中暗示了20世紀50年代的阿拉伯世界以及納粹德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動蕩。小說《神燈》通過對東方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的《阿拉丁與神燈》的改編和陌生化,批判了阿拉伯的極權、專制的政治現實,并試圖喚醒被法西斯統治奴化的德國民眾。瓦爾迪認為,兩位作家在對格林兄弟所謂的民間童話的局限性和表面化進行批判這一點上達到了一致,認為“革新的童話想象力也許是唯一被保留下來的進入被簡化的現實的可能性”。[5]可以說,在與其他作家的比較中,格拉斯的創作特色以及其小說主題的世界性進一步得到了彰顯。
文藝詩學視角
小說詩學是對小說創作風格和敘事結構進行研究的一項審美策略,是以小說形式研究為基本內涵的研究方法。格拉斯對小說形式的不斷探索,使得從小說形式入手研究其文學創作成為可能。
克勞斯·席林的《罪責動力——君特·格拉斯〈旦澤三部曲〉的藝術的敘述》(2002)從藝術的自我反思這一視角出發探討了《旦澤三部曲》的表現主題和藝術手法。席林指出,《旦澤三部曲》是繼托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之后的藝術小說,它們都受到雙重關系的制約。一方面它們是對過往政治文化狀況的討論,這種話語將第三帝國造成的文明破壞和大屠殺的痛苦作為主題,并將此后如何懷有罪責生活下去這一問題提升到決定一切的高度。另一方面他們將這種反省移入藝術,認為只有當包括美學在內的逃避被看作一種立場,并且這個立場成為對文明破壞的充分回應時,作家才算是擺脫了過去。在這個意義上,“罪責”是旦澤三部曲敘述情境的共同特征。席林認為,《貓與鼠》遵循著現實主義寫作傳統,其中的一些相關結構讓讀者聯想到《鐵皮鼓》。《狗年月》則回歸到《鐵皮鼓》模式,并通過介入現實將這種模式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鐵皮鼓》在開始進入真正的敘述之前,小說主人公奧斯卡就清楚地表明他是在寫小說,也就是創作一個藝術作品。”[6]因此,這部小說就具有元小說的性質,文本外的作家格拉斯和文本內的作者奧斯卡這一設置要求讀者閱讀時必須兼顧屬于文本不同層次但卻同時存在的視角。可以說,席林的研究展現了格拉斯小說敘事的復雜性,對深入理解格拉斯小說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結 語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世紀以來德國的君特·格拉斯研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但還難以構成對其小說藝術的整體、系統的研究。格拉斯的小說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對其小說藝術的探討,應該將其置于具體的歷史語境中深入把握,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挖掘格拉斯小說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和深刻的當下意義。
[1] Heinrich Vormweg. Günter Grass[M].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2002:109.
[2] Ute Brandes. Günter Grass[M]. Berlin: Wissenschaftsverlag Volker Speiss GmbH,1998:13.
[3]Harro Zimmermann. Günter Grass unter den Deutschen, Chronik eines Verh?ltnisses[M]. G?nttingen: Steidl Verlag. 2006:638.
[4] Sabine Moser. Günter Grass,Romane und Erz?hlungen[M]. Berlin:Erich Schmidt Verlag, 2000:23.
[5]Haimaa El Wardy. das M?rchen und das M?rchenhafte in den politisch engagierten Werken von Günter Grass und Rafik Schami[M].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GmbH, 2007:284.
[6]Klaus von Schilling. Schuldmotoren, artistisches Erz?hlen in Günter Grass` ?Danziger Trilogie“ [M]. Bielefeld: Aisthesis Verlag, 20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