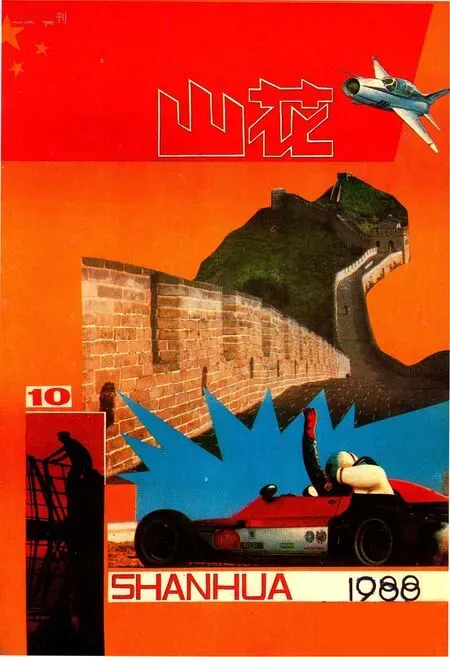深厚的文化底蘊與詩意的文人——兼論唐代詩歌發展
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鼎盛時期,在平定其他政治力量統一全國之后,唐代進入了迅速的發展壯大階段,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都達到了同一時期世界上少有的規模。縱觀中國歷史上所有朝代,唐代的盛世景象及強大的國力是首屈一指的,唐代的文學更是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高峰,在諸多文學樣式中,詩歌脫穎而出,發展的繁榮程度可謂空前絕后,無論是詩歌的數量還是詩人的數量,都遠遠超過以往各朝代,甚至是前朝的總和,成為唐代文學的主要標志,同時也成為我國文學史上詩歌發展重要的里程碑,其影響不僅波及當時世界上諸多國家,而且時至今日我們依然能夠感受到其風韻,為后世的詩歌創作奠定了基礎。唐詩的發展兼收并蓄,前代的文學思想為唐詩指引了方向,充足的社會人文條件及開放的文化環境為唐詩的發展提供了土壤,偉大的詩人層出不窮,諸多因素推動唐代詩歌整體向前發展。唐代詩歌在六朝文學和魏晉南北朝文學的基礎上,總結前人創作經驗,取眾家之所長,同時結合自身的特點及優勢,發展達到了高度成熟的階段。唐代文學的發展從分期上看可分為前、后兩期,承上啟下成為文學發展的過渡帶,前期順承魏晉南北朝文學,后期引導兩宋文學發展。而唐詩的發展又經歷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階段,每一階段都有自己的特點及代表詩人,這些詩人及其創作構成了唐代詩歌的整體風貌,寫下了中華民族文學發展的不朽篇章。
唐詩繁榮的原因及背景
1.唐代國力強盛、經濟政治高度發展
唐王朝建立之后,短時期內就將經濟從王朝更替的衰敗中恢復過來,并迅速地發展經濟,國力的逐漸強大為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在政治上為鞏固李唐王朝的穩定,實行了一系列的新制度,如在選拔官員制度上廢除了魏晉時期沿襲下來的九品中正制,轉而實行科舉取士。加大力度穩定社會秩序,維護社會安定。為加強中央集權制度,統治者一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緩和社會矛盾,穩定人們的反抗情緒[1]。另一方面加強生產發展,土地實行均田制,賦役制度采取租庸調制。商業也得到了長足發展,涌現出一批大型的商業城市。在人民安居樂業、國泰民安的社會環境下,文學擁有了發展的空間,整個唐代在“安史之亂”以前都稱得上是封建社會發展的上升時期,統治者對國家的統治合理且順應民心,從杜甫對唐朝盛世的描寫“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唐代國力的強大,人民生活的富庶,經濟的大繁榮和邊塞戰事的穩定為文化發展營造了有利的環境。而唐代又是一個繁榮及動蕩都經歷的時代,文人經過前后兩期的過渡階段心中不免慨嘆,因此社會時局也增添了唐詩的主題和寫作素材,從另一角度促進了唐詩的繁榮。在外交方面,唐代的政治開明使不少異域文化相繼傳入,且始終保持與亞洲各國進行經濟、商業、文化的頻繁交流。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唐詩的創作主要受引入的宗教和藝術影響較大,如白居易的《琵琶行》,琵琶本是由西域引入的樂器,可以說《琵琶行》是中外文化交流后的作品。在國內南北文化相互交融,唐代以前,國家一直是分裂多于統一,因此各個地域間出現了不同的地緣文化,這些差異給文化交流造成阻礙,同時也限制了詩歌的發展,局限了詩歌的題材和風格變化。而與前朝相比,唐代的疆域版圖擴大,國家統一,詩人大多有去各地游歷的經歷,因此寫作風格集眾家之所長,與前代相比有了明顯的變化。
2.唐代文化政策開放,科舉考試促進唐詩發展
盡管唐朝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盛世王朝,但中國古代各朝中經濟繁榮的也并非只有唐代一個,因此將唐代文化繁榮的原因歸結為經濟繁榮是不正確的。經濟是文化繁榮的重要前提,但文化政策和開放的文化環境才是唐詩發展的土壤,與其他朝代不同的一點是唐代民風平等自然,男女較為平等,女性在社會生活中有較高的地位。因此誕生出一批杰出的女詩人,以武則天和上官婉兒為代表。除此之外,唐代政治開明,在文化政策上也相對寬松,因此唐代文人與其他時期文人相比局限較少,思想活躍,言論較為自由,甚至一些鞭撻當朝統治者政事失誤等言論也不必過度拘束。統治者對文學給予大力提倡,許多君主本身就是詩人,自唐太宗始,歷代君主都十分喜愛詩賦創作,重視文化素養的培養。另外唐代君主大多數都十分重視招賢納士,對賢德之才十分贊賞,設立國子監,下轄六學。且這一時期的科舉制度實行“以詩賦取士”,統治者對詩賦的重視使全國“重文”現象蔚然成風。若要步入仕途,詩賦創作是最有效的敲門磚,科舉制度的盛行使詩賦創作的地位得到極大的提升,甚至因詩賦得君主賞識可以免科舉考試之勞,直接接受任用,李白就是典型的例子。科舉取士使下層知識分子在仕途上嶄露頭角,對于文化的繁榮具有有利的推動作用。
3.宗教文化對唐詩發展的影響
唐代是當時最強大的封建國家,在不容忽視的大國地位的影響下,各國的文化相繼傳入,而唐代外交政策開放,因此吸納了大批的優秀文化,唐代對儒、釋、道三家思想采取積極的態度,對于各種文化兼收并蓄。在宗教文化領域,我國自古以來受本土宗教——道教——的影響較大,包括詩歌的浪漫主義風格的產生都與道教有直接的關系,李唐王朝與道家淵源頗深,因此到唐代道教及其思想在社會上尤為盛行,從李白的仙風道骨與詩作的浪漫主義風格中我們不難發現這一點。唐代受佛教的影響,文學上出現了“俗講”和“變文”兩種新文體,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對唐代文學的發展造成的影響更加直接。唐代真正的純儒很少,由于儒、釋、道三家思想兼收并蓄共同發展,這一時期的詩人三種思想都有,只是各自的側重點不同罷了。儒學給唐詩以動力,佛學給唐詩以心境,道教給唐詩以豐富的想象,三者共同影響唐代詩歌的發展。
4.詩人的思想革新
唐代詩人思想的活躍為其詩作埋下伏筆,對于前代文學發展抱有推陳出新、批判繼承的態度,如“初唐四杰”對于齊梁時期詩歌走形式主義路線給予批判與反對,唐代詩人對六朝時期發展的宮體詩的奢靡之風進行革新,將詩歌的發展推向一個新的局面。以陳子昂為首的一大批先進文人高舉反齊梁文風的旗幟,主張繼承漢魏時期的文學風骨,認為文學應摒棄浮艷奢靡的風氣。唐代詩人研究詩的格律,宋之問、沈佺期等人以永明體為基礎,將五、七言律體初步定型。可以說唐代文人進步的思想是推動唐詩走向鼎盛的最主要因素,這些詩人以積極的文學主張和有益的創作實踐不斷對詩歌創作思想進行革新,引領唐詩一步步突破傳統模式的枷鎖,既發揚了自己的詩歌創作風格,同時又將詩歌的發展領向新的高度,為后世的詩歌創作開辟新路。在得天獨厚的社會背景之下,唐代詩人突破文學禁錮,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向陳腐詩風發起挑戰,同時借鑒唐朝以前近兩千年的創作經驗,學習“建安文學”、六朝時期先進的詩作風格,從自我出發,不斷革舊迎新,最終使唐詩向著正確的方向邁進。
唐詩的發展階段及派別
1.初唐詩歌
初唐詩歌的發展總體上來說是一個對唐代詩歌自身風格的探索過程,也是王朝間交替的過渡階段,這一時期詩歌創作前承魏晉南北朝之風,后繼名聲大噪的盛唐文學。由于唐代尾隨南朝而來,在詩歌創作上難免受其牽制。隋朝的詩歌成就不高,僅隋煬帝個人的幾篇詩作中略露明快之色,然而隋朝對文學要求不高,貴族文學也漸漸附庸風雅,駢體的隋文也逐漸沒落于平庸,無足稱道。唐代開國初期,值得一提的是虞世南的詩歌,清人評價其詩作“漸開唐風”,為后世的詩歌發展開辟了初路。然而初唐是詩歌從沒落到繁盛的過渡期,受前朝詩風影響,難免在形式和題材上顯示出拘謹狹隘之色,在詩歌語言上以華麗為主。貞觀時期為初唐詩壇發展的主要時期,以李世民及其群臣為中心展開詩歌創作,他們對南朝齊梁詩風持批判態度,然而并沒有反對聲辭韻律之美[2],這也為后來的律詩成熟埋下伏筆。受南朝風氣影響,貞觀時期詩風宮廷化加強,出現了一位重要詩人上官儀,形成了“上官體”的詩風,上官體重視詩的形式,主要特點是歌功頌德、綺錯婉媚,對于寫景和詠物有很高的成就,沖淡了齊梁詩風的浮艷卻也未能跳出宮廷文學的狹隘牢籠。王績是初唐詩人中詩風獨特的一位,對于唐初的詩壇現象,王績自拔于俗眾,對仕途有遠大抱負的他面對現實選擇了隱退田園,形成了平淡恬然的隱逸詩風。此外,初唐末期詩人中還有一位獨居一方,成就極高,即張若虛,在唐代詩歌前期做好鋪墊之后,張若虛攜其代表作《春江花月夜》洋洋灑灑而來,以一首詩獨勝群雄,在意境營造方面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為后世提供了成功的案例,隨之為盛唐時代詩歌的到來做好準備。
2.盛唐詩歌
盛唐時期是唐代詩歌發展的最高峰,這一時期唐王朝國力強盛,出現眾多詩人,同時也出現許多詩歌派別。
首先是以王維、孟浩然為首的山水田園派詩人,王維是唐代所有詩人中受佛教思想影響最明顯的一位,同時也是唐代著名的畫家。早年王維與其他文人一樣追求功名,所作詩歌如《使至塞上》,表現出豪邁氣概和雄渾壯闊的意境,后期詩作極其具有特點,蘇軾評論其詩畫為“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在其詩作中,能夠感受到靜怡明秀的意境,同時在感受自然的美麗的同時感受心靈的升華。在詩中感受詩人縱情山水的樂趣及純美詩境[3]。孟浩然則是提倡以最少的筆墨,抒寫最真實的田園山水風光。孟浩然的田園詩盡管少于山水詩,但其中悠然自得和自由安定的農家生活卻被表現得淋漓盡致,如《過故人莊》中對田家安逸自在的生活以及熱情好客的待客態度的描寫。盡管孟詩主題多與田家生活和山水自然風光相連,但并不能就此誤認為其思想單薄、主題乏味。孟浩然和王維的詩作風格打破了前期單一的“詩言志”的創作思想,在詩歌美學藝術的創新上作出了重要貢獻。與山水田園詩派同時出現的是邊塞詩,以王翰、王昌齡、高適、岑參、崔顥等人為代表,他們大多到過邊塞,切身感受過邊塞的壯麗景色。十分熱衷政治及功名,且十分自負,希望保家衛國并希望立下戰功。詩歌風格普遍具有豪爽勁健的特征。高適、岑參兩人詩風相近,并稱“高岑”。除以上兩大詩派的詩人外,最值得一提的是代表盛唐時期詩歌發展高峰的詩人李白,他是盛唐孕育出的天才詩人,以其狂傲自負的人格,豪邁瀟灑的氣度及浪漫且變幻莫測的詩風,使無數后來人為之傾倒。被稱為“詩仙”,他的樂府詩及歌行體十分出眾,詩歌注重抒情且氣勢磅礴,如代表作《蜀道難》,在寫蜀道之難的同時,又表達出自己功業未就的苦悶。除樂府詩外,李白的七言絕句也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與王昌齡的七言一道,成為唐代七言絕句詩人的代表。在其詩作中,李白常常將自己的想象作為詩的主題,且慣用夸張的手法,其勢可吞吐山河,如《夢游天姥吟留別》等作品。盛唐另一位偉大詩人即“詩圣”杜甫,他與李白的詩風截然相反,杜甫是現實派的代表作家,生活在“安史之亂”唐代社會由盛轉衰的過渡時期,嘗盡生活悲苦的杜甫,將當時的唐代社會現實表達得淋漓盡致,其詩作似是有意識的字錘句煉,譏諷社會的黑暗面,杜甫心系家國,“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從中可以看出詩人的百感交集。杜甫的律詩有很高的成就,打破了格律的束縛。其詩作特點是沉郁頓挫,具有很高的史學研究價值,因此也被稱為“詩史”。對后代的詩歌創作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
3.中唐詩歌
中唐詩歌在藝術表現形式上呈現出多元化,流派分立現象明顯,在盛唐的詩歌余韻籠罩下,詩歌風格開始另辟蹊徑,呈現出另類的美感,以韓愈、孟郊、李賀、劉禹錫、柳宗元、白居易等人為代表,認為詩歌應因時而作,韓愈、孟郊的詩歌創作逐漸成為一種詩派,被稱為韓孟詩派,稱詩歌創作主張不平則鳴,崇尚雄奇怪異之美。李賀的藝術表現形式追求怪奇,詩歌語言奇特、想象怪異且詩歌意境幽森異樣,因此李賀被稱作“詩鬼”。中唐其他優秀的詩人還有劉禹錫、白居易等人,他們的詩歌創作特點各有千秋,大都有過被貶經歷,詩歌主要表達個人心境,劉禹錫的詩作透露著哲人的智慧,在懷古詠史方面有巨大成就。
4.晚唐詩歌
唐代詩歌至長慶時期逐漸低落,詩歌改革的銳氣逐漸消失,詩歌創作走向平穩,典型的詩人有杜牧、賈島、李商隱等人。杜牧可稱為詠史詩的大家,其詩大多如其人,爽快、明麗、瀟灑豪邁。典型的詠史懷古詩如《赤壁》,對古代遺跡發表慨嘆,帶有傷悼歷史的情感。晚唐詩歌成就最高的詩人是李商隱,他關心國家命運,多作詠物詩和無題的愛情詩,詩意朦朧,以《錦瑟》、《馬嵬》等詩為代表,具有凄婉艷麗的風格,其七律、七絕造詣較高,深婉清麗,注重抒情。盡管晚唐詩人詩作風格各有特色,但與盛唐詩人相比,已呈現低落趨勢。
結 語
唐詩是我國古典詩歌發展的頂峰,是唐代社會整體風貌的集中表達,更是詩人畢生經歷的真實寫照,無論是哪一種詩歌風格,都有其自身發展的土壤,浪漫派浩浩如激流,激蕩人心;邊塞詩鏗鏘如戰鼓,響徹曠野;山水田園詩醇醇如美酒,愈品愈香;現實派郁郁如羽聲,凄切悲壯。在歷史長河中,詩歌顯然是極其具有代表性的文學樣式,唐代則賦予其更深的內涵,使唐詩成為盛世籠罩下的不朽篇章。
[1]李亞.唐人論唐詩研究[D].鄭州大學,2004.
[2]王玉晶.唐詩中象征詞語的文化意義及其成因探討[D].長春理工大學,2008.
[3]劉芳.唐詩與原型[D].南京師范大學,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