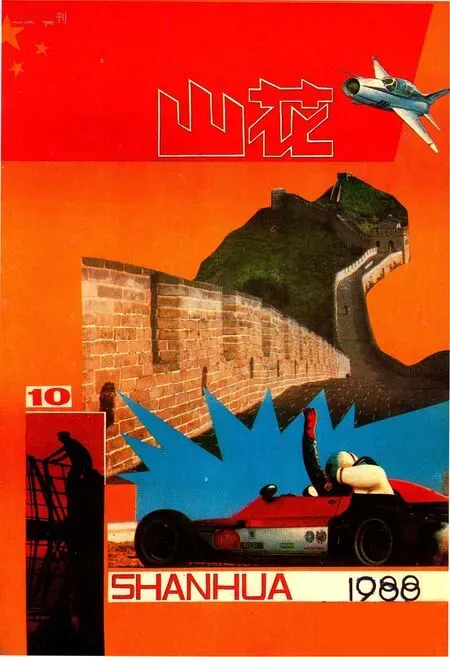紹興庖人
陳寶良
一種美食佳肴的創制乃至得名,離不開兩類人,即廚師與食客。前者是美食的創造者,后者則是美食的享受者,有時甚至是捧場者。食客若是無法獲得廚師創制的精美食品,雖不致落到難以“果腹”的尷尬境地,但也不得不失去通過舌尖刺激而獲取的精神愉悅。廚師若不得食客的捧場,就難免有點落寞,甚至缺少了提升烹調技藝的動力。兩者的完美結合,最終才形成了一部精彩的飲食文化史。
好吃甚至貪吃之人,實有高下之分。古人有個形象的比喻,稱其為“饕餮之徒”。而在今天已然風行的“美食家”,乃至“吃貨”等帶自嘲意味的比喻,這大概也是從古時“珍饈家”的名頭中演變而來的。還是鄉間的百姓比較純樸,如我的家鄉紹興稱這些人為“吃食戶”,一個“戶”字,已經道出這些人猶如今日的專家性質,其境界的高處甚至可以自立門戶了。至于我現在的客居地重慶,民間更是加封這些好吃之人一個“好吃狗”的名頭。這個名號有點有趣,在道出了此類人貪吃的精髓之余,多少還有說這些人在吃食種類方面貪多、貪雜,疏于對飲食精粗的揀擇。
現在所謂的廚師,古稱“庖丁”、“庖人”,有時又稱“饈人”、“膳夫”。在我的故鄉,則稱廚師為“水工先生”。此稱得名不詳,望文生義,大概是說這些人從事的是水里來、水里去的活計,且工于用水。傳統中國的女性,在家庭中承擔著“主中饋”的職責,但在市面上專門從事烹調的女性,其起源或許還應追溯到宋代的杭州,“宋嫂魚羹”的出現,堪稱是典型的一例。演變至明、清兩代,更是出現了專業的“廚娘”。不過,從總體來看,歷代廚師這一職業,大抵還以男性為主。
俗語有云,真正的美食在民間。對此我深有體會。我在故鄉紹興一個叫作周家橋的小鎮上,曾經生活了整整十七個年頭。鎮上有一座石拱小橋,以“周家橋”命名,且周姓為鎮上的望族,故鎮以此得名。這個小鎮頗有些歷史的淵源。據各家初步的考證,宋代理學大家周敦頤的后人,自南遷之后,其家族的血脈,在紹興分為兩支:一是侯馬周氏,二是周橋周氏。這個周橋,就是后來的周家橋。小鎮上的人們,多以從事油紙折扇為業,在清代甚至達到了“日出萬扇”的繁榮景象。記得小鎮上,有兩家飲食店:一個是飯店,屬于正宗的餐館;一個是餛飩店,屬于小吃店。此外,尚有不少四鄉之人趕來買賣吃食之人,猶如北方人的趕集與西南人的趕場。正是這些飲食店鋪,以及四鄉趕來的買賣之人,使生活在這座小鎮上的人們,在滿足日常飲食生活之余,尚有自己解饞與待客的去處及美食佳肴。我有清饞之癖,這里選取的有關故鄉小鎮上的庖人二三事,既是對故鄉吃食的一種夢憶與夢尋,更希望通過自己的記錄,為后世撰寫“方伎傳”一類的史記提供一份真實的史料。
羊肉阿水
有一年的春節,回老家省親,不免有一番走親訪友的應酬。在舅舅招待我的家庭筵席上,盡管家常菜已經相當豐腆,舅舅還是從市面上買回白水羊肉,以解我饞。選取其中的一片,在小碟中蘸一些醬料,咀嚼下肚,感慨良多。無論是原料羊肉,蘸水中的醬油,還是加工制作的技巧,白斬切割的刀工,有的僅僅是“有”聊勝于“無”的想法,很難再找回兒時吃白水羊肉的感覺。
兒時所吃的白水羊肉,當數阿水所制最為聞名,所以有了“羊肉阿水”的名號。這種“物帶人號”的習俗,也是淵源有自。我們從司馬遷所著的《史記》中,就可以找到“弓箭張”一類的稱號。這代表著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就是對工匠技藝之人的鄙視,以致他們的大名湮沒無聞。大概自宋代以后,由于“東坡肉”的出現,以及蘇東坡的名頭之大,終于使傳統的觀念有所改觀。明代以著名山人清客陳眉公命名的“眉公餅”,也是相同的例子。于是,技藝之人通過他們精湛而又嫻熟的技藝及其相關作品,在名揚四鄉甚或四海的同時,還享受到了流芳百世的額外待遇。
阿水,是他的小名,其大名應該帶有一個“水”字。在我的故鄉,當小孩出生之后,取名習俗有兩大特點:一是寄名,就是在祠廟神座之下寄名,使小孩成為神靈的寄子,便于小孩長大。譬如我小時就曾經寄名于包公殿,成為黑臉包公座下的寄子,取了一個“包焱”的寄名。二是小孩生下來之后,通常要找一個瞎子掐算一下祿命,看看小孩五行中究竟缺少哪些。譬如魯迅小說中的“閏土”,就是五行缺土。我小時寄名中有一個“焱”字,就是因為五行中缺火。照這個常理推去,取名“阿水”,應該是五行中缺水。
記得秋末冬初,寒潮來臨。鎮上專有一類喜歡傳播家長里短新聞的“包打聽”之流,其中一個綽號叫“黃包車”的,就四處散發消息,說阿水進山買羊了。于是,小鎮上的人們為自己又能暫飽口福而歡呼雀躍。過不了幾日,阿水就挑著擔子,來到小鎮上,走街串巷,前來販賣他自制的白水羊肉。一般的擔子是一根扁擔,挑起前后兩個籮筐,而他的擔子很特別,只是用扁擔將籮筐擔在后面。籮筐之中,放一個厚重的樟木墩子,作為砧板,上面擱置整方已經用白水鹵制好的羊肉,再蓋上一塊洗過多次的白色洋布。與一般的小販沿街叫賣不同,他從不叫賣自己的羊肉,而是走進一個臺門里,先是與熟人攀談家常,聊完家常,才開始做他的正經生意。
“阿水,給我來二兩羊肉。”小鎮上的人家,很多是靠每月在扇廠做工時得的計件工資吃飯,收入并不很高,所以一般都只買二兩羊肉,最多不過半斤,過過嘴癮而己。
“好的!”在一聲特有的綿羊音式的答應之后,阿水掀開白布,熟練地操起他那把如同程咬金所持斧頭般形狀的大刀,精準地在整方肉上切下一小塊,放在銅制的桿秤秤盤上,不多不少,正好二兩,然后操起大刀,上下切削如飛,很快將羊肉切成薄如紙的羊肉片,再用壓了膜的紙包好,外面用橡皮筋捆好。
阿水羊肉的美妙,在于最適合冷吃。用筷子夾起一片切得薄薄的羊肉,無須其他佐料,只需在純釀造的醬油里一蘸,放入口中,當一股淡淡的羊肉清香開始散發出來的時候,沒等食者再加咀嚼,羊肉已經化入肚中。如此吃法,雖不像現在在內蒙草原吃烤羊或在北京東來順吃涮羊肉那樣大快朵頤般的痛快,但我對羊肉的喜好,實在是得益于羊肉阿水的培育與滋潤。
1980年,當我負笈京師,求學于北京師范大學的時候,在師大的北飯廳,再次嘗到了羊肉大蔥餡的包子,但這次吃羊肉的經歷,反而引發了我拒絕吃羊肉整整七年之久。何以如此?一則加了大蔥,就會失去羊肉本身的清香之味,二則即使加了大蔥,還是很難壓住羊肉的膻味。難怪,中午賣五分錢一個的包子,到了晚餐,降到兩分錢也無人問津。直到1987年冬,當我開始工作且吃過涮羊肉之后,才重新萌發對羊肉的喜愛。在我的舌尖的記憶中,阿水的羊肉從來都是味中極品,他鹵制羊肉的羊,雖是從山中購來,但必須是湖羊,沒有太多的膻味。他鹵制白水羊肉之法,究竟加了哪些去膻的香料,這是他的獨家秘方,外人不得而知。有幾次,有人闖入他的家里,想探個究竟,還是未能得逞。endprint
在小鎮上,阿水算得上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甚至終身未娶。這種傳奇,倒不是阿水制作羊肉的神秘性,而是他的奇異人生。阿水長得瘦瘦的,高挑的個子。他的脖子很長,臉甚至與羊臉有幾分相似之處。最為巧合的是,一開口說話,也是弱弱的綿羊音。阿水很愛干凈,腰上的白布圍裙與蓋羊肉的白布,盡管有一些洗不凈的羊油污漬,但其他地方顯然已經過反復搓洗,干干凈凈。他善于攀談,賣完羊肉,總能看到他在橋頭喝著老酒,以他獨有的綿羊音與人說些“大頭天話”。他的家并不在周家橋,而是住在另一個叫作華舍的鎮上。有小時的同伴,出于好奇,曾去他家探訪過,回來說家徒四壁,無床,還夸張地說,阿水睡在吊于房梁的繩子上,幾乎將他夸大為武俠之流。現在想來,較為準確的說法,應該是睡在吊在房梁上的布兜里。
20世紀90年代初,當我從京城回老家探親的時候,因為對阿水羊肉的念想,曾經向父母打聽過阿水的下落,卻被告知阿水喝醉酒后,睡在一個橋洞里,睡熟后掉入水中,溺水身亡。晚景凄涼,令人惋惜。
餛飩阿土
盡管我走南闖北,也曾吃過名聞遐邇的北京“餛飩侯”的餛飩,以及成都的“鐘抄手”,但在我的記憶里,兒時吃過的“餛飩阿土”做的餛飩當數第一,迄今還讓我口饞。
餛飩阿土是小鎮橋腳下一家小吃店的廚師。姓甚名誰,已不可考。阿土是他的小名,說明他五行中缺土。這家小吃店,位于河北岸的橋腳下,所賣的有餛飩、面條、饅頭、面包等小食。鄉間民風淳樸,很多飲食品類還保留著古時的稱謂。如所謂的饅頭,盡管形為圓狀,卻已經不是北方人通常所說的饅頭。我家鄉所稱的饅頭,其實就是北方的包子,分為糖饅頭與肉饅頭兩種:糖饅頭內放白糖餡,五分錢一枚;肉饅頭內放豬肉小蔥餡,六分錢一枚。饅頭一稱,較為古老,原本作“蠻首”,后陸續衍變為“饅首”、“饅頭”。而北方人所謂的饅頭,我的家鄉稱之為面包,用糖精和面蒸制而成,只是形為長方。
小店做生意的時間,主要集中在早晨六點直至下午三點。下午三點以后,直至打烊之前,基本不再有生意,只是賣一些剩貨而已。小鎮上的人們,生活較有規律,除了一日三餐之外,在上午十點與下午三點,講究一點的人,還要各吃一道點心。故鄉人的時間稱謂,尚存一些古意。除了“早上”(早晨)與“夜頭”(夜里)之外,通常將上午稱為“上晝”,正午稱為“晏晝”,下午稱為“下晝”。所謂的點心,就是“上晝”與“下晝”的應景之食。
每天清晨五點,阿土就開始生起爐灶,忙碌他一天的生意。到了早晨六點,橋頭已經聚集了前來賣菜的四鄉農民與小鎮上來買“小菜”的居民。那些講究一點的農民與小鎮居民,就在小店里吃早餐。一個說:“阿土,給我來一碗餛飩。”一個又說:“阿土,給我來一碗面。”過不了一會兒,隨著一聲“來哉”,阿土就將熱氣騰騰的餛飩、面條端到客人的面前。
面條分為兩種:高端的為榨菜肉絲面,一毛二一碗;低端的為“光面”,又稱“陽春面”,八分錢一碗。除了有錢的人吃肉絲面,其他人還是很節儉,多吃光面。所謂光面,就是除了面條之外,清光光的沒有“澆頭”,有的只是大骨湯,再在上面撒上一些小蔥的蔥花。
小時家里光景清苦,照理說我是無福享用阿土的餛飩的,因為一碗餛飩需要一毛錢,而我自己有時跟家長討要一分、兩分的零花錢,也不很容易。不過,我的祖母卻是一個很會享受的人,對我較為鐘愛,而且她每月都能收到上海的姑姑寄給她的十元零花錢。每當上午十點,她就要光顧阿土的小吃店,要上半斤黃酒,一碟茴香豆,慢慢享用。每當此時,我就站在橋上,不停向店里張望,目的就是讓祖母看見我。這時候,她就會向我招招手,我就進到店里,得以享用她為我點的一碗餛飩。
阿土店里,最受歡迎的有兩樣:一是餛飩,二是扎肉。兩者所用的原料豬肉,都是本土的豬種,黑毛,養一年才能長到一百二十斤。這種豬,號稱“壽頭豬”,因其額頭上有形似“壽”字的皺紋而得名。餛飩所用的餡料很簡單,就是在剁碎的肥瘦相間的豬肉餡中,加上少許的醬油、鹽與小蔥的蔥花。餛飩皮薄晶瑩,個小,里面僅有一點肉餡,一般每碗十只。在中號碗中,放入醬油、蔥花、紫菜、蝦皮,加入煮好的餛飩,再加上熬制好的大骨湯,即成。吃時,用調羹連湯將餛飩舀起,用嘴輕吹氣,待其稍涼,放入口中,稍加咀嚼,即可咽入肚中。故鄉人把餛飩當作點心,所以講究的是皮薄、個小、湯鮮,相當精細。這正好與北方人把餛飩當作主食形成鮮明的對比。
扎肉所用是上好的五花肉,先將豬肉切成兩寸長、一寸寬的塊狀,用箬葉殼細絲扎緊,放入鍋中,加上醬油、白糖及大茴、桂皮一類的香料,大火煮開,用小火燉煮三到四個小時,盛入陶制的缽中,待其凝結后,再整塊倒出,置于一個大號的盤子里。扎肉都是論塊賣,一塊八分錢。通常食客買上一塊,作為佐酒之物。此肉經過長時間的燉煮,味道醇香,肉質酥爛。
阿土體型胖大,一如很多廚子的模樣。他為人豪爽,嗜好老酒,且有海量,一次即可飲二斤。飲后,滿面飛霞,就更健談,甚至說“我家也曾風光過,館子開到紹興城里”一類的話。四鄰鄉親見他好酒,好心勸他少喝酒、多吃飯。他還是一概故我,一等有暇,又喝上了酒。據說,最后死于心肌梗塞,年過七十,也算是善終。
飯店寶發
小鎮庖人中,還有一位寶發,因開有一家小餐館,所以鄉里人稱他為“飯店寶發”。其人姓氏,因為小時不曾問起大人,且年代久遠,也就不可知道了。這個名字,顯然寄托了他的父母對他的鐘愛與美好愿望,既視他為一塊寶玉,也希望他長大以后能夠發家致富,光宗耀祖。
飯店就是他家自己的房子,位于小鎮南北向的熱鬧街上,這條街鄉里人稱為“橋弄”。這既是江南的弄堂,寬只堪四駕馬車,又直通橋頭,故有此稱。記得寶發開飯店的時候,已經年過半百,體型精瘦矮小,一如老頭兒,但身體精健,健步如飛。
他家的飯店是鎮上唯一的一家餐館,館子中主營家常炒菜,也兼賣點心。鎮里人家,有時想改善家里伙食,或者家里突然來了客人,會從飯店中買一些菜肴。寶發年輕時就進城里“同心樓”飯莊學藝,所以廚藝精湛。
飯店所賣,有“白斬雞”、“肉絲小炒”、“三鮮”三樣,屬于寶發的招牌菜,深得小鎮居民及四鄉里人的贊譽。白斬雞的原料,是紹興特有的三黃雞,而且是一種閹雞,即公雞在小時將其閹割,從此圈養在狹小的空間里,大致將近一年,才可宰殺,紹興人稱為“棧雞”。將此雞整只在白水中煮熟,撈出,涼后切塊,即成白斬雞。此雞皮色油黃發亮,肉質細嫩,很有鮮味。吃時,不需要添加任何其他佐料,只用蘸著醬油吃即可。肉絲小炒,這是故鄉人家的家常菜,家家都會做,但以寶發店里所制為最美。此菜主料為精肉絲,配料則為韭黃與紹興柯橋的香豆腐干,經過爆炒而成,很考驗一個廚師的火候功夫。寶發炒出來的肉絲,細嫩不柴,再與韭黃的香味混在一起,不失為日常小炒中的佳品。至于“三鮮”,屬于紹興的一種湯菜,與北方的什錦菜式有相類之處,卻又別具風味。此菜的原料,主要有魚圓、肉圓(紹興人稱為“笨子”)、油炸之后的肉皮、金華火腿、冬筍與水發以后的香菇。將各式食材下鍋,加入雞湯燉煮而成。寶發所做的“三鮮”,湯鮮味美。尤其是魚圓,將河中胖頭魚肉剁成魚茸,加水、紹酒,順著一個方向不斷地攪拌,使其上漿。將鍋上灶,鍋中加滿涼水,將魚茸由手掌擠出,依次下入水中,沉底不久,浮出水面,隨即撈出,置于涼水盆中。魚圓雪白晶瑩,嫩軟細滑,入口即化。紹興人有句俗語,稱檢驗一個“水工先生”(紹興人對廚師的稱謂)的手藝如何,只要嘗一下他做的魚圓,即可知曉。
寶發的飯店,不曾開上幾年,就歇業關張了。而寶發終究也沒有富貴發達起來,圓他父母的心愿。不過,在大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年代里,憑借個人開設一家餐館,且靠此維持一家人的生計,實在已經是萬幸的事情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