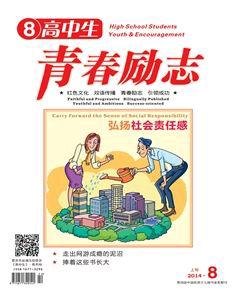誰來滿足我們的需求
佚名
李飛在中學的時候就玩網游上癮,因為和父母關系不好,內心比較孤獨。“有時會痛苦,覺得自己浪費了時間,想做的事沒有做好。但每次停下來,失落感和負罪感又會壓過來。我感覺缺乏戰勝自己的勇氣。”李飛很清醒,始終在作自我分析。他還告訴我,今天家里一下子來了三位客人,這還是第一次。看得出來,他渴望跟人交流。
我遇到的網癮者大多喜歡玩網絡游戲。玩家在網游中可以得到他們在現實中難以獲得的成就、榮譽、財富等。這時已經很難說玩家仍然只是在玩網游,或完全處于虛擬世界之中。對于社會現實感正在逐漸形成的未成年人來說,虛幻和現實的界限更是難以確切辨別。“這里的孩子常常固執地用自己喜歡的虛擬世界中的用語和邏輯跟他人交流,根本不管對方能否理解。”北京軍區總醫院的網絡依賴治療中心主任陶然說,“他們分不清什么是現實,什么是游戲。”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高文斌教授向我解釋了網絡中需求滿足的一個重要特點:“即時滿足性。”許多需求在現實中都需要“延遲滿足”。你在社會中要得到“尊重滿足”有時需要幾年乃至幾十年,而在網絡中可能只要半個月或一個月。
“每一代青少年都傾向于采取風險性最小但可能性最大的探索方式了解世界,驗證并肯定自我。”心理學博士劉蓉暉說,“20年前中學生用詩歌、吉他和體育,現在的一些青少年則用電子游戲和其他網絡工具。”
針對“網癮”,高文斌教授還提出了“失補償假說”。他認為長期以來中國存在著社會價值標準單一的問題,形成了價值觀的“單一評價體系”,使得許多人在網絡中尋找缺失補償。其中一項同伴關系,便是由于社會的基本組織結構變化,即城市化、小家庭化、獨生子女化引起的缺失。“現在很多家庭都只有一個子女,父母去上班,孩子就留給了老人,溝通起來有困難,網上卻什么都有。缺什么補什么啊。”陶然發出如此感嘆。
我們福爾摩斯式的探案已接近尾聲。我們一路追蹤“嫌疑犯”,直至我們每個人的體內,但懸在我們頭上的問號卻沒能去掉。我傾向于認為:“電子游戲”尤其是“網絡游戲”存在著致人上癮的許多因素,但并不是一個必須對之負全責的“元兇”。“網癮”應該是各種社會因素和人自身復雜因素的綜合作用的結果。
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