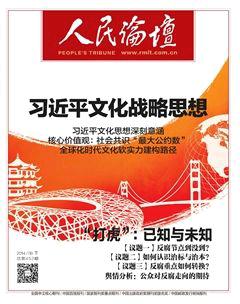蘇軾向南
2014-09-24 00:35:30林那北
天涯
2014年4期
一
公元1097年的天空是怎樣的呢?我指的是海南。
孤懸海外的一個島,像一個被關在家門外的落拓棄兒,漫無邊際的海水箍出貌似柔軟卻比巖石更堅硬的邊界,路延伸到這里戛然斷了,不再通向遠方,僅能夠年復一年默默眺望,望斷夏水春水冬水以及浩蕩秋水。
那一年七月,蘇軾必須繼續向南。從汴州到惠州再到海南的儋州,家越來越遠,步履越來越沉重。老了,風刮動稀疏的胡子。老漢貴庚?六十有二了啊!背已經佝僂,四肢已經僵硬,但不能不走,必須立即迅速刻不容緩地啟程,渡過海,渡向他生命的崎嶇角落。
一介書生,無非是寫寫詩文抒一抒腹中若干不滿,竟把權貴得罪了。所謂新黨,新在哪里?所謂舊黨,舊在何方?其實厭倦一切以名利為前提的紛爭,無非懷揣一腔“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理想,區區幾十年,以才華立身,以抱負濟世,提筆的手握不了刀槍劍戟,傷不了別人官椅官帽的一絲毫毛,卻還是不經意間卷進朝廷那么多骯臟的是非,被那么多蠅營狗茍的庸才視為眼中釘,盛怒再盛怒,恨不得剝掉他的皮,最終雖留存他性命,仍是咬牙切齒地一而再地將他驅逐。之前他已經謫居惠州三年,斗轉星移,江山依舊。他在惠州過得好嗎?還好,至少比很多人想象的好很多。有書籍筆墨為伴的歲月在他手中從來不曾黯然,一撇一捺都是萬千風情——也許正因此令那些恨他的人格外嫉恨與不爽吧?于是向南,再向南,向海之南。
他沒有求情,因為沒必要;……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