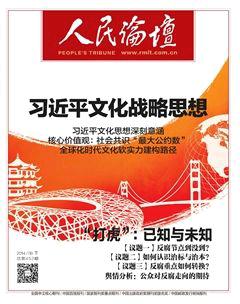遷移(外三首)
2014-09-24 00:43:06胡桑
天涯
2014年4期
關鍵詞:生活
我幾乎愛上了這個地址,
但我知道,
痛苦如此精確,
裁剪出那么多疲憊的島嶼。
路邊的旅館教會你沉默,
就像一滴落入裂縫的水。
無盡的漂流,
每一個地址都偏移燕子的到訪。
那些樹,多么奇異,
生長在秋冬的空氣里,
在同一個地方領受回去的路。
一個囚禁于生活的人
被遣送到了希望的邊緣,
依然試圖醒來,
在星期一的下午,
在一條陌生的路上,
受雇于殘缺的影子,
看見了另一條街在等待,
“難道你不該在那里?”
炎癥
我離開嘈雜的大門,
會遭遇什么?
疾病入侵喉嚨,
像閃電撕裂了謊言,
沉默開始了,我聽見別人在說話。
其實,看不見什么面容,
人如此盲目,
假如,目光從不凝視缺席的事物。
工人們身穿黃色工作服,
在教堂前,切割著一株冷杉,
用電鋸摧毀了一個約定。
只在一夜之間,
無處不在的黑暗,像樹干一樣被拆開,
錯亂地放置在一起。
我的喉嚨,在疼痛的時候,
突然走到了人們的背后,
聽見均勻的呼吸
在數著陽光。
滯留者素描
飄蓬忽經旬,今此又留滯。
——余懷
一
在霧霾中,他走過一片街區,
國定支路像一個忍受著沉默的島嶼,
菜場的叫賣聲加速了他的漂移。
散步猶如一場收集誤解的旅行,
他醒來,腳上踢著
疑惑的落葉,在歧義中徘徊。
初冬的樹葉已被裝載,而驕傲
使垃圾車失去了平衡,
他一邊走一邊低語:“是我。”
這兩個字消失于汽車的鳴聲中。
他走入暮靄深處,一陣刺痛
找到了他,寒冷在加重。
二
接受一場失敗。窗子關閉著,
提防著渾濁的寒冷,
但是無法抵擋屋內逐漸增加的黑暗。……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風流一代·經典文摘(2018年1期)2018-02-22 09:00:43
黨的生活(黑龍江)(2017年12期)2017-12-23 17:01:20
求學·文科版(2017年10期)2017-12-21 11:55:48
求學·理科版(2017年10期)2017-12-19 13:42:05
民生周刊(2017年19期)2017-10-25 07:16:27
特別文摘(2016年19期)2016-10-24 18:38:15
爆笑show(2016年3期)2016-06-17 18:33:39
37°女人(2016年5期)2016-05-06 19:44:06
爆笑show(2016年1期)2016-03-04 18:30:28
爆笑show(2015年6期)2015-08-13 01:45:40